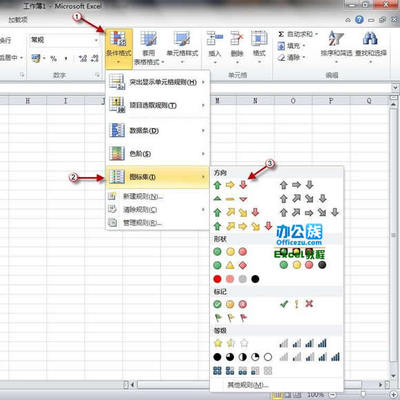艺术家艺术表现的任务,是要把客观物象最终转化为艺术意象,在此过程中,必不可少地还有一个环节:对客观物象的表象化——对于客观物象的主观记取。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有一段话,讨论光明与失明以及记忆与画家的关系:“就算是最无能的画家……当他看着一匹马来画马时,画出来的仍是记忆中的景象。因为,谁也不可能同时看着真的马又看着纸上的马。画家会先看马匹,接着迅速把停留在脑中的印象画到纸上。在这当中,即使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画家表现在纸上的并不是眼前的马,而是记忆中刚才看到的那匹马。”(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95。)而这也正是艺术家无不强调“记忆”二字的原因之所在。贝多芬没有因为耳聋而听不到声音,“失明”的画家没有因为失明而看不到事物景象。“我的记忆弥补了我的失明”(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94。)艺术家头脑中表象世界的丰富多彩弥补了艺术家对于世界的暂时疏离,或者说甚至决定着他们的艺术表现之丰富与深远。
但是表象之于物象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半主观性,即表象记忆事实上已对现实事物的物象进行了选择性的处理——记忆于是就不再是简单的复制。比如记忆把一部分物象作为知觉的对象而表象化,而把另一部分物象仅仅作为了知觉的背景而有待表象化。也就是说,表象操作的几个基本动作——分解与组合、简化与细化——是具有双关性的,即它们既是表象对物象的动作,也是意象对表象的动作——意象的形成就是主体对表象记忆的再次选择性处理。所以,从物象到表象再到意象,事物本身的言说性渐渐减弱而人的言说性渐渐增强,也就是说:现实的信息越来越少了,人们的言说离事物的真实越来越远了。所以,所谓作家们让自己的作品竭尽全力地逼近现实,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表象是物象从外向内位移之后的形成,但是,表象的位置,虽然已经在大脑中了,却并非意象,而仅仅是“前意象”,因为表象要成为意象,尚需为之赋予意义,即康德所谓的灌注生气。正因为它是尚未被加载意义的,所以,“表象”之“表”,如同“白丁”之“白”,指的是意义的空无。例如在“等你等了好半天,等得花开花又落”这句话中,当“花开花又落”独立存在的时候,它是没有意义的;同样,“等你等了好半天”这句话虽然有意义但其意义却并非文学意义,因为它还没有被形象化。现在,让它们在“等你等了好半天,等得花开花又落”这一语言结构中猝然遇合而成为相映生辉的一个组成,这时,对于“等你”句而言,它被形象化了;对于“花开”句而言,它就是被赋予意义了,也就是从表象一跃而成了意象。李煜词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是同样。
这样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最终去理解诗歌意象中意与象之间的关系。
【意与象之间的关系】
意象,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意与象的结合。关于它们之间的基本结合关系,以王弼的阐述最为精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见《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P609。)
“象”何以能够“出意”?
《周易?系辞传》说,象:“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语中就包含着形象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以具体体现一般的基本观点。而西方人则认为象之所以能够表意,是因为意与象的关系,是一种富于张力的对应性结构:“网结”。阿恩海姆《力的结构》指出:不具意识的事物,也具有其自身内在的表现性,它与人类的情感构成某种对应。例如垂柳之所以被人知觉是悲哀的,是因为其枝条、形态、方向的被动下垂。神庙的立柱被知觉是挺拔向上的,因为其位置、比例、质地、形态无比的坚强。
古代中国人显然不知道阿恩海姆,但是古代中国人自有自己的哲学家,比如庄子。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思想,其实老早就给中国诗歌的意象理论提供了“物我与共”、“主客为一”、“情景交融”的美学基础。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思想,早就告诉我们:形象比语言更有表现力。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中的一段话,可为象能出意说的极端表述:“人言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人者,不能绘其情;此数者虚,不可以形求也。不知实者逼肖,虚者自出,故画北风图则生凉,画云汉图则生热,画水于壁,则夜闻水声。”
然则意与象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呢?
当象的表意作用如此自然而然地被人们认识之后,则象与意之间的结合关系,无非在以下三种可能中摇摆:
一、意在象中
即因象生意,有什么象,生什么意,强调象的能指,象大于意、景大于情。这样的意象关系,即是以兴为诗手法的基础。“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姜斋诗话》)意即一个诗人在其写作的过程当中,表象世界应该率先活跃。当然,表象世界的活跃,在文学表述中固然求之不得,但在理论表述中却会压抑概念思维,比如在中国古代的诗论文本中,表象世界活跃的中国古人往往以诗说诗、以喻解诗甚至以禅悟诗,因此西方理论家对中国古代的文论颇多微词。
二、象在意中
即以意统象,有什么意,生什么象,强调意的所指,意大于象。所有理论语体即论理语言中意与象的关系即如此,因为此种语言重理而不重象,重目的而不重过程;重结果而不重方式——此即刘勰所云之“舍容取心”。人们喻之为“义理寄宿之蘧庐也”、如“过客之于旅亭”。比方《易?坤》的象“履霜,坚冰至”,“盖言顺(慎)也”。有人把这种“得意”称之为“超象”,说是一种大象无形的象外之象。对此,钱钟书先生提醒他们:不可“超象揣形上之旨”、“以深文周纳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
三、意共象生
即意与象高度默契,几不知是象生意还是意生象,达到了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的神与物游之境界。刘勰对它的表述是“拟容取心”。
显然,意与象“意共象生”,就是历代中国诗人们醉心追求的艺术理想。
意与象的结合模式如上所述,意与象的结合之密切程度,也大有不同。明何宗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云:“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当主体情思与具有客体性质的记忆表象复合且拥抱,意与象就“遇合”且“粘接”,如“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意与象就十分契合。权德舆《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疏导情性,含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表现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就是读者们往往“得意而不忘象”,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的语言中,意与象的关系正应该这样如聚骨肉。
《管锥编》里有一段话讲《易》象与诗喻之别,也可谓精辟:“《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乃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P11-12。)元好问《陶然集诗序》说:“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此话也可以理解为“诗家圣处不离象,不在象。”
【基于意与象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对诗歌的类型划分】
诗歌的类型很多,但是,基于诗歌意与象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对诗歌进行的类型划分,似乎更能体现出诗歌意象对于诗歌的决定意义。
一、意象结构诗歌
也叫感性结构诗歌,或称“间接抒情式”,是借助于诗的形象,将诗意隐含在形象——景象或事象——中的一种诗歌写作。由于其形象大多为意象,所以习称意象结构诗歌。这样的诗歌含蓄隽永,表现出对意象的无比尊重与信赖。托马斯说:“我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为诗建立一个‘基础’。这基础有时是一个地点。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我用清晰的方法描绘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北岛《时间的玫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32。)诗歌是想象的艺术,然而诗歌的想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依凭,这让诗歌的想象之双翼振翖而高翔者,就是意象。
需要说明的是,意象的运用固然可以使诗人之情感客观化、具体化,但是,诗歌创作如果过份强调意象而排斥一切直面抒情,也会有不利的影响,一些不露情感、不涉理念的作品就不易让人看懂,如庞德的《地铁站上》:“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郑敏译),好多人都觉得看不懂。【注】意象派大师庞德谈自己的《地铁车站》:“那一刹——那一刹中一件向外的和客体的事物使自己改观了,突变入一件内向和主观的事物。”(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导论)“的确,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瞬间互射凝成为结实的意象——理智和感情的复合体,是意象派诗人的拿手好戏。”(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P217。)另如北岛的《生活》等。这一类的诗,或称晦涩,或称蒙胧,多为象大于意的结构,它们“常常将自己的情思深深隐藏进意象之中”。
理解这一种结构的诗歌,主要依靠的是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中的“先天共感”。它要求我们能够通过联想,尽可能地理解“意象上粘附的情感取向”。这种理解,一般需要读者具有较强的生命直观能力。比如现代诗人废名的《理发店》:
理发店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干,
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类的理解,
划得许多痕迹。
墙上下等的无线电开了,
是灵魂之吐沫
人们曾试图解释这首著名的“朦胧诗”,有说它赞颂劳动者的,也有说它表现人类沟通之困难的,也有说要理解这首诗必得知道庄子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其实,只要一个人对鱼相处于江湖的生活状况有过观察,并对“忘记”和互不往来的人间冷漠有过体验,即可直接进行生命的直观——悟,不必经由知识也不必到达理性。
二、言说结构诗歌
也叫理性结构诗歌,相对于意象结构诗歌,这一类型的诗歌多由直接的抒情或议论构成,一般都只有诗人自我形象,而没有材料性的意象。“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的这首《论诗》就是一首典型的直接式表意诗作。主张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现代诗歌理论家胡风在其《关于“诗的形象化”》一文里说:“人不但能够在具象的东西里面燃起自己底情操,人也能够在理论或信念里机燃起自己底情操的。”如赵丽华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亲爱的
我肯定也老了
那时侯,我还能给你什么呢
如果到现在还没能给你的话
如苏浅的《理想主义》:
只学习一种技艺:
爱大多数人
并宽容剩下的少数人
如水晶珠链的《羡慕》:
我看到一些无边无际的东西
天空、海洋、草场、吃草的牛羊
它们跟爱一点关系也没有
无边无际的天真与好胃口
让他们顾不上
心碎
法国人格洛舍《艺术之起源》中收录了几首土著人的原始诗歌。其一为:《跛脚人》:“哦,那是什么脚哟/哦,那是什么脚哟/你这混蛋的袋鼠脚哟”,其诗意得以体现,其诗体得以成立的地方,在于其想象:袋鼠一样的脚!这首诗显然是意象结构的诗;其二为:《酋长》:“酋长是不晓得害怕的哟”。这一首又显然是言说结构的诗。这样的诗歌,可称“零意象”诗歌,如谢轮的《家》:“没出门/就等于不认识/不管你怎样查字典/也弄不懂/这个字的含义/这个字/每个人都在写/写完一生/这个字/完完全全的注解/是异地他乡”(《读者》2005年第17期,P5。)即是直来直去的言说而已。
这种言说结构的诗歌之成立自有其诗学合理性,因为,诗向来就有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一是立象尽意,一是直言其意。诗既可以形象性强于思想性,含蓄隽永,也可以思想性强于形象性,明朗畅快。“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思想的直陈未必不能得到世人的诗称。“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叶燮(原诗》)从来都是多元并存多样共生方显出生命的繁荣。而且,“诗歌的抒情本质和它的多种样式,决定了意象不是所有的诗歌的建筑材料。一些直抒胸臆的诗就没有意象。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的《将进酒》、拜伦的《若国内没有自由可为之战斗》、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就是直接抒情的名篇。”(江凡《形象与意象》,《武钢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其实,这样的诗歌,名为诗而实为歌,如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等。再如这首伊拉克的古诗:
多谢命运对我的宠爱和诅咒
我已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天使还是魔鬼
是强大还是弱小
是英雄还是无赖
如果你以人类的名义把我毁灭
我只会无奈地叩谢命运对我的眷顾
这首“诗”,用现代的诗歌理念来看,更像是一首“歌”。
“诗”与“歌”的分离,早成事实,“诗”与“歌”的分水岭之一,就是“诗”多以“意象结构”为主而“歌”多以“言说结构”为主。。
这种言说结构的诗歌作品最大的缺点就是意大于象,不够含蓄。诗人马拉美在《谈文学运动》中说: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这种趣味原是要一点一点地去领会它的。暗示,那才是我们的理想。(《象征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中国诗歌到了宋代,出现了偏于说理的倾向,但毕竟“立象尽意”的传统仍然十分强大,所以宋人的说理,仍然追求“理趣”而力避直陈。所以,我希望把直接的言说结构的诗歌排除出真正真正上现代诗歌的队伍,可是……我们不得不给这样的诗歌一席之地。
和诗歌的“零意象”现象不同的是,当代诗歌写作中有人却明确地主张要“反意象”。伊沙就是一个自称的反意象的诗人。他说:“意象诗与口语诗能够兼容吗?我认为不可以。”(伊沙等编著《十诗人批判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P274。)伊沙最为得意的反意象诗,就是《结结巴巴》:
结结巴巴我的嘴
二二二等残废
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
还有我的腿
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
散着霉味
我我我的肺
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
你们莫莫莫名其妙
的节奏
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
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
的语言
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
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
你们瞧瞧瞧我
一脸无所谓
他在这首诗里反抒情,反意象,但是他却投靠了音乐,他自己就这样交代:“《结结巴巴》让我最不舒服的一点是:它太崔健太摇滚歌词化了!这种节奏感,这种EI声韵……我从崔健那里没有偷到对诗而言有益的东西,除了他的节奏加强了我语感中的力量成分。”(伊沙等编著《十诗人批判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P276。)其实,“口语照样可以入诗成象表意。其实在口语中同样蕴藏着汉语的诗性精神,同样可以建构出丰富而有韵味的意象,就看你能不能把它发掘出来。”(和磊《意象的重新认识》,《诗刊》2003年第15期。)所以,我认为像伊沙这样的追求确实是有些过份,而和磊先生的说法比较温和:“即便是再强调诗的开放性,它也必须附着在相对固定的局部或整体意象之上。比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它虽然不再着意营造传统的有关大雁塔的意象,但整首诗在一种漫不经心的叙述中,营造了一种消解传统与经典的整体意象,给人一种深深的思索。”
三、“感性+理性”结构即“意象+言说”结构
这是最为经典也最合诗歌之理于是也最常见的一种诗歌的意象结构,如以色列诗人耶和达?阿米亥(YehudaAmichai)的《和平幻景的附录》:
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之后
不要停手,别停!继续锤打
从犁铧之中铸造出乐器
无论谁想要重新铸造战争
都必须先把乐器变成犁铧
诗中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以下的三个意象:
意味着战争的武器——刀剑。
意味着和平的劳动工具——犁铧。
意味着诗意生活的事物——乐器。
这三个意象恰恰暗喻了人类存在的上述三个层面:追求存在(可以名之为“刀剑式存在”)、追求温饱的存在(可以名之为“犁铧式存在”)、追求诗意的存在(可以名之为“乐器式存在”)。以犁铧为一种和平意象,以乐器而为一种诗意生存的意象,这位以色列的诗人感觉到的,应该是人类的共识。“铸剑为犁”,这个中国的古老成语,早就表达了犁铧式生存对刀剑式生存的超越。在这三个意象的基础上,诗人自然而然地说出了最后一节,其战争等于倒退的思想也呼之欲出。再如艾青著名的《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就是典型的“感性+理性”结构。其第一节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抒发感情。诗人把自己比喻为一只鸟。其第二节,以抒情主人公形象直接倾诉:“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第二节意象之间: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
在一首诗中,使用单一意象者并不鲜见,但是更多的则是使用多个意象。在这样的诗歌中,意象双双出现或者成群出现,通过多种方式的组合,组织为一个浑然的整体,构成感觉的和弦效果,从而表达作者更复杂更深厚的寄托。
【意象的常见组合方式】
一、并置式组合
也叫并列式组合,将有关的几组意象罗列出来,构成一个意象的群体,西方人称之为“格式塔”质——布洛克通俗地解释说,把一个柠檬放在一个橘子边,它们就不再是一个柠檬和橘子,而成了水果。如孟浩然《宿建德江》之“野旷天低树,风清月近人”即是;如元代散曲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即是;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著名诗篇《乡愁》中的邮票、船票、坟墓、海湾这四个意象即是;如艾青《向太阳》中的“是的/太阳比一切都美丽/比处女/比含露的花朵/比白雪/比蓝的海水”即是。这种组合的操作要点是:并置的事物之间,性质的距离越远越好。
二、交错式组合
其实就是反置式组合,即将相反的或者相矛盾的两样事物进行对照式并置。在王朔的小说中,这样的语言组织十分常见,如《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句:“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猪头肉等等?”在诗歌作品中,如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高适的《燕歌行》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等,皆是。再如当代诗人车前子的《天涯》:
一个村庄的天涯是另一个村庄
一个朝代的天涯是被故意忽视的思想
一个的思想的天涯是信以为真
一块手表的天涯是发条坏了
一根恶棍的天涯是桌子的腿
一条脖胫的天涯是脖胫上的脑瓜……
再如史蒂文斯的《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之第一节:
周围,二十座雪山,
唯一动弹的
是黑鸟的眼睛
诗人伊甸分析道:“肃穆、庄严的二十座雪山中间,惟一动弹的是黑鸟的眼睛,周围一片明亮、寒冷的寂静,整个世界仿佛已被冻结。恰恰在这一片凛然的寂静中,惟一动弹的那双黑鸟的眼睛,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生命或者某种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珍贵和美丽。气势磅礴的二十座雪山和小小的黑鸟眼睛的对比是惊心动魄的:如此的巨大与微小、纯白与深黑、静与动的强烈对比,不能不造成某种艺术的震撼力,将我们的灵魂紧紧抓住。我们不能不久久地沉浸在这一个奇异境界中,一步步深入它内部的层层意蕴,就像走入一座渐次展开其辉煌、庄严的奥妙无穷的宫殿。”(伊甸《直觉—想象—思考——读史蒂文斯〈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名作欣赏》2003年第6期。)
三、突反式组合
相当于小说中所谓“情节的逆转”,在大量某一类意象罗列到一定程度后,突然出现一两个极为相反的意象类型,以求得情绪的突转与心灵的冲击等艺术效果。如敕勒川的《邂逅》:
是八月间的事了,我在草原上
遇到了一棵我认识的小草
它遇到我时一脸哀痛,它向我讲述了
另一棵健壮的草,是怎样转眼就夭折了
“它是那么英俊,充满生气,然而……”
它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看见
它流下的眼泪比我们人类
稠多了
我想安慰它几句,但一个人
怎么能安慰一棵草呢
这首诗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娓娓道来,有叙事,有拟人,也有滥情处,总之一切为了铺垫。下半部分用足力气抖出包袱——像溪水缓缓流来,突然遇到块大石头,就腾翻起一个浪头,让读者的内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而诗人显现出的真功夫就是:见好就收。
四、焦点式组合
众多看上去甚至有些杂乱的意象统一在某一个核心的意象周围,比如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亚尔美利亚》:
一盆菜献给主教,脔割的,痛苦的,
一盆菜,盛满废铁,骨灰,搅拌着眼泪,
悲惨的一盆菜,里面是叹息和倒塌的墙壁,
一盆菜献给主教——亚尔美里亚的鲜血。
一盆菜给银行家,一盆菜盛着
南方孩子们的脸颊,一盆菜——
轰炸,狂浪,废虚,惊惶。
一盆菜——叉开的绞刑棍,扭断的脑袋,
黝黑的一盆菜——一盆亚尔美里亚的血。
繁复杂乱的意象,被组织在统一的以“一盆菜”这个意象为核心的情绪之中。其中错综的意象和单纯的情绪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场。一盆菜……一盆菜……一盆菜式单纯的反复,形成了一种焦点式的意象组合。
【意象的密度】
有没有意象,是诗与非诗之间一种重要的区别。伊沙著名的“无字诗”《老狐狸》,其实也使用了一个所谓大象无形的“无”之意象。而意象的多少,往往能够显示出诗人的才华之是否富赡。诗的创作,就是诗人捕捉意象,然后加以有序化组合的过程。意象成分越充分,诗的成分越丰满。所以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诗歌的意象密度。
意象密度,指一首诗中意象的疏密程度。孙绍振先生认为:“有时一行诗(应该包括一首诗)只有一两个意象,特别是直接抒情的诗句。例如,陶潜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是,这样的诗句有较大的感情密度。”(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616。)孙先生认为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的诗句,意象的密度就比较高。(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616。)孙先生在讲述意象的疏密相间之变化时,以舒婷《致橡树》中的一节为例进行了分析:(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P518。)
诗行
意象数
你有你的铜枝铁杆
2
像刀,像剑
2
也像戟
1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1
像沉重的叹息
1
又像英勇的火炬
1
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
3
如果用“意象树”这一“意象”,来言说我们对于诗歌意象的理解,则一首诗,就如同是一棵“意象之树——挂着意象之叶的树”,此叶可疏可密,即一首诗的意象可多可少,并无一定之规。如余光中著名的《乡愁》,使用了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北岛著名的一字诗《生活》,只使用了一个意象:网。
但是,对于一首优秀的诗歌而言,无庸置疑应该强调意象的高密度,虽然意象密度与感情密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即意象密度似乎会压迫感情密度,但是,诗歌艺术感情内蓄而借物言说的本质,却更喜欢高密度的意象而不喜欢高密度的感情。物以稀为贵,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感情,事实上正是对感情庄严的敬重与维护,而感情的泛滥,在反过来压迫意象的同时,不也同时消解了感情的宝贵么?
诗歌艺术对意象密度的追求,甚至以牺牲语言的精确度为代价。即如“鸡声茅店月”,即如“古道西风瘦马”等,因为语法的严密与逻辑关系的显现,必然需要相应的语言体现,必然在仅有的语言空间里占据相应位置,也必然会压迫意象的密度。在诗歌中,狭路相逢,何者胜之?曰诗、曰诗意、曰诗意的承载者意象。而且,这样的牺牲并非无谓,而是建立在对读者鉴赏力的高度信赖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牺牲并非无奈的被动,而是理当如此的主动——读者应该从中感到作者对自己智慧的尊重。
诗歌艺术追求意象的密度唯一需要注意的,应该是意象的体系化即意象的纯度。也就是说,诗歌意象的高密度,非指诗歌中意象的胡乱堆砌与东拉西扯的肆意罗列,而指诗歌意象的相对统一与相对和谐。强扭的瓜不甜,强求的高密度意象非但无助于诗意甚至是对诗意的破坏。喻言之,当一个大学文学教师把一柄管钳从包里掏出来放在讲桌上时,人们会感到万分惊讶,因为文学教授的包里,本来是应该掏出香烟和讲义的。
【关于意境】
意境,是诗歌的初学者喜欢掉在嘴边的一个词,也是诗歌的古典主义者缅怀不已的一个词。然而一般人所谓的意境,不过是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画意”而已。由于他们是在空间概念的意义上理解意境的,于是他们难免殃及池鱼地把意象看做是构成意境的单位,并认为“意象群”会靠着人多势众而形成“意境”。
意境,正确的理解是“诗意的境界”。“境界”,本指人的意识和感受所及的领域。《佛学大辞典》解释“境界”是“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又解释“境”为“心之所游履攀缘者谓之境”。然则诗歌的境界,即诗意的境界,也就是诗人的艺术精神与力量所到达的疆域与高度,也就是诗意的高度、深度与远度。如王国维所举之例“红杏枝头春意闹”,说是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再如“云破月来花弄影”,说是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所谓境界全出,也就是其诗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与浓度以及一定的深远度。诗意的境界不同于文意的境界,一如诗人的境界不同于商人的境界,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云:“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也就是说,意境其实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空间概念,是一个过程概念而非目的概念。注:如此则意境似乎也不可用大小来区分。杨义《李杜诗学》云:“境界当然有大小之分,鸟鸣涧(王维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境界小得玲珑剔透,而张若虚那首被认为‘以孤篇压倒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则显得境界波澜壮阔。”(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1,P851。)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应该把意象看成诗歌前往意境而必须借助的手段,没有意象,就没有意境。先有意象,而后才可能有意境。同时,基于这样的理解,意境这一词语本身就并无褒意,不能把“有意境”视为是对一首诗的肯定,而只能把“有新奇的意境”等等视为是对一首诗的肯定。王昌龄《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有些人的诗,只有物境,有些人的诗,只有情境,而有些人的诗,则可达到意境——至于达到什么样的意境,那是又一个问题,意味着诗人需要付出的是又一种的努力。
第三节意象与词语:从意象到词语
关于意、象、言三者的关系,王弼阐述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以上讨论了意与象之间的关系,下面讨论意象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意象和词语】
诗歌意象就是以词语为物质外壳的被赋予了一定诗歌意义的事物,这个事物,它最早只是客观世界的物象,后来成为诗人主体大脑中的记忆表象,但它最终成为了诗人作品中的意象。
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以词语为物质外壳”,是因为有人说:在诗歌中,“意象的定义可以说成是:通过情感以传达经验的语言。”(殷宝书《怎样欣赏英美诗歌》,北京出版社1985,P41。)这样的解释让人纳闷——即使他说意象是通过情感以传达经验的词语,仍然让人纳闷。
意象必须通过词语而符号化。意象的选择体现在诗歌的内孕生成上,就是对表象的选择,体现在诗歌的文本生成上,就是词语的选择。词语的选择包括意象的选择却不仅仅是意象的选择,所以既不能把选择意象等同于选择词语,也不能把选择词语等同于选择意象。杜甫诗《客亭》有云:“秋窗犹曙色,落木更高风”,其中的“犹”与“更”,固然是杜甫精心选择的“词语”——在这里是虚词,但是却不可以称之为“意象”。
即使是实词的词语,也有以下三种状态:
一、字典里的词语
这是词语的前意义状态,或称意义的空载阶段,这时候它们只具有意义的可能性而不具有意义的事实性。
二、非文学语境里的词语
这是词语的意义状态,这时候它们在一定的语境中出场,进入意义状态——或称加载意义阶段。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们却属于文学意义的空载状态,即它们已经拥有了一般文化意义上的意义却并不一定拥有文学意义上的意义。比如:
蛋?蛋?鸡蛋的蛋
调皮蛋的蛋乖蛋蛋的蛋
红脸蛋蛋的蛋
张狗蛋的蛋
马铁蛋的蛋
?
这是甘肃乡土诗人高凯著名的诗作《村小:生字课》的第一节。在“蛋?蛋?鸡蛋的蛋/调皮蛋的蛋乖蛋蛋的蛋”这个句子里,“蛋,蛋”,只是处于意义空载状态的词语,而“鸡蛋的蛋”,就是意义的加载——却也不过是一般文化意义的加载。?
三、文学语境里的词语
这是词语的文学意义状态,这时候它们在一定的文学语境中出场,进入文学意义加载状态。而词语的文学意义则是对词语一般文化意义的超越。在诗歌作品中,这样的词语往往就是诗歌的意象。如果忽略了词语的字典意义,如果说一般所谓的词语,是指一定语境中的文化意义上的词语,是对事物的认知化命名或科学化命名,则意象——诗学词语——则是对事物超出认知意义的诗学意义上的命名。
诗学命名是建立在科学命名的基础之上但是高于科学命名的——诗人因此就是世界的“非物质意义上的命名者”。这种“高于”的命名是必要的:我们不得不用“词语”来对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命名——初始化命名,我们也不得不用“意象”来对事物进行再次命名——甚至是不断的命名。比如,人们如果满足于对“蛋”的“鸡蛋的蛋”这样的认识与感受,则这个世界就不再需要诗人。再比如,对笔者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如果人们满足于用“天水”二字命名它,我们就不再需要“天水:水天相接的地方”或“天水:天上的水/渭河、葫芦河、牛头河、羲河、曲溪/是她伸出的五根秀丽手指”这样的诗意命名。
?所以,诗学意义上的命名,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基于科学命名的二度命名,或者叫做重新命名——或者也可以说是对人和世界具体存在的不断发现和不断指认。因为这种命名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于是,用“二度命名”来称呼它,只是区分了它和初始化命名的不同,如果要准确地表述,就是“不断的命名”。因为我们的所有命名,在对事物进行某种意义之揭示的同时,也在对事物的另一种意义进行遮蔽。所谓再度命名,显然是想揭示事物另外的意义。
所以,“意象才是诗歌真正的语言。借用‘符号’这一符号学概念,我们可以说,意象是诗歌用以表情达意的符号。”(邓朝晖《意象——诗歌表达的另一种语言》,《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语言显然只是意象得以符号化呈现的物质外壳。如果说语言——词语的组合——这一物质外壳是诗歌浅表层面的符号系统,则它要呈现的却是诗歌深在层面的符号系统:即意象世界。“诗人们并不以词句为思想情感的最终载体,他们又以词句为媒介,创造了另外一套语言系统,或叫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挣脱言语层面,表现为更纯粹的艺术形式,以形象、色彩、节奏抒写情意。其中形象运用最为明显。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诗歌的这一特点,古典诗歌很少直抒胸臆,诗人们总是用词句营造形象,然后借形象抒情写意,形象自然也就成为诗歌的一种特殊语言。而这些形象往往倾注了作者满腔深情,往往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在古典文论中被称为‘意象’。”(邓朝晖《意象——诗歌表达的另一种语言》,《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显然,“意”隐藏于“象”中,“象”又隐藏于“词句”中,这就是诗歌作品从词句层面到形象层面再到意义层面不断深入的过程。所以,“我们解读诗歌,其实是在解读一种不同于词句语言的另一符合系统。”(邓朝晖《意象——诗歌表达的另一种语言》,《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这个系统就是意象,所以,只认识字的人或者只知道讲解词语的人永远也讲不出诗意。
这就是词语和意象的不同。海德格尔说:“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命名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显现。”(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P57。)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如果我们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从中抽取其中一词,它的审美价值就会随之丧失。这就是说单个意象如‘枯藤’一旦离开了该话语系统,‘枯藤’便失去了整体赋予它的悲凉色彩,成了语言学的词语。”(张燕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意象”辨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第1期。)结合前述词语的三种状态,则将“小桥”独立置放时,其意义为前意义;如将其放入科学语境,则其意义为文化意义;如将其放入文学语境,则其意义方为文学意义,则其方可称为“意象”。
?诗人路也在《诗歌的细微和具体》一文里说:“有一首歌,是有关亚运会的,曲子还是蛮好听的,歌词大略是:‘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是热血流,我们亚洲,大树根连根……’这歌词不能细想,越想越空,哪个地方的山不昂着头呀,哪个地方的河不是像热血在流,哪里的大树不是根连着根呢,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全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首歌稍加改动,改成‘我们欧洲……’或者‘我们非洲……’都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用到欧运会或者非运会上去。”他接着说:“像上面这首歌词一样的诗是很不少的,不过是从词到词,作者爱的是某些词语本身,其感觉是飘浮的,仅仅停留在词语的表面和外壳上,而对词语背后所代表着的那个真实的事物则忽略了。读者从中读到的也仅仅是一些汉字,看到的是一片虚空,到头来,这诗跟什么也没说一样。”(路也《诗歌的细微和具体》,《诗刊》,2003年第8期上半月刊。)显然,对于诗歌而言,意象——满载着文学意义的词语,而不是人人皆知的大白话般的文化意义上的词语——才是让诗歌有硬度也有质感的基本依靠。所以,意象是诗的基本艺术符号,是诗人感情、智性和客观物体在瞬间的结合,它暗示着诗人内心世界的图景,是具体化的感觉。意象毫无疑问是诗歌艺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基本表意单位,是构建诗歌大厦最基本的材料。

【意象选择的个性化】
写作的过程,与其说是词语的使用过程,不如说是词语的选择过程。只要是选择,其选择就必然是个性的体现,即词语也是可以表现个性的,比如,同是对父亲的称呼,有称“爹”者,也有称“父亲”者,复有称“大大”者。语言,就是在这样包括了名词、动词、量词等等的个性化选择中形成的,诗歌语言同样。贺拉斯《诗艺》说:“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义,表达就能尽善尽美。”(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P139。)
但是诗歌语言比一般文体的语言更为重视其语言个性化之处,在于诗歌语言在从词语到意义的过程中,又多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个性化意象的营造,即诗歌语言先通过个性化词语营造个性化意象,再通过个性化意象完成个性化表意。词语不过是个符号,如同钱币不过是些符号。一个诗人必须透过符号看到符号背后的事物,必须透过词语看到物象,并且通过词语的组合赋于物象以意义——最好是个性化的意义。比如,同样是几块钱,有的人拿它去买本书看,有的人拿它给自己买个冰棍吃。钱本身是没有意义与个性的,可是在使用的时候使用者却赋予了它意义与个性。
所以,诗歌的写作,其语言表层是词语的选择,其语言深层,是意象的选择。庞德似乎说过:发现一个高妙的意象甚至比完成累牍的作品更有意义,其实,发现至少是与选择同步进行的,甚至选择一个意象比发现一个意象更能显示出一个诗人的性情与美学追求。“在意象的选用上,闻一多偏爱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象,如红烛、剑匣、秋菊、红豆等,而徐志摩主要选用玫瑰、产妇、教堂、铁轨、骷髅等西方文化的产物。”(李怡《中国现代诗歌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P235。)当代中国诗歌更倾向于运用最为平常的物象来建造不平凡的诗歌意象世界,似乎这样更能表现出一个诗人出自于“平常心”的真功夫。
不过诗歌的语言选择主要是意象的选择但不只是意象的选择,诗歌语言中的有些语言,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认知语言,对它们的选择,是在诗歌意象选择的基础上对诗歌意义的辅助与补充、丰富与深化。我把诗歌语言这种意象个性化的实现手段,名之为:语言的炮制。
【诗歌意象个性化的实现手段:通过语言的炮制】
传统医药学里的药材加工,俗称炮制。当医生们不满足于某个药材原有的药性而要让它产生另一种药性时,医生们就会对药材进行加工:“揭示”药材的某一个性能同时也“遮蔽”它的另一个性能。越是伟大的医药师,其才华越是体现在对普遍药物的非凡炮制上。
诗歌语言也一样,为了实现个性化的诗歌表意,就有必要进行个性化的词语炮制——让各个语言单位更加趋向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组织。柯尔律治说,诗是“最妥当的字眼放在最妥当的地方”,他的这句话是有毛病的,天下没有“最妥当的字眼”,只有“放在最妥当的地方”,它才是“最妥当的字眼”。而把一个词语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就是词语的炮制。对此,有人曾经不甚理解,认为我所谓的炮制词语就是创造词语——他显然没有理解传统医学中的“炮制”概念。
字眼,即词语,我们的祖先早已替我们创造好了,任何一个想“自给自足”地“亲手炮制”字眼的人显然是愚蠢的,也是不自量力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中药师曾经或者正在炮制一种新的药材——比如说炮制出一种叫做“当去”(相对于当归)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在“炮制”一种叫做“(蜜)炙当归”或者“(醋)炒当归”的东西。炙当归以蜜,或者炒当归以醋,就是把一个词语放在最妥当的地方——让它产生预期的意义。
这就是我所谓的诗人的语言“炮制”。如果说“枯藤”等等不过是词语,则“枯藤老树昏鸦”就已是词语的炮制了。而“枯枯的藤老老的树昏昏的鸦”就已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诗歌口气了。以某人的网名“城市月光”为例,“城市月光先生”、“尊敬的城市月光先生”、“光先生”、“光光先生”,这四个称呼,所指虽然同一,然而语感不同。语感不同,所传达的情感也不同。什么是不同称呼的必要性,情感就是不同称呼的必要性。于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虽然起步于意象的选择却不停留于意象的选择,虽然落笔于词语的选择却不收笔于词语的选择。诗到语言为止,什么是诗歌的语言?那就是:意象通过词语的情感化组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