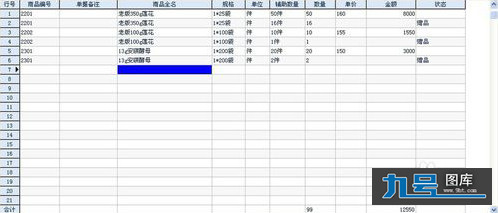(五常按︰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在昆明以《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为题讲话,内容不少在其它文章发表过,事后读报,一般没有误解,可能因为讲得够清晰。细想之下,这清晰应该源自我把题材的先后安排改变了,于是要凭记忆把这次讲话写下来,作为将要出版的《货币战略论》的压轴文章。
正要动笔,三位朋友不约而同地传来克鲁格曼(Paul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题为《中国格格不入》(The ChineseDisconnect,《信报》按内容翻为《中国策动人民币大贬值》)。克大师之文措辞刻薄,态度轻浮,颠倒是非,敌意明确,看不出是学者之笔,而其中所谓经济分析我没有半点同意。因为克大师之文与区区在下的昆明之说息息相关,遂决定把二者混合起来潇洒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读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经济学者骂战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发一年多了,但经济学行内还没有明确地解释发生了些什么事。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学者之间吵得那么厉害,互相对骂无日无之。我隔岸观火,对资料与实情的掌握当然比不上美国的行家君子。然而,我们的苏东坡曾经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这话题上,我远看庐山,可能有旁观者清的方便了。
我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起自他们的货币制度与金融制度一起出现了问题。美国的货币是无锚的,学术上的称呼是「法币」制度,fiatmoney是也。这是说货币或钞票的本身没有实物本位或外币本位的支持。历久以来,在这制度下,稳定物价的调控主要是调控货币量,有几种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师兄AlanMeltzer提出单以调控银根(monetarybase,有几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钞票的发行量)的方法来调控币量。币量是包括钞票之外的支票及其它银行存款了。那所谓M1、M2、M3的计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为币量调控这个话题,有了数十年的大争议。师兄一九六三的贡献,是有说服力地指出,单是调控银根,货币量就会得到适当的操控,因而可以稳定物价。然而,需要的调整时日通常要六个月至十多个月才见效果,所以不管怎样算币量,币量的调控与物价的反应是有着不容易处理的困难。货币理论的大争议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离开美国时还是争论不休,虽然那时行内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货币观是胜出了的。
大致上,师兄的鸿文发表后几年,欧洲与美国都接纳他提出的以调控银根的方法来调控币量,从而调控物价。问题是一九九五师兄访港,在雅谷跟我进午餐时,对我坦言感到困扰。那是因为美国的货币量——不管用哪种算法——相当急速地上升了好几年,但通胀却没有出现。他当时提出的解释,是美元奇怪地强劲,而强劲的货币是不容易有通胀的。我当时的看法跟师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美国显示的军力举世无匹,苏联解体,各国争持美元作为储备,而这样促成的美国币量上升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换言之,币量理论(quantitytheory of money)的困难,是当一种货币在大量国际化、电汇神速的情况下,调控物价的变动我们不知以哪种币量算才对。

可能是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转用调控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美国的经济。他对多方面的经济数据掌握得充分,于该年七月把联储局的利率下调,二十六个月内一连下调了十八次,跟着是调上七次,调落三次,调上一次,调落三次,调上六次,调落十三次,调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虽然联储调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银行借钱的利率,但有直接的关系。读者可能记得我说过几次,这样把利率辘上辘落早晩会辘出祸来。市场的利率应该由投资的回报率决定,而投资的回报率与市场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个重要的价,刻意地把利率辘上辘落是价格管制,会扰乱市场的运作功能。当然,市场的投资者会看着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个平均利率的预期。事实上,为了赚钱,市场的金融机构利用各种富于想象力的工具,包括国家债券的买卖,来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几年甚至多年利率不变的合约安排。问题是,如果市场一般对联储利率调控的预期大幅地猜错了,灾难不容易避免。
灾难终于出现。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调高利率第十四次后退休,伯南克接掌联储,再调高利率三次,然后坚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贷出事才把利率下调。当时大家知道,美国的房价上升了很多,那里的居民很多以几年不变的利率购买了房子。这使我推断,次贷出事起于利率辘上辘落终于使市场的利率预期大幅地出错,闯大祸。当时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场对这样的观点敏感,没有写出来。
我可没有想到,我认为是严重的其实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后,才知道通过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借贷与抵押的比率竟然远高于一;才知道保险的安排把金融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才知道这种复杂无比的金融体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评级机构维护着。无锚的货币制度失败,在于有关当局逼着要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经济。金融制度的失败,在于贪婪的众君子把它弄得复杂无比,就是经济专家也搞不清楚如何运作。君不见,金融风暴事发后,美国数百位经济学者签名说是伟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复杂难明的证据吗?
美国的经济前途怎样了?复苏的机会是有的,但重振雄风的机会,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出现。这两点,经济学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间的理由可不一样。我自己对雄风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来没有机会引进。撤销最低工资会解困,但政治不容许,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为三年前定了下来,美国的最低工资还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胀会有大助,好些美国学者知道,但从伯南克的言论猜测,政治上也不容许。其二是财政赤字的问题。目前美国的财赤只是近于纪录,但各方面的估计,说未来的财赤会破纪录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计,但所有估计都高得发神经。
佛利民当年认为财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国家负担得起,对经济不会有大影响。他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美国面对的未来财赤会是那么庞大的吧。未来的庞大财赤,会使市民担心抽税会增加,或债券之价会下跌,使联储无从约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负债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税收打主意,或美元会暴跌,导致通胀与利率上升。无论哪一项,市民采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没有一项防守对经济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九十四岁的大师森穆逊(PaulSamuelson)在《纽约时报》为文,重复了他不久前说过的观点。主要提到两方面。一方面他认为他的孙子那一代会见到中国的实质总国民收入超于美国,成为地球上的经济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国际币值会暴跌,导致灾难。我不认为中国当上地球上的经济一哥是好事:这几年北京已经未富先骄,树大招风可免则免吧。客观地看,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出那么多,物价调整后的实质总国民收入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则遥遥无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气地指出「人均无期」这一点。在美元可能暴跌这话题上,森前辈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还没有呈现大弱势,主要因为人民币钩着美元!
后者的经济逻辑是简单的,用不着多说。我的本领是可以提出证据。有经济触觉的人,如果跟踪人民币的国际汇率转变,会察觉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币从单钩美元转钩一篮子外币之初,该篮子内的美元含量应该还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比重其后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年来,我的观察是人民币再加重以美元为锚的成分,有时甚至全钩美元。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过后再说,但绝对不是因为什么阴谋或什么「格格不入」。是的,我认为人民币加重钩着美元是帮着美国一个大忙,克鲁格曼的恶意言论是浅见。他在专栏的最后说:「一个大国向邻国行乞的行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对中国的货币做点事。」说得潇洒,但要对人民币做点什么事,才有利于美国呢?此君在国际贸易的分析上拿得诺贝尔奖,堪称奇迹!
克鲁格曼认为美元下跌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因为可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圣的经济学了。弹性系数与贸易逆差这个话题是本科三年级的学问,而美元暴跌会使美国债券之价暴跌,等于美国利率暴升。与债券之价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联储局无技可施,房价不知会跌到哪里去。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经验——债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经验——怎会这么快就忘记了?
在同一文内,克氏提出一些其它美国经济学者的看法:因为中国购买外地的资产,促成美国的楼市泡沫,带来金融危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年外资涌进中国,比中国投资到美国去的钱,多出很多,北京可没有哭出来。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黄子孙能投资一点钱而把美国的经济搞垮,将来的历史学者怎会不哗然大叫,心脏病发呢?
这里顺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认为北京蠢,购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这可能又是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扰乱美国经济的原因。我不会为北京朋友的智商辩护,但他们多买美债是源于不好写出来的政治压力,神州大地一些担瓜卖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说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应贝加(GaryBecker)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谬误。人民币从一九九四至二○○五这十一个年头紧钩美元,不可能有操控汇率的空间。其后人民币转钩一篮子外币,是美国的议员逼出来。不知是谁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师们,少说几句不是较好吗?要向克鲁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币兑美元的黑市汇率是十一元七角兑一美元,今天没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兑一。这反映着些什么?反映着这些年中国的生产力增长,远超美国的。虽然伊拉克之战对美国不利,但人民币兑美元的大强势始于二○○三年初,在伊战之前。除非是蠢才,没有谁不希望美国的经济继续强劲,但事实是在地球一体化这个严重关头上,美国的经济结构的确是出现了不少问题。他们不应该向往着昔日的雄风,漠视了落后之邦的人也有头有脑,有手有脚。这一点,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我跟佛利民解释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当时也有点轻敌。但我深信,如果佛老还健在,他会支持我的看法。
回头说人民币的困境(是的,人民币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还要钩着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兑美元的汇率。这不是要向美国行乞,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业产出外销主要还是用美元结算。说过了,基本上中国的产出不是与先进之邦竞争,而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后者竞争大致上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如果中国的产出外销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让其它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杀下马来。千夫指着骂中国,只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哥。所谓树大招风也。
要脱离使用美元结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种费用最低,麻烦最少。这是撤销还余下来的不成气候的外汇管制,把人民币自由外放,从而使中国的厂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币结算。这简单的处理有复杂的一面。解释过多次,撤销汇管给中国带来的利益数之不尽,这里不再说。这里要说的一个重要的复杂点,是撤销汇管后让人民币兑所有外币自由浮动,人家要搞你,或联手来搞你,有得搞。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坚持人民币要下一个固定的锚的其中一个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经验应该教训了大家,以任何外币为锚,或以一篮子外币为锚,皆非善策。中国的央行要选货币以外的实物为锚,然后让人民币兑所有外币自由浮动。我建议的下锚制度说过无数次了,这里只再说其中一点︰依我的建议,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实物储备的。转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人民币之锚,对央行的君子们只有一个不利之处。那就是他们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权力会大减。但货币政策是不应该用作调控经济的。每次我听到周小川先生说他的货币政策是多目标的,必摇头兴叹。货币的基本用场是什么我解释过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标也闯大祸。
放开汇管,采用我建议的下锚之法,聪明的发展中国家会知道怎样做才能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条件。这对中国有利。先进之邦呢?他们会考虑作为人民币之锚的一篮子物品来选择他们的策略。北京不用管这些。富有的老大哥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选择。
我很欣赏森穆逊十月二十四日说的两句话︰「当一个工资低、可以学习的民族能仿效先进之邦的科技时,他们会仿效。这是为什么保护主义像疱疹毒素,我们一定要预防染上。」这才是经济学。
(五常再按:区区在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神州增订版已经出版,印制精美、价格相宜,只在神州大地销售。一百元买四本送给亲友吧。)
分享到新浪微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