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弦(1913- ),原名路逾,曾用笔名路易士,台湾现代派诗人之一。出版的诗集有《易士诗集》(1934)、《火灾的城》(1937)、《三十前集》(1945)、《摘星的少年》(1954)、《隐者诗抄》(1963)、《晚景》(1985)、《半岛之歌》(1993)。
《火》
开谢了蒲公英的花,
燃起了心头上的火。
火跑了。
追上去!
火是永远追不到的,
他只照着你。
或有一朝抓住了火,
他便烧死你。
《海的意志》
——天哪!天哪!
在梦的漩涡里,
我是时常做着
苦痛的**的。
可是飓风袭来了。
我是一个浪。
这是海的意志。
不容你多想。
忘了自己,
不再垂短蜡之泪——
伟大的,海的意志呀!
伟大的,海的意志呀!
《乌鸦》
乌鸦来了,
唱黑色之歌;
投我的悲哀在地上,
碎如落叶。
片片落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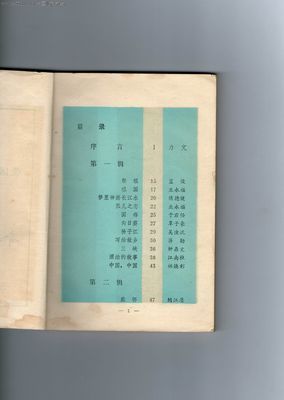
驮着窒息的梦;
疲惫烦重的心,
乃乘鸦背以远飏。
《幻像》
幻像是一个难忘的
天长地久的情妇,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黄昏时分,
她来了。
我看见她着了一袭
雾色的轻衫,
而那一双馥郁的红唇,
遂益觉其魅人了。
她悄悄坐下,
在我身旁,
抚弄我长披之发,
以她多情的手。
我倾听着她之诉语,
而她也懂得我的凝眸。
她常播一粒种籽,
在我荒凉的心里,
而让花在笔尖上开,
结通红的果子在纸上。
若有庸俗的脚步闯入我幽静的书斋,
她乃迅速地奔避了。
《舷边吟》
说着永远的故事的浪的皓齿。
青青的海的无邪的梦。
遥远的地平线上,
寂寞得没有一个岛屿之飘浮。
凝看着海的人的眼睛是茫茫的,
因为离开故国是太久了。
迎着薄暮里的咸味的风,
我有了如烟的怀念,神往地。
《火灾的城》
从你的灵魂的窗子望进去,
在那最深邃最黑暗的地方,
我看见了无消防队的火灾的城
和赤luo着的疯人们的潮。
我听见了从那无垠的澎湃里
响彻着的我的名字,
爱者的名字,仇敌们的名字,
和无数生者与死者的名字。
而当我轻轻地应答者
说“唉,我在此”时,
我也成为一个
可怕的火灾的城了。
《烦哀的日子》
今天是烦哀的日子,
你突然做了天国的主人,
你说梦有圣洁的颜色,
如爱人天蓝的眸子。
于是你便去流浪,
学一只心爱的季候鸟。
涉过了无穷尽的川河,
越过了无穷进的山岭,
你终于找到了一片平原,
在一片不可知的天蓝之国土。
那里是自由的自由,
你可以高歌一曲以忘忧。
而你将不再做梦——
“如今的天国是我之所有。”
《古城七月》
七月的古城里
扬起了一天的风沙。
(末日写在人脸上)
如今的汽车里
载去了贵男贵女们的笑。
那管他火热的太阳
炙在赭黑的皮肤上。
嗟彼闲人们如醉如痴,
手摇着折纸扇
大街上步着悠然!
(天生就一颗奴隶的心)
终日价胡琴大鼓——
啊,这满城的后院花!
《狼之独步》
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嗥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
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
这就是一种过瘾。
《在地球上散步》
在地球上散步,
独自踽踽地,
我扬起了我的黑手杖,
并把它沉重地点在
坚而冷了的地壳上,
让那边栖息着的人们
可以听见一声微响,
因而感知了我的存在
《飞的意志》
一种飞的意志永远支配着我。我想飞!于是我长了翅膀,我试着鼓动我的双翼,觉得它们的xing能极强,
虽大鹏,鸿鹄,鹰隼,也不可同日而语。自信我的速度,高度,和持久力,不仅是超越凡诸鸟类,抑且是凌驾各种飞机。凭着这对翅膀,不飞则已,要飞,起码是一飞冲天,二十四小时周游太阳系,啊,
多好,飞吧!哦,再见,丑陋的世界,
但是,我展开的双翼,刚刚使劲一扑,扑了一点点,
两足离开地面还不到半公尺的光景,就整个的跌下来了。而且,多惨,连所谓强有力的翅膀也从此折断了。这是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我不知道。而我知道的是,现在,我清楚地看见了:就在那边,站着的,那家伙,名叫“现实”,他手里拿着一杆猎枪,无声地狞笑着。
《6与7》
拿着手杖7.
咬着烟斗6.
数字7是具备了手杖的形态的。
数字6是具备了烟斗的形态的。
于是我来了。
手杖7+烟斗6=13之我。
一个诗人。一个天才。
一个天才中之天才。
一个最最不幸的数字!
唔,一个悲剧。
悲剧悲剧我来了。
于是你们鼓掌,你们喝彩。
《彗 星》
说吧,什么是自由自在的
是那急驰的,一去不复返的彗星吗?
对啦,彗星是自由自在的,
它有一根扫帚一般的光的尾巴。
太阳也许摇摇头,
轻轻地骂声:“小流氓!”
可是我却非常喜欢它,
而且作诗热烈地赞美它。
我还有一个奇怪的念头:
如果一跃而骑上了它的脊梁……
《人 间》
那些见不得阳光的,
给他一盏灯吧!
那些对着铜像吐唾沫的,
让他也成为铜像吧!
而凡是会说会笑的
洋囡囡似的可爱的小女孩,
请抱着丑小鸭米老鼠和狗熊
走进我的春天的园子来;
只要不是塑料不是尼龙
也不是赛璐珞做的,
都可以吃我树上的番石榴。
《不再唱的歌》
当我的与众不同
成为一种时髦,
而众人都和我差不多了,
我便不再唱这支歌了。
别问我为什么,亲爱的。
我的路是千山万水。
我的花是万紫千红。
罗门诗选
罗门(1928- ),原名韩仁存,蓝星诗社成员之一,出版的诗集有《曙光》、《死亡之塔》、《罗门诗选》等。
《麦坚利堡》
超过伟大的
是人类对伟大已感到茫然
战争坐在此哭谁
它的笑声 曾使七万个灵魂陷落在比睡眠还深的地带
太阳已冷 星月已冷 太平洋的浪被炮火煮开也都冷了
史密斯 威廉斯 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你们的名字运回故乡 比入冬的海水还冷
在死亡的喧噪里 你们的无救 上帝的手呢
血已把伟大的纪念冲洗了出来
战争都哭了 伟大它为什么不笑
七万朵十字花 围成园 排成林 绕成百合的村
在风中不动 在雨里也不动
沉默给马尼拉海湾看 苍白给游客们的照相机看史密斯 威廉斯 在死亡紊乱的镜面上 我只想知道那里是你们童幼时眼睛常去玩的地方
那地方藏有春日的录音带与彩色的幻灯片
麦坚利堡 鸟都不叫了 树叶也怕动
凡是声音都会使这里的静默受击出血
空间与时间绝缘 时间逃离钟表
这里比灰暗的天地线还少说话 永恒无声
美丽的无音房 死者的花园 活人的风景区
神来过 敬仰来过 汽车与都市也都来过
而史密斯 威廉斯 你们是不来也不去了
静止如取下摆心的表面 看不清岁月的脸
在日光的夜里 星灭的晚上
你们的盲睛不分季节地睡着
睡醒了一个死不透的世界
睡熟了麦坚利堡绿得格外忧郁的草场
死神将圣品挤满在嘶喊的大理石上
给升满的星条旗看 给不朽看 给云看
麦坚利堡是浪花已塑成碑林的陆上太平洋
一幅悲天泣地的大浮雕 挂入死亡最黑的背景
七万个故事焚毁于白色不安的颤栗
史密斯 威廉斯 当落日烧红野芒果林子昏暮
神都将急急离去 星也落尽
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
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
《窗》
猛力一推 双手如流
总是千山万水
总是回不来的眼睛
遥望里
你被望成千翼之鸟
弃天空而去 你已不在翅膀上
聆听里 你被听成千孔之笛
音道深如望向往昔的凝目
猛力一推 竟被反锁在走不出去
的透明里
《车祸》
他走着 双手翻找着那天空
他走着 嘴边仍支吾着炮弹的余音
他走着 斜在身子的外边
他走着 走进一声急刹车里
他不走了 路反过来走他
他不走了 城里那尾好看的周末仍在走
他不走了 高架广告牌
将整座天空停在那里
《流浪人》
被海的辽阔整得好累的一条船在港里
他用灯拴自己的影子在咖啡桌的旁边
那是他随身带的一条动物
除了它 娜娜近得比什么都远
把酒喝成故乡的月色
空酒瓶望成一座荒岛
他带着随身带的那条动物
朝自己的鞋声走去
一颗星也在很远很远里
带着天空在走
明天 当第一扇百叶窗
将太阳拉成一把梯子
他不知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诗的岁月——给蓉子》
要是青鸟不来
春日照耀的林野
如何飞入明丽的四月
踩一路的缤纷与灿烂
要不是六月在燃烧中
已焚化成那只火凤凰
夏日怎会一张翅
便红遍了两山的枫树
把辉煌全美给秋日
那只天鹅在入暮的静野上
留下最后的一朵洁白
去点亮温馨的冬日
随便抓一把雪
一把银发
一把相视的目光
都是流回四月的河水
都是寄回四月的诗
--------------------《生存!这两个字》
都市是一张吸墨最快的棉纸
写来写去
一直是生存两个字
赶上班的行人
用一行行小楷
写着生存
赶上班的公车
用一排排正楷
写着生存
赶上班的摩托
用来不及看的狂草
写着生存
只为写生存这两个字
在时钟的砚盘里
几乎把心血滴尽
《痖弦诗选
痖弦(1932- ),原名王庆麟,创世纪诗社成员之一,出版的诗集有《痖弦诗抄》(1959)、《深渊》(1968)、《痖弦诗集》(1981)等。
《故某省长》
钟鸣七句时他的前额和崇高突然宣告崩溃
在由医生那里借来的夜中
在他悲哀而富贵的皮肤底下——————
合唱终止。
《神》
神孤零零的
坐在教堂的橄榄窗上
因为祭坛被牧师们占去了
《山神》
猎角震落了去年的松果
栈道因进香者的驴蹄而低吟
当融雪像纺织女纺车上的银丝披垂下来
牧羊童在石佛的脚趾上磨他的新镰
春天,呵春天
我在菩提树下为一个流浪客喂马
矿苗们在石层下喘气
太阳在森林中点火
当瘴疠婆拐到鸡毛店里兜售她的苦苹果
生命便从山鼬子的红眼眶中漏掉
夏天,
我在鼓一家病人的锈门环
曲嬉戏在村姑的背篓里
雁子哭著喊云儿等等他
当衰老的太阳掀开金胡子吮吸林中的柿子
红叶也大得可以写满一首四行诗了
秋天,呵秋天
我在烟雨的小河里帮一个渔汉撒网
樵夫的斧子在深谷里唱著
怯冷的狸花猫躲在荒村老妪的衣袖间
当北风在烟囱上吹口哨
穿乌拉的人在冰潭上打陀螺
冬天,呵冬天
我在古寺的裂钟下同一个乞丐烤火
《上校》
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
自火焰中诞生
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
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
他曾经听到过历史和笑
甚么是不朽呢
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
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
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
1960年8曰26日
《伞》
雨伞和我
和心脏病
和秋天
我擎着我的房子走路
雨们,说一些风凉话
嬉戏在圆圆的屋脊上
没有甚么歌子可唱
即使是秋天,
即使是心脏病
也没有甚么歌子可唱
两只青蛙
夹在我的破鞋子里
我走一下,它们唱一下
即使是它们唱一下
我也没有甚么可唱
我和雨伞
和心脏病
和秋天
和没有甚么歌子可唱
1958年6月
《红玉米》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
挂着
好像整个北方
整个北方的忧郁
都挂在那儿
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
犹似唢呐吹起
道士们喃喃着
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
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
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以及铜环滚过岗子
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
便哭了
就是那种红玉米
挂着,久久地
在屋檐底下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你们永不懂得
那样的红玉米
它挂在那儿的姿态
和它的颜色
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
凡尔哈仑也不懂得
犹似现在
我已老迈
在记忆的屋檐下
红玉米挂着
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
红玉米挂着
1957年12月19日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托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驼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鹫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托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1958年1月14日
《坤伶》
十六岁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里
一种凄然的旋律
那杏仁色的双臂应由宦官来守卫
小小的髻儿啊清朝人为他心碎
是玉堂春吧
(夜夜满园子嗑瓜子儿的脸!)
“苦啊……”
双手放在枷里的她
有人说
在佳木斯曾跟一个白俄军官混过
一种凄然的旋律
每个妇人诅咒她在每个城里
1960年8月26日
《C 教授》
到六月他的白色硬领将继续支撑他底古典
每个早晨,以大战前的姿态打着领结
然后是手杖,鼻烟壶,然后外出
穿过校园依旧萌起早岁那种
成为一尊雕像的欲望
而吃天下是无用的
云的那边早经证实甚么也没有
当全部黑暗俯下身来搜索一盏灯
他说他有一个巨大的脸
在晚夜,以繁星组成
1960年8月20日
《巴黎》
奈带奈霭,关于床我将对你说甚么呢?
——A·纪德
你唇间软软的丝绒鞋
践踏过我的眼睛。在黄昏,黄昏六点钟
当一颗陨星把我击昏,巴黎便进入
一个猥琐的属于床第的年代
在晚报与星空之间
有人溅血在草上
在屋顶与露水之间
迷迭香于子宫中开放
你是一个谷
你是一朵看起来很好的山花
你是一枚馅饼,颤抖于病鼠色
胆小而[xue悉][xue卒]的偷嚼间
一茎草能负载多少真理?上帝
当眼睛习惯于午夜的罂粟
以及鞋底的丝质的天空,当血管如菟丝子
从你膝间向南方缠绕
去年的雪可曾记得那些粗暴的脚印?上帝
当一个婴儿用渺茫的凄啼诅咒脐带
当明年他蒙着脸穿过圣母院
向那并不给他甚么的,猥琐的,床第的年代
你是一条河
你是一茎草
你是任何脚印都不记得的,去年的雪
你是芬芳,芬芳的鞋子
在塞纳河与推理之间
谁在选择死亡
在绝望与巴黎之间
唯铁塔支持天堂
1958年7月30日
《芝加哥》
铁肩的都市
他们告诉我你是yin邪的——C·桑德堡
在芝加哥我们将用按钮恋爱
乘机器鸟踏青
自广告牌上采雏菊,在铁路桥下
铺设凄凉的文化
从七号街往南
我知道有一则方程式藏在你发间
/出租汽车捕获上帝的星光
张开双臂呼吸数学的芬芳
当秋天所有的美丽被电解
煤油与你的放荡紧紧胶着
我的心遂还原为
鼓风炉中的一支哀歌
有时候在黄昏
胆小的天使扑翅逡巡
但他们的嫩手终为电缆折断
在烟囱与烟囱之间
犹在中国的芙蓉花外
独个儿吹着口哨,打着领带
一边想着我的老家乡
该有只狐立在草坡上
于是那夜你便是我的
恰如一只昏眩于煤屑中的蝴蝶
是的,在芝加哥
唯蝴蝶不是钢铁
而当汽笛响着狼狈的腔儿
在公园的人造松下
是谁的丝绒披肩
拯救了这粗糙的,不识字的城市……
在芝加哥我们将用按钮写诗
乘机器鸟看云
自广告牌上刈燕麦,但要想铺设可笑的文化
那得到凄凉的铁路桥下
1958年12曰16日
《水夫》
他拉紧盐渍的绳索
他爬上高高的桅杆
到晚上他把他想心事的头
垂在甲板上有月光的地方
而地球是圆的
他妹子从烟花院里老远捎信给他
而他把她的小名连同一朵雏菊刺在臂上
当微雨中风在摇灯塔后边的白杨
街坊上有支歌是关于他的
而地球是圆的
海啊,这一切对你都是蠢行
1960年8月26日
《如歌的行板》
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认识之必要
欧战,雨,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点钟自证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
之必要。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
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
姑母继承遗产之必要
阳台、海、微笑之必要
懒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1964年4月
《焚寄T·H》
诗人,我不知你是如何找到他们的
在那些重重叠叠的死者与死者们之间
你灰石质的脸孔参加了哪一方面的自然?
星与夜
鸟或者人
在叶子
在雨
在远远的捕鲸船上
在一零四病室深陷的被褥间
迟迟收回的晨曦?
老屋后面岗子上每晚有不朽的蟋蟀之歌
春天走过树枝成为//另一种样子
自一切眼bo的深处
白山茶盛开
这里以及那里
他们的指尖齐向你致候他们呼吸着
你剩下的良夜
灯火
以及告别
而这一切都完成了
奇妙的日子,从黑色中开始
妇女们跳过
你植物地下茎的
缓缓的脉搏
看见一方粘土的
低低的天
在陶俑和水瓮子的背后
突然丧失了
一切的美颜
至于诗这傻事就是那样子且你已看见了它的实体;
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
热切地吮吸一根剔净了的骨头
——那最精巧的字句?
当你的嘴为未知张着
你的诗
在每一种的美赞下
抛开你独自生活着
而你的手
为以后的他们的岁月深深颤栗了
1964年9月为纪念覃子豪先生而写
《弃妇》
被花朵击伤的女子
春天不是她真正的敌人
她底裙再不能构成
一个美丽的晕眩的圆
她的发的黑夜
也不能使那个无灯的少年迷失
她的年代的河倒流
她已不是今年春天的女子
琵琶从那人的手中拾起
迅即碎落,落入一片凄寂
情感的盗贼,逃亡
男xing的磁场已不是北方
她已不再是
今年春天的女子
她恨听自己的血
滴在那人的名字上的声音
更恨祈祷
因耶稣也是男子
-《乞丐》
不知道春天来了以后将怎样
雪将怎样
知更鸟和狗子们,春天来了以后
以后将怎样
依旧是关帝庙
依旧是洗了的袜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