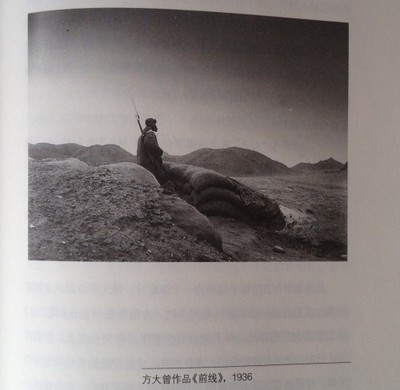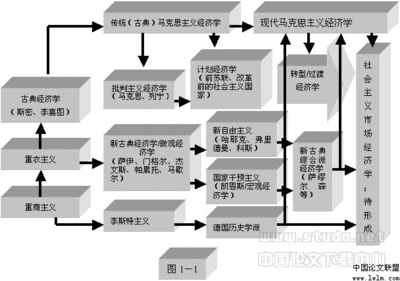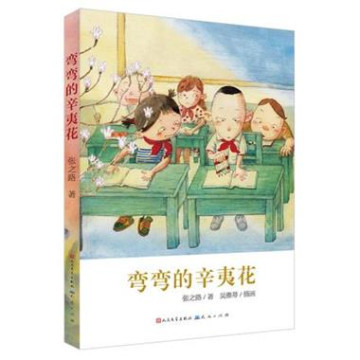内容梗概
《生活在别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画。昆德拉以其独到的笔触塑造出雅罗米尔这样一个形象,描绘了这个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具有“发展小说”的许多特点。就其题材而言,表现一个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是本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展示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也只有复杂的人物才能承担。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诗人创作过程的分析是微妙而精细的。创作过程当然不仅指下笔写作的过程,而且更广义地指一个诗人的全部成长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意图下,这部书最初曾被题名为《抒情时代》。作者所要表现和所要探究的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它的产生和它的结果。因而这本书又是一本现代心理小说,表现了一个诗人的艺术感觉的成长。书中每一章 节的名称都展示了诗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怎样读书,怎样恋爱,以及怎样做梦等等。关于时代的全貌和他人的活动都驰到了远处,一切观察的焦点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并且与他的内心活动有关。有如激情的涧水,在时间的乱山碎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溪流将流向沃野还是沙漠。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诗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发育。为了潜入到人物意识中最隐秘的角落,作者采用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时间与空间交织(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常常出现在同一段叙述中),现实与梦幻交织(第二章 《泽维尔》完全是一个梦套一个梦),情节的跳宕,思考的猝然与不连贯,故意模糊主语的陈述,这些都使此书更接近于诗歌而不是小说。假如我们把书中这些抒情性的因素去掉,这部作品的内容就剩不下什么了。这种形式使我们更能切近诗人的内心活动,感触到诗人的激情是怎样产生和燃烧的。生存于人类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对于“诗”、“抒情”、“美”这样的字眼,总是保持着崇高的故意。人类不仅具有抒情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这样抒情诗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问题,抒情态度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范畴。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原名就叫做《抒情时代》。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抒情诗具有最古老的起源,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G·B·维柯便把人类原初状态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称为“诗性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出现了专司诗歌的“诗人”。诗人与非诗人的分裂便产生了。诗、诗人总是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诗人被认为是由神灵所选中并赐予灵感的特殊而神秘的人物。曾几何时,诗与诗人成为一种神圣的价值体系的象征,屹立在宝座上,享受众人崇敬的注目和向往。
但是,对于米兰·昆德拉这位东欧作家来说,他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他看到了他所崇敬的法国大诗人艾吕雅,在他的布拉格朋友被斯大林最高法院送上绞刑架上之时,公开正式地宣布与之脱离关系。他深受创伤。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一切都变成了怀疑的对象,包括诗歌。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接近(进入)诗歌?小说中的主人公、年轻的诗人雅罗米尔第一次作为一个诗人而诞生是在他的初恋失败之时。在一种对自己的嫌恶和耻辱之中他蓦然面对的是自己的卑贱与渺小。他依靠写诗,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奇异世界,使他高出了现实的笨拙,得到了一个第二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是出于伟大和崇高的激情,而是它的负面,使雅罗米尔成为诗人。诗成为一种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诗人从诗与现实分裂的隙缝之中滑落下来。生活产生了离析,日常领域是单调乏味的空虚,“而天上却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灯火辉煌的路标,时间分割为一道灿烂的光谱。他无比兴奋地从一道光跳到另一道光,每次都坚信落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时代。”
自从诗获得了与现实相对立的象牙之塔的贵族含义之后,我们应该承认,这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诗的含义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分裂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厄运。在昆德拉看来,诗人似乎成了这种厄运的象征和化身。“雅罗米尔究其一生辗转于两个世界的边沿。昆德拉认为,当诗人们处于无力突破现实的行动世界而面临的基本境遇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态度。但是处于这种境遇的,并不仅仅是诗人。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境遇,是人类对永恒、崇高、美等一切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而上追求所注定的宿命。
《生活在别处》所描写的时候被昆德拉称为一个“抒情时代”。50年代的捷克,今天的人们把它视为一个政治审讯、迫害、禁书和合法谋杀的时代。但是,昆德拉说,我们这些还记得的人必须作证:它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抒情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激情的时代。大学生们的墙上刷的标语写道:“梦想就是现实”,“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千百万人振臂高呼,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昆德拉认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描写一个时代,选择一个特定时代并非因为对它本身感兴趣,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中只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是的,雅罗米尔是个“邪恶”的人,他毁灭了情人,也毁灭了自己。但这样的邪恶同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所有制度所有时代的每个年轻人身上。并不是特定时代才产生雅罗米尔,只是特定时代释放了他的这种心理因素。所有的时代都产生潜在的雅罗米尔。他并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恶人,他是一个人性意义上的恶人。昆德拉展示了这位有天分的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年轻诗人一生的心理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的内涵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雅罗米尔终其一生都在为进入现实的行为世界而努力。昆德拉告诫道,请别以为雅罗米尔是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一生的廉价解释。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自我与现实的对立之中,我们都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我。这样,对自我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恐惧便与生俱来地高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之上。现代心理学认为,正是这种压抑的升华产生了文学。
问题便变成了这样:文学的存在论意义是什么?
昆德拉说,“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人类的生存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的回答形式。昆德拉所做的是这个问题形式的展开。
雅罗米尔的母亲把对爱情的浪漫梦想转移到儿子身上,她醉心于当一个天才儿童的母亲,并且最早把诗人的桂冠赋予了雅罗米尔。有一个文学史的现象是:抒情诗人大部分都诞生在由女人所主持的家庭。这种母性家庭从小给予诗人的是一种精神庇护,一种与现实隔断的耽于幻想的温床。母亲与诗人的关系同诗与诗人的关系有一种神秘的相似。母爱是不需要自身努力便与生俱来的,母爱是儿童的整个世界。儿童在母亲的眼光中寻找对自我的肯定、理解与世界的关系。当他意识到母爱变成一种专制的力量限制着他的现实行动时,往往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一辈子都无法逃脱母爱世界所加之于他的束缚。从母爱世界过渡到诗的世界,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它兆明了一切诗人们的宿命,这便是两个世界的分裂。现实的行为世界像遥远的地平线一样,永远在远方。“生活在别处”,对于诗人们来说,他们相信真正的生活,具有行动力的现实生活永远在召唤着,仿佛伸手可及,却永远被一层透明的墙所阻隔。他们永远是不成功的幻想世界的迷亡者。诗人写诗,让诗如行星般绕着他运行,以此来弥补对外界的焦虑和对自我渺小的恐惧。诗成为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征明。它与我们通常对诗的理解是多么大相径庭。
雅罗米尔创造了一个叫泽维尔的人物,作为他在幻想世界中的替身。泽雅尔的生命是一个梦,他睡着了,做了个梦,在梦中他又睡着了,又做了个梦,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前一个梦里,梦的边沿模糊了,他从一个梦过渡到另一个梦,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不存在任何障碍。雅罗米尔在泽维尔身上否定了梦与现实的分界。而梦与现实的最大分界便是:梦是对无限、永远的可能的相信,而现实并不。他在爱情诗中描写死亡,死亡是个关于无限的梦。,因为生活是渺小的,死亡才是绝对的,死亡证明爱情的伟大崇高,他表达的渴望是在一种近似永恒幸福的死亡之中跟一个女人结合——省略掉现实的过程。他写老人的爱情是幸福的,因为老人已不再有未来,不再受变动不居的未知领域的侵略。对姑娘的裸体,他头晕目眩,“他并不向往姑娘的裸体,他向往的是被这裸体照亮的姑娘的脸庞。”“他并不想占有姑娘的身子;他想占有的是愿意委身于他以证明她爱情的姑娘的脸庞。”他需要的不是肉体,而是肉体的抽象。他采用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的语气描写子宫与乳房,因为他惧怕肉体的爱,并且试图从成人的领域中把爱取出来,把女人看作一个小孩,这意味着他没有能力把自己当成一个成熟的男人看待。诗成了他的“人造童年之乡”。他希望把爱情限定在它永恒不变的成分之中,以此战胜展开在他面前的潜藏着危险的肉体。他在诗中取消了肉体,用自然主义的丑陋衰老的身躯来替代一个年轻女性傲慢的身躯,剥除肉体躯壳以追求爱情永恒。
诗人在母爱世界中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对立,而在诗的幻想中则又逃避着这种对立。那么,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幻想中过生活,还是在现实中过生活?人如果丧失幻想,是很可怕的。如果一夜之间,人类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消失殆尽,人类便成了野兽。但是,文学传统美学原则并不能保障人类不成为野兽——互相残杀的野兽。现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意识的心理能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黑格尔早就把人类心理中的“恶”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文学往往根基于人类天性之中的乌托邦冲动,美学则赋予了这种冲动以科学的名义。而美学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一种神圣价值标准,因为这样一束,我们都会沉溺在乐观的迷雾中认不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昆德拉笔下的雅罗米尔,他的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崇高的美学原则,而且实践了它,他用诗歌的美学原则作为他现实行为的准则和解释,最终溺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永恒的深渊之中。
看一看雅罗米尔的性爱经历吧。性爱是人生存的最本质状态。把性爱放到昆德拉所说的“抒情态度”的范畴之中,它便获得了另一个名字,叫做“爱情”。青春、诗、爱情,都属于人类抒情态度的表达方式。雅罗米尔的爱情总是在达到它的现实层面的时候归于失败。所以,当他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性爱关系时,就颇有意味了。这是一个平凡的很不漂亮的女售货员,所以他意味着一个被减轻了形而上压力的女性躯体。在雅罗米尔的爱情幻想猝不及防的时候,是女售货员俘虏了他。所以爱情幻想的作用只能在事后弥补了。雅罗米尔把减轻了的东西又重新压了上去。在他看来,女售货员标志着他与人群之间创造了一种肉体联系,标志着到达了真正的生活领域。他为此而激动,这才是爱情的涵义。对他来说,仅仅是美好的瞬间还不令人满足,除非是作为美好的永恒象征才有意义。所以,在爱情中,他要占有的不是别的,而是“永恒”,完全地和永远地属于。他告慰自己说,他需要的不是美貌。爱上美貌并不难,人人都会,那不过是机械刺激反应。但伟大的爱情却是在寻求从不完美的造物之中创造可爱。而伟大创造的主人是他,所以姑娘必须把自己完全浸在爱的浴缸里,满足于呆在被他的言语和思想淹没的水面之下,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必须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爱情幻想所做的工作带来的结果是:忌妒。忌妒是对权力欲没有满足的忿忿不平。他很快意识到他的爱情并不能用“绝对”的观念去要求,他发现他是在以惩罚他对售货员姑娘的感情来弥补他对漂亮的电影拍片姑娘爱而不得的怯懦。他原以为现实领域的大门已经为他敞开,现在发现他们重新关闭,并且把他重新撞回原来的世界。
雅罗米尔走入国家安全局大楼,是他一生中最富于命运感的时刻。他看见了一道神秘的门槛,他一生都在企求跨越的门槛,那边是真正的生活。成熟的成年男人生活门槛的名字,不是爱情,而是责任。他告发了他的情人的兄弟。他终于完成了一个真正的行动,他一生所渴望的真正成年人所拥有的行动。
我们总是迷惑不解于艾吕雅与布拉格朋友绝交、海德格尔与纳粹涉嫌、周作人与汉奸为伍……这样的现象,空洞的道德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在人性的深处,在善与恶的畛域分野之前的原初,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从那隐秘的所在涌流出的“诗”,它并不仅仅是美好的,它还是危险的,它能够杀人,让血迹变成玫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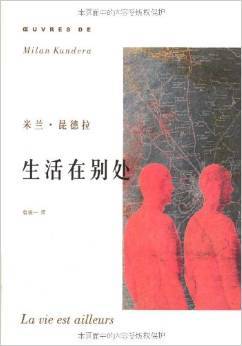
因此,我们该怎样反思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美学、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性?米兰·昆德拉诉诸我们的是,在一切神圣价值的后面潜藏着的往往是危险。这让我重新想起希腊那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人能够认清自己吗?几千年的文明史,战争的硝烟依然弥漫。“人啊,认识你自己!”是恨铁不成钢的神谕,还是悲天悯人的天启?多么神秘的语言,人类的命运尽在于此了。
幸福是人类对命运的自我许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在静默中等待。文学,这从人类生存的根基深处生长出的花朵,在时间之中依次开放;浇灌它们的是人的血和泪,诗因此而美丽妖娆。文学的热带丛林一步步掩盖着人类历史艰苦跋涉的足迹,足迹之下是掩埋祖先骸骨的土地,这唯一实在的东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