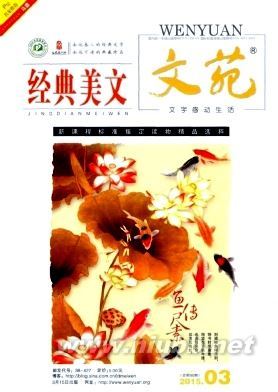第七个房间
寄萍每夜都会在于22点准时出现。她一身红衣,红唇,头发也染成耀眼的红。浑身上下的红,张扬着,欲点燃什么,也似要毁灭什么。她有百灵鸟一样的歌喉。可是酒吧里真正听歌的人,寥寥无几。这世界都在忙碌,除了我,蝶语心丝的电吉它手。无聊,只有在不能喝酒的时候,才会听她低声喃诵,爱情里的悲欢。
那是我永远也走不出的伤城。或许,也是她的。所以她的每一首歌,都和爱情有关。我每一次聆听,也都只和她有关。
下了场,寄萍隐在酒台的角落里,一杯接一杯,喝着醉生梦死。
缄默的青春,沉沦在醉生梦死的迷幻里。顾盼,忧郁,寂寞,微笑。仿佛,那是个禁地,谁都不肯向前迈出一步。终于有一天,她将手伸向同样醉生梦死的我。于是那夜我迈进她租住的小屋,一间只有十几坪米的阁楼。楼下士多店红色的灯光,映衬着她火红的衣裙,泛出冰冷的光。
第七个房间里,灯火昏黄,有股蘼颓的味道。
我杀过人,你信吗?红唇凑过来。
我也杀过人。嗤笑,喝干高脚杯里最后一口醉生梦死。
一年前,我杀死了自己。就在放手让她离开的那天。伤疤在腕间扭曲,提醒着某种不能遗忘的疼痛。我庆幸还有这样的疼痛。这样的疼痛,证明她恰在我生命里真切地出现。
你看,他还在那里。寄萍指着几上一只帆布背包。
我把他带来了。红唇再次凑近,眼里闪着魅惑的光。

我把她也带来了。我抚着胸,阵痛袭过,鬓角微微冒出冷汗。
哦。她歪过头看我。
我用刀子,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割开他的喉咙。长长的指甲从喉间划过,刀锋般尖利。
看,他现在多听话,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她转过身,拉开帆布包的拉链,赫然,一颗男子的头颅,正躺在里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