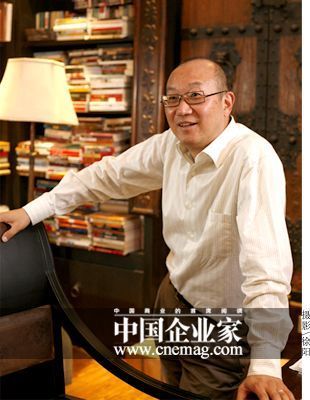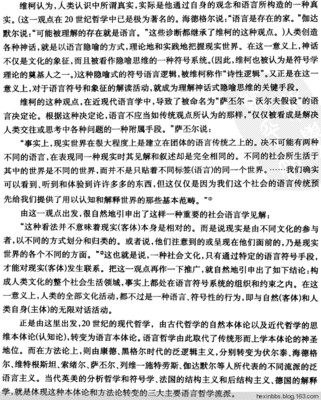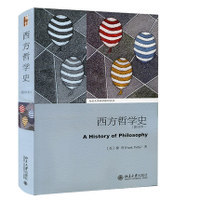冯俊
引自:http://eidos.bokee.com/4876441.html
(一)中国人探索西方哲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哲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起源于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碰撞,当时的“中国人的礼仪之争”,不仅体现了中西哲学的对立,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冲突。当“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发现夷之所长不仅是船坚炮利、科学技术,还包括支配它们的哲学、政治、法律思想。因而就出现了像严复这样的从学海军而转学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学者。梁启超等1898年的变法者们是引进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先驱。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引进西方的哲学,翻译介绍西方著名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原著。在1897—1907年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拉美特里、狄德罗、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斯宾塞、达尔文、约翰?密尔都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科学、民主、进化、自由和人权、社会契约等思想开始被国人所熟知。王国维等著名学者通过日本的文献对德国古典哲学家如康德、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哲学顶礼膜拜。
“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 “科学”和“民主”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约翰?杜威来华讲学15个月,走遍上海、北京和华北、华东、华中11省市,演讲了100多场,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兴趣,由于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的帮助,这些演讲同时编辑成书在中国出版,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紧随杜威之后的是贝特兰?罗素,1920年9月来到上海、南京、长沙和北京,宣讲了数理逻辑、哲学问题、心灵分析和社会建构理论等专题,特别是他对英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友善,使得他的哲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一时间在中国出现了“罗素研究会”、各种罗素哲学讲座和研讨会、出版了“罗素季刊”,张申府翻译了罗素的多篇著作并写了大量的文章来介绍罗素哲学的方法论和数理逻辑。1922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到上海、南京和杭州讲授他的新生命主义,《东方杂志》为他出版专号,许多研究其哲学的论文和专著随后问世。其实早在杜里舒来华讲学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1922年杜里舒来华讲学时,柏格森哲学的各个方面在中国都得到了介绍,许多学者对其都有比较深入地研究,例如,冯友兰就对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观有深刻地分析,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和佛教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
20世纪的30—40年代是西方哲学的大量引进和研究繁荣的时代,其主要原因是有一批到西方求学的学者回国。他们广泛地翻译了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并对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合会”、1935年“中国哲学学会”以及40年代“西方名著编译会”等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把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繁荣时期。
有一些留学回国学者中尔后成为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大师和著名的专家。例如,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有陈康和严群。陈康先后在英国和德国求学20年,研习希腊哲学,尤其是擅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国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他翻译和注释的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为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经典之作,他的格言是,我们中国人研究希腊哲学要做到使西方人研究希腊哲学以不懂中文为遗憾。严群是严复之孙,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求学,1930年代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希腊哲学,1940年代回国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他的《希腊思想》一书系统地探讨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古代自然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在德国古典哲学领域有张颐、贺麟和郑昕等。张颐1913就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研究康德、黑格尔,1919年以黑格尔的伦理学为题而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开设康德、黑格尔和西方哲学的讲座。贺麟是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大家,早年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哲学,接受了英国新黑格尔哲学家格林和美国哲学家刘易斯的影响。后转至德国学习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1931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后来翻译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贺麟除了他自己的“新心学”的哲学体系和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贡献外,还有两大贡献。一是在1940年代末成立了西方名著编译会,翻译介绍了一大批西方哲学的名著,商务印书馆后来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当时他们选定和翻译的;二是培养了一大批研究西方哲学的学生,他们成为新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坚力量,如王太庆、张世英、陈修斋、杨祖陶、钱广华、叶秀山、梁存秀、王树人、洪汉鼎都是他的学生。他研究西方哲学60年,视学问为生命。他的名言是:“你可以迫使我与我心爱的妻子离婚,但你绝不可能让我离开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界,人们常常将郑昕的名字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1927—1933年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学习,后来回国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十年,他的《康德学述》(1946年初)成为中国人研究康德哲学的传世之作。另外杨一之1931—1936年间也曾游学英德法诸国,回国后也先后任教于迁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讲授德国哲学、思想和文化,1956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康德和黑格尔哲学。
在法国哲学研究领域,庞景仁是一位代表人物,他于1936—1942年在巴黎大学求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巴黎大学和瑞士弗莱堡大学任教,1946年回国,1956年以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伽森狄的翻译和研究在中国具有开拓性,同时他对康德的翻译和介绍(如《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是有着广泛影响。
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的研究更是有几位不可忽视的大学者。他们是金岳霖、洪谦、熊伟。金岳霖于1914—1920年求学于美国的宾西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转到剑桥大学师从贝特兰?罗素学习逻辑学和逻辑经验主义,后又游学于法国和意大利。1925年回国,1926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解放后先后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哲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于40年代出版的《知识论》和《论道》以及后来出版的《逻辑学》都是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经典之作。洪谦在19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学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师从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石里克,是参加“维也纳学派”活动的唯一中国人,1934年以《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一文在石里克手下获得博士学位,40年代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新学院任教,1945年出版的《维也纳学派哲学》、1949年出版的《石里克和逻辑经验主义》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维也纳学派”的专著。1949年以后洪谦一直执教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熊伟1933—1936在德国德弗莱堡大学师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两位哲学大师,1937年转到波恩大学,1939年获博士学位,1939—1941年任柏林大学讲师。1941年后回国任教于中央大学和同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转至北京大学。可以说熊伟是中国最早研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第一人,特别是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和介绍是功不可没的。
到1950年代又有一批哲学学者从海外归来,例如,葛力先生从美国归来,王玖兴先生从瑞士归来,他们后来分别在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阶级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禁止讲授西方哲学,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作为被批判的案例。原先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教授和学者们都集中起来接受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培训,特别是听苏联专家亲自讲课。到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为了配合中苏论战和批判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国开始组织一批老学者翻译并内部出版“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资料”,因而中国人开始以某种隐蔽的形式又重新接触到西方哲学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出版了由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和朱伯昆共同编著的《哲学史简编》一书,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编写哲学史、同时又力图突破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同时,为了配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重要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对康德、黑格尔、谢林和费尔巴哈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著作、论文和译著相继问世。
十年“文革”,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又再一次被中断和停止,它们作为封资修的“毒草”被横扫和铲除,一大批从事西方哲学的学者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斗争中,毛主席号召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还要读几本哲学史。毛主席的号召被“四人帮”所利用,哲学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西方哲学虽然再一次被人们提起,但是西方哲学家和哲学学说被政治脸谱化和随意曲解,西方哲学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婢女。
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西方哲学的引进、介绍和研究和中国当时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西方哲学的引进、介绍和研究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料,西方的哲学理论是对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一种冲击,使国人开眼看世界,吸收到丰富多彩的精神养料,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理论铺垫;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帮助西方哲学研究跳出了为政治服务、做政治图解、简单化、脸谱化的“极左”窠臼,使科学客观地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成为了可能,从而给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创造了一个好的客观环境。
1978年在安徽芜湖市召开的“西方哲学研讨会”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空前的盛会,几代学者济济一堂,讨论如何拨乱反正,使西方哲学的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会议围绕着西方哲学史的性质、哲学史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西方哲学史的分期、哲学史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反对把哲学史看作是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以及仅仅以社会形态或阶级属性作为分期标准的简单化倾向。尔后的十年(1978—1988),西方哲学不仅是我国学术界的显学,而且也成为广大文化青年所追求的时尚。西方哲学的名著大量地翻译和介绍到国内,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学术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面向世界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杂志、《外国哲学资料》,三联书店的《现代外国哲学论集》和《现代外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都是西方哲学学者们发表专著、译著和学术论文的园地。在社会上,随着人文精神的复苏,一大批青年欣赏和追求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于是在他们中开始流行“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虽然他们很多是出于对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的哲学的误解或不太准确的理解,但是他们使本来是西方哲学的学者们研究的理论和学说成为了一种体现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的社会思潮。随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西方的科学哲学和英美的分析哲学也在学术界激起了很大的热情,江天骥、夏基松、舒炜光、邱仁宗等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涂纪亮先生对英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89—1999的十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从热情躁动转向冷静深沉,从80年代注意在政治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转向90年代更注意在学理上的穷经究理、探幽入微。90年代的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对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更加全面系统,补充了以往的许多重要缺憾,并且开始翻译重要哲学家的“全集”,如苗力田主编的十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家的“全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梁志学主编的四卷本的《费希特著作集》、孙周兴选编的两卷本的《海德格尔选集》也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第二,对重要的哲学家、重要的学术思潮和思想流派研究更加深入,产生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例如,汪子嵩、姚介厚、陈村富、范明生等人主编的《希腊哲学史》多卷本相继出版;赵敦华的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使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冯俊对笛卡尔哲学的研究、洪汉鼎对于斯宾诺莎的研究、傅有德对于贝克莱哲学的研究、周晓亮对于休谟的研究都填补了以往研究的许多空白;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杨祖陶、韩水法、陈嘉明、范进、张志伟、温纯如等人对康德的研究,张世英、王树人、宋祖良、邓晓芒、舒远招、赵林等对黑格尔的研究,使我国原来就重视的康德、黑格尔研究又有了更新的佳绩。
第三,西方的一些重要的哲学流派和思潮如现象学运动、诠释学流派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倪梁康、张庆熊、汪堂家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翻译和研究,陈嘉映、靳希平、孙周兴对海德格尔的翻译和研究,洪汉鼎对伽达默尔和诠释学的翻译和研究,都体现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杜小真、刘北成、冯俊、尚杰、莫伟民、汪堂家、佘碧平等人对于现代法国哲学的研究也成绩斐然,另外,在英美哲学方面,以往我们很少关注的心灵哲学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高新民的《现代西方心灵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第四,在我国西方哲学界实现了新老交替,一批外语好、学术功底深厚的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的培养下成长起来,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
第五,西方哲学开始实现了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贯通。由于历史和学缘的关系,在80年代,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仍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而到90年代,这种壁垒已经打破,很多大学里两个教研室也已经合并,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十分注重现代西方哲学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视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十分注重当代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学理背景。这就使历史上人为割断的西方哲学又重新恢复了本来的统一。
(二)世纪之交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和热点
应该说世纪之交或进入新世纪以来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最好时期,学术空气自由健康,学术讨论活跃频繁,理论研究深入,学术成果卓著,能够就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讨。我认为,这一时期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除了一些常规的学术问题有新的进展之外,还特别关注以下十个问题和热点。
1. 通过对eimi(be,原型动词),einai(to be,不定式),on(being,动名词,分词)和ontology 等词译法的讨论折射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关注。
eimi(be),einai(to be), on(being) (“是”、或“有”、“在”、“存在”)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形而上学的基本内涵、演变和扩展都是从这一概念出发的,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是形而上学的传统,因而它是西方哲学在不同的时代或各个时代的不同学派演化的基础性范畴,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各个流派演化的基础性范畴,在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同时代的哲学家赋予它们丰富和多方面的内涵。
西方哲学中eimi(be),einai(to be), on(being)这些概念如何翻译成中文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学人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界一般讲起译作“有”(最初起源于日本)或“存在”(见《逻辑学》和《小逻辑》的翻译和《反杜林论》的翻译)。40年代,陈康就对将eimi(be),einai(to be), on(being)译为“有”或“存在”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只有将其译为“是 ”才合其希腊文的原意。在90年代初,苗力田翻译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将以往中文译成“本质”的希腊文词组“to ti en einai” 翻译成“是其所是”,而与另一希腊文词组“to on hei on)即“作为存在的存在” 相对应。这一译法激起了王太庆和汪子嵩对以上几个词的译法的讨论,他们发表文章赞成陈康半个世纪前的意见,并认为可将动词原型和不定式eimi(be),einai(to be)译为“是”,将名词on(being)译作“是者”,从而以引发了近几年来的大讨论。从王树人、杨适、陈村富等资深学者到赵敦华、俞宣孟、王路、孙周兴、韩林合等中青年学者都著文加入到讨论中去。还有学者如韩东晖等翻译美国著名学者C. H. 卡恩(Kahn)对于“古希腊语中的动词‘be’”的研究成果[1],来为这一场争论做裁决。这场讨论的成果甚至还编辑成两卷本的文集《being和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宋继杰编)。 对于eimi(be),einai(to be), on(being) 和ontology等概念的翻译的讨论体现了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关注。
2.古希腊哲学开始升温。
随着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和王太庆翻译《柏拉图文集》的出版,以及前面讲到的对于西方哲学基础性的范畴being的讨论,对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升温。标志性的成果当然是汪子嵩等人的《希腊哲学史》多卷本的陆续出版,同时赵敦华在朱德生主编的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第一卷中、靳希平在《亚里士多德传》中对希腊哲学有专深的研究。可喜的是又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懂得希腊文的学者来研究希腊哲学,而突破了上个世纪50—70年代给一代学者所造成的局限。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不仅对希腊主要哲学家的研究和对being和ontology的讨论更加深入,而且对古希腊哲学的神话和宗教背景的研究、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灵魂问题的研究、希腊哲学中的价值观和伦理学的研究、晚期希腊哲学和早期基督教哲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
3. 对康德和维特根施坦哲学的研究加强。
借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的机缘,康德哲学的研究又产生了新的热潮。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被人们不断地翻译着,出现了多个版本,尤以杨祖陶和邓晓芒的“三大批判”译本影响最大;李秋零翻译的《康德全集》的头两卷也已经问世。20年前曾提到过的“离开黑格尔而回到康德”已经成为现实,人们似乎觉得有很多哲学问题在康德那里都可以找到答案,过去人们更多地是研究康德的认识论问题和伦理学的问题,而现在人们更加关注康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问题。
维特根施坦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被人们研究得最多的哲学家之一,在中国,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哲学研究》和《逻辑哲学论》分别都有四个版本。涂纪亮主持翻译的《维特根施坦全集》的出版对于中国哲学界加深维特根施坦的研究无疑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4. 实用主义研究的复兴。
实用主义的发展大约经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作前期或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后期或“新实用主义”。前期的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后期或“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而在80—90年代保持强劲势头的奎因、普特南、罗蒂和戴维森等人,很多人认为80—90年代是“实用主义复兴”的时代。
到80—90年代分析哲学在美国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新实用主义的出现既可以看作是对分析哲学的反叛,也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合流。实现实用主义发展这一重大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奎因,他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见《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断言:“一旦抛弃了这两个教条,就会打破思辨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就会转向实用主义”,并明确表示“赞成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普特南则是从科学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他本人对老实用主义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士、杜威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在复兴实用主义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罗蒂在他的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对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进行了批判,而转向实用主义,把杜威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戴维森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也被看作是实用主义的“新的形式”或“最高发展”。除以上几位主要代表外,还有像伯恩施坦等人的哲学也都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潮流。这一潮流的形成,一方面和分析哲学发展的困境有关,一方面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美国的流行有关,同时和哲学更加关注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世界潮流有关。
实用主义复兴的这种潮流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学者对新实用主义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如陈波对奎因的研究、陈亚军等对普特南的研究、牟博和江怡等对戴维森的翻译和研究都是很有成就的,国内研究罗蒂哲学的更是大有人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哲学界对于前期或传统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作过一些工作,可到80—90年代分析哲学大行其道,基本上很少有人再研究实用主义了。而随着对新实用主义的研究,学界又重新产生了对传统实用主义研究的兴趣,近几年来对于詹姆士和杜威的研究又出现了不少著作,例如尚新建研究詹姆士的专著。特别是刘放桐先生启动了翻译30多卷的实用主义的文丛的大工程,涂纪亮先生也组织了一批学者启动了美国实用主义的重大研究项目,这些都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界的大事。
5. 对现象学及其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勒维纳斯的研究成为显学。
现象学产生于20世纪初,它的标志是胡塞尔提出以“现象学”命名的哲学理论与方法的两卷本的著作《逻辑研究》在1900-1901年发表,至今恰好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的头30年中,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等人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现象学的重要著作,从而使现象学成为一股重要的哲学思潮,并且影响到各国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象学思潮在德国趋于沉寂而兴盛于法国,40—50年代,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关于一门现象学的本体论的论述》和勒维纳斯的一系列著作都标志着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复兴。此后,保罗-利科,米歇尔?亨利和当今非常活跃的马里翁(Marion)分别成为现象学在法国不同时期的代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展开和阐发。除此之外,德里达、福科、利奥塔和拉康、雷蒙-阿隆等各派哲学家的哲学都带有现象学的倾向。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法国引领了现象学的潮头。现象学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运动,它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影响不是个别性的、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世界性的,它代表着改变了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一种风格和一种精神,它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路径。所以,也有人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大转向,即“语言学的转向”和“现象学的转向”。

对于现象学的几位创始人的思想的研究在50—60年代就开始了,在80—90年代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现象学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勒维纳斯的研究成为显学,更加深入系统,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几乎都被翻译成中文,研究的专著也不断涌现。梅洛-庞蒂前些年不太引人关注,而近来他的《知觉现象学》、《符号》、《哲学赞辞》、《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等书纷纷出版,研究著作连篇累牍;数年前,勒维纳斯还不太为学生们所知晓,而今以勒维纳斯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人也大有人在。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专门成立现象学分会,召开经常性的学术年会;出版有专门性的学术期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建立了“现象学文库”,搜集了国内最全的研究现象学的资料;学者们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际现象学学会的领袖人物克劳斯?赫尔德(Klauss Held)教授是中国现象学研究者家中的常客。在国内产生了一批研究现象学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如倪梁康、张庆熊、靳希平、张祥龙、陈嘉映,杜小真、孙周兴、彭富春等,我国今天研究现象学的鼎盛状况可以和70—80年代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状况相比。
6. 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是新时期的热点。
后现代主义哲学于90年代初传到中国后就引起了哲学界的极大的关注,而随着一些主要哲学家的著作的中文译本越来越多,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成为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笔者检索了970余篇国内研究西方哲学的论文,其中以“后现代”为题的有70篇,在文中提到“后现代”的有275篇,这些数字足可以看出“后现代”之热。目前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有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学行动》、《多义的回忆》、《马克思的幽灵》纷纷出版;几乎福柯的主要著作都翻译成汉语,如《临床医学的诞生》、《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词与物》、《性经验史》以及在法国也是刚出版不久的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系列《不正常的人》和《必须保卫社会》等。利奥塔的《后现代的状况》有几个译本,《非人》和《后现代道德》也已出版。德勒兹的《解读尼采》、《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和《哲学与权力的谈判》,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物体系》、《完美的罪行》等都接二连三地被翻译出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哲学流派的主要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如此成规模成系统地翻译出版,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即使我国哲学界研究得最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原著翻译,都没有如此全面和如此成规模,而这样大量的工作并不是通过组织推动,完全是学者个人兴趣的驱使。德里达2001年来华巡回演讲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他关于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的谈话在哲学界引起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广泛讨论,使得德里达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间,而是整个中国哲学界,《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主编)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影响。
除了对后现代主义主要哲学家的主要著作的翻译介绍外,对他们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已经脱离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简单的介绍阶段,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例如,对福柯的研究继90年代末刘北成的《福柯思想肖像》、莫伟民的《主体的命运》之后,又新出了汪民安的《福柯的界线》。仰海峰、孔明安研究波德里亚的论文也有较大影响。对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有冯俊等中外学者合著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一书。
除对法国的几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翻译和研究外,对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逊的翻译和研究也有新的进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四卷本的《詹姆逊文集》,并且詹姆逊本人也亲自来参加了新书的首发式和发表演讲,在中国再次掀起后现代的热潮。
7. 政治哲学的众多流派及其相互论争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
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越来越引起了学界的兴趣,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80—90年代在西方政治哲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英美哲学,从分析哲学的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而更加关注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问题;另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学界也有对更深入的政治改革的期盼和对政治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的渴求。
在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界研究得最多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流派和论争主要有以下4个:
(1)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中国出版已近20年,他本人也于2002年11月去世,但他仍然是被人们研究得最多的人之一,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的《正义新论》也在中国出版发行,通常人们喜欢将他和另一位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进行比较研究,将他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他们在自由、正义、平等等问题上的差异进行比较,也有人将罗尔斯本人的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作为新自由主义哲学的对立面的社群主义如麦金泰尔,桑德尔,查尔斯?泰勒等人的哲学是近几年翻译介绍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桑德尔和查尔斯?泰勒的哲学前几年在国内研究的人不多,但近几年韩震等人对他们开展了研究和介绍,国内以查尔斯?泰勒为题写博士论文的人也在逐年增多。
(2)对伯林和哈耶克的研究。谈到对自由问题的研究,人们就自动地想到另两位对自由有着深入研究的哲学家,一位是伊赛亚?伯林,一位是哈耶克,他们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门人物,特别是在伯林去世前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和纪念论文,他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以及对消极自由的青睐,他所倡导的价值多元论,在美国“9.11”之后世界呼唤文明的对话和文化多元性的时代更显示出它们的重大理论意义。继80—90年代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如《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89),《自由秩序原理》(1997),《通向奴役之路》(1997)被翻译成汉语之后,《致命的自负》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又同时于2000年在中国问世,除了邓正来等资深学者对哈耶克有专深的研究外,近几年来哈耶克成为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热门题目。
(3)对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及其学派的的研究。随着小布什在美国上台执政,近3-4年来,代表着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也成为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有人将施特劳斯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几年来,以刘小枫和甘阳两人为代表对施特劳斯的翻译和研究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施特劳斯的小小的热潮,刘小枫选编的《施特劳斯和古典政治哲学》,甘阳主编的施特劳斯文集《自然权利与历史》两本书都在2003年出版,刘小枫的研究施特劳斯的系列文章,和他对施密特的翻译和研究引发了许多学者对施特劳斯的研究兴趣,施特劳斯的其他几本著作也正在翻译和编印之中[2]。
(4)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也是学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哈贝马斯就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等人的论战,对启蒙精神和现代性的辩护在中国可以找到大量的支持者。他的社会交往理论,仍然是人们广泛研究的一个课题,他的社会真理观、民主观、他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哈贝马斯于2001年4月来中国讲学,在中国唤起了研究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热情。我们认为,除后现代主义者如福科等人的政治哲学外,哈贝马斯的社会政治哲学成为当今欧洲大陆社会政治哲学的代表。
8. 全球伦理、生命伦理和环境伦理引起广泛关注。
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世界伦理(world ethics)与普世伦理(universal ethics, 又译作普适伦理)是在使用和解释上有些差异、但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类似概念。他们起源于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所达成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关于“全球伦理”的定义是:“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行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3]。在经济日益全球化,政治走向多极化和文化力图保持多元化的时代,对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要求已经成一种客观需要;而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如果看作是文明的冲突的表现的话,文明的对话和建立统一的行为规范或道义准则也成为全世界的共同的呼声。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伦理和普世伦理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门。而作为全球伦理的倡导者之一的德国著名学者孔汉斯(Hans K?ng)在世纪之交多次来到中国参加和主办有关全球伦理的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演讲。国内的宗教学和伦理学的学者如何光沪、万俊人等人对全球伦理也有专门的研究。
因为克隆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生命伦理学又再一次成为学术关照的焦点, 许多新的伦理问题又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我们去解答、去回应。例如,克隆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生育模式和生育观念,它是否会引起伦理观念的混乱? 如果克隆人体用于医学目的如提供器官移植,那么,人就成为服务于他人的工具或手段,这不是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道德律令相违背了吗?如果生命也像商品一样可以成批地生产,那么人还会是独立的精神主体、行为主体和道德主体吗?另外,如果允许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克隆人体,是否会为希特勒式“优等民族的优生理论”的复活而破坏人类各民族和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平等呢?如果说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体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话,假设他们都要克隆自己的话,又有谁来决定谁可以被克隆?克隆的标准是什么呢?克隆是否剥夺了个体的选择权和人权呢?克隆是否减少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适应性,导致了人类遗传新的退化、而最终对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呢?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将应用于基因诊断和致病遗传基因的检测,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如果可以获得病人的所有的基因信息,那么谁(医生、病人本人、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可以了解这些信息?隐私权如何保护呢?如果诊断出了遗传疾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平等地或有同样的机会被予以治疗呢?有谁能决定人类最佳基因选择、基因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如何体现呢?这些问题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引起了重视,而且也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不伤害生命,尊重人的生命权、自主权、知情权、隐私权,确立起平等和公正的原则,这是中外生命伦理学界所形成的共识。
中国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和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在环境伦理学中有许多流派如人类中心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力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各种学说,但是核心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解决自然到底有没有价值和权力问题。
反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主张,自然物也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应该把道德关怀领域扩展到自然界。地球是人和其他生物共有的资源和生存环境,生态系统不以任何物种为中心,对大自然的保护不应该建立在关于自然的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丢掉动物弱肉强食的规则,而代之以用伦理的规则来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把大自然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之内。物种和生态系统有依据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它们的这种内在价值和权利是它们获得伦理关怀的依据。他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作是唯一的主体、是自然界的主人,鼓励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无限制的开发。人类中心主义是物种自我保存的生物本能的体现,这是把人降低到一般生物水平,同时,也是一种放大了的利己主义。人类相信依据自己的理性能力就可以认识和把握生态的规律、正确地判断各种利益关系、从而有预见性地解决好环境问题,那是对人类理性的过高估计和盲目乐观。
人类中心主义者们认为,人是宇宙中的唯一目的物,自然物没有价值观念、没有权利意识,自然也不是权力的拥有者,自然物只有在它们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上才存在价值判断,它本身不能成为权利主体和道德主体。道德是调节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不能构成伦理关系。人类可以从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利益的理性判断出发解决好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保护好大自然。破坏环境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集团利己主义。
因此,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界也存在着三派观点:(1)反对人类中心主义;(2)坚持人类中心主义;(3)“超越和整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前任主席罗尔斯顿,现任主席詹密森(Dale Jamieson)都和中国环境伦理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2004年10月召开了中国首届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实践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将会是形成中国自己的环境伦理学派的前提条件。
9. 女性主义哲学兴起。
在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了女权运动,但是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到90年代才开始传播到中国,主要是一些留学西方的女性将其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目前国内的妇女研究或妇女学研究的非常深入和火爆,如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男女平等、妇女就业、家庭暴力等都是热门话题,但这些都不是本文所要考察的范围,在这里要考察的是西方的女性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来后我们做了哪些研究或研究了哪些问题。目前,我国哲学界对女性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1)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和社会建构论的研究,社会性别是指妇女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条件下形成的社会角色和特性;社会建构论反对本质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有本质区别的主张),反对和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和性倾向(sex disposition)三者的固定联系,认为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出来或社会的权力运作而产生的。
(2)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认为传统的认识论是一种男性的认识论,把男性的认识方式或认识规律看作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试图发现一种女性特有的认识方式或思维方式,或探讨女性认识世界的独有的视角。
(3)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女性主义一方面求助于现代性,要高举启蒙、解放、平等的大旗;另一方面又主张差异、去(非)中心,极力吸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许多话语和观念,这种复杂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探讨。
(4)对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或代表性理论的专门研究。例如,国内对法国的“女性主义三剑客”即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露茜?伊里格瑞和埃莱娜?西克苏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朱迪斯?巴特勒、塞拉?本哈比的研究近几年来也已经开始。肖巍对女性关怀伦理学的研究也有专著问世。除以上对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的四点研究外,目前中国的女性研究学者们对于女性主义的本土化也很感兴趣,认为中国妇女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生存状况都和西方妇女不一样,女性主义的“洋理论”不服中国水土,力图建构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理论。
10.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西学东渐史研究已经成为一批资深学者新的转向。
在中国进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原来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见到原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西方哲学或比较哲学。原因之一恐怕是对外语的掌握决非易事,西方哲学的功底不好补;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西方哲学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发产生了一种“文化寻根”的情节和对自己学术立场的考问。近几年,国内几位研究西方哲学的资深学者如张世英、叶秀山、王树人、杨适转向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或完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王树人提出西方哲学的特点是逻辑思维、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象思维”;叶秀山原本就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对于中国的戏剧、书法和古代美学的兴趣一直与他对古希腊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兴趣并存。杨适研究“原创文化”,主要还是研究东西两种不同的原创文化。叶秀山和王树人共同主编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第一卷就是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来撰写的。在中青年学者中进行中西比较的有张祥龙和张汝伦,张祥龙继《海德格尔思想和中国天道》之后,又新近出版了《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特别是他“建立传统文化特区”的提议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张汝伦近几年发表的主要作品都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其他一些中青年学者如赵敦华、张志伟也偶尔发表一些中西比较哲学的论文。
此外,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也备受关注,早在90年代黄见德等人就写过《西方哲学东渐史》和《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而汤一介主编的计划出14本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研究丛书近一两年陆续出版。同时,世纪之交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历史地回顾,近几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如“论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黄见德)、“现代外国哲学在中国”(倪梁康、江怡、陈学明、顾肃、贾泽林等)、“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陈应年)、“20世纪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杨河)、“20世纪中国的费尔巴哈研究”(李毓章)等等都是对中国学人艰难探索历程的回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