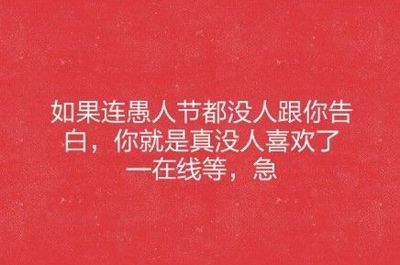今天清明节,我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已逝去的父母和岳父。
上午,我和太太把一大堆照片簿找出来,边查阅其中与父母、岳父有关的部分,边回顾前尘,缅怀最挚爱的亲人。
母亲早年留下的照片不多,只有一二十张。那时,照相是很奢侈的事,一般百姓很少消受得起。我考上人大新闻系后,学会了照相,有一年回家,就和妈妈一起到长风公园玩,照了几张。还有一张,是弟弟給她和远道去上海的姨妈照的,姐儿俩正坐在桌前说话。后来,照得稍微多了些,有几张是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孙女站在门前晒太阳。那年,我曾把女儿送到上海呆了半年,后来母亲得了胃出血,我就又接回身边。母亲六十大寿那次,照了一卷,占了一本大相册里的好几页。那是1975年,我和太太、姐姐和姐夫专门从外地赶回上海,和弟弟一家为老人祝寿。有一张是,我们围坐在餐桌旁,母亲站着吹灭生日蛋糕的蜡烛。那天,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的隐花短袖衬衫,花白的头发还很浓密。她笑得是那么开心,旁边的我们也很开心。
有一本相册是1998年的,我们在图们姐姐家为父亲过八十大寿。那次,我和女儿从北京、弟弟弟妹和侄子从上海赶去东北。这次照片是侄子拍的,拍了好多,除了寿宴,还有许多合影,子女辈和父亲合,孙辈和爷爷合,每一家单独和父亲合。不用说,照片充溢着浓浓的亲情,老人的嘴都没合上过。
父亲母亲都是普通百姓,一生平凡琐碎,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们为人都极正直厚道,做事都极规矩认真,对子女的身教重于言教。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东西,至今仍在受用。
一辈子当记者的岳父,曾为国家为人民做过贡献。他存留的照片很多,没办法都看,就挑了前年为他和岳母写传记的那些插图,浏览了一过。
我关注的重点,其实是他们去世后向遗体告别及举行葬仪的图片。
母亲是1991年秋在家里去世的,享年76岁。弟弟为她拍了几张遗照,那面容就像熟睡一般,非常安详,也非常饱满,这让我感到奇怪。母亲罹患肺癌后,一年之中,我回沪四次。每一次看上去都更瘦一些。最后一次,是我和弟弟把她从医院接回家的。医生对我们说,没办法治了,回去设个家庭病床吧。母亲也坚决要求回家,不得已,我们只好回到狭窄而简陋的家中。那时,她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白天黑夜都无法躺着入睡,一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我到商店里买了一把沙滩椅,架在她的床上,心想这样她可以趴在椅子上休息,可以减轻一些痛苦,又不会压到腿。她顽强地坚持了两个月,还是走了。

母亲的遗体告别,是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我写了两句话,“每思高堂悲白发,寸草难报三春晖”挂在大厅里。姐夫主持仪式,我致悼词时,几度呜咽,讲不下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除了亲属,还有街道的众多邻居和她的教友。照片忠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母亲静静地躺在罩着玻璃罩的灵床上,接受了亲友的告别。由于等东北的姐姐一家来沪见最后一面,母亲在太平间等了几天,面容已大改。我重见到自己走了形的哭态,也看见伤了脚踝的外甥架着拐,围着灵床大恸,不禁又一次流下泪水。
母亲生前选择把骨灰撒到吴淞口,我们照办了。父亲2003年去世没有留下遗嘱,我们子女商量后,决定让父亲去找母亲。我看了两次送灵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游船的船尾举行告别仪式,都是用红绸布裹住骨灰盒,都是带有余香的玫瑰花瓣伴着细白的骨殖,都是我们一抔一抔地把它们抛洒到滚滚的江水中,然后看着骨灰盒载浮载沉飘向远方……
岳父和父亲同一年去世,相隔整整百天。那时候,北京正闹非典。人民日报不建议同事亲友搞告别仪式,但去八宝山送别的人还是很多。除了人民日报的同事、学生,还有不少前身是大公报的经济日报老友。我和朋友赶制了一份纪念折页,彩印,精装,上面有黄苗子、郁风、谢蔚明、邵燕祥、丁聪、方成、舒展等人送的挽联、挽诗、漫画像,还有他各个时期的工作照、生活照。我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散文,由岳母题签。还作了一副挽联,印在纪念折页的封底。挽联是:
重庆试声南京喋血莱蒙频发檄文万里烽烟堪追忆;
弱冠反蒋壮岁崇毛晚年独尊民主一生轨迹耐寻思。
照相簿的现场照片中,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这个册页,认真翻阅。记得事后,一些前辈曾给岳母来信,夸这个纪念册页做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所以,在这个清明节,我的最后一个祭祀节目,是又看了一遍这个册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