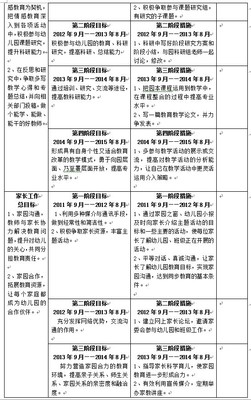在书的第五章,他给我找了个女朋友,一个披着金黄波浪卷发,穿着宽松灰格子衬衫和紧身长裤,在某个星期天下午到市中心图书馆无聊闲逛的女生。
相遇时的场景我不太喜欢,我刚从美国文学的书架上取下那本约翰·李博士写的《马尔科维奇传》,就在转身之际,便看到一摞子的书“啪啪”几声从她的怀里掉落到地上,《古埠街》、《风华正茂的时代》、《旋转阶梯》、还有一本薄薄的《懒人食谱》。伴随着她那一声短促的惊叫,整座图书馆似乎都跟着晃动起来了。
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他总对这类有些神经质又爱赶时髦的文艺女青年情有独钟,并且花如此多的精力和语言去刻画她的语言姿态。但紧接着,他便让我把脚边的《古埠街》捡起,然后我得露出了那一如既往稍显得僵硬的微笑,把书交给那女孩:“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不是我吓着你了?”
然而,话一说出口,吓到的不是她反倒是我了,我从未预想过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意思是,在那有限几章的回忆中,我从未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一个陌生女孩站在我面前,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以一个疑问句开头,话语还带着点有意为之的轻松的语调,让我主动与之搭讪。这种情绪的骤变让我顿感措手不及,当初我还以为,在书的第五章还未动笔之前,我存在的使命就快要结束了呢,要么逃离,要么自杀,那样的结局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了,任何有可能看到这部小说手稿的人都可以在书的第三第四章的字里行间嗅到那股浓浓的抑郁的气息——那些无休止而又毫无意义的自我唾弃,那种无望而又枯燥的工作生活,铁一般的纪律,漫长而又吵杂的无眠之夜——没有的感人肺腑的定语长句,没有渲染生活的流光溢彩,文本里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像是死一般地凝滞,我想,任何小说人物都渴望逃离这种宿命吧。
与一个女人在图书馆里不期而遇,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叙述基调,让我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我几乎看到了更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后头等着我。当然,你也应该晓得,我所有的存在都掌控在他一人手里,在船还没下水之前,每一块甲板都有可能被换掉,那句随口而出的俏皮话,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被他用作一个引子——在他往后的精心设计的布局中——把某种可能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分裂人格给慢慢勾引出来——最终把我引入一个更加难以想象的自我折磨的悲剧漩涡中?这种事,他不是没干过,在书的第二章里,他就让我变成了一个赌徒,在我明知道我家里的小妹妹急需一笔学费去上学,他却还让我与舍友通宵达旦去赌博,最终结果,你知道的,当然是我把钱输了个精光,在随后的那半个月里,那种无处不在的罪恶感与锥心刺痛的自我唾弃,几乎把我整个人给纠缠崩溃了。要是他要继续那么玩,当然我也是完全地无可奈何的。现在,他每停顿一下,我是既感到急不可耐,又惶恐不安。
“没有。”她说,也对我笑了笑。
“哦,你的《古埠街》。”
“谢谢。”她瞥见了我夹在胳膊里的《马尔科维奇传》,“你手中的那本书,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
接下来又该轮到我说些什么了,我张开了口,一个““”已经来到了我的嘴边。但不知道怎么地,我的这一句话他竟酝酿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又完全摸不着头脑,只能张开了嘴巴心急如焚地在这完全静止的空白中默默地等待着,而女孩子呢(他还没有给我她的名字呢)似乎也迫切地想要知道我会对她说些什么。
感觉这就有点像那些突然暂停的电影了,男主角越过马路中央的栏杆去追捕一个抢包的劫匪,就在男主角手撑着栏杆身体越过的那一刹那,画面突然停止了。对于一个逃命的劫匪来说,没有什么比脚步突然被截停更糟糕的了,但我想,如果劫匪聪明一点的话,他知道电影画面里的时空也是等距静止的,那么他大体可以在那短暂的静止里保持着逃命的姿态私底下好好地喘上一口气,等那个看电影的观众拉尿回来按下播放键后再接着逃命。然而,像我这种情况,生存在一个文本里,境况可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一个标点、一句话可以引申出无限的可能性,作者完全可以把我们玩弄于鼓掌之中,所以,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接下来我可以说出那么一句话,比如“那你.......”嗯,这我就不说了,事实最后总会证明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白忙活,变化得太快了,一句话还没说完整,过了两秒即被删去,然后又重新组织排列,然后又删去,又重新组织排列......没玩没了,十分恼人。说实在话,我都开始有点羡慕那些电视框框里的人物了,比如我之前说的那个劫匪,无论他怎么玩命跑,最后都会指向一个明确终点——他要么被捉住要么不被抓住,在等距的电影时空中,所有的结果早就被确定了,在预设好的情境中,他尽管跑就行了。
“是吗?”他写道,这下我如释重负了,“那你觉得书写得怎么样?好看吗?”我又露出那抹轻松的笑容。
“这个......我不太记得里面写的是什么了。”那女孩子抓了抓后脑勺,她倒也不太介意我停顿了那么久。
但紧接着,他又停顿下来了。
这下我们又重新变回两具虚无的雕像。一个图书馆,两排书架,其中一排是美国文学书架,地上还散落着一些书,也就是说那里还有一块平整的地面,是的,就你所知,我们生存的空间也就这些了。
对此,我也无可奈何。我开始有点担心,会不会又像之前一样上面的对话再一次地被他无情删去,然后再进行没玩了没了的重新解构、拆散与重组。
“我倒看过约翰·李博士的另一本书,叫《撒旦之后》,(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看过,至少在前几章中,我听都没听过这本书,如果我确实有看过的话,那么我记忆并不是来源于过去,而是在未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里面大概讲的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书写的就是这个画家的故事。”我又可以开始说话了。
不过,很快他就把这整段话给完完整整地给删去了。
这回变成:“是吗?这本书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看的,(谁呢?我也说不出个名字来,如果有的话,可能以后他会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不过我听他说挺好看的。”
但还没等那女孩子开口,他又把整段话给删去了。
不断地前进,又不断地被拉回到原点。
就上面这段话,我得换两种不同的语气去诉说,一种轻松快意,一种沉静冷淡,但哪一种语气更像我?我也说不清楚,或者说说出这两套语言的都是同一个我,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消失而又不断重现。
我们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没有半点笔墨滴落下来。我们还得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继续站着。我对面的女孩子,我想,没有所谓的回忆的包袱,脑袋就像纸页一样的空白,要应付这样的等待,对于她来说,那最轻松不过了,不像我,我还得在这里担惊受怕,我总怕他会把我整个人变得让人不可捉摸,前后脱节,而破碎不堪。
因为他写的是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所以大概你也知道了,午后的阳光总是从书馆墙上的玻璃窗呈45度角斜射进来,书架投射在地上的阴影大小不变,虽然他没说这星期天下午的阳光呈现出怎样的一种质地,但我想,那大概和昨天的也别无二致。许多年以来,我总喜欢一个人在周末天晴的午后进行一段长距离的散步,线路也总是固定不变,从万花路口出发,经过滨江走廊,在走廊上的长条椅子上稍停一会儿,拐进江滨公园,穿过万花路下面那段幽暗狭小的地下隧道,最后折返回到那间小小的出租屋。春天,万物苏醒,百花争艳,午后公园草地上的情景让人印象深刻,那繁茂的像火一般的紫荆花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公园干道的两旁,孩子们开始在小土丘上放风筝,女人们则把外套都脱去了只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在空旷的平地上打羽毛球。要不是因为被我眼前的这个女人耽搁,我想,过会儿我又得出发了,也许说不定我将在滨江走廊上碰到另一个人,一个老头坐在长条椅子上无所事事地看着白肚皮的鸟儿从江岸的这边飞到江岸的另一边,我们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天气,回去我还可能以那个老头的形象写一首诗。
不过,现在情况变得有点复杂了,我们完全停滞了下来,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在一个凝固了的时间的点上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等待。如果说有什么能让我感知到外面的时间正在飞速的话,那就是我开始感觉到我的记忆变得模糊。因为所有的小说手稿他都是用铅笔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铅字会在层层叠叠的纸张的挤压之下从前一页的纸张里慢慢剥落下来,然后印染到下一页的文字中,也就是说,当我回忆起某一件发生在昨日早上的事时,伴随着前天留下了灰色模糊的阴影,如同层层叠叠的梦境一般,它们纵横交错一同显现在我的脑中,有时我一时也分不清楚哪些是昨日的记忆哪些又是往日的记忆,当它们越积越多,最终变成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于是,我大概知道了,我们被丢弃了,被丢弃在虚无的荒原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思想,没有回忆,也没有时间,等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