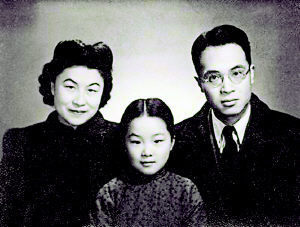“文章憎命达”意谓有文才的人总是薄命遭忌。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痛。
“文章憎命达”之句,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此诗以凉风起兴,对景相思,设想李白于深秋时节在流放途中,从长江经过洞庭湖一带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李白深切的牵挂、怀念和同情,并为他的悲惨遭遇愤慨不平。
徐凝《和夜题玉泉寺》说: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娱之词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这似乎也是文章憎命达的佐证。
欧阳修言“诗穷而后工”,厨川百村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
“憎命达”之“憎”乃指“天憎”。从“天”(历史)的角度看,文章不关照“命达”者,毋宁说“天”总是把大师、文豪桂冠赏赐给那些命运乖舛的人,而被赏赐者并不一定能够在有生之年领取奖赏。“人”与“作品”形成残酷的二律背反,面对这一吊诡,文学家很难抗拒,一般只能等待命运安排。
之所以自古哀怨起骚人,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普遍有两种生存本能:一种是“穷则独善以垂文”,另一种是“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为文,达则作官;与“应景文章”对应的是千古文章,之所以说文章憎命达,就是因为命达必写出“应景文章”来。
历史上,作家的求真与先觉,都会受到诽谤、侮辱、打击、压制、迫害、摧残,他们处于贫病交困的境地,不得“平”而鸣,因“激”以致高远。
翻开史籍,那些千古传唱的锦绣文章,几乎都是在那些文人骚客失魂落魄的贫穷时期写就的,而一但飞黄腾达却又写不出好文章了。
历史上的王阳明、韩昌黎、屈原、司马迁、李后主,如果不遭贬逐、不受刑罚、不穷困、不失国、高官厚禄,既富且贵,能留下这许多传世之作吗?
李白在长安郁郁寡欢,索性漂泊四海,后来又搅进了安史之乱的战争,但是也正是如此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一代诗仙的风骨。
司马迁被鲁迅先生高度赞扬称其所做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作为男人被处以宫刑,是多么大的耻辱和打击,如果是换成我等之流,估计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可是司马迁却妙笔生花般完成了《史记》的鸿篇巨制。

我们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作者也都是坎坷沧桑走过一生的。吴承恩是才华横溢,无奈命运不济官运不通,就借题发挥用孙悟空的形象来表达作者对世界的反叛之心。而施耐庵和罗贯中这对师徒,都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战争时代,因此他们的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是以战争为主要表现场景展开的,这也是他们生活经历的某些映射。至于《红楼梦》这部在文学艺术上登峰造极的小说,几乎完全是在描写曹雪芹家族自身没落的故事,书中的细节和大的结构框架和他们曹家从富贵走向衰败的史实如出一辙,而曹雪芹也是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撒手人世的。
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心态、晦涩阴暗的笔锋,都与他不幸的婚姻不无关系。如果他一直高官坐定,娇妻美妾拥身,他还能写出那些愤世嫉俗的文章吗?
张贤亮后来做了企业家,日进斗金,他再也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了。别管他如何辩解,其实已经江郎才尽了。
纵观古今,其实不光“文章憎命达!”但凡是能够轰轰烈烈的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豪杰,皆是命运曲折坎坷,因为越是悲惨,才越激励人,正如先知所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不英雄!”
窃以为,如果老天赋予某位文学家才华,他就应该尽力攀登高峰,以不废其才,让生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能量,使逝去的生命化为文学苍穹中一颗耀眼的恒星。溺于俗流,岂不可惜。俗流给予人的,不过是溢美的虚名而已,唇舌流芳,能有几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