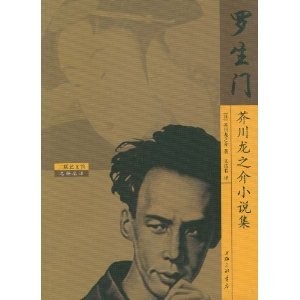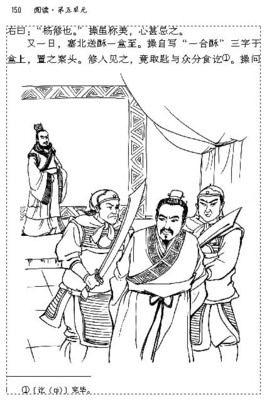【陈独秀之死】(小说连载11)
【第十一章】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对派”的事业中去。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他费尽心机,最终促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
(四十八)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时隔一个月,十二月十五,陈独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托派组织,树起了反对派的旗帜。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被推选为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会议还决定出版刊物《内部生活》,因不久该刊改名为《无产者》,所以中共党史上将这一组织称之为“无产者社”或“无产者派”。
彭述之很满意“无产者社”的领导班子结构,他对陈独秀说:“我们这班常委是清一色的‘老干部’、‘元老派’,你原来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当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任资深则当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秘书长,我们这个班子完全有资格与现在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陈独秀点点头道:“资格是次要的,关键是路线对头,我们坚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们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真理在我们手中。”
陈独秀原本是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的,而是准备加入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
早在一九二九八月间,陈独秀和“我们的话派”进行过一次谈判。但是,“我们的话派”的主要领导成员梁干乔自持是中国托派的“开山鼻祖”和惟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他以水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看待陈独秀,深怕陈独秀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地位,因此不但不欢迎,反而很厌恶,借口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向我们托派投降了”,主张不予理睬。“我们的话派”中的区芳、史唐、张师则认为,陈独秀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是托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分别而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
陈独秀一口答应了这个条件,但是彭述之、尹宽却坚决反对。彭述之认为,“‘我们的话派’成员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的领导”。尹宽提出,“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应该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彭述之、尹宽的条件梁干乔等人自然也不同意,于是,陈独秀和“我们的话派”的第一次谈判就这样流产了。
恰在这时,在苏联已秘密加入托派组织的刘仁静、王文元、吴季严回到国内。
王文元、吴季严回国时还没有暴露托派身份,于是被分配到中组部和中宣部任干事,而刘仁静则公开向中央表明托派观点,然后就宣布脱党,自由活动去了。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生于一九0二年,一九一八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即而又转往英语系。受陈独秀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与,为当日爬入曹汝霖住宅,打开曹府,痛殴章宗祥的5人成员之一。他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早的参加者,又是中共“一大”代表,一度还是团中央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人送外号“小马克思”,在中共党内曾经也算是个显赫人物。刘仁静这次回国途中,曾绕道土耳其拜见过托洛茨基。因此,除了梁干乔外,他成了中国托派中受到过托洛茨基接见的第二个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将亲自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交给刘仁静,让他带回中国,并亲自给他起了个“列尔士”的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因此,回国后他便以“老托代表”自居,自报奋勇地调解起“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之间的矛盾。
刘仁静回国后首先拜会了陈独秀,介绍了托洛茨基的近况。陈独秀和刘仁静虽然多年未见,但毕竟过去是老战友、老朋友,现在又多了托洛茨基的共同语言,所以两人谈得甚是投机。言谈之中,刘仁静慢慢说明了来意,陈独秀当即表示,只要“我们的话派”同意和“陈独秀派”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他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错误,接受托派理论和策略。
于是,几天后,在刘仁静的牵线搭桥下,两派代表在尹宽家再次举行了会谈。
尹宽家坐落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房里,四周僻静,十分安全。那天到会的“陈独秀派”代表是陈独秀、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唐、宋逢春,刘仁静做为调解人列席会议。
史唐是浙江诸暨人,曾是上海中共中央的机要秘书。宋逢春则是河北景县人,出国前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工作,他们都是因参加莫斯科红场上的反斯大林游行而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的。论起来,大革命时都是陈独秀的部下,因此,见到陈独秀倒也十分恭敬。
互相寒喧一阵之后,宋逢春问道:“总书记,大革命失败时,我们正在苏联学习,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陈独秀连连摇头说:“惭愧,惭愧,都是听了老毛子的话。唉,老毛子懂什么,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国情。”
刘仁静说:“仲老,你别小看这些在苏联学习的年青人,虽然没有经受过国内大革命考验,但回国后他们意志十分坚强,在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仍然坚持干革命,没有一个退缩的。”
陈独秀十分感慨,道:“你们这帮青年人很有革命朝气,能吃苦,中国的未来要靠你们。”
史唐、宋逢春顿时受宠若惊:“总书记过奖了,和你们这些老前辈相比,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陈独秀道:“我们这些老家伙的优势是斗争经验丰富,再加上你们年青人的热情奔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刘仁静接过话头道:“其实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论策略,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在当前中国革命形势下,双方唯有求大同,存小异,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就,大家以为如何?”
陈独秀当即表示:“我同意养初的意见。但对于合并,我有两点要求,一是请你们提供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以便大家共同讨论问题;二是我们要集体加入组织。”
宋逢春道:“我个人完全同意总书记的这两条要求,但最后结果还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才能作出正式答复。”
这次谈判陈独秀感到十分满意,不像上次那样,进退两难,总算有了初步结果。
但陈独秀万万没想到,当史唐和宋逢春向“总干”汇报谈判成果时,双方达成的协议不仅被梁干乔一口拒绝,宋逢春还因擅自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联合的意见,被指责是“投降主义”,反而被“总干”开除了。
一九二九年九月,“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刘仁静的再次努力之下,史唐、区芳主持大会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
刘仁静感到这“三个条件”太过苛刻,陈独秀恐怕难以接受,便提出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改组“总干”,以扫除阻挠陈独秀、彭述之加入托派组织的障碍。他对梁干乔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可以说完全是为了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陈独秀是大旗不能丢,有了陈独秀,中国的托派组织才有希望发展壮大。”
但是他的提议,遭到梁干乔的断然拒绝。染干乔不但反对刘仁静的提议,甚至反对史唐、区芳提出的“三个条件”,他说:“三个条件是区芳、史唐受了陈独秀的收买,接受他加入反对派是个阴谋。”就这样,刘仁静的调停终于彻底宣告失败。当刘仁静无可奈何地将染干乔的意见转告陈独秀时,陈独秀火冒三丈,大骂:“乳臭未干的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搞独裁,未必太早了。”
时隔不久,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他思考再三,终于下定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自立门户。就这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第二个小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便宣告成立了。
(四十九)
“无产者社”成立的当天,发表了由陈独秀等81人联名签署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为政治纲领。“意见书”指出: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次大会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党的现状与危机也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的表现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下……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无处无事不举行‘自己失败主义’,弄得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至于“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箝制党员之最大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即“利用党内一般政治水平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酷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员及空洞的工会机关和雇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权威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问题。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是特别在中国范围内形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由斯大林、布哈林等所领导的整个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政策之一部分”,即斯大林为解决苏联危机而采取一系列“左”倾政策,“遂经过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在各国党中形成了一般的机会主义路线。”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针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自然要产生反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之斗争,即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之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担负了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换言之,“现在整个的第三国际中显然有两个根本不同的路线:一个是以斯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即现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路线;一个是托洛茨基所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即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路线”,“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也只有这两派路线之彻底的斗争。”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恢复其党籍和领导工作,公布近五六年来联共(布)及国际内部路线斗争的相关材料等,重审近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和国际的政策,恢复中共内部被开除党员之党籍并立即在党内公开讨论根本政治问题,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改组联共和国际及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纲领既立,活动随即进一步展开。曾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虽号称81人,但实际上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为了虚张声势而杜撰的。真正加入“无产者社”的主要有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何资深、汪泽楷、蔡振德、薛农山、罗世藩和吴季严等人。
鉴于陈独秀领导的“无产者派”明确表示拥护托洛茨基而反对斯大林,并尖锐抨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现行政治路线,在国际上和中共党内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斯大林改变了对陈独秀的策略态度。一九三○年二月初,共产国际以审查中共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为理由,发来给中共中央转陈独秀的电报。电报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处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附言中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但是陈独秀再一次表示拒绝。二月二十九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回信中写道:“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尤其涉及到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应该从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既然共产国际没有诚意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如国际“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托洛茨基的主张,“驻中国的国际代表曾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那么我和国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就“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便可解决的。”
至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最后一点联系割断了。
他开始全部精力用到“反对派”事业中去。
(五十)
陈独秀原本以为,斯大林路线在中共党内不得人心,已是怨声载道,只要他凭借着往日的威望,振臂一挥,便会有人一呼百应,蜂拥而来,取李立三而代之。但没有料到的是,“反对派”的事业并没有他想像得那样乐观。“无产者社”刚成立,就面临着中共的猛烈反击和托派组织内部咄咄逼人的挑战。
首先,中共中央对他这种“反对派”行为采取了果断措施进行反击。
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由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后,马上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尚在党内的签名者,要他们公开表明对意见书的政治观点的态度。“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消取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地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员会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遂将他们开除出党。接着,中央又逐个清除了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藩,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了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林琳、谢庄、薛农山等8人的党籍,纯洁了党的队伍。
在对“陈独秀派”成员采取组织制裁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除托派运动。周恩来在分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时,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周恩来的精辟论述,及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来势凶猛的冲击。
陈独秀面临的另一方面压力是来自“无产者社”组织内部的混乱和矛盾。
先是两个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之间闹起了矛盾。彭述之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封建家长”和“英美民主派”;陈独秀则骂彭述之为“不学无术,寡廉鲜耻”,“通天教主”和“孔夫子的生殖器”等,并讥讽他的文章“如王婆裹脚布,又臭又长”。而搞实际组织工作的“四大金刚”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和薛农山与搞理论宣传工作的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和高语罕之间也有矛盾。前者看不起后者,认为“这些书呆子写一百篇文章,还不及我们在工厂里搞一个支部来得有力。”甚至当“无产者派”受到其他托派组织的攻击时,内部也有人支持起哄。一九三○年三月,“我们的话派”发表文章批判陈独秀,马玉夫和罗世藩竟然公开表示赞同“我们的话派”的观点,并提议系统指出陈独秀的错误,以提交扩大会议讨论。
由于“无产者派”内部矛盾重重,加上一些人因生活困难而生计难以保证,因而气势消沉,心灰意冷,一切事情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肯积极参加活动。骨干分子蔡振德干脆不辞而别,到西安投靠杨虎城,当起《西京日报》社长去了。
面对内部这种混乱局面,陈独秀并未气馁,而是于一九三○年春开始对“无产者派”进行组织整顿。他找到了刚刚被开除出党的曾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何资深出任“无产者派”秘书长,又对本派成员的工作活动进行了调整,在上海,新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同时在北平、香港两地也分设了支部,摆出一副与中共抗衡的架势。
一九三○年六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无产者派”的代表会议,并作《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会议同时通过决议,决议声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报告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
不过,这次会议之后,陈独秀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决议提出的工作重点上,而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最新指示,开始运筹国内各托派组织的联合问题。
(五十一)
一九三○年夏秋,陈独秀在整顿了“无产者派”内部组织之后,面临着另外一个大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其他托派组织对他的不信任。他明明是被中共以“托派分子”的身份开除出党,而托派分子却坚持认为他并没有和斯大林派彻底划清界线,这就导致托派组织之间相互攻击,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其中,最让他头痛的就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刘仁静对他的倒戈。
一九二九年秋天刘仁静从苏联回国后,曾经非常卖力地调停“陈独秀派”和“我们的话派”之间的矛盾,力促两派实现联合,这使陈独秀对他大有好感。然而刘仁静这样做并非完全为了陈独秀,而是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自认为自己原是中共“一大”代表,现在又是“老托代表”,应该在中国托派组织中仅居陈独秀之后,坐第二把交椅。但彭述之根本不买他的账,彭述之在中共党内的职务比他高,当过中共中央常委,自然不甘居他之后,而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又态度暧昧,似乎还有点偏向彭述之,这使刘仁静感到非常寒心。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之后,曾要求他帮助起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没想到,他将意见书起草完后,陈独秀又作了大量修改,将自己《告全党同志书》中的许多政治观点加了进去,这使刘仁静感到十分不快。他认为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因屈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盲目地执行”,他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想“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刘仁静对陈独秀的这番指责,也正是“我们的话派”在和陈独秀谈判过程中为什么坚持让他完全承认大革命失败错误的原因。同时,刘仁静认为,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因而刘仁静断然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
在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攻击“我们的话派”。他责怪梁干乔把持的“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路线分歧”。他又批评梁干乔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中共党外活动。由此他得出梁干乔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的结论。
就这样,刘仁静两面出击,先和“我们的话派”谈崩了,又和“无产者社”闹僵了,只好另起炉灶,同王文元以及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等九人,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发起成立了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派”的错误,“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由于他们出版的机关报名为《十月》,于是又称“十月社”。
刘仁静成立“十月社”后,“我们的话派”马上做出强烈反应,召开大会,做出决议,宣布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并未长久。这年十月,刘仁静在批判陈独秀时,由于坚持认为一九二三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却被王文元等人将他开除出“十月社”。王文元他们的理由是,中共根本就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刘仁静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后,一气之下,开始单干,独自出版《明天》刊物,自称“明天派”,但因势单力薄,均未为其他各派所认可。
“我们的话派”在开除刘仁静的同时,内部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加入“总干”,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人“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反对派”,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入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才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就在上述三个托派小组织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另外几个从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李逸民、严灵峰、陈岱青等7人,还有刚刚被“我们的话派”开除的张师,又发起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由于该组织出版机关刊物《战斗》,史称“战斗社”。
一九三○年夏天,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四个托派小组织,就这样先后粉墨登场了。他们一方面各自称王,自命不凡,惟我独尊,勾心斗角;另一方面又都拥有同一个主子-----托派茨基。在争斗中,他们既频繁地向托洛茨基写信,互相倾轧,攻击对方,期待“以我为中心”来“统一”其他各派;而在互相指责中,又常常不约而同结成暂时的统一战线,对付共同的“眼中钉”陈独秀。生怕陈独秀以及特殊的社会政治经历为资本,出面“统一”他们。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混乱局面,也算是中国政党历史上的奇观了。
“我们的话派”因最早建立托派组织,于是自视为中国托派的先驱;而“十月派”首领刘仁静,则自恃在党内的资格很老,还与托洛茨基有过直接的接触,便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并以“托派在中国的代表”自居;至于“战斗派”之所以挂牌子,仅仅是出自这样的考虑:“与其参加他们的组织不如独树一帜,‘因为’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势必会趋向统一”,而“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个位置”,由此出发,他们也就事先极力地贬低其他各派,如称“无产者派”为一群“老机会主义”,“十月派”是一伙“空头理论家”,“我们的话派”则是既无理论又无实践的群氓;陈独秀是中共的开山鼻祖,当然就更加看不起其他三派,在他看来,那三个组织“不过是乳臭未干”的“猴儿崽子”,“想学斯大林未免过早了”。
各派互不服气,就向托洛茨基打小报告。当时,“我们的话派”和“十月派”都与托洛茨基有直接的通讯联系,所以不时写信给他,除了相互攻击外,更多的是一致批判陈独秀,希望得到托洛茨基的最高指示来压服异己。
这个时候,托洛茨基的态度就对中国托派组织向何处去显得十分重要。
(五十二)
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素昧平生,从未打过交道,他只是曾就事论事地对陈独秀有过若干评论。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曾赞扬陈独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无条件正确的”,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又认为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主张中国革命“扩大后再深入”的观点,体现了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因此,在陈独秀筹建托派组织之初,他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审慎和暧昧的,既欢迎,又有疑虑。
一九二九年九月,刘仁静致函托洛茨基抱怨说:“我们的话派”不与陈独秀谈统一,所以我本人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托洛茨基则回信阻止道:“你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们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指陈独秀--引者)之间,在过去的政见(1924------1927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虑,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说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托洛茨基回信说:“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的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陈独秀此时的政治观点,托洛茨基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15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与我们是否原则一致”的标准。
甚至到了一九三○年二月,托洛茨基还对和陈独秀合作毫无兴趣,他给刘仁静写信说:陈独秀“这一派继续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即“站在斯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其实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从一九三○年四月开始,托洛茨基对于陈独秀的认识和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这时候,托洛茨基为了进一步与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抗衡,同时也为了扩大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力量,以加强相互联系、合作和统一行动,正在着手酝酿组织“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局”(亦称“托派国际”,一九三八年后改为第四国际)。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有俄、法、德、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等国的托派团体,惟独没有东方国家,因此,托洛茨基开始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四月三日,他在回答刘仁静二月二十一日批判陈独秀等81人意见书的来信时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八十一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你翻译得尽可能的完美确切。”就在同一封信中,托洛茨基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问题,并明确要求“十月派”与“我们的话派”停止理论上的“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的争吵,先行联合。
很显然,托洛茨基此时已有意挑选陈独秀出来统一托派组织。
八月二十二日,托洛茨基再次致函刘仁静,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明确表示了选择陈独秀出面统一中国各托派组织的倾向性意见。
托洛茨基说:“直到今天我才得读陈独秀同志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和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洛茨基在信中还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他还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托洛茨基最后对刘仁静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九月一日,托洛茨基又致函“十月社”,更加明确地表示:“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因为“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地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左派’的理由”。信中,托洛茨基还指出,中国的四个托派组织可以“组成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
托洛茨基的这两封信对于中国托派的未来政治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他否定了“我们的话派”与“十月派”的正统地位,从根本上阻止了这两派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攻击和侮辱,这就迫使国内其他托派组织不得不把联合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托洛茨基给予陈独秀极高的评价,不仅完全改变了原先“妾身未明”的被动地位,而且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这就使陈独秀在日后的联合统一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
为了抬高陈独秀的威信,托洛茨基还直接写信给陈独秀,对陈独秀的文章推崇备至,称赞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甚至肉麻地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独秀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
“我们的话派”和“十月派”自然明白托洛茨基的用意,虽然心里老大的不服,但又不敢违抗洛茨基的指示。不得已,到了一九三○年十月,四个托派组织终于组成了协议委员会,开始具体讨论统一问题,并专门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
然而,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首先跳出来发难的是彭述之。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派”为中心,以便联合后,他能坐上第二把交椅。但这明显违背了托洛茨基要求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彭述之就背着陈独秀暗中指示“无产者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代表吴季严和马玉夫,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王文元起草的托派政纲中要对过去的政治原则和策略上的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并且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
一九三一年一月,陈独秀收到托洛茨基急切呼吁各派组织迅速统一的来信。托洛茨基在信中说:“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
读罢此信,陈独秀甚为感动,他马上撰写发表《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一文,再一次诚恳地呼请各派从大局出发,停止争纷,立即着手统一工作。他说:读了托洛茨基的来信,“使我惭愧无比”,“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未能迅速实行统一,本是“罪恶”了,“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他呼吁各派:“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轧乱麻地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
为了表示诚意,陈独秀首先在“无产者派”内部开刀。当他从尹宽那儿了解到彭述之指使吴季严、马玉夫破坏统一的情况后,马上召开全体会议,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之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接着,他断然撤换马玉夫和吴季严的代表资格,由自己和尹宽二人出任“无产者派”的代表。同时,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组织上的措施,削弱了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陈独秀又主动与“我们的话派”的代表梁干乔和王文元交谈,诚恳地表示:“统一是中国反对派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
陈独秀之所以大刀阔斧采取这些措施,不惜牺牲“无产者派”的利益,一再向其他各派做出让步,争取尽快实现统一,是有目的的。因为当时中共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垮台、王明刚刚上台的交接时期,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党内思想再次出现混乱。陈独秀是想借这个机会,混中夺权,取王明而代之。因此,他迫切希望托派早日统一。他一再对大家讲:“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并说:“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
陈独秀在真诚促成各派组织统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姿态,令王文元等人十分感动,也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至此,由于托洛茨基的亲自干涉,特别是陈独秀最后的推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