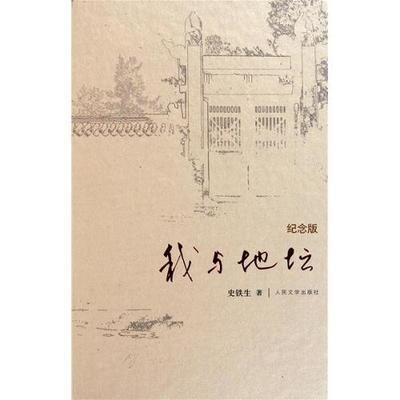于文华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yuwenhua我与姨妈韩少云
——重访一代评剧宗师韩少云故居感怀
于文华
今年夏日格外热,演出任务多多,心绪也随之烦乱。很想利用些时间出去转转,放松一下身体和心理。我立即想到了沈阳,我很想去沈阳。沈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又是个很沧桑的老工业城市,更重要的是在那里留下了我青春足迹和一些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故事,我和沈阳是有缘分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都是如此。
我立即打电话给巴哥(巴俊宇教授),巴哥是我少有的多年知友,我们之间的情谊时断时连的可以追溯很久,就在这个城市。兜兜转转的许多年过去了,现在他作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学者仍然活跃在那座城市里。巴哥还是那么幽默诙谐,爱开玩笑:“我代表沈阳730万人民热烈欢迎人民歌唱家于文华莅临沈城!我可以给你做导游、保镖兼业余摄影师。”巴哥是个才情并重的学者,人品好,人缘好,学问深,善良又仗义,在东北有很好的社会影响,用句东北话说是个纯爷们,而难得他又是平易近人并且是很懂人、很率真和很真诚的,我很尊敬他,一些事情总愿意和他说说。突然出来多少有些不安,但想到有巴哥在身边就感到无比的踏实了。
(一)
其实真的说不清我去沈阳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根还是寻缘?也许是突发奇想,我这个人啊有时就是这样风一阵雨一阵的。沈阳的朋友们真得很好,几日来我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和关照,走走看看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个大工业都市那博大胸怀和气度。
虽说是没什么目的,其实内心里却有一种不好用语言来表达的情绪和牵挂,我知道我有一项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我必须去看望一个老人,那就是我八十二岁高龄的姨夫著名作曲家王其珩。那日我打电话和姨夫说我想您了,我要去沈阳看看您,姨夫竟然如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内心里除去挂牵、思念还有丝丝的愧疚,我已经许久没来了……
其实也许熟悉我姨夫的人有限,但提到我的姨妈可以说家喻户晓了,她就是一代评剧表演艺术大师——韩派评剧艺术创始人韩少云。而人们就更不知道我从小就在姨妈身边,在她的关爱、呵护、教导下渐渐成长起来的,而她嫡传给我的韩派评剧的艺术修为是我一生受用不完的精神财富。可遗憾的是姨妈几年前突发心脏病辞世,除了留给人们的艺术财富和人们深深的怀念外,也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久的失落感,今年我深爱的母亲也驾鹤西去了,我这个从来就是个长不大的人就像一个可怜的孩子失去了亲人的呵护一般,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落寞。
那日我扯着巴哥和我一起如约来到沈阳西郊姨妈的故居,姨夫和表哥表弟表嫂一家人早早等候,亲人相见亲得不得了,姨夫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在老人身边我感受到了父亲般的感觉,使我想起了父亲为我剥苦杏仁的情形,想起了我十几岁时在姨妈家生活的那些时光,想起了姨妈姨夫对我的呵护和爱怜……
姨夫和巴哥是个忘年交,见到巴哥一起来高兴得不得了,这一老一少一见面就打开话匣子,天南地北的说个没完,看到老人身体还健朗,精神头也很好我心里多少有些慰藉。
趁着这一老一少在兴致勃勃的交谈,我在这个房子里默默的徜徉,寻找着过去的遗痕,感受那些已然飘逝的情思。墙上依然挂着姨妈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一幅幅怒放的梅花真墨跃然纸上,触景生情,感怀万千。
与姨夫和表弟禾阳
姨夫和巴哥是个忘年交,这一老一少一见面就打开话匣子
最叫我伤怀的就是姨妈居住的房间,虽然是后来装修的新房子,但房间里依然摆着几十年的漆雕的老床,我站在门前没有走进去,只是在远远的望着那张床,我知道那里仍然活跃着姨妈的精灵……姨夫为了我的到来把姨妈的老床换上了新床单,可是我无法住在这里……
细心的巴哥走过来关切的说,为什么不进去?我说:我不敢,我怕走进去就出不来……
……

(二)
大约在上个世纪84年第一次去沈阳见姨妈,心里很是忐忑,不知姨妈到底是什么样,严厉还是温和?能否喜欢我这个土土的小丫头?毕竟她是全国知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大师,而我只是个河北省艺术学校评剧科的一名学生,那时候的她除了要完成沈阳评剧院的工作安排外,还有很多社会性的工作要做,因此她当时的工作很是繁忙,甚至都无暇顾及家里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到来会不会给她添很多麻烦,因此心里不免有些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
我清楚的记得我跟妈妈和舅舅是早上六点左右下的火车,七点多就到了姨妈家,舅舅轻轻的敲了敲门,开门的是我的小弟禾阳。进得门来,看到姨妈正在整理一些材料,像是要去开会,见我们进来,匆匆的和我妈妈我舅舅打了个招呼说:“大哥、二姐你们先休息,中午回来再聊”。但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姨妈的视线一直没离开我,她用艺术家那特有的眼神上下打量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不知如何是好,正当我手足无措之际,姨妈轻轻的拉起我的手进了当时既是卧室又是客厅的房间,把我按在沙发上,就像一个玉雕家把玩一个未经雕琢的玉石一样,坐在那张老床上上下下细细的打量我,满眼笑意的看着我,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地,满脸生出的都是喜欢和爱怜……
姨妈生活非常简朴,吃饭也极其简单,就爱吃东北那些汤汤水水的炖大罗卜、炖大白菜,尤其爱吃高粱米水饭和小葱沾酱,而且酱都是姨妈自己亲自做的,用姨妈的话说,自己做既省钱又好吃,还能带来很多乐趣,吃起来也就更加香甜。说到省钱,记得一次姨妈和姨夫大动肝火,吵的非常厉害,开始我很莫名,后来逐渐听出点倪端。原来,姨妈生活非常节俭,每次牙膏用到最后实在挤不出时,便用剪刀把牙膏头剪开,将剩下的那一点全部用完为止。而那次争吵,就是因为姨夫用完牙膏觉得实在挤不出了便把牙膏皮丢掉,便引来一场“战争”。说来不值当,但仔细想来却透出姨妈当时的生活状态,要赡养我的姥姥、奶奶(姨父的母亲)和八老爷(从小就带着姨妈演戏)三位老人,又要供表哥和表弟读书,一切开销就是姨妈和姨夫的工资支撑,当时姨妈和姨夫的生活非常艰难,这也是我长大之后才逐渐感悟到的,这次来沈阳重提旧事,姨父才告诉我说,三位老人生病住院,都是评剧院垫付医疗费,直至几位老人相继去世后许多年才逐渐还清院里的债务,抚今追昔,我的心隐隐作痛……
姨妈做梦都想生个女儿,可偏偏三个都是男孩儿,这也许是她偏爱我的原因吧。即便在生活那样紧张的状态下,还要把我拉到街上给我买了一件紫红底白花上衣和一条白色的裤子,为使我看起来更可爱,发式上更能与这身衣服相配,姨妈拿起剪刀亲自为我剪了个三齐式的学生头,边剪便端详,嘴里不断叨咕着好看,不时的还要叫我姨夫过来欣赏她的“杰作”,而姨夫也是不厌其烦的,乐呵呵的过来欣赏,那笑容、那温馨的场景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际,仿佛就在昨天……
(三)
“小河流水呀,还是哗啦啦的响,河边的柳树,还是那么样的弯,那一天,薅草回来天色晚,满天的彩霞,那太阳它下了山……”那天中午,姨妈利用午休时间,教了我这几句《小女婿》中的经典唱段,之后便和姨夫一起匆匆出门,家里只剩我一人,在把房间收拾完之后,我便坐下来仔细回味姨妈教我的这段唱,她的咬字、她的润腔是那样的细腻,那样讲究,尤其是“下了山”的“下”字,由于我的尖团字较重,姨妈便着重为我纠正了这个字,使我在以后的学习中没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可说是受益匪浅。还有就是她的“小擞音”处理的非常有味道,也可以说非常独到,一般很难唱好,尤其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更难做到,也许是我和她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居然她一教,我便会,不用重复第二次,当时姨妈惊喜的神情真是难以形容!
由于家里没人,我便大胆的把姨妈教我的这几句唱用家里的盒式录音机给录了下来。反复听,反复唱,正当我还沉湎其中时,姨妈和姨夫回来了,我急忙关掉录音机,不想还是被姨妈听到,她急切的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没啥,她说快把录音机打开我听听,我只好顺从,放了一遍又一遍,她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开怀,她感慨的跟姨夫说:“其珩啊,这孩子太像我了,你听她“小擞音”唱的多到位呀,这么些年我还没遇到过学我学的这么像的学生”后来他把录音放给团里的同志们听,并问:“你们猜这是谁唱的呀”,大家几乎异口同声毫不犹豫的说:“这还用问,这是您年轻时唱的!”自此,姨妈便有心想让我继承韩派,收我做嫡传弟子。
姨妈韩少云与姨夫王其珩在熊岳梅园写生(1996)
可那时我已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在留到沈阳继承韩派评剧艺术,还是到北京读书深造,姨妈和姨夫思前想后,考虑再三,面对风靡的歌坛和无奈的社会,他们最终作出了送我上学的决定,我知道他们是矛盾的甚至痛苦的,但不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他们不论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是从有利我发展出发。我到今天也无法知道我的抉择是否是对的,但我更深切的感受的却是姨妈对我深深爱……
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北京发展,姨妈对我十分的不放心,经常在电话里问长问短,在我人生遭遇坎坷不幸时,姨妈每每都第一时间坚定的站在我的身旁,我知道她老人家给与我的爱可以比母,而母亲做到的她做到了,母亲做不到的她依然做到了。
姨妈一生刚直不阿,清廉自爱,作为有如此声誉和影响的艺术大师,她从没有一丝自傲和特权意识,浓浓的平民情怀始终伴她淡定的生平。她从不利用自己的影响为自己和家人谋利,从不求人。几个表兄弟丝毫没有借到姨妈的光,完全靠自己打拼安身立命,实现自我价值。
姨妈还是求人了,她为了我,她实在不放心我在北京独闯天地,利用在北京开‘两会’期间找到了时任文化部某部长,要他关照我。部长满口应允,事后姨妈亲自给我写了信,要我去找部长,这是她唯一的一次求人,却是为了我。可是过了许久姨夫曾问我:
“你找部长部长怎么说?”
“我根本没去,我要自己闯,相信我!”我告诉姨夫。
姨夫摇了摇头无奈的说:“小华啊,你这丫头太像你姨妈了”
姨夫:“你这丫头太像你姨妈了”姨夫、巴哥和我在欣赏姨妈作品
尾声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2003年的夏季,一天我正在彩排,突然接到一个沈阳的电话说姨妈……我顿感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仿佛已凝固。2003年7月20日早7时我亲爱的姨妈——一代评剧宗师韩少云突发心脏病在沈阳去世,享年仅75岁。
我扔掉了手头所有的工作赶到沈阳,在太平间里我最后看了姨妈一面,姨妈脸色很好,依然是那样的有神韵,安详的就像睡着了一样,想到姨妈一生喜欢美丽和洁净,想到那些和我的点点滴滴久远的故事和对我的深爱,我失声恸哭不能自己。
回到北京我病了,从那以后我的内心深处越加孤独了……
这次回沈,看到了姨夫为姨妈出版的《韩少云书画集》欣慰之余知道整理姨妈的作品已成为姨夫晚年的全部寄托,最近由姨夫主编纪念姨妈韩少云的文集正在收尾中,姨夫邀请巴哥(巴俊宇教授)和我分别为姨妈写篇纪念文章,这几日我们怀着复杂的心绪和深深缅怀的心情写下自己的感怀,希望能告慰我的至爱姨妈韩少云的在天之灵!
姨妈在世时一直希望我做女儿,几次和妈妈说要过继我,可是直到姨妈离世我也没叫过姨妈一声妈妈,至今觉得很对不住姨妈。我有个心愿,等腾出时间我要专门去姨妈的墓地去祭扫,到时一定会跪在姨妈的坟前说声:
妈妈,女儿给您磕头了……
于文华2009年8月4日于沈阳西郊顿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