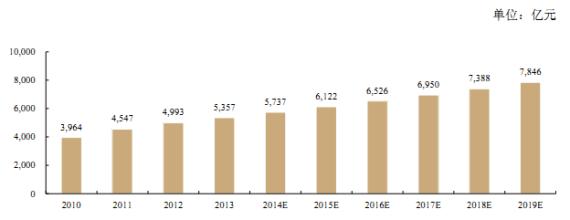首先我是音盲。只适合听一些流行的缠绵悱恻的伤感歌曲,虽然这无可诟病,只多是缺少音乐修养的下里巴人罢了。
日本电影《入殓师》的海报是在一片无边翻滚着绿浪的原野上,男主角拉着低缓华丽的大提琴。乐队解散,一个大提琴手做了一个入殓师,生命就这样充满了起伏转折与“无奈。”剧情在浑厚舒缓的大提琴伴奏下展开,展现着主人公内心的洪流翻滚。每个人都会经历生与死,人生不过在睁眼与闭眼间徘徊,《入殓师》看似通篇在讲述不同人的逝去,但它笑中有泪,散发着亲切的人情味,大彻而大悟,活得坦然。不再是生存无奈与梦想的冲突,而成为对生命的珍惜,对死亡的敬重。电影完毕,大提琴的乐音在耳边盘旋,无以言表。或许这就是卑微的个体生命对契阔生死的最真切的感悟吧。

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次乘车在广播里听到杜普蕾演奏的大提琴曲,慨然长叹“她这样把所有复杂的情感都投入到大提琴的演奏中,一定会迅速地消耗生命的。”一语成谶,42岁的杰奎琳·杜普蕾烟花易散,香消玉殒。那首曲子以《Jacqueline'stear》而闻名。觉得这名字太感性太直接,远远没有概括出音乐本身的份量。还穿凿地想曲名中的tear是不是tears的错误拼写呢。而听完全曲,没有可以制造的华丽和廉价的悲伤煽情,只有来自心底的悚动与感叹。生命的tear是一种形而上的与生俱来的宿命。无关它的长短,它的荣枯,它的灿烂与寂灭。或许当那神圣的tear变成具体的量化的繁琐的可细细道来,可滔滔痛陈的tears时,一切都变得太过平庸。我喜欢莫名的潸然,莫名的泪流奔淌。那时不是单纯的伤及自身的狭隘,而有了一种人同此心的“同情”,成为一种高尚的悲悯。
马友友评论杜普蕾“她的演奏像要跳出唱片向你扑来。她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演奏者,她手中的音乐永远是随心而动。因此,她的每一张唱片都是一种全新的音乐旅程。”我喜欢有这样的良友,能从我的图画和文字中看出我律动的心。如果他真的看懂了,一定会说“她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投诸到线条的海洋,心一定成了虚谷,没有了堵塞与负累,与天地同化,活得天长地久吧。”在这样孤独肃穆的乐曲中,我站南山之颠,且放一笑吧。哇哈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