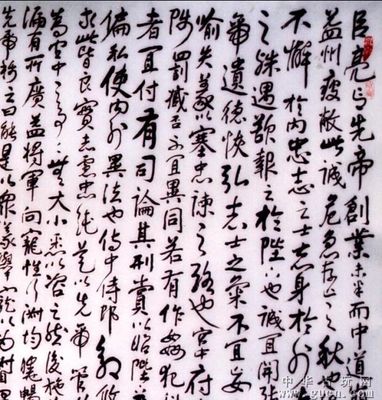池莉与《不谈爱情》--刘荣秀
一、池莉作品简析:
读池莉的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是—真、实在。她写的都是些琐碎的生活片段,可她一样把你带进去读,让你感动。《不谈爱情》是池莉“烦恼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烦恼人生》和《太阳出世》。在“烦恼三部曲”中,池莉塑造了以印加厚、庄建飞为代表的一系列在现实里挣扎着的男人。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顿,犹如一把利剑,从肉体到灵魂对他们进行了层层的剥离。正如池莉所说的,他们是生活在风口浪尖上的一群,生活跌宕,好事坏事都是他们先摊上,压力特别大。在粗糙生活的砥砺下,打磨掉了所有的激情与幻想放逐了崇高的理想,消解了爱情神话,他们“活着就好”,他们“不谈爱情”。
二、“不谈爱情”的真实内涵
如果说印家厚的苦恼更多的是物质上的话,那么《不谈爱情》里的庄建非就是精神上的困顿。庄建非和吉玲的恋爱过程首先体现为本能情欲的满足,后又服膺于社会秩序、婚姻规则。婚后两人的第一次争吵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混战,惊动了双方的父母、同事、单位领导,并且直接影响到庄建非出国进修的大事。“从庄建非的妻子到他的岳父岳母,从他的妹妹到他的亲娘老子,从一般的社会团体组织,都不把婚姻和家庭当作两个人感情上的事情,他们在这里溶解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和世俗利益内容,都想在这里实现一点卑微的欲望。”“不谈爱情”事实上是平凡的男人对生活的尊重和珍惜,是他们抵消了理想和憧憬,稀释了浓烈和灼热之后找到的世俗美好,是对幸福的另一种注解。
三、池莉小说中的女性视角
1、女性欲望为主体所谓“女性欲望为主体”是指女性不再被当作男性欲望的客体并以之塑造和束缚自己,而是成为一个欲望的主体,去追求其欲望的实现和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男性成为女性欲望的客体。这种主客体之间的颠倒互换成为池莉作品的一大特色,也暗合女性创作的原则。《不谈爱情》中的梅莹,尽管她不是作品的主要人物,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成功的中年职业女性,在她的身上呈现出一种精明干练,成熟且迷人的个性,她强健、清醒,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生活的舵柄,因此她成为庄建非的人生指导者——“良师益友”。同时,作为庄建非的情人,她不压抑自己对性的需求与满足欲,但又不会给予它特殊的位置与特殊的意义,她更不会为它而放弃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在梅莹身上体现了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的一种颇为成熟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梅莹不同于别的女性形象,通常的女性在成为别人的情人之后总是要求由第三者变为第一者,这是由于女性本身不能充分地把握自身从而成为男性附庸的缘故。在池莉的笔下,或者说在池莉的心里,她是不喜欢女人成为附庸的。所以,在其写作中,她不断地寻求独立于男性的可能性和可行之途,但是,这种寻求并未使其小说蒙上多少探索的味道,因为这是一种不太真实的探索,而其提供的路径也是极端化和幻想性质极其浓厚的。
2、逃离爱情的意义池莉本人一直说她在试图使用新眼睛,她的成名心理也使她拒绝迎合,而要采用一种对峙的态度,一种撕裂的态度。这种对峙于撕裂同样带到了她的爱情字典中。
《不谈爱情》是对爱情真理或学问的探讨,从世俗人生过日子的角度来看的。半年的夫妻生活,夫妻的感情相撞,使庄建非在对自己的婚姻做了一番新的估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了出自己结婚的理由:“性欲”。吉玲找庄建非是为了改变自己“花楼街”的底层身份,谈情说爱是“人工创作”。于是,婚后的生活便原形毕露。池莉在小说里,首先寻求的乃是逃离爱情的合行动唯一合法法性。因为爱情毕竟曾经被无数人歌颂为世间最为美好的东西,在她的主人公那里,逃离行动唯一的合法性乃是:没有爱情这回事。这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和决绝态度。
四、池莉爱情观的探讨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被认为是人类最圣洁的情感,爱情主题也因此经常被推为文学古往今来艺术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人们一直用最美丽的字眼来咏叹它:生活即使苦难,无坚不摧的爱情可以打败它;生活固然富足,没有爱情,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可以说,爱情是非常富有理想色彩和浪漫气息的,传统文学中视它为珍宝。
对于池莉的爱情观,在大家的理解,都是“不谈爱情”,即只谈物质生活中的现实法则,而不谈精神层面的所谓爱情。
表面看来,池莉这部小说似乎是“不谈爱情”回避爱情,拒绝精神的追求,其实,在拮据的物质生活或受人左右的现实生活环境中,仍可以看出小人物对诗意浪漫的追求,它是灰暗的人生图景中的一点渴望。对于庄建非,许多人都把婚姻对于他的意义仅仅看作是性欲的饿满足,其实,内心一直在寻求诗意浪漫的爱。他之所以选择吉玲,其一,是吉玲最初给他留下了浪漫美好的印象。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吉玲包里掉出的“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手帕里包着的樱花瓣、零花钱和一管香水”富裕吉玲一种浪漫的色彩,给庄建非留下优雅纯情的印象。其二,还有他的审美价值观的原因,吉玲“村姑戴野花”的美感与魅力,是庄建非无法抗拒的。由此看来,池莉不仅“谈爱情”,承认爱情的存在,而且对爱情有自己独特的思考。
池莉和丈夫是冲着爱情走到一起的,可是婚后不时有大争小吵,由此也说明感情的脆弱。池莉悟出:“婚姻绝不仅仅是爱情问题,它还是个结构问题。夫妇两人一人主内一人就得主外,一人内向好静,另一人就得喜欢交际,不然日子真的确是很难过的。”这就是生活的法则。爱情首先依附于生活,生活包括的内容其实很多。生活下去靠的也不只是激情。事实上,池莉构筑的婚姻图景是一副社会图景。这不仅因为婚姻原本是一种社会行为,还在于池莉撕裂了上世纪80年代女性叙事中对婚姻之于个人意义的放大,将它还原为社会秩序的一环。如她自己所言,“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从“不谈爱情”到“拆穿爱情”,她开始了其小说创作的目的性的更变,完成了对爱情的叙事的解构,毫不客气的撕裂了父权社会所定义的“爱情”神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