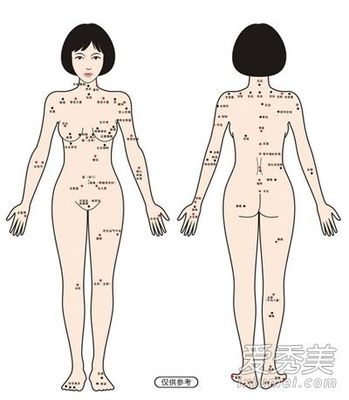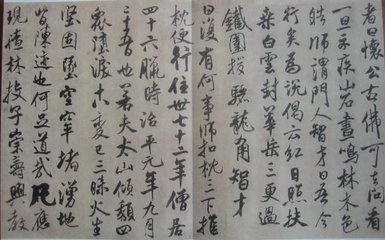问:“鲁迅全集”和鲁迅作品出版已很多,您觉得为什么有必要编一套《编年全集》?
答:以编年体而且是具体系于年月日的方法,来编排一位作家现存的全部日记、创作、翻译、书信,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正如我们在“凡例”中说的,“本书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鲁迅的文本”,具体说来,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反过来说:假如读者和研究者希望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希望具体详细地了解他的创作轨迹和思想进程,了解他的创作与翻译如何相互影响和补充,以及他私下给朋友信中的说法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的异同,等等,看看这套书大概有些帮助,或许能发现过去分开看他的创作、翻译、书信、日记,或者只看其中某一部分时,所不曾发现的一些问题。这套《编年全集》,有如一部“鲁迅年谱长编”。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值得“纵读”一番。
然而正如“凡例”讲的,这套书“在编辑体例上仅是一种尝试”,无意以此替代此前出版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先后出版过一九三八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八一年和二〇〇五年几个版本,都是保留“鲁迅自编文集”原貌的编法,在此之外,不妨另有一种编法。就各种已出的《鲁迅全集》而言,一九三八年版虽然有不少遗漏,譬如未收书信、日记,很多佚文也有待日后陆续发现,但它却更接近于“全集”,因为包括了鲁迅的翻译作品和所整理的古籍作品。一九五八年版实际上是“鲁迅创作全集”,此外另出了一部十卷本的《鲁迅译文集》。一九八一年版较之一九五八年版内容上多有补充,编辑思路却是一样的,仍然属于“鲁迅创作全集”。二〇〇五年版是对一九八一年版的修订,整体框架上并无改变。去年出版的《鲁迅译文全集》,则是从前那套《鲁迅译文集》的修订增补之作。
问:《编年全集》“凡例”称“收录迄今所发现的鲁迅全部作品”,请问此书与人文版《鲁迅全集》相比在收文方面有何不同?篇幅是否比人文版要大不少?
答: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新版《鲁迅全集》修订概况”称:“根据鲁迅著作的出版规划,将以《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从编》、《鲁迅科学论著》来分类整理出版鲁迅的著作。”我们这套书,大概相当于《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和《鲁迅科学论著》中鲁迅自己作品的全部,加上《鲁迅全集补遗》中可靠的篇章,以及到《编年文集》付印为止新发现的鲁迅佚作。单就鲁迅创作来说,比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增补了四十篇左右。另外还收录了鲁迅的全部日文作品。
另一方面,则如“凡例”所说,“鲁迅生前编入自己文集而确系他人所作或由他人代笔者,列为附录。”这包括周作人的四篇文章(原收《热风》)、瞿秋白的十二篇文章(原收《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以及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
“凡例”又说:“其余他人之作,包括鲁迅编集时文后所附‘备考’,概不收入。”这还包括曾收入《鲁迅译文集》和《鲁迅译文全集》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周作人译),《项链》(常惠译)、《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冯雪峰译),《〈毁灭〉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朱杜二君”译)、《〈毁灭〉作者自传》(亦还译)、《关于〈毁灭〉》(洛扬即冯雪峰译),以及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著《小彼得》一书。《小彼得》系许广平所译,曾由鲁迅“大加改译了一通”,但是在他自拟的《鲁迅著译书目》中,属于“所校订者”,与《二月》(柔石作)、《小小十年》(叶永蓁作)、《穷人》(韦丛芜译)、《黑假面人》(李霁野译)、《红笑》(梅川译)、《进化与退化》(周建人译)、《浮士德与城》(柔石译)、《静静的顿河》(贺非译)和《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侍桁译)同归一类,这些都不是鲁迅的著译。《小彼得》署“许霞译”,这是许广平的笔名,鲁迅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网上有种说法:“鲁迅全集在建国前早就出版了,建国后再版,据说都被阉割了。”这里可以说明一下。鲁迅生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确常遭当局删改,他说:“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而他汇集出版时,“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准风月谈·前记》)几种《鲁迅全集》,除一九五八年版删去《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中“托洛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一句,而一九八一年和二〇〇五年版又予恢复外,对于鲁迅自己的文字并无其他删改。
鲁迅的译作也曾遭到类似“阉割”:他翻译的托洛茨基《亚历山大·勃洛克》一文(作为序文收入胡斅译《十二个》,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为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所漏收,而一九五八版《鲁迅译文集》有意不收。二〇〇八年版《鲁迅译文全集》和我们这套书均已补入。鲁迅其他译作涉及托洛茨基,《鲁迅译文集》都有所删改。这包括D.孚尔玛诺夫著《革命的英雄们》(收入《一天的工作》)中的两处:
“‘不是赶走——而是消灭。’那时托罗茨基命令说。”
“到八月底,敌人离古班地方的首都克拉斯诺达尔市,已只四五十启罗密达了。这时便来了托罗茨基。议定许多新的紧急的策略,以排除逼近的危险。后来成了最重要的那一个策略,也就包含在这些里面的。”
以及L.班台莱耶夫著《表》中的一处:
“他们走进一间大厅里。壁上挂着许多像,李宁,托罗茨基。”
《鲁迅译文全集》只恢复了其中一处,另两处一仍其旧。我们这套书一律按原貌印出。
问:书中的每篇文字均要以完成时间排序,但恐怕总有一些文字写作时间难于确定,对此如何处理?某些作品写作时间的考定很费周折吧?
答:“凡例”:“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著译作品先小说,后散文、诗歌。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写作时间未明,则系以初次发表时间,于题目右上方标一星花以示区别。”
鲁迅不少文章篇末署有写作日期,再加上日记、书信的相关记载,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能系上写作时间。不过有些篇末所署日期,是鲁迅后来编集子时添加的,与日记记载并不一致。譬如鲁迅一九二〇年八月五日日记:“小说一篇至夜写讫。”此即《风波》,发表于同年九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收入《呐喊》时,篇末却署“一九二〇年十月”。又如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日记:“作《眉间赤》讫。”《眉间尺》发表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莽原》第二卷第八、九期。收入《故事新编》时,改题《铸剑》,篇末却署“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凡此等处,均从日记。又如鲁迅所说,《坟》和《热风》之编集,各出自“几个朋友”之手。收入《坟》中原载《河南》的几篇文章,篇末均署“一九〇七年作”,其中《人之历史》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发表于第一号,《摩罗诗力说》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月发表于第二、三号,《科学史教篇》一九〇八年六月发表于第五号,《文化偏至论》一九〇八年八月五日发表于第七号,不大可能都是“一九〇七年作”。《热风》之《智识即罪恶》、《事实胜于雄辩》、《为“俄国歌剧团”》、《无题》、《“以震其艰深”》、《儿歌的反动》、《“一是之学说”》、《不懂的音译》、《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即小见大》和《望勿“纠正”》,篇末所署,实际上均为发表日期。除《儿歌的反动》和《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外,其余难以考证具体写作日期,为稳妥计,我们将各篇分别系于发表时间。
“凡例”中说“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又说“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每有修改,此次编集,只收录最后定稿”,实际上是以“最终完成”来确定“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譬如鲁迅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夜译《溃灭》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日记:“夜校《毁灭》讫。”我们将《毁灭》的写作时间系于后一时间,而不系于前一时间。又如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夜草《中国小说史略》下卷毕。”同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四年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分别出版。此后鲁迅不止一次改订,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印行定本第十版。我们既采用《中国小说史略》定稿本,只能按发表时间——最后一次修订的具体时间不详——系于一九三五年六月。

“凡例”:“凡能独立成篇者,无拘长短,均单立一题;中、长篇作品,亦一律保持完整,不予割裂。”也来举个例子。鲁迅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日记:“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一月二十五日:“夜译文一篇。”一月二十六日:“下午至夜译文三篇。”一月二十八日:“夜译白村氏《出了象牙之塔》二篇。”二月十一日:“夜伏园来,取译稿以去。”二月十八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译《出了象牙之塔》讫。”此系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之第一篇《出了象牙之塔》,共十六节,日记提到的“篇”即“节”。该文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月二日至五日、七日连载于《京报副刊》。虽然有这些线索,但此乃一篇文章,不能拆析,故完整地系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我们一再斟酌,反复讨论,才拟定这套书的“凡例”;力求以此贯穿始终,杜绝例外,做到自圆其说。
问:《鲁迅全集》校勘和注释的问题颇受关注,《编年全集》校勘和注释的原则是怎样的?据“凡例”,《编年全集》中,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请问,日记、书信为何未直接移用以前出版的《鲁迅全集》或者《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呢?
答:从一九五八年版到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的几次修订,很大精力花在注释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注释本只是一种有可能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我们这套书则是“白文本”,除了“凡例”所说“编者于各篇篇末,对最初发表时间,所载报刊,作者署名(署‘鲁迅’者略)及首次收集情况(限于鲁迅自己所编者)略作说明”外,别无注释。
“凡例”:“收入本书的著译作品,均以鲁迅生前最后定稿版为底本,未收集者以原载报刊为底本,参校各版《鲁迅全集》及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某些篇目据手稿录入。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鲁迅作品虽经多位专家反复校勘,但仍不能称作“定本”,尚存在不少失校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譬如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致章廷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七日)中有“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一句,核对手稿,“鼻子傀儡”当作“鼻之傀儡”。又如《鲁迅全集》第十七卷,日记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项下印作:“晴,午得雷金茅信。孟十还赠《密尔格拉特》一本。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核对手稿,“自此以后”以下本是另外一段,不应与六月五日所写接排。这种地方,我们都订正了。
问:在编《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您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
答: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
且举一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继而又供给了《毁灭》之类作品。这正是编《编年文集》时体会所得。鲁迅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日记:“译《思想,山水,人物》迄。”——创造社、太阳社批评他“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何大白《文坛的五月》,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然而同年六月二日,鲁迅翻译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评谈会速记录》,推想起手移译当在译布哈林文之前。六月五日,鲁迅为《奔流》该期所写编校后记中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假如要给鲁迅文学生涯和思想进程的中、后两期划一界线,应该在译完《思想,山水,人物》与开译《文艺政策》之间。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中说:“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随后他自己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是为所译《文艺与批评》一书中的一篇;二月十四日,译完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所谓“新兴文学”,亦即无产阶级文学。四月二十日,所作《〈壁下译丛〉小引》有云:“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四月二十二日,“夜半译《艺术论》毕。”十月十二日,“夜译《艺术论》毕。”前一种系卢那察尔斯基著,后一种系普列汉诺夫著。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
以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翻译。他先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之作,如雅各武莱夫的《农夫》(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译)、伦支的《在沙漠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译)、理定的《竖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译)、费定的《果树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译)、皮里尼亚克的《苦蓬》(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译)、扎米亚京的《洞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译)等。鲁迅在为《竖琴》所写附记中说:“……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乃是试图通过“同路人”的作品来了解俄国革命;然而又针对《在沙漠上》说:“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一个于十月革命并不密切的文学者团体——中的少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只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不相类的也已不少了。”可见鲁迅不满足“同路人”之非真的左翼或无产阶级文学家。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法捷耶夫的《溃灭》(出书时改题《毁灭》)。二月八日,所作《〈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赞颂原著“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并针对书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说:“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在同年三月二日出席“左联”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之前,鲁迅已经开始为中国文坛奉献“先进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