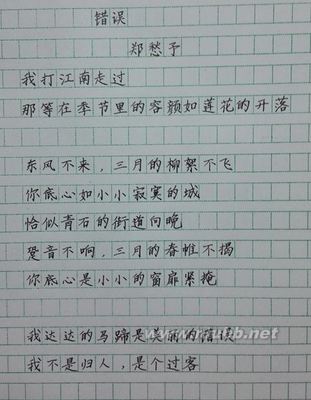◎ 文/本刊记者 陈佳冉
许子东实现从“人名”到“名人”的跨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0年前他录的那一集《锵锵三人行》。从此,在大学教书的“许老师”,研究郁达夫、张爱玲的“许教授”,插过秧炼过钢的“许知青”,统统淡出,留在公众视野里的是一个常在谈话性节目中天南地北侃侃而谈的文化人——许子东。
2011年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许子东的作品集,一套三卷——《重读“文革”》、《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越界言论》。书里有他历年来研究成果的展示,讲现代文学,讲郁达夫与张爱玲;有他走出讲坛,“越界”电视的言论,大到“9•11”小到“躲猫猫”;还有他个人经历的自述“废铁是怎样炼成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丰富的许子东,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一个可以“越界”但绝不“逾矩”的固执文人。
1.从“教书匠”越界“媒体人”
我相信,《锵锵三人行》是大多数人对许子东认知的起点。
着衬衣,打领带,戴一副眼镜,发型不乱。口齿清晰,语速均匀,带着柔和的南方口音。这是我初见的许子东,也是他在电视上十年一贯的样子。所以,听他讲话的一个多钟头里,有时竟有看“加长版”《锵锵三人行》的错觉。
“学校里的同行不会去看我的节目,也不关心。”许子东一语道破了“教书匠”与“媒体人”间的界限。
他说:“我的电视节目,对我在大学里的工作、职称等没什么影响。正面效应看不见,负面影响不想见。”学界或者同行也有人觉得他“不务正业”、“玩物丧失”,至少损失了研究的时间。但他的态度比较释然:“知识分子通过电视媒介走入公众也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你说了什么,传达了什么,而不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书本、报纸上的文章有好有坏,也不见得全是优秀的。”
《锵锵三人行》曾被媒体誉为“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事实上,它确是中国电视史上寿命最长的“谈话性节目”。筹备之初,曹景行就给许子东打过电话,说三个人的谈话节目,知识分子话题,每天录影。许子东一听“每天录影”,马上就说不行。“我是教书的,每周三天上课,怎么可能天天去录影?”
挂了电话妻子怪他,“有人请你做节目,你问也不问清楚就拒绝了?”妻子陈燕华曾在上海电视台主持儿童节目,是许多孩子记忆里著名的“燕子姐姐”。电视人的职业本能是做节目第一,做什么节目第二。许子东说,这和我们这一行的行规不大一样。我们写文章,应该是写什么第一,能不能发表第二。
真正拉许子东“试水”的是梁文道,香港颇为活跃的文化名人,《锵锵三人行》的“元老级”嘉宾。许子东对梁的最初印象是“相貌、衣着都挺特别。”2000年年底,梁文道致电许子东,说“三人行”想访问他一次,话题随意,他便答应了,不想就此展开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时一周几天,有时一月数次,一不小心,我在‘三人行’做嘉宾总数已在一两千集以上。以至于今天在Google或百度输入许子东三字,几十年教书生涯毫无痕迹,学术研究成果也少人关注,反而音频、视频和文章,大量都和我越界玩票的电视言论有关。”这个情况,完全在许子东的人生计划之外。
许子东做起半个“电视人”后,得到的反响是复杂的。因为电视节目的观众远比学术论文的读者构成要复杂得多。他自己归纳了三种反应:
第一种是北京知识分子的反应。如《文艺报》的应红(李辉的太太)对他说:“你怎么也去耍嘴皮子了呢?”学者陈平原等人要客气一些,不直说,但也暗示这不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你讲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吗?说了也没用。”
第二种是“凑热闹”群众的反应。许子东说,在公众场合被陌生人盯住看了半天,然后过来眨眨眼睛,拍拍肩,说:“你是何亮亮吧?”最后目的是打听“窦文涛住在哪里?”“孟广美嫁了意大利人了吗?”
第三种是忠实观众的反应。一次在深圳某大楼乘电梯,进来一老人,看了许子东一眼,半天没出声,最后终于说出三句话。第一句:“许老师,你们的节目很受欢迎。”第二句:“为老百姓说话。”第三句:“可惜黄山松太多。”(《锵锵三人行》在国内播出时,遇敏感内容,画面就被一幅“黄山松图”屏蔽。)
许子东把《锵锵三人行》当作他人在香港和故土同呼吸的一个渠道。早期节目还有编辑,每星期策划、写稿。后来,越来越依靠主持人和嘉宾的临场发挥——有点像爵士乐,大致有个基调、旋律,但演奏起来每次都不同,每个人皆有即兴发挥。为了改变知识分子不上电视的习惯,他还“拉别人下水”——李欧梵、白先勇、葛兆光、汪晖、陈冠中、戴锦华、郑培凯等。有的如王蒙、查建英后来成了常客。
窦文涛、许子东、梁文道是我们在“三人行”里能看到的最稳固的三角构图。许子东形容“三人都戴眼镜,目光不同:文道追求平等理念,子东珍视自由权利,文涛喜欢博爱和谐。”归纳起来——自由、平等、博爱,这不就是法国大革命时高举的旗帜?我想这种嘉宾间价值观的坚持和补充也是让“三人行”在每个社会话题中发出声音,尽量允执厥中,逾十年不衰的奥秘之一。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许子东说:“在电视里发言,远比做学问写报告困难得多。”对于媒体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有说话的资格,而不是说什么话。对于许子东的“教书匠”身份来说,或者正好相反。所以矛盾。
窦文涛老批评许子东和梁文道:你们为什么总想说些什么呢?你们不说人家就不知道吗?说了也没用,说了你们有什么好处?
好友吴亮(文艺理论家)也对他讲:“俗东西,可以讲成雅;雅题目,一讲就俗。”
有人说,写文章把一个人的优点放大;上电视把一个人的缺点放大。许子东至今仍记得钱谷融先生对他说过:“文章能不写就尽量不写,除非你非写不可,说话也是如此。”可人上了电视,也就身不由己了。
不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就是言不由衷,媚迎大众趣味。知识分子拥抱大众传媒,“堕落”起来比谁都容易。许子东抵抗这种“堕落”的策略是:不管哪种形式,在我看来,随波逐流然后到中流偶尔击水,虽书生意气但不敢也不能浪遏飞舟⋯⋯
2.从“伤身体”越界“伤脑筋”
有一次,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许子东和主持人调侃,说务农插秧弄伤了腰,做钢铁工人损伤了肺,后来弄文学是“伤脑筋”,直到做电视才真正“伤心”。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许子东身上有“知青”的影子。无论是在江西广昌的水稻田里“开头路”,28条蚂蟥缠上双腿;还是在上钢八厂轧钢车间“做盘条”,拉着热浪滚滚五六百斤的钢条,面不改色。看他在“废铁是怎样炼成——自己的故事”里娓娓道来种种细节,就像看一部反映那个时代青年生活的纪实影片,片子的主人公叫许子东,也可以是张三李四。
“如果是自愿,到今天也是伟大的”。许子东回忆“插队岁月”,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松弛。他说:“‘插队落户’概念上没有错,错就错在变成了全民运动,变成了强迫迁徙,用道德的口号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许子东从“开头路”的插秧能手身上看到了做一个农民的职业精神。他说:“我从不后悔自己在广昌的生活。教给我太多东西,我的生活从此不同。”
恢复高考后,许子东废“铁”从文。他一生经历过多次大学考试。第一次是“文革”工农兵大学生考试,未成;第二次是七二一大学;第三次是恢复高考时被取消资格;第四次是考华东师大研究生。如果说“入学”、“读书”对时下的年轻人来说好像“蹲监狱”,那时的许子东却是鲁迅所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心态。
“要让自己过去那被浪费的青春重新产生价值,唯一的途径是文学。”许子东给自己从小的文学兴趣找到了理性依据。杰克•伦敦说过,只有在文学艺术里,人生中的任何垃圾都是财富,任何失败都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变为成功。
许子东起步是写很多的短篇小说,关于知青高考,关于乡村初恋。先投《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文汇报》,被退稿;退一步投《萌芽》、《青春》、《清明》、《百花洲》,还是被退稿。他急中生智,将一份稿子寄给“上海作协李芾甘先生收”。大约是写了作家原名,巴金还真亲笔给他回了信,大意是“许子东同志,我虽写过一些作品,但不会评论。大作已转给我的一位编辑朋友,他们会答复你,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巴金的回信令许子东大受鼓舞,但那篇稿子,仍然没能发表。编辑回信要他修改,他拒绝了。
许子东有一句话:“我是个可以堕落的人,但不能在文章和女人问题上妥协。”
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时,许子东的导师是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他说“中国大学里‘先生’和‘老师’的称呼原来有重要区别,‘旧社会过来’的学者,称之为‘先生’。钱先生是‘先生’辈里最年轻的一位。”
钱先生并不授课,学生下午两点后可找他闲谈。每月一次讨论会,由一位学生准备报告,先生和其他同学提意见。第一个作报告的是后来因研究赵树理出名的戴光宗,“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居然一下子拿出一份上万字的讲稿,《试论胡适之五四文学革命的地位和影响》,云云。读完之后,我们均傻眼:太正式,太出色,几乎是篇论文。”下月轮到许子东,怎么办?
钱先生说:“你不是对郁达夫感兴趣吗?”
许子东匆匆恶补,两三周内读完郁达夫的几十万字小说散文,抛出一个一目了然的题目《郁达夫和日本》。做报告时,许子东心慌意乱,报告完了,钱先生改了六个错别字,说:“可以推荐到‘学报’,看看能不能发表。”
刚入校门,即在学报上发表论文,这是了不得的成就。许子东把它称作“从小到大,第一件可以称之为‘成功’的事情。”此后,他开始名正言顺地做起“郁达夫研究”了。
《郁达夫新论》的发表是许子东在学术上打响的第一枪。“我们那一代人几乎都是搞‘作家论’起步的,后来到海外读书,才知道那是老土的方法。”许子东说。
《新论》出版后颇受好评,浙江文艺以此编成一套“新人文论”丛书,作者有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蔡翔、程德培、吴亮等等。这也就是后来被研究当代文学批评者称为“80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一个基本阵容。
《新论》让许子东29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一度曾是全国中文系最年轻副教授)。此后,无论是邀请他去芝加哥做访问学者的李欧梵,还是邀请他赴日讲学的伊藤虎丸都是研究郁达夫的专家,彼此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新论》发表第二年,许子东与陈燕华结婚。因为年轻老师出版了专著,系里向学校打报告,校长袁运开特批,分给新婚燕尔的小夫妻一套住房。房子位于南京西路重华新村,弄堂清洁明亮。
十几年后,许子东才从陈子善的考证中得知,重华新村原是张爱玲的故居之一。1949年夏天,张爱玲就在重华新村的沿街公寓里,看着解放军进城。“原来我的‘张缘’,始于新婚之时。”前些年,许子东回上海,指与梁文道那被卖掉的“旧居”,梁感慨:“可惜!可惜!太傻!太傻!”
1984年,许子东在杭州参加了一次由上海作协主办的会议,与会者有李子云、茹玉娟、李陀、黄子平、阿城、郑万隆、陈建功、曹冠龙、陈村、陈思和、韩少功、李育杭、李庆西、蔡翔、季红真等等。这次会议对1985年的“寻根文学”有直接影响。
许子东回忆:“一向颇有抱负的韩少功很少发言,却在西湖边上散步时对我说:‘我回去要弄点东西出来。’”果然,会后他就发表了《文学的根》,触发了一个文学潮流。
岭南大学中文系有一次把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拿来做教材,书中放了一张“杭州会议”与会者的集体照,学生们惊讶地发现“子东老师竟然这么早就挤在‘文学史’里啦!”
3.从“插洋队”越界“慢船回港”
1987年,许子东初次越过“国界”,到香港讲学。香江纸醉金迷,楼宇林立,让内地学人眼花缭乱。
许子东说,“港岛高楼扑天扑地而来⋯⋯再看薄扶林道港大高级讲师宿舍,200多平方米全部海景,当时我愤愤不平:教的课差不多,为什么他们薪水四万多,住这样大宅和开两辆车,而我学校特批照顾才12平方米住房?我立刻发现自己是个贪图物质享受之人。询问如何可到香港大学教书,回答是要海外文凭及海外身份,‘至于学问,你已足够’。”
妻子在尖沙咀丽晶酒店的咖啡厅眺望港岛夜景,流光溢彩,由衷感慨:这一切应该出现在浦东外滩。
许子东回忆,1986年他曾受邀到复旦中文系开一门选修课:“郁达夫研究”,竟来了一百多名学生。很多当年的学生,现在遇到,都已是报社总编、集团经理、航空公司高层等社会中坚。那是他教授生涯中颇为得意的一段。但整整半年,每周骑车50分钟到复旦,学期末收到讲课报酬仅二百多元。之后不久,他到香港大学,在校外部讲当代文学,只有十来个不知戴厚英、白桦,不知林斤澜、汪曾祺的学生,随便闲谈两个小时,工资1600港币。
当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既做有意义的工作,又有合理的收入呢?
“十里洋场”此时比“东方之珠”,远远不及。
“出去”就“出去”吧。许子东说,“去做什么,不知道。总之,那个时候,突然间‘出去’像一个magicword,含义不清,魅力无穷。”“我们这些人总在被时代潮流卷携着。刚刚学会造反,就要下乡了;刚刚要扎根,就要‘上调’了;刚刚回到城里,人人要恋爱结婚了;刚刚分房安家,又兴‘出去’了⋯⋯”
学者许纪霖在访港后总结,说中国学者在国内是个“人物”(却不是自由人),到了海外是个自由人(却不再是个“人物”)。
从“人物”到“自由人”,这道心理界限的跨越,许子东是通过跨越“国界”,重做学生来实现的。
1990年,许子东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重做学生,做过“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和最佳节目主持人结婚,和一班全国有名的学者共商研究计划以后,突然又变回学生。“住厨房边的小房间,申请美国运通卡被拒,只花2500美金买的二手车因走错线收到264美金罚单,一天辛苦上课回来等着我的只有快速面和明天要交的英文功课⋯⋯”许子东说:“没想到,这么困难。”后来,李欧梵为许子东的论文集《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作序时说:许子东“随我到加大洛杉矶分校做研究生,这是一般人不愿为的‘下地狱’做法。”
令许子东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在UCLA构思关于张爱玲的论文的时候,张爱玲正住在他日日盘桓的停车场附近。一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讨论课在UCLA敞亮的课堂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一半的时间,人们在议论她。而被议论的“中心”就在学者文人的眼皮底下,和他们“同用一个邮局,同一家Kinko’s复印店,可能还曾同乘一辆巴士。”
后来,负责料理张爱玲后事撒骨灰入大海的南加大教授张错对许子东说:子东,你很可能已在街上或超市见过她,但擦肩而过,你也不会认识她。因为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张走在外边,只是一个baglady(流浪汉),永远穿2.99美元的中国产塑料拖鞋,衰老到毫不起眼的样子。
“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长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少女时代的佳句,晚年的她拒绝媒体,愈加神秘。显然是放弃了做个“人物”,却一定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插洋队”,受洋罪。许子东后来格外珍惜在乡村和在美国生活的记忆。他的结论是——因为在其他地方其他阶段,我都想努力追求事业,暗暗希望做一个有成就的“人物”。只有在这两个接受“再教育”的阶段,生活告诉我怎样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怎样做一个穷人。
一次,许子东在洛杉矶的一家旅馆见到王沪宁。两人一个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一个曾在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任教;一个29岁当上副教授,一个28岁当上副教授。同是“破格”选拔的青年才俊,曾经常在一起参加上海的各种学术活动。许子东在复旦上课时,王沪宁说他的课堂爆满,且前三排都是女生。异地重逢,王沪宁西装领带,刚见过美国国会议员,许子东汗衫短裤,典型的“穷学生”打扮。
“你在美国读什么书嘛!来复旦,先做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王沪宁劝许子东说:“中国正在发生极深刻的变化,外面还没意识到,比如说中国人家家有了冰箱,有了电话,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现在想想,他讲的也有道理。”
1993年秋,许子东回到香港教书,直到今天。
回港前,在加州的艳阳下,许子东与李欧梵促膝长谈。李说,假如你想继续你以前在中国的事业和影响,仍想直接为中国做些事,那就再去香港。
香港与大陆,这“稍稍离开一点”的距离让许子东找到了新的学术视角。在他看来,批评家对他研究的对象,不“进入”不好;太“进入”,距离太近也不行。
他说,香港是个从边缘观察中国的好地方。若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现象,太沉醉在“中心”或体制内,或精忠报国或愤怒绝望,都不容易看清庐山真相;但是距离太远隔洋眺望,不管极右抑或新左,却又常常隔靴搔痒。
1997年,许子东在香港完成《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一书。正在中文大学访问的汪晖将书稿推荐给三联。时任“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季羡林先生看过书名,即刻质疑“此书是否要为‘文革’翻案”?书稿送审很久,终于以《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出版。
王安忆说:“我以前认为读中文的人出国是浪费时间。看了你这本书,觉得也不尽然。”

⒋后记
“越界”的许子东,如今常被人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
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很了不起的称号。它不仅意味着这人是个社会学者,资历过关,并在某个社会研究领域严谨治学,拥有著作若干;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自己的丰富知识和强有力的笔头来分析热点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冷静而热情地为弱势群体说话,对抗大公司或者政府谎言,追求真相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比如乔姆斯基(NoamChomsky)、诺齐克(Robert Nozick)、罗尔斯(John Rawls)⋯⋯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走入公共领域,讨论社会话题,不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吗?在一个好的时代,固然可以畅所欲言;然则在一个次好的时代呢?不更需要有人出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吗?
钱谷融先生为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作序时曾写下这么一段话:
“日光之下无新事”。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世间并没有什么全新之物。但从另一意义上说,则任何事物、任何思想,只要你真正亲自考察过、体验过,就总会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自己特有的认识,自己特有的体会的。⋯⋯许子东的评论,自然不见得都得到读者的同意,但读者听到的,总的确是许子东个人的声音,总是在在是一种不同于他人的,他人未听过的声音。那就一定会使读者感到兴趣,并且有所启发。
对错不论,无论在书中,还是在电视里;无论是本行,还是涉及四面八方的各种话题,许子东的“越界”言论也总的确是他个人的声音,是他“心灵之眼关照过”、“感情之海浸染过”的独一无二的声音。
在“自己的故事里”,许子东回忆起父亲:“父亲晚年时,我问起过:40年代何以人在学术圈而参与医师公会的社会工作?忘了父亲是怎么回答的。但现在我发现,不知不觉,我现在不也在重复父亲的道路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