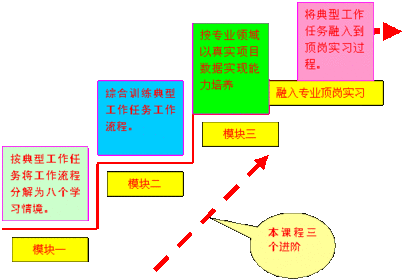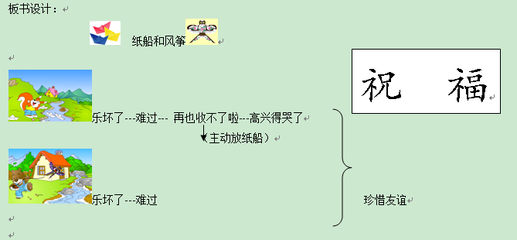陈曦从帐篷里钻出来四处了望:“靠,这他娘的也忒荒凉了,大漠孤烟直我是看了好几天了,怎么就不见长河落日圆呐?”
她疲疲塌塌拖着步子一辆车一辆车敲过去:“都起来都起来,凉快点儿了,开工了。”
八辆车,16个人,哼唧着爬起来,收拾帐篷,灌两口水,吃一快压缩饼干,开路。
这一行人来沙漠探险,最大的陈曦,四十五岁,可她那体力,那精神头儿,那火暴脾气,最小的王小彬,二十七岁,一米八六壮小伙子,都不敢不服。大家一起驴友了五年,这阿姨特豪爽特仗义,对了路子能跟你掏心挖肺的好,惹翻了那也是不死不休。
冯宁宁特自觉地爬上陈曦那辆沙漠王的驾驶室。陈曦从昨天黎明开到今天上午早晨10点了,开了三个路时了,该她了。
陈曦坐进汽车,又下去了,绕过车头拉开驾驶室的门:“去,后面趴着去,我开。”
冯宁宁不好意思,刚要开口,陈曦瞪眼:“少跟阿姨罗嗦,看看你那小脸,防冷涂了蜡是不是?”
冯宁宁没力气罗嗦,乖乖下车,吃了片扑热息痛,到后座上躺下,陈曦又削了个大梨,嘱咐她吃了,回身系上安全带,点火走人。
两个小时以后,陈曦也开得烦了。往后打死也不干什么沙漠探险了,这还不如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呢,都怪王小彬个死孩子,要不是他玩儿了命的撺弄她怎么也不会跑这么个荒漠来呀。接天连地一片黄,连个变化都没有,她都视觉疲劳了。还没个音乐,她瞄了N遍后视镜了,冯宁宁这丫头睡的那叫一个死,还打着小呼噜,她连音响也不敢开,奶奶的,凑齐了整她。
四个小时以后,黄沙尽头落日圆。好看,虽然还是没有长河,看了这么多天陈曦也没看够,随后第N次赞美,王小彬个死孩子,出的主意也不算太馊。
她按喇叭,示意前后的车停下来,她打算摄它几张影了。
头车王卓点上支烟,一手点着地图:“从地图上看,要是提点速度,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出了沙漠了。哥儿几个怎么说?”
“还用说,开呗。都举手,都举手,上路喽。”
“走了走了,阿姨上车。”
“阿姨你别拍起来没完,就那么个红心蛋黄你拍了多少天了?”
“靠,阿姨拍您的,拍够了才走,他再吱声我替您拍他。”
陈曦还真没拍够,可她知道时间紧,真入了黑在沙漠上开就危险了。她恋恋不舍地看着太阳,爬上车。冯宁宁睡醒了,烧已经完全退了,就是还有点儿软,她知道自己没精神开车就嗫嚅一句:“要不让别的车换个人来吧,阿姨您累坏了。”
“他们也累了,阿姨没事儿,晚上睡一觉就好,你再吃个苹果。”看她还要说陈曦一瞪眼。
冯宁宁爬到前面来,老老实实靠在副驾驶位置上啃苹果,不再招阿姨不待见。
现在陈曦成了后车。她打开音响,爽啊。
陈曦又一次看看车上的表,九点了,转头跟冯宁宁说:“呼叫头车,该休息了,我这老骨头可熬不住了。”
冯宁宁嗤地一笑,赶紧吐吐舌头,拿起对讲机。她还没说话呢,王卓焦急的声音已经传过来:“沙尘暴,沙尘暴,各车右前方200米处集合,右前方200米处集合,速度着。”
陈曦急打轮,加速,冲过去。沙尘袭来,什么也看不见。
晕了,可千万别碰上前车。陈曦嘀咕着。
雨季快要来了,也许再坚持几天就能得救了,可她们已经很难坚持几天了---她们的箭用光了。沙曼看看前方一眼看不到头的大荒原,荒原上密密麻麻乱哄哄的蒙泽人,又回头看看城墙下面伤残累累的士兵,缓缓地走下破败的城墙,来到中间的祈祷柱前,几个卫兵紧随着她。沙曼精神恍惚,身上烧的厉害,左肩上的伤一抽一抽的疼。
二十几天来,她们撤退了上百里,放弃了一道又一道防御线,她的卫兵数量从一百人减少到如今不足二十人,活下来的也各个挂彩,她自己的左肩也厚厚地包扎着。
看看天空,积雨云正在缓慢地形成。
苍天之神,请怜悯我们吧,我们在你之下匍匐祈祷,求你别抛弃我们。沙曼艰难地把双手高举向天空,虔诚地祈祷着,这个动作让她的左肩痛得要离体而去。
她放下双手,再次看向那片曾经的镇子,如今的废墟。
每隔三五年,大荒原上的蒙泽人必来一次劫掠。茨夏,这个流放者的国度,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轮回着建设,被摧毁,再建设,再被摧毁的命运,人口已经从近两千万成了如今的几百万,而沙曼的宁诺一族现在只有不到三万战士了。若苍天之神不与护佑,或许不用沙曼培养出继任者,宁诺一族就不存在了。
一股大力传来,沙曼不由得向前栽去,几个卫兵从后面使劲全力拉住她。
一个深绿色的庞然大物凭空出现,伴随着刺耳的声音,从她面前冲过去,停在十几步远之外。
陈曦一脚急刹车,随后一拍脑门:“完,没见过我这么笨的蛋,弄个破海市蜃楼还让我当真了。”
“我怎么觉得是真的呀,等会儿,阿姨你没觉得不对吗?刚才咱们都开了大灯了,现在怎么看着也是白天呢,再说你觉得没,好象这个天气也不对啊,还有,他们呢,大伙儿呢?!”冯宁宁语气严肃,还带着种说不出的情绪,让陈曦一凛。冯宁宁是个医生,通常是个爱笑爱闹的好孩子,她要严肃一定是有事儿。
陈曦不敢造次,连忙定了定神仔细观看,还真看出点儿意思来。
夕阳照着破破烂烂的残垣断壁和倚靠着残垣断壁的残兵败将,这些人长着欧洲人的脸形,亚洲人的皮肤,穿的是粗糙的麻质上衣,无袖无领,麻质皮质短裤,露着半截腰,大部分人衣服破烂,带着血渍,无精打采,呆楞楞地望着陈曦这里。还有些人正慢慢向这里走来,带着一丝犹疑,一丝试探,一丝好奇,还有点儿,敬畏?
那什么,这个是哪个民族?还有这些人的衣服和装扮,中国古代好象也没有女战士吧?要不这个是亚马逊女战士?可那个,不是传说地干活?
这些人,我靠,有这种人吗?
陈曦愣了,她看见几个高鼻深目的生物,墨绿的头发,粗糙的袍服覆盖着脖子以下脚趾以上全部身体,腰上根粗布带子,说不清为什么但她就是知道那是雄性,不敢说是人是因为他们的脸上好象是银白色的细细的鳞片。她猛回头看看冯宁宁,她也正呆愣愣盯着她。
“宁子你掐我一把?”陈曦很不确定地说。冯宁宁犹豫了半秒钟伸手狠掐了陈曦一把。
“唉呦唉,你个丫头这么狠?!”陈曦怒瞪冯宁宁。
冯宁宁哆嗦了一下,转头看看车窗外,又回头看陈曦,眼里带了惊恐。
陈曦赶紧安慰她:“没事儿,别怕,有阿姨呢。你坐这儿等我。”说着回身把后坐向上抬,掏出一把小巧的手枪塞裤兜里,一把81-2刺刀插靴子里,又掏出一个TOPS格斗手刺,冲冯宁宁一乐:“阿姨有了这个,万马千军不在话下。”说着,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陈曦跳下去,好些人跪下去,伏低了头趴着。她往前试探几步,更多的人跪下去趴着,等她走到车前面,所有人都跪下去了。
沙曼听见砰的一声,然后看见那些人一个个跪伏在地,她有点儿迷惑,心里又觉得有点儿明白,好象还无端带了点儿期盼和喜悦,然后她看见了陈曦。
多年以后沙曼给她的孙女讲述她第一次见到圣武皇帝的时候,脸上依然带着喜悦。这些内容被记录在鸿蒙公爵回忆录中。
“我在第一眼看到陛下的时候就知道,茨夏得救了,苍天之神听到了我的祈祷,派了神使来拯救我们。我到死,到我的灵魂消散之际都会记得陛下当时的样子。
陛下那时候是红头发,很短,比现在男人们的头发还短的多呢。陛下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闪着光的,别提有多么好看了,我是说衣服好看。至于陛下么,陛下那是英俊,你明白吗?别提多英俊了,我当时就明白只有神的使者才能那么英俊。
我胡里胡涂的就走到陛下跟前去了,陛下看了我一眼我才知道我犯了多大的错,我竟然没跪下行礼,你说,丫头,我可有多糊涂。可是陛下一点儿都没责怪我冒犯,等我跪下行礼,乞求她拯救我们的时候,仁慈的陛下居然扶我起来了,还让她的仆人,我们的圣医大人给我治疗伤口呢。
我跟你说丫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说我是个有福的,到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才终于相信,我呀,还真是有福的。不过我的福气还没你的大,所以你呀,要好好的给陛下效忠,才能报答陛下的恩泽于万一。”
这最后一句话成了沙曼家的祖训,也是很多茨夏人的祖训。
冯宁宁第一次看到这段对话的时候笑的满床打滚,完了驾车直奔皇宫告诉了陈曦,陈曦听了就拍着龙案乐得前仰后合,冯宁宁本来不那么乐了,看她乐成这样就又乐得满地打滚,一边指着陈曦鼻子:“哈哈,神使,天下第一大骗子!”
陈曦大怒,回指着她:“你个傻丫头,人家说你是我仆人,还美呢。”
冯宁宁立时敛了笑,坐起来嚷,你应该给我封口费!
陈曦乜视:还封口费,我拿胶水给你粘上好不?!
沙曼伏身跪倒,左肩的伤让她疼得浑身颤抖。她竭力忍着不断袭来的眩晕,亲吻了陈曦的鞋子,高呼着:“苍天之神,感谢您的降临,请您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苦海。”
不过当时,陈曦完全没能预想到她后来的伟大,她也不想冒充什么神,因为冒充不来。可是她又是个聪明的女人,一人打理着拥有几万员工的跨国公司,当然,这句话她哥哥们,她的总经理们,她的死党兼总财务主管可能不敢苟同,不过既然他们都不敢公开跟她叫板,她就假装不知道了。
话说回来,陈曦是个聪明的女人,所以她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听了会儿沙曼的呼喊,她得出一个事实:他们的语言她完全懂,但是就素不盟白他们索滴四虾米易西。
陈曦看过几篇穿越文,玄幻啥地,也看过关于平行空间的文章,可她从不不信那鬼话。不过她也可以肯定,这个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际存在。她再踅摸踅摸,王卓他们的车一辆没有。掏出手机拨王卓的号码,没信号,靠,再拨王小彬,还没有;她望望天,心跳的厉害,很可能是真有问题了。
妈的,哪个白痴二百五跟你阿姨开这类国际玩笑呢?有种下来咱们单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