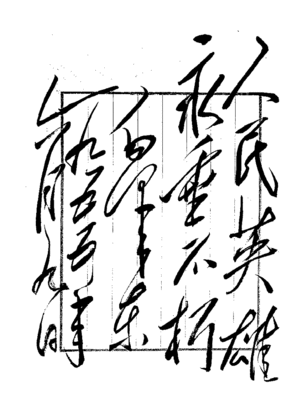感谢张老师精彩的序和鼓励!
序邓小川诗集《微风如你》:穿过黑夜的火车(序一)
张德明
迷醉于石椅上的梦境
一阵断然的鸣笛
划开寂静的夜空
一列火车开进了黑夜
猫舔舐流血的伤口
秃鹫,断翅
忍着巨痛奔跑,一列火车
驶进了我们的睡眠
梦里有猫的脚印
还有一群扑棱的鸟
一列火车就这样
带走了我们的心跳
——《穿过黑夜的火车》
阅读邓小川的诗集《微风如你》,这首题为“穿过黑夜的火车”的诗章,给我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在黑夜笼罩的茫茫旷野,带着巨大身形和无穷耐力的火车,穿过了数不清的时间和空间,承受了难以预知的无数寒冷、风雨、黑暗、孤寂等自然险境,它毅然决然地向前,直到如愿抵达目的地。从“一列火车开进了黑夜”的诗句中,我突然领悟到的,并不只是诗人通过艺术形式所虚拟和构想的景致,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心声,那从诗人的内心深处涌荡出的对生活质量的热望,对生命高度的追寻。我深知,某种意义上,这辆奔突在黑夜中的“火车”,或许正是诗人的自况之词。
从精神层面上,“黑夜”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正视的一种生存场景。一百多年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发出过“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的理性诘问,那是在西方世界面对“上帝死了”的精神局面下,一个具有着历史责任和艺术良知的优秀诗人所发出的大声疾呼。在当代中国,我们也同样遭遇着某种精神的危机,遇到了无法逃避的“黑夜的时代”(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语境的日益形成,物质化的利益追求已经取代了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审美追求,逐渐成为国人主要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曾经作为“文学中的文学”的诗歌,便沦入不断边缘化并最终淡出人们关注视野的历史命运。而作为如邓小川这样的80后青年,在他们的学习阶段,在他们人生的重要成长期,无疑就亲眼看见了文学从中心向边缘滑落的残酷现实,更为残酷的是,当这些青年出人意外地喜欢上了诗歌,迷恋上了缪斯,他们拼命读书、写作,将无数激动和兴奋的夜晚,兑换成了诸多分行的诗意文字,但他们的文字,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也无法用以改变他们的生存处境,他们内心的惶惑、不安与对诗的酷爱纠缠在一起,扭打在一起,一种富有悲剧意味的宿命,就此形成。邓小川所提炼出的那“忍着剧痛奔跑”的“火车”意象,勾勒的不正是以他为代表的80后诗人们共同的精神缩影吗?
尽管80后诗人们一开始就遭遇到了一个并不如意的文学环境,但艺术本身存有的神奇魔力是能够穿越一切时代的雾障,捕获人类心灵的,它可以令所有走近的人都为之心潮起伏,为之忘乎所以,为之奋斗终生的。何况,文学史上影影绰绰的文学前辈,那些有着传奇的人生故事和美丽的诗章文句的诗歌先行者,是80后一代不可或缺的人生榜样和精神导师,他们的存在和受人敬仰,无形之中也增强了80后一代钟爱诗歌的信心。毫不夸张地说,每个80后诗人都是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导师的,邓小川的精神导师也许正是海子,他酷爱诗歌的心灵追求,也许是阅读了海子的优秀诗歌,受到了强烈的美学震撼之后形成的,而他的诗歌中的很多意象、情绪乃至思想,都留印着海子的显在影子,比如“春天,听你讲述/人类回到童年,万物光彩夺目/三颗星:一颗悄悄诞生/一颗穿上雨鞋,寂然隐去/一颗永驻心间/守候人遥远的童年”(《春天·海子》),“在雨水中的桃树下/神在说话”(《对话》),“恋爱的女神带走了干粮/四月的马蹄向西”(《碎》),等等。邓小川描写岁月感知和季节中生命迹象的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习得了海子诗歌的真髓的,例如《四月,忘记所有的雨水》一诗:
四月,忘记所有雨水
疼痛的羊羔自山坡而下
雨水绵绵
更多的人从远方来
四月,雨水齐聚河岸
淹没村庄
此地汪洋
我们唱一支离散的歌
忘记了生殖的使命和人类的快乐
忘记恩泽
四月,我们齐坐河岸
荒芜打湿双睫
雨水浸漫的四月是令人难忘的,在这个一片汪洋的四月里,诗人打算“唱一支离散的歌”,并且准备“齐坐河岸”,看“荒芜打湿双睫”,这些的诗意绘制,给人以某种心难平静的刺痛之感。读这首诗,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海子,想到他的“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的不朽名句。
还有这首《八月》,也可以说在许多地方都与海子诗歌有着密切的灵魂沟通和精神握手。诗歌如此写道:
在八月光芒的日子里
让我用强过太阳的烈焰
在众神飞翔的大地深处
在精灵安息黑夜的中心
用一万颗烈士的头颅
画下绝世的祝福
在光芒高过一切的八月
让所有的道路染上你的病疾
在诗中出现的一些语汇和意象,如“众神”“飞翔”“黑夜的中心”“光芒高过一切”等,也是海子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语词,而这首诗所呈现出的神秘气息和宗教意味,无疑流淌着海子式的精神血液。
因为学习海子的优秀诗歌而迷恋上缪斯,因为借鉴海子的艺术创作而使自己的诗艺不断提升,80后诗人邓小川是幸运的,他在诗歌上迈入的无疑是一条正途。然而,由于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语境里生存,物质欲望甚嚣尘上,金钱崇拜大行其道,世俗的镣铐,锁住了人们飞翔的翅膀,遮没了人们遥望的目光,邓小川选择诗歌创作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又多少有些无奈,多少有些不幸,这不幸的遭遇,其实在诗人那里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读读他的《路途》,我们就能隐约窥探到诗人的心迹:
路途遥远,迢迢无期
马匹走失平原,故乡
就像诗人的归隐
看不见飞翔的翅膀
思念安坐,抵达季节的车厢
闪电快过一切速度
还是那辆“穿过黑夜的火车”,如果说最初驶入黑夜的时候,它是带着无视一切困难的气势和果敢,一路狂奔,勇往直前的话,那么当它行驶了一定路程之后,便可能会自然而然产生“路途遥远”的想法。这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是自我生存的确认。意识到路途的遥远,意识到困难的不凡,就会不断增长心智和慧眼,就会慢慢去却莽撞和虚妄,变得成熟而老练。从《路途》的文字中,我察觉到邓小川思想的不断成长和情感的日益丰富。
穿过黑夜的火车,尽管有着一往无前的雄心壮志,尽管有着使不完的奔突能量,但过度地奔跑,一味地冲刺,还是免不了有需要喘气的时候,需要歇息的当儿,因为身体的不停透支,还是可能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积劳成疾。在《我写下一些病重的词语》里,我们似乎看到了那辆“火车”身体上的不良反应:“胃胀像饱食的后山/母亲摸黑咽下两片止痛药/夜晚,我写下一些/病重的词语,不断堆积//抒情,惊醒夜/文字喘息,像母亲的骨头/坚硬,却不堪一击”。在精神的世界里,诗人永远是王者,是无法打败的猛士,但在现实面前,诗人却必须适当低下高昂的头,尊重身体的运行规律,不宜做永不休息的永动机。诗人可以把自己拟想为黑夜中不断奔突的火车,那是精神上的战无不胜,但从生理学的角度说,人毕竟是人,不是火车,即便是火车,也会有快有慢,也会停停走走。在此基础上,我一方面欣赏诗人作为穿过黑夜的火车的那种精神上的自觉,一方面也愿提醒诗人,要在可持续发展上做文章,厚积薄发,“早熟而晚成”(木心语)。这个角度上说,我有时更喜欢《慢》所呈现出的生活节奏:“青草如梦,杨柳轻柔/午后,我们静卧向阳坡/远处车辆川流不息/近处静水流深鱼儿跃//两极世界,我们心境平和/忘记炎热忘记喧嚣/漫无目的,话语点缀时光/拉下黄昏的遮羞布”,“心境平和”“漫无目的,话语点缀时光”,这是多么惬意爽心的存在样态,这是多么令人艳羡的生命场景。我赞叹火车的奔突,那是意志的大写,我更喜爱午后的闲暇,喜欢傍晚的宁静,那才是舒爽真切的人生。我想,作为80后诗人的邓小川,随着生活阅读的增长和创作道路的延伸,一定会越来越同意我的观点。
诗集《微风如你》收录了邓小川从2006年到2014年这8年多时间创作的百余首诗,这些诗歌是按创作时间的先后编排起来的,这样的编排方式不仅遵从了诗歌诞生的先后顺序,也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诗人艺术探求的前行轨迹。整体上说,邓小川早期诗歌的模仿痕迹稍微明显些,尤其对海子的借鉴印记过重,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尚未建立,而2010年之后,他的诗歌开始摆脱海子的影子,逐渐呈现出自我风格,从意象的使用,到诗行的安排,到语言的组织,都慢慢凸显出个人化的美学特性。早期诗作显而易见的稚嫩性,可以通过创作于2007年的《晴朗》一诗来感知:
晴朗的日子
有些干燥有些炎热
有些幽静有些旷远
白云如我放牧的羔羊
又似母亲种植的棉花

点缀我们的眼睛
幽深的天空
挂着片片蓝布匹
如同跳动的只只羊羔
“晴朗”是一种美好天气的描述之语,晴天带给人的心灵愉悦和视觉享受应该是绵绵不尽的,因此,对“晴朗”这一自然风景的诗歌写照,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路径。王小妮的《我感到了阳光》是写“晴朗”的一种方式,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是书写“晴朗”的一种方式。邓小川的这首诗直接以“晴朗”为题,本身就为自己的写作预先设定了难度,因为“晴朗”是一种抽象性的语汇,缺乏具体而微的特定物象,而诗歌中的比喻又显得陈旧和老套了些,不够新奇和别致,这就自然影响了诗歌整体上的艺术质量。我认为,诗歌中的比喻一定程度上是诗人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感受力的直接折射,要想使自己的诗歌能在艺术水准上更上一层楼,想象力的培养和理解力、感受力的提升是必要的。早期诗歌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时期对很多诗人来说,都处于艺术的自发阶段,远没有达到成熟和老练的境地。随着写作历练的深入和人生阅历的丰厚,诗人的创作自然会达到新的层面,体现出明显的腾跃。邓小川的创作轨迹就遵循这样的规律,他在2010年后创作的一些诗歌,如《持灯的使者》《凌晨五点的歌者》《城市灯光照亮的夜晚》《在四月的孤独》等,都是质量不俗的佳作。
那辆穿过黑夜的火车,载满了诗情与梦想,它仍然在一往直前,没有停靠下来。像火车一样坚韧、奔突的80后诗人邓小川,他的诗歌,还在生长和蜕变之中,远没有达到顶峰,他的文学未来,的确值得期待!
2014年8月29日,南方诗歌研究中心
(作者系广东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兼职教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