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如何向外人道中国
向美国人讲述和解释中国,始终是件让我挠头的差事。虽说生长在北京,但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往来于中美之间度过了大部分成人岁月。时光如箭,然而,刚到美国时碰到的那些关于中国的提问,让我至今记忆如新。那是1981年。那年,我到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市。21岁的我之前从未坐过飞机,讲一口嗑嗑巴巴的烂英语。中国此时已经启动了它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但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国内也还没有“托福”考试。作为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获得奖学金去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英文系读书,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奇迹。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奇迹背后的主要原因:南卡大学英文系在历史上从未接到过一份来自中国大陆的入学申请——不是台湾,不是香港,而是来自那个红色大中国的申请!显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录取这名勇敢的年轻申请人的诱惑大到难以抗拒。我现在还能记得英文系系主任罗斯?罗伊(Ross Roy)博士是多么地乐于带我在校园中漫步,兴高采烈的他,甭管遇到什么熟人都会这样介绍我:“这位是查小姐。”然后卖关子似地停顿片刻,接着爆出我的惊人来历:“她来自北京,中国!”
最初的美国生活令我手足无措又兴奋不已。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拉里?拜戈维尔(Larry Bagwell)——一个来自美国南部的、身材高大但特会关心人的帅小伙儿,我英文系的同学,我第一个美国“哥们儿”——开始让我给他解答各种关于中国的问题。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俩课后喝着可口可乐,坐在草地上闲聊。“简,”(因为老美们根本无法念对“建英”的发音,我请求拉里给我起了这个英文名字)他问我:“中国人真的会把炸蚂蚱沾上巧克力酱当作美食来吃吗?”“什么?”我眨着眼睛,差一点被口中的可乐噎着。我知道“巧克力”这个英文词,但是,“蚂蚱”是什么?
如果这还算是半开玩笑的问题,接下来拉里的发问则显得颇为郑重其事:“中国有电视节目吗?比如肥皂剧和情景喜剧之类的?说实在的,中国人家里有电视吗?”没等我回答,他就带着歉意地补充道:“我们对中国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这儿有些人还认为你们那里连电都没有呢!”我瞬间如释重负,而这次交谈也因此嵌入了我的记忆。我发现,原来并非只有我对地球上另外一个大国、它的人民和文化一无所知。虽然我把“肥皂剧”听成了“许多肥皂”,但至少我听懂了英文的“电”和“巧克力”这些单词,这真是个超级棒的开始!那时我就知道,美国难不倒我。
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的祖国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的巨变!我更无法预料到,拉里不经意间把陌生而怪异的英文词“肥皂剧”甩给了我的14年后,我会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还用了这个词:《中国波普:肥皂剧、小报和畅销书如何改变着一个文化》。
2008年,拉里终于踏上了探索那个“吃炸蚂蚱沾巧克力酱”国度的旅途,他和他的女儿登上了越洋航班飞往遥远的中国。在寄给我的信中,他兴奋地描述了同女儿一起骑着自行车漫游浙江农村的见闻,在唐代僧侣诗人寒山打坐的天台翠屏山山洞里体会到的感悟,在上海的疯狂购物。“我们在这儿过得妙不可言,”拉里写道,“不管走到哪里,遇到的中国人对我们太好了:你的同胞们真是些热情好客、慷慨大方的人。”我很高兴,给他回信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当年对我的善意和帮助,但看起来我的同胞们正在帮我偿还一些欠你的旧债。”
我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童年的记忆中穿插着一些无以释怀的画面:七岁时的那个恐怖夜晚,父母被批斗,家里被一群陌生人抄得底朝天;亲眼看见邻居被殴打致死或是从屋顶跳楼轻生;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中每月收到他从干校农场寄来的信;学校里每天都有的政治课以及课外读物的匮乏。1977年高中毕业时,尽管毛泽东已于一年前去世而且“文革”已经结束,我们还是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插队务农。在一切都还动荡不定之时,共产党领导层匆忙扭转了毛的一些政治实践,并把国家推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比如重新恢复已经被停止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那年秋天,我回城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和村民们正在田间耕地,消息传来: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此生难忘1978年的春天,我初入北大校门后欣喜如痴的那些日子。我那年18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而许多同学则已经在工厂或者农村度过了十年甚至更长。我们做梦都不敢相信自己生命中会有这么一天——在中国最高学府读书!对于那些还记得红卫兵时代的人和第一批改革的受益者、一群经历了幻想破灭但又理想不死的人来说,“七七级”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和传奇。这一代人在激进的政治烈焰中遍体鳞伤、青春早逝,但对国家前途的使命感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生命之光。若干年之后,七七级的学生中很多人走上了政治、商业、学术、文化和传媒等领域的领导岗位,其中许多正处于职业生涯和影响力的顶峰。他们形成了当今中国新体制中的一个精英阶层。
我选择的路与同学们稍稍不同。北大的同学们认为我去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同学称其为“美国的贵州”——是迹近神经错乱之举,失去了毕业时唾手可得的、优厚的工作机会。但是,不管是出于我与外祖父之间某种遗传的因素(他上世纪初离开湖北老家赴法国求学),还是出于对外面世界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和对冒险的疯狂渴望,我就是要走出去。南卡罗莱纳构成了美国留学生活中令我陶醉的、田园般的序曲。正是在那里,我发现了弗兰纳里?欧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猫王”的不朽魅力,还有那些大烟山脉中带着吉他和大麻的宿营以及南方农场里马背上的时光。
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我爱上了后来成为我第二故乡的纽约。然而到了1986年,正值我对成为职业学者的前景越发焦虑不安、爱恨交织的当口,我内心感到了故土的呼唤。国内造访纽约的朋友和北大同学兴奋的来信给我勾勒出一幅画面:文化、知识界被变革之风吹得躁动不已,藩篱被一片片拆除,新的观念和做法不断被付诸实践的检验。听上去,此时的中国像极了一块希望四射、机会无所不在的浪漫热土。我一直想当个作家,一个置身祖国变革和进步过程中的作家。
1987年,刚刚通过了博士学位资格口试,我便启程返国。接下来激动人心的两年让我终生难忘。我重回大学同学们的怀抱,结识了许多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新朋友,写作并出版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参加了形形色色针砭时弊的政治、文化类的讨论会,帮助创建并参与编辑了独立刊物。1989年春天,我作为助理为《纽约时报》工作。在此之前,应中国著名导演张暖忻的要求,我还把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行色匆匆之中,我原本计划进行的中国“文革”文学与美国越战文学的比较研究被束之高阁。
1989年5月,我辞去《纽约时报》的工作。不久我回到了美国,被迫中止正有起色的中文写作生涯的打击,忽然间意识到我不得不在美国永久安家,如果不想完全放弃写作就必须尝试用英文代替中文??所有这一切,将我拖入了一段抑郁和茫然。在随后的日子里,通过自己的坚持和与一些友人的促膝交谈,再加上点运气,我慢慢从阴霾中走了出来。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在芝加哥心理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论坛,会上高质量的讨论让我见识了美国知识人的活力。论坛的主持人是李湛忞,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我在会议中结识了两位优秀的作家:大名鼎鼎的记者简?克莱默(Jane Kramer)和小说家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她们的鼓励和友谊启发了我,我不再把用英文写作仅仅看作是一种被迫接受的挑战,更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之旅,而这一旅程将给我一双新的眼睛和翅膀。
上世纪90年代期间,在工作、婚后生活和回国调研之际,我完成了我第一本英文书《中国波普》,每月为香港一家杂志撰写专栏,为《美国之音》录制散文札记。丈夫转到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任教,女儿斯蕤在那里出生。那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向休斯敦的郊区式生活让步投降。但是,我忘不了中国。2003年,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写作奖金,丈夫也恰好有长达一年的带薪假期。女儿在休斯敦长到了七岁,但我们培养孩子双语、双文化的宏伟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于是,当年的8月,怀揣着兴奋和无限的期待,我们一家三口打好行装,回到了北京。
说来惭愧,到了北京我才发现,原来七岁的孩子在吸收新语言和融入新文化上比成年人灵得多,哪怕这个成年人是个重归故里的本地人!刚到北京时,斯蕤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成天不是宣布“中国学校是监狱!”就是叫唤“我天生就是要玩儿的!”但不到一年,她的成绩就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能用北京俚语与邻居以及她的新朋友们叽里呱啦地聊天儿了。与此同时,我却仍然在左试右探,东寻西找。我计划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虽说这个新的北京还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这个新的中国还是我的祖国,但与我上次住在这里时相比,一切再次发生了让人瞠目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惊愕、兴奋、充满好奇而又一头雾水。这座城市满眼赫然耸现的摩天大厦背后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每周都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那些看上去精力无限、终日奔波的人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快乐、兴奋吗?是否充满了希望和梦想?还是沮丧、疲惫和晕头转向?就我个人来说,我有时甚至弄不清自己是着了魔还是置身云端。但是,我决心找到重返中国生活之路,我不想如异乡人那样去写自己的故乡。
我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参与到北京的文化生活里。重拾旧友与结交新友之余,我担任了北京一家时尚生活杂志《乐》的顾问和特约撰稿人。为了亲身体会北京城的脉动,我和《乐》的年轻记者们跑遍了京城,捕捉和采访那些鲜活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话题和人物。
为了体验一把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经历,我做了件每个当地房主都会做的事:监理装修我的北京公寓。但是,真正把我拉进中国公众视线的是我的中文新书《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其实是对12位极富反思精神的杰出人物的访谈录,它从文化角度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铺垫了最终通往事件之路的关键十年。书中12个访谈对象大都是艺术家、学者和知识人领袖,其中一些人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当中有六位曾旅居海外多年,然后又回来,就像我一样。对我来说,或许也包括对他们,这本书使我们内心对那个以悲剧落幕但却意义不凡的十年有所释怀。
2006年书出版之后,媒体如潮的报道和读者热烈的反响令我大感意外。《八十年代访谈录》竟然在很多书店的销售榜上位居前列,并搅起了一股怀旧思潮;年轻读者们也对那个他们几乎不了解、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燃起了好奇之心。公众对国家那段记忆断层的讨论接踵而至。评论家们认为,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审视过去以及造就一个文化复兴的需求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兴趣,催生了更多对被忽略和被压抑的当代往事进行探讨的书籍及电视节目。2010年,《八十年代访谈录》被评选为上个十年中全国最具影响的书籍之一。可以说,是公众对此书的关注把我卷入了媒体,此后我频繁地被邀请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对各种大众关心的话题发表评论。
那段时间里,我已完成了《弄潮儿》的部分初稿,并接受了一家美国研究机构驻中国代表的工作,这份要求经常飞往印度和美国的工作占去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知道自己的战线拉得有些过长,我也意识到在激烈的公众辩论中失去理智可能招致的风险。但是,与志趣相投的人们共同推促有意义的变革,以及为建立一个更民主、更人性化的中国做些事情的机会让我无法割舍。随着与各种媒体打交道的增多以及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做了固定嘉宾之后,我逐渐读懂了中国新闻媒体人的老练与成熟,他们躲避风险的本领和周旋的战术。而在这些背后,是他们为推动言论更加自由的顽强努力。
当然,我永远都会记得叶利钦去世后那个星期录制节目的情景:讨论话题是叶利钦给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留下了哪些遗产,刚刚录制完,未及我们走出录像棚,便得知那期节目没过关。化妆间里,每个人都在一根接一根狠狠地吸着烟,愤怒和失望弥漫整个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录制,内容换成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但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摧毁大家继续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推进的决心,尽管这种努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谨慎。我为自己不再仅仅是个旁观者而满怀喜悦,我终于找到了重归中国生活的道路。
由于对在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局面有了某些感同身受的了解,我在讲述书中人物的故事时,一方面尽力保持清澈的目光,同时笔端又常带同情之心。我一面努力深入探究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内心世界,一面积极整理为写作收集的大量信息和素材。同时,为了能更好地描述一个在自己的历史负担和未来目标之间苦苦纠结的社会和人民,我不得不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而冥思苦想。我当然明白贪多嚼不烂的道理,人总不能见着一头牛就想张嘴吃到好牛肉,何况中国这头牛是如此之大,无人能轻易下嘴。我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农村的生活,小镇的故事,在大工厂劳作的新移民们,这些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写作题材,许多优秀的作家也正在写这些题目。内地乡村持续的贫困,沿海工厂里农民工此起彼伏的骚乱,司法不公与官员腐败,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自然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既紧迫又重要的事情都值得给予特别的和持续的关注。
但是,我最了解的还是大城市。作为一国之心脏的大都会,巨大的财富在这里源源涌出,剧烈的政治和思想较量在这里展开,巨型的文化企业和传媒机器在这里运转。她是一国之精英的大本营和家乡,是吸引四面八方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青年才俊前来一试身手和争取荣耀的圣地。在城镇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在中国于新千年之际再次崛起为强大国家的历史时刻,八面来风、群英荟萃的大都会成了中心舞台,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人们激情四射的奋斗和光怪陆离的社会大剧。特别是北京,它正向外界传递着国家机器掌控者的姿态,国家前途探索者的思考。
我是北京人。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大城市中——北京、纽约、南京、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劳德尔堡——北京和纽约是我的最爱。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城市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驻扎在我的灵魂中,那就是,而且永远都会是,北京。在这块饱含历史和记忆的土地上,你可以领略到浑厚的文化,令人炫目的国家庆典,放浪形骸的艺术家部落,风趣的北京方言,这样那样的宏伟计划,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以及大大小小的悲喜剧。在我眼中,毫无疑问,北京是中国最伟大的大都会。
但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个北京,悠悠然中似有沧海桑田之变。尽管宽阔气派的大街、美丽的皇家公园和苏联风格的纪念碑依然故我,但街上自行车的长龙、蓝灰两色衣装的人群、各处的毛泽东雕像已全然不见踪影。如今的北京是个巨大的都市丛林:风格前卫的地标性建筑,俗气奢华的购物中心,大型的封闭式小区,日渐萎缩的老胡同邻里,路面上拥堵的车流和地铁里穿梭不息的乘客,身着国际时尚服装的少男少女,农贸市场里高声讨价还价的老头老太。
2005年夏天,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纽约客》杂志建筑评论家、帕森斯设计学院院长——第一次访问北京,我带着他四处去转。他极其热切而专注地游览了几天,然后对我说:北京让他想起了休斯敦。我的心都碎了。必须承认,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休斯敦。30年马不停蹄的拆迁和大规模不计后果的建设,难道只是把北京这个东方辉煌帝国的庄严象征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变成了??休斯敦?我心情大坏,一言不发,一连几天都对保罗心怀忌恨。但我又如何能与他争辩?以其专家之敏锐,保罗的这句概括实在是一针见血。刚搬回北京时,满眼硕大粗蛮的新建筑,不也曾让我郁闷不已?而且,从北京朋友们口中,我听到过远为难堪的评论!
不过,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坚持认为,北京一直是个伟大的城市,并且至今未曾改变。它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其建筑的风貌,而在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正是这些数以千万计的人们赋予了北京与众不同的性格和独一无二的品质。在受到刺激的情绪平复以后,我劝保罗一定要再来一次北京,尤其是要接触、了解一些北京人。我在心里对他说:真的,如果你懂这里的语言和这里的人们,你就会明白,在物质环境之外,北京与休斯敦是多么的不同。北京永远都不会是休斯敦,哪怕再过一千年。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的评论帮我找到并敲定了一个基本的叙事原则,我确信这是最好的方式,并最终将其贯穿本书始终:以聚焦中国人去诠释中国。如果北京是我选择的中心舞台,我就应该把聚光灯对准一组精心挑选的演员,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故事、思想的曲线以及所作所为,将会帮助读者了解一个处在飞速变化的物质环境和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之中的民族及其心路历程。我希望,通过了解他们的奋斗与顿悟,他们的成败与得失,读者能够抚触到一个城市的脉搏和灵魂,一个国家的精神。
书中的主人公们是身处改革浪潮前沿的杰出人物,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在我眼中,正是他们这样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与实践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与智慧,而他们在争取尊严和荣耀的道路上从未止步。追踪并记录这些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是一段令我入迷的学习旅程。我期望着这些故事能够加深读者对我故乡文化的理解。同时我也希望,我的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目前发生在中国以及中国人身边的、错综复杂的、前景未明但却生机勃勃的历史转变。
更多阅读

查建英推荐:谁在灌输近于无耻的教育
微阅读(微信号:wyd513720)阅读人生,阅读社会,阅读中国。手机上网,就看微阅读。来源:高和分享(微信号Gohighshare)作者:著名作家查建英一个国家怎样办教育,关系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总体人才水准,以及这个民族的青年人是否会输在起跑线上。为什么有

管理沟通案例分析 之一:如何向下属委派任务?
注:以下内容为原创作品,并首发于中人网http://community.chinahrd.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485&extra=page=1,任何个人或机构转载或其他方式公开使用须征得作者授权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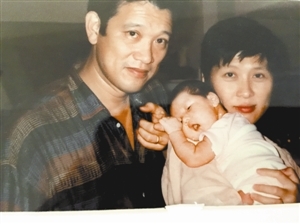
查建英 国家公敌查建英
30多岁的人了,看电视剧本来就不合适,还陷着看好久,浪费时间,就更有点说不过去了。前一段好些小朋友更我说《蜗居》,我愣是没看出好来,心里还暗自高兴,毕竟是成年人了,不会把精力花在姑娘婆婆之流的爱好上。看《人间情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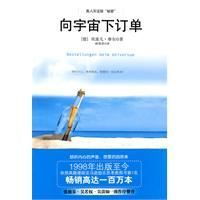
转载 如何向宇宙下订单 向宇宙下订单光盘
原文地址:如何向宇宙下订单作者:孙爱中如何向宇宙下订单一、潜意识的力量——冰山理论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揭示了人的意识分为显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有它自己的特点:1.能量无比巨大:潜意识是显意识力量的3万倍以上

电子卖场 转型 谈传统金店如何向专业珠宝卖场转型
众所周知,国内珠宝零售终端目前有三大模块:传统金店(银楼)、综合性购物中心珠宝区、珠宝品牌专卖店。近些年,随着购物中心、品牌专卖店的不断扩张,传统金店的市场份额被不断打压,很多老字号金店已经出现了营业额增长停滞乃至下滑的局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