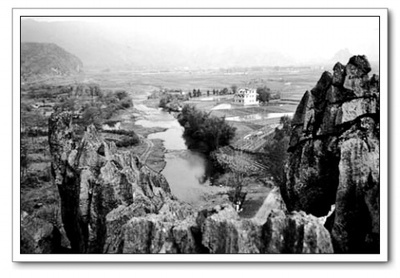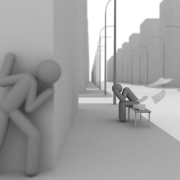兰亭流水,青山玉管修。风和日煦,一觞一咏幽情叙。人生苦短,物非人非情亦迁。千古名序,墨笔一挥就。
桃园夜饮,明月粉桃秀。阳春烟景,琼筵飞觞坐花醉。光阴易逝,浮华如梦欢几何!诗书文章,百篇一杯酒。
——题记
一个是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一个是鼎盛繁荣的大唐盛世,一个是酷爱白鹅的风流书圣,一个是嗜酒如命的游侠诗仙。两个兴衰迥然的朝代,两个地位悬殊的名士,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差近四百年,但是《兰亭集序》与《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却能碰撞出相同的火花,燃烧出不同的火焰。
两篇文章碰撞出相同的火花,其实是指文章中表现出两位作者的人生观或者说生命观有相似之处。《兰亭集序》作成之时,东晋王朝已经偏安江左36年,士族制度下的政治腐朽黑暗,社会矛盾重重,当权者安逸享乐,不思进取。文人士大夫意志消磨殆尽,崇尚老庄思想,清谈玄学。有忧民忧国之心,治国安邦之才的贤才大多苦于门阀制度的阻碍,也只得为一布衣,或隐居山林,醉于杯酒之间,或寄情山水,游于书画之中,看似风流潇洒,实是寂寞无奈。王羲之也是一个清谈文士,但是他与一般清谈之士不同,他曾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在《兰亭集序》中反对那种“一死生”“齐彭殇”的虚妄的人生观,肯定人生命的价值,感叹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积极入世。但是,王羲之代表的是极少一部分人,在士风日下的东晋,他能有这种人生观,不得不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琅琊王氏世家大族的出身,当时王家位高权重,东晋初年的王导和王敦更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前者掌握着东晋王朝的政治大权,后者则掌握着东晋王朝军事大权。这样一个世家大族出身的王羲之,自然是积极入世,而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就很难说了。《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作成时正值开元盛世之时,是大唐帝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文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也是感叹光阴易逝,人生苦短,虽然是感叹,但是其中的豪情也在“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两句中隐隐体现出来,全文则更将李白这位“谪仙人”豪气纵横的情怀,积极入世的态度展露无疑。从人生观或者生命观这方面来说,就个体而言,王羲之与李白都是积极入世的,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魏晋人的就有些崇尚虚无,消极避世,远远不如唐人那样从骨子里透出一种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延续帝国盛世的人生观了。

两篇文章燃烧出不同的火焰,其实是指文章中表现出两位作者的精神气质的不同之处。首先,《兰亭集序》成文之时王羲之官居会稽内史,已经51岁,已经是进入知命之年了,而《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成文之时的李白一介布衣,刚刚32岁,正值而立不久,恰是建功立业的年纪。再者,东晋士大夫都好清谈,崇老庄,民间也佛教盛行,而盛唐士大夫都愿为君主治国平天下,民间百姓有兵役者也渴望建功立业。正是在这种个人地位、年龄的差别与时代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同是名家的书圣和诗仙所展现出的精神气质大不相同。《兰亭集序》文中第二段写了两种人,一个是喜“静”之人,一个是喜“躁”之人。前者“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后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性格乃至行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本质上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快乐之时得意忘形,人却悄悄衰老,等到厌倦,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和“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慨。光阴如白驹过隙,事物的由生到死,情感的由乐到悲,都是转眼之间,都是自然规律所定,也正因如此,作者发出“岂不痛哉”的慨叹,先前的宴饮之乐到此全为陈迹了。《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表现了李白的乐观豁达,积极向上,“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更是表现了李白纵笔挥洒的豪放与才气。从全文可以看出,当时的李白虽然求官未得,暂时隐居于安陆,但身处开元盛世,对国家的兴盛和个人的发展都抱有非常乐观的期望。就文章情调而言,王羲之的低沉清幽,如秋月之洞箫,吹奏的是美景,却含有丝丝哀情,而李白的高亢明朗,似春日之竹笛,悠扬婉转之余,更含着勃勃的生机。从此之中,不难影射出魏晋人与唐人的精神气质,两者表面并无太大差别,但是魏晋人的精神气质内有颓然之势,想勃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唐人的精神气质则是由内自外的奋起之势。
从魏晋人与唐人的生命观和精神气质的比较而言,不难看出,时代背景大环境是影响一个生命观和精神气质的非常主要的因素,而无数个体人积极入世,乐观向上的态度也势必会影响整个时代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正因如此,人们才更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个体促成整体,以整体带动个体,以千万一己之力去改变时代,以时代去改变千万个一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