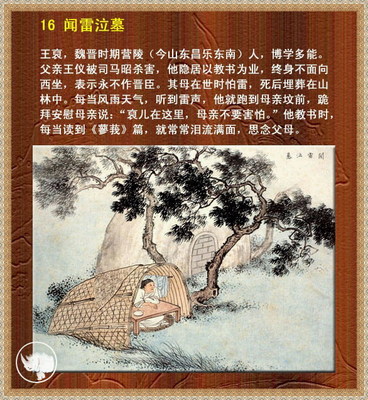(鲁迅)
他仿如大漠惊沙,乱云飞渡,沧海明月,从天外走来,从黑暗中走来,带着忧郁和冷意,他一生被孤苦包围、被冷寞裹藏,他被毛主席赞誉为“中国第一等圣人”,因为是圣人,人们敬重他,钦佩他,接近他,却走不进他的世界,因为是人,在他的生命中驻足了朱安、许广平、萧红三个全然不同的女人,在他不长的生命里凋谢、绽放!
朱安,只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

(朱安)
1906年夏天,母亲不断从家里来信,催促日本留学的鲁迅回乡成亲。不见儿子归来,老太太干脆拍了封电报:母病速归!鲁迅揣着电报,遥望远方,母亲憔悴的脸,温和的目光,还有她不幸的一生,令他泪光闪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
农历六月初六,周家上下张灯结彩,唢呐吹奏着欢快的迎亲曲,鲁迅被装上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一身新郎行头,木然地站着迎亲,新娘的脚从轿帘里伸了出来,悬在空中,急欲着地时,可绣花鞋却不慎掉地,露出了一只三寸金莲(精心装扮的新娘听说未来的男人不喜欢小脚,刻意在换上了一双大鞋子并塞进了一大团的棉花),新郎的眼中露出了嫌恶。洞房花烛下,鲁迅揭开盖头,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泛黄,颧骨凸出,前额近秃,似有病容,他闭上眼睛,扶着床沿,慢慢地走到边上的桌旁!
她无数次小心走到他身边,轻声说:“睡吧”,他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醉意深了,愁绪浓了,黑夜弥散开来,天空也在流泪,她的泪水与雨水连在一片,这是心酸的痛和天的嘲弄!
那一夜,没有春宵一梦,只有梦碎之痛!
朱安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他只能接受;鲁迅是朱安命里的男人,她愿意等待!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半夜睡在母亲屋中另一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的屋中。
几天后,他东渡日本,一走四年!
(鲁迅在日本)
朱安陪伴着婆婆,日日向东眺望,读着从日本的来信,盼望着男人早点回来!她曾给鲁迅写信,诉说思念之情,鲁迅却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
鲁迅回国后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可他心境寂寥,形容枯稿。他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正所谓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埋首故纸堆,寄托青灯黄卷,编成了《古小说钩沉》。
朱安,她等回了男人,却等不到他掀开罗帐走进温柔梦乡,只能独守空房!不久,他又独自北上。
朱安又等了7年,直到1919年冬天举家搬至北京,可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形同陌路,日日无话,仅有的饭间对话,无非就是咸淡如何,回答也只有“是”或“不是”。朱安为鲁迅缝的衣服他不想穿,就从屋中扔出来。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俩人只能分屋而居。
面对男人的冷漠,她却默默地承受着,鲁迅生病时只能吃粥,她就在熬粥前,把米弄碎,煮成容易消化的粥糊,为吵着鲁迅写作,她不让邻居们吵闹……她默默地付出,婚姻仍是一片荒漠!
母亲责问儿子:“朱安有什么不好?”
鲁迅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有味道,有时还好自作聪明。”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朱安称鲁迅为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待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地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头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再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朱安想南下参加葬礼,可周老太太身体不好,她只能在鲁迅以前的书房设灵堂,为自己三十年婚姻守灵!
鲁迅去世后,朱安与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和周作人负担,1943年周老太太去世,朱安拒绝用周作人的钱,因为大先生与二先生不合。许广平少许的资助,令朱安生活非常清苦,每天只能小米面窝头腌菜过日,很多时候,这样的生活也无法保障,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许广平得知后,托人找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那是鲁迅先生的遗物。”
朱安激动而尖锐地回答:“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先生的遗物,我也是鲁迅先生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可当她得知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受刑后,不再提卖书的事,还明确表示把遗物交由周海婴。社会得知她生活困境后,捐助到了一笔钱,可朱安一分钱也没有收下!
死前她曾泪流满面地向鲁迅的学生要求:“死后葬在大先生旁!”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永远离去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没有葬在大先生旁,死后也没有一块墓碑!
她空盼了一生的情,独守了一世的寂寞!
许广平,鲁迅生命中迟到的爱
(年轻时代的许广平)
祖父入狱、父亲逝世、肩负家庭重担,留学日本遭遇种种挫折,让鲁迅的心从小就非常沉重和孤独。
与朱安结婚后,苦而乏味日子一天天过,痛楚和寂寞缠住了他的灵魂,让他窒息,让他无望。上课、读书、写作成了他生命的全部。《伤逝》里那种绝望的晦气和充满幻灭的心境,无不寄寓着鲁迅婚姻悲剧的哀歌,却也隐隐夹带着一丝生命的冲动。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依靠女人。
1925年3月11日,鲁迅收到了一封署名许广平的信,他记得这个高高、大眼浓眉的南方女孩,上课时总坐第一排,聪颖好学、有活力、好提问。
广平最喜欢鲁迅的《小说史略》课,他一走进教室,四周立刻安静得只剩下呼吸的声音。讲课中,他总是激动地从讲台走上走下,幽默的语调,让教室里爆发阵阵的笑声,双眼的异彩,能把人带到他的思想中。他的思想、才华、远见、谈吐让她震动与折服。
(鲁迅书法)
1925年3月,作为反对北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学潮的骨干,广平陷入深深的苦恼中,于是写信向鲁迅求教。两天后,她收到回信,想不到昔日严师的文字如此温暖和轻松。她一遍一遍读着,联想着、微笑着,把它贴在脸上,捧在怀里……他们的通信很快频繁到两三天一封,广平的署名变成了“广平兄”、“小鬼许广平”、“害马”(许广平被校方开除,被斥为“害群之马”)鲁迅的署名也变成了“迅”。
她忘却了年龄界限、忘却了妻妾身份,忘却了道德舆论,落地有声地告白:“喜欢他,爱他!”
信,就象阵阵带着阳光和花香的春风,轻轻吹开了迅哥儿这扇关闭已久的心门,他第一次感受到异性带来的快乐。他想打开这扇门,走进无边的春色中,却想到她风华正茂,自己已是中年,身体不好,还有妻子,只能无奈地告诉她:“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
她在夜色茫茫中惦念,在晨梦依依里想望,烟雨凄凄时等待……她不会放弃!
当广平再次走进鲁迅的小屋时,看到了他脸上的笑:“我可以爱,你胜利了,小鬼!”她满脸的泪,呆呆地站着,他走上前去,用手衣袖轻轻地为她擦试眼泪。
她抽着鼻子:“你就爱我一个人么?”他笑着点了点头!
鲁迅在厦门大学与爱人分别的日子里,他在信中用画细说自己生活的点点点滴滴;为了让她放心,他在信中发誓:“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
面对来之不易的爱,广平写出了《风子是我的爱》:“它——风子——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
(鲁迅与许广平)
1927年10月,他们在上海同居!婚后,鲁迅教广平日语时,她常常天真地问:“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迅听了,总是抚着她的头惬意地笑笑:“你这傻孩子!”
因为爱,他的作品不再黑暗;因为爱,他再次迎来创作高峰。
鲁迅喜欢在深夜写作直到东方欲晓,早上广平接班,开始抄写他昨夜的书稿,他们就象一个岗位上的两个战士,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周而复始!她用才能成全了爱人,带孩子、抄稿子、做家务。据萧红回忆:“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所穿衣裳都是旧的,布纽扣都磨破了,冬天的棉鞋也是自己做的……”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鲁迅很忙,他们有时也会摩擦。过后,他把女人搂在怀里:“做文学家的女人不容易哩,是我脾气不好!”在广平忙完一天的事情后,他会赔罪似在她睡前,陪在身边:“我陪你抽一支烟好么?”聊到兴奋时,他就会再抽一支。看着女人睡下,他才轻轻离开去工作。
她是他的挚爱与助手,鲁迅后期十年的著作成就,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二十年。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
1936年10月,55岁的鲁迅留下最后一句:“忘记我,走你想要的人生”,永远地离开了!
广平在《十周年祭》“……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爱情需要勇气,也需要真诚付出。十年的爱,让她回忆一生,怀念一世!
萧红,走进鲁迅孤独的内心深处
萧红萧军到达上海前,就曾与鲁迅通过信,鲁迅对他们的态度不冷不热,似乎也没有什么感情。萧红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因萧妹妹信中一次天真的“抗议”,发生了戏剧性突变。
一次回信中,鲁迅在信尾加了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萧妹妹对“女士”一词十分不满。下一封信里鲁迅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不好,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鲁迅挑逗性的回信,只因为萧红的大胆、淘气和热情,仿如年轻时的广平!
1934年11月30日,萧红与萧军在内山书店见到仰慕和期待已久的鲁迅,气氛和谐自然,鲁迅喜欢上这个年轻活泼、淳扑爽直的小妹妹,萧红也被鲁迅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
(萧红与萧军)
从此萧红成了鲁迅家常客,给鲁迅带来了笑声与快乐!
有一次,萧红在鲁迅家聊到凌晨一点,早就过了晚班电车时间,天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一片漆黑,鲁迅不停地叮嘱广平,一定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还让广平先付了钱!
不久,萧红搬到鲁迅家附近,每天晚上饭后到准时到鲁迅家报到,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一回,萧红穿了件红色新上衣,独自咚咚地跑到二楼鲁迅书房,娇嗔地问道:“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放下手头的工作,仔细地打量:“不太好看!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弄得不漂亮了。”鲁迅还告诉她,这都是在日本时看美学书学来的!
一个下午,萧红要去赴宴,让广平给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广平拿来了米色、绿色还有桃红色的,两人一起选定了米色的绸条。可为了取笑,广平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头发上,很开心地说:“好看吧!好看吧!”
萧红也非常得意,顽皮地等着鲁迅看她。鲁迅看了广平一眼,严肃着脸,眼皮往下一放:“不要这样妆她……”
萧红曾调皮地问:“先生,你对我的爱是什么爱?”她一双大眼睛正凝望着,鲁迅一下子愣住了,轻声回答:“大概是母爱吧!”
1935年,在鲁迅帮助下,萧红完成了震惊文坛的《生死场》,鲁迅以他少有的热情在序言中写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死前数月,还向红色汉学家汉斯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续者”,他丝毫不掩饰对萧红的怜惜与钟爱!
中年意气浑似酒,少女情怀总是诗。
椐广平回忆:“鲁迅晚年常夜不能寝,独自走到阳台,和衣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鲁迅的灵魂深处的孤独,广平无法读懂,可温柔纤细的萧红如清风明月,照亮了鲁迅孤独的心,而鲁迅也深味萧红内心之苦楚,他们心照不宣地守护着彼此!
鲁迅对萧红的喜欢和溺爱,打翻了广平心中的醋瓶,她向朋友抱怨萧红来得太多,还经常呆到深夜,扰乱了家人的作息,有一次还连累鲁迅受凉生病!
萧红读出了广平眼中的醋意,为了生病的鲁迅好好休养,为了理清与萧军零乱的情,她东下日本!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萧红都没有消息,鲁迅就经常叨念:“怎么去了哪么久也不见音讯?”
萧红在日本时得知鲁迅离世,想到他那父爱般的目光、远行前放心不下的叮咛……泪眼迷蒙写下:“先生走了好几天了,不知道他现在睡在哪里?”捧着鲁迅的照片,她深长地说:“说不出的痛,才是真的痛。”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让人感动的。
萧红也从不掩盖自己对鲁迅的情感,临终前,她说过要葬在鲁迅的墓旁,不行就葬在海边!
鲁迅临终前,枕边放着一张木刻画,画上是一个穿长裙子的女子,长发飘飘,迎风萧萧奔跑,她脚边盛开着一丛红玫瑰!人们重读鲁迅时,认为这幅画与萧红有关,因为萧红梳着长辫子,而画中女子迎风奔跑,有“萧萧”状,脚边的花为“红”,玫瑰代表着“爱情”,意为“青春与爱情”!
2008年1月5日,濮存昕在东方卫视《名人讲堂》讲到他扮演的鲁迅,他说以自己人到中年的理解和感受,认为鲁迅是喜欢萧红的。
莱蒙托夫的诗这样的写道:
我被你深深地吸引,
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逝去的青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