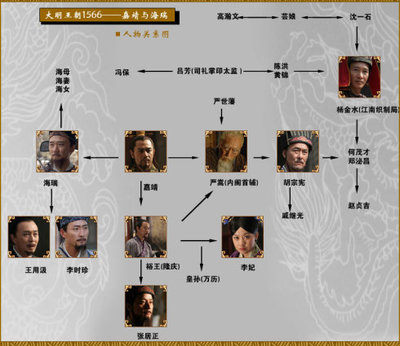本文从利用传播学的方法解读朱元璋的相貌之谜,可以说学术上解决了几百年来人们对于朱元璋相貌的争议。作者胡丹,发表于《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摘 要]在历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存世画像较多,且一人拥有一正一异两种面孔,十分奇特。就朱元璋相貌变迁之政治文化动因而言,信奉相术的明成祖朱棣是其相貌的第一个“整容师”,这是他试图用相学理论重新阐释开国历史的一部分,从而启动了朱元璋容貌变异的进程。其后,朱元璋的脸上被逐渐添加了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他的形象与故事在传播中愈传愈奇。在明代中前期,朱元璋相貌已由“奇貌”发展为“奇骨”,却还未化作一副“猪龙”之形;但到了嘉、万年间,已完成“龙形虬髯”的转化。在朱元璋新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各自追求自己的“真实”,并积极互动,从而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中形成一个诡谲多幻的朱元璋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异人必有异相。如古代帝王,几乎无不具有“奇骨”“重瞳”“龙章凤姿”等一些典型的外貌与形体特征。但没有哪位帝王的相貌,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充满传奇色彩。朱元璋存世画像有正像与异相,或称真容与疑像之别。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两副面孔?朱元璋相貌之变的推手是谁?这两副容貌是如何在文本与图像中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本文将通过对文献与图像两种历史材料的追踪,探析朱元璋相貌之变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一 朱元璋的“异相”的由来
1、《明史》所记郭子兴“奇太祖状貌”事
据清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相貌,对其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郭子兴传》记:“(子兴)袭据濠州。太祖往从之。门者疑其谍,执以告子兴。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其次妻小张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异人也。’乃妻以所抚马公女,是为孝慈高皇后。”[1]《太祖本纪》也有相同的记载,称郭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战辄胜,遂妻以所抚马公女,即高皇后也”[2]。
朱元璋濠梁投军,是其奋迹之始。钦定“正史”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是支持朱元璋异相说的重要文献基础,有必要对其史源加以梳理。
其实,朱元璋曾撰《纪梦》一文,回忆了投军这件往事:“……遂决入濠城,以壬辰(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日至,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余,为亲兵。”[3]其中并无郭子兴“奇其状貌”的内容,甚至没提郭氏出手相救之事。
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为滁州郭子兴庙立碑,“亲稿滁阳王事实”,令太常司丞张来仪撰写《敕赐滁阳王庙碑》。碑文根据朱元璋本人提供的材料说:“(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郭子兴),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4]永乐初成书的《天潢玉牒》亦载此事,文字相仿,当据碑文写成。
《滁阳王庙碑》相比于《纪梦》,补充了郭子兴“亲驰活之”的情节,称拔擢他为亲兵,是因为“间召与语,异之”,当是异其谈吐,未及其相貌。
显然,朱元璋关于此事的两次自述,都没提到自己的相貌。
然而《明太祖实录》在记述此事时,已发生变化:“(上入濠州,)门者疑以为谍,执之,欲加害。人以告(郭)子兴,子兴遣人追至,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因问所以来。具告之故。子兴喜,遂留置左右。寻命长九夫,常召与谋事,久之,甚见亲爱”[5]。朱元璋得郭子兴知遇之故,已由“与语异之”,潜变为爱其“状貌奇伟异常人”。
《滁阳王庙碑》又说,朱元璋入军数月,郭子兴欲为之择配,一日“与夫人饮食,语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6]碑文借郭子兴次夫人之口,谓朱元璋“举止异常”,是称赞他才干出众,亦非诧其容貌。
这段对话为闺阁密语,朱元璋或得自马皇后的转述,其他相关记载必采自碑文,然而内容已发生变化。如清人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载:“太祖在军中,子兴妻张氏(按应为妾小张夫人)奇太祖,力劝子兴妻太祖以(马)后,曰:‘是人有异相非常,当藉此收之,且马公不可负也。’子兴以为然,遂赘太祖于其家”[7]。原文的“是子举止异常”,至此已变作“是人有异相非常”;朱元璋得郭氏青目的缘由,也变简单了:因为他长着一副“异相”。
通过以上对文献的初步追踪,可知《明史》所记朱元璋初从军时,因其“状貌”异常,而获得特别的机遇,此说殆非朱元璋口述原始史料的本意,在传播过程中已发生变异。其变化之始,可追溯到永乐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
2、朱元璋“异相”始见于永乐中年官方文件
前引《天潢玉牒》一书,记明太祖开创事迹,其成书时间在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至永乐四年(1406年)八月之间,即成祖朱棣即位之初,作者可能是内阁学士解缙[8]。该书记载了许多奇异事件,为明王朝的开国史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如谓朱元璋微时,“潜居草野四载。往来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9]。这是笔者所见,关于太祖之“奇”的最早文本。那位“奇士”指朱氏为非凡之人,至乃逊避不敢与之同城,可是没有说明朱元璋奇在何处。
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已着力刻画朱元璋“非凡”的外貌:“(太祖)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10]。御制碑文中的朱元璋,生着一部长而茂密的龙须,项上“奇骨”隆起,隐然上行,直至头顶,确乎一副骇人的异相,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张具象的“龙颜”。
然而朱元璋的“奇骨”并非天生,而是在他登基前不久突然形成的。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十二月戊申条:“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今见《太祖实录》为永乐九年(1411年)至十六年(1418年)的三修本,与碑文同一时期。考虑到更早些的《天潢玉牒》尚未将朱元璋的“非凡”坐实,孝陵碑出现“项上奇骨”而未明其故,唯实录介绍最详,因推断其演变过程应是:朱元璋对其出身原本朴实的自述,如“朕本农夫”“淮右布衣”等,到永乐初年已开始添加神异的因子(“非凡人”),但还未形成具体的表象符号。到永乐中年建孝陵圣德碑,这一符号(即“奇骨”)诞生了,并被进一步加工,写入实录。实录的记载更具神秘色彩,实际上起到了为“奇骨”解码的作用(代表天命)。
“梦”一类的记事,本在实录凡例之外,但《太祖实录》破例记载此事,且将这个在现实中得到呼应的“异梦”系于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戊申,别有用心。因为这一神秘事件就发生在朱元璋紧锣密鼓筹备称帝之际,他随即于次月,即戊申年(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乙亥日登基。以彼戊申日暗指此戊申年,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正是《太祖实录》开始系统地利用相术原理构建朱元璋奇特的容貌特征。朱元璋由奇人到奇貌的变化,并非野史向壁虚构,它由官方的历史书写首先完成,《太祖实录》反复渲染太祖相貌的奇伟,是这一转换的关键[11]。
实录在追述朱元璋少年之事时,赞曰:“上稍长,姿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12]《明史》据此写道:“(上)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13]“奇骨贯顶”是对“奇骨”的发展,但这四个字在实录原文里尚未出现,只是到了明代晚期始为描述朱元璋容貌的经典用词。《明史》乃径采之,并羼入历史文本中,实际上是用后起的观念对历史本态进行追改式的重写。
实录还记载:已入寺为僧的朱元璋,一日游方至六安朱砂镇,有老儒相其面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朱元璋具以实告。老儒默然良久,叹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又“历告以未然事甚悉”。别去时,“问其邑里姓字,皆不答”[14]。
前引《天潢玉牒》里一“奇士”指朱元璋为“非凡人”,此老儒也是一位奇士,他用相术及星历之学,准确推出朱元璋非凡的命造。如果我们从官方文献叙事的连贯性上观察,就会发现,朱元璋之奇与非凡,正由空泛一步步落到实处。老儒相面,是朱元璋“贵相”的最早记录。
前文已指出,朱元璋本人的自述,并无其容貌的信息,而《太祖实录》却直指“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在实录郭子兴小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兴)其先曹州人也。父郭公,少好星历,年壮犹未娶。游术至定远,言人祸福寿夭多验,邑人信之。邑中富翁家有女,瞽而未嫁。郭公过其门,翁以女命使推之,惊曰:“贵人也!”翁曰:“此女瞽,故未有配。”郭公遂纳礼娶之。既娶,不数年,家业日殷。生三子一女,子兴其中子也。始生,父卜之曰:“是儿得佳兆,异日当大贵。兴吾家者,必此儿也。”[15]
此段文字被《明史》采入《郭子兴传》,并在其后记“子兴奇太祖状貌”及小张夫人称“此异人”等事,形成一个基于相术的完整的叙事结构。
实录郭子兴传谓郭父是一名“日者”,即以卜筮为业的术士,等于暗示郭子兴“奇太祖状貌”,是有术学依据的;子兴初生时,“郭公卜之吉”,于此亦有了着落[16]。其实不单郭子兴遭遇朱元璋为命中注定,就连马皇后缔婚朱氏,也是前定。实录说“马公有季女,甚爱之,常言术者谓此女当大贵”[17]。马氏大贵,仍由术士之言着落在朱元璋身上。
可见,围绕朱元璋何以发迹,《太祖实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它主要的理论工具,就是相术。朱棣与其父不同,在诸般术数里,他比较偏好相术,在其发迹史上,相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实录等官方文献的修纂中,成为解构、重塑本朝历史的工具。当然,对于“得国不正”的他,这主要还是为了服从他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说,朱元璋相貌之变,其子朱棣是第一个“整容师”。
3、“奇骨贯顶”与相术家笔下的朱元璋像
明初,袁珙、袁忠彻父子,都是深受朱棣信任的著名相士。袁忠彻在景泰二年(1451年)编纂《古今识鉴》一书,其中记朱元璋尚居人下时,有一个叫铁冠的方士来谒,说道:“天下扰攘,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观之,非明公而谁!”朱元璋问其意,答曰:
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应在一千日内。[19]
这段文字纯为相术家言。我们看到,此时的朱元璋尚未“奇骨贯顶”,还只是“辅骨插鬓”(又叫“辅角插天骨”,以辅骨[20]长耸为上,是清贵之像)。在《古今识鉴》中,有多位士人生有此像,似乎并不甚奇。“奇骨贯顶”就非常尊贵了,指额正面头骨方正而大(名伏羲骨),上至头顶百会穴,相书又称朝天伏羲骨、方伏羲骨,也就是常说的“日角相”,多被视作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
相语中常见龙行虎步、龙姿凤质、天日之表一类的判语,其实与形容人器宇轩昂一样,盖皆泛语,不是具体的体态描绘,“奇骨”却是一种较为显眼的体貌特征。然而,无论是孝陵神功圣德碑,还是《太祖实录》,它们所描绘的项上奇骨,与此并不相类。所谓“奇骨贯顶”,应是后人借用相术词汇对朱元璋“奇貌”所作的符号化的再概括。
虽然孝陵碑与实录首发“奇骨”之端,但“奇骨贯顶”一说还未出现在《古今识鉴》里,而到明晚期何乔远撰《名山藏》时,已称“太祖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21],全然为相学家口吻。由于《名山藏》出世较晚,作者应受到当时流传的太祖异相的影响,可能属于“看图说话”。又由于相术的广泛影响,相家术语强烈渗透到文艺创作及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奇骨贯顶”之类多属俗语套话,未必一定都有史料的渊源与依据[22]。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识鉴》对朱元璋容貌“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的形容,已与传世的异相或丑像颇为相似了。天地是指天庭和地阁,分别象征额头和下巴,相朝之状,是形容其突崛相对——异相的朱元璋,不正长着一张两头弯弯的鞋拔子脸(或称“猪龙形”)吗[23]?
考虑到“铁冠”这位相面之人都不太可靠,则他所称的“明公状貌非常”云云,很可能就是袁忠彻本人的生花妙笔,不过借铁冠做代言罢了。显然,这副以相术理论为依据写出的太祖容貌,已较官方钦定的版本有了更大的丰富,加进了相术家自己的想象与改造。
如果说,永乐时期的碑文、实录,为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的“形象建设”,指出了一个神性的方向。这有一个过程,那么到袁忠彻奉敕辑纂《古今识鉴》时,已“实证”地推出一个颇具异相的太祖皇帝了。
明中期正统、景泰时的太祖御容,已经显出奇异的特性,但还走得不太远;至少这时,朱元璋的脸孔上还没有“黑子”,奇骨还未贯顶,“龙颜”也还没有异化为一副丑陋不堪的猪龙之形。
二 朱元璋“异相”中的符号意蕴
1、清宫南薰殿藏朱元璋图像
列代帝后图像,明代藏于内库,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加装潢,移藏于南薰殿[24]。南薰殿所藏历代帝王画像中,以朱元璋存像最多,共立轴12、册页1,计13幅之多。嘉庆二十年(1815年),胡敬为编辑《石渠宝笈三编》,曾作《南薰殿图像考》,详细开列了12立轴的情况。兹引如下:
(1)绢本,纵六尺三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高五尺二寸,凤眸龙颐,黑痣盈面,服冕垂旒,被衮执圭。
(2)绢本,纵六尺三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高五尺一寸,冠服同前。
(3)绢本,纵六尺二寸,横三尺三寸,设色。画坐像,高五尺一寸,乌纱折上巾,织金盘龙袍。
(4)纸本,纵二尺六寸,横一尺五寸,设色。画坐像,高二尺二寸,冠服同前。
(5)纸本,纵五尺三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高五尺,皮弁织金盘龙袍。
(6)纸本,纵三尺三寸,横二尺,设色。画半身像,冠服同前。
(7)纸本,纵六尺,横三尺四寸,设色。画坐像,高五尺七寸,折上巾,黄袍绛履。
(8)纸本,纵五尺二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高四尺八寸,折上巾,赭袍。
(9)纸本,纵三尺三寸,横二尺二寸,白描半身像,折上巾,盘龙袍。
(10)纸本,纵三尺三寸,横二尺,白描半身像,冠服同前。
(11)纸本,纵三尺四寸,横二尺,白描半身像,皮弁盘龙袍。
(12)绢本,纵八尺五寸,横五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高四尺八寸,乌纱折上巾,黄袍,紫面虬髯,与前像迥异。[25]
其中第12幅设色绢本坐像,原有按语:“疑是成祖像,误题签”,实为朱元璋像,就是那幅广为人知的中年坐像立轴。隆庆六年(1572年)出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瀚回忆:“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大不类。”[26]可能就是此像。此外,南薰殿藏明代帝后册页中,还有朱元璋老年半身像一帧。该像须发皆白,与中年全身坐像一样,绘制精细,面貌相似,是为所谓“正像”。
张瀚已注意到他所见御容“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大不类”。而所谓“奇异之像”,应该就是常见的“龙形”之像(或称丑像、猪像),南薰殿所藏朱元璋异相,皆是此类。
这么多图像中,正像无疑是明代宫廷所绘朱元璋真容。因为它们是非常规范而精致的,这是古代帝王肖像画的共同特点,与其他明帝画像显然出自同一系统。不管画师如何处理“神似”的问题,画中的朱元璋相貌应该与本人具有相当的形似[27]。当时的人物肖像画也具有这个水平。朱元璋这两幅正像画于不同时期,但从容貌上能看出是一个人。其老年半身像的两颊上生有银白色短髭,这是朱元璋面部的一个明显特征,笔者将他中年坐像的高分辨率电子图片放大,发现在同样部位,也有短髭,只是那时还是黑色的。两幅图像在细节上具有如此的一致性,表明它们在绘画技法上,是追求高“写真”的。
而11幅异相图像,无论从其材质、用色与尺幅,还是画中人物的冠服装饰来看,都是杂乱混搭的随性之作,显示其来源之复杂,与宫廷帝王画像严格的规范性(包括姿态、布景、衣冠等)差谬千里[28]。这些画像多绘制粗糙,衣冠错漏百出,人物面貌不一,如无签题,根本无法识别是一个人,也看不出年龄,有的甚至怪异到不似人类的地步。
2、朱元璋异相的形成与传播
清人胡敬的“图像考”,对朱元璋异相的来历并无考证。他在案语中摘引了《明史·舆服志》中关于明代皇帝衮冕、皮弁及常服之制的内容,却没有指出异相中的冠服与典制完全不符;他还引了何乔远《名山藏》对明太祖“日章天质、奇骨贯顶”的描述,以及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所记相士郭山甫为朱元璋相面的记载。可能胡敬已意识到,朱元璋的这些异相几乎就是一堆相理符号(如脸型、黑子、五官形态)的堆积,不太可信;但他对于这些怪异之像何以尊藏于宫廷,却觉懵然,不敢擅断,故只排列材料,而不做结论。
《胜朝彤史拾遗记》卷一记郭山甫事曰:“山甫善相人。上龙潜时,尝游临淮,过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见上大惊,急呼内治馔。治毕,夫妇捧七箸侍上饮,笑语甚欢。中酒,阖外户跽曰:‘公非常人也,自爱。尝言钟离有王者气,当在公矣。’上去,山甫谓诸子:‘若曹皆田舍郎耳,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
郭山甫的相术可谓神验,其女后封宁妃;二子,长封巩昌侯,次封武定侯,死皆赠公,山甫本人亦赠国公。
我们从现代科学观念出发,当然不信这样的“神术”。前文已指出,首先依据相理对朱元璋相貌进行“整容”的,是永乐时期的重要官方文本,如实录与孝陵碑。然而《太祖实录》并不载郭山甫的预言。且山甫之事与秦末吕公(吕雉之父)相刘邦故事异常相似,或者就是从前者脱胎而来,只是换了主角。但因为毛奇龄的关系,被载入《明史·后妃传》。毛奇龄参与了《后妃传》的写作,因为实录等官方文献殊乏宫闱的记载,他便多“取外史所记与实录稍不符者,草成应之”,余剩未用的材料,复为《胜朝彤史拾遗记》一书。郭山甫之事应是“外史野记”的一种,它甚至不载于武定侯郭英六世孙郭勋在嘉靖中所著《三家世典》一书,笔者因疑它的出现应更晚一些,或在万历朝乃至更后。
从张瀚的记载来看,到明代中晚期,太祖异相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南薰殿所藏应该只是其中一部分[29]。比如同为嘉(靖)、万(历)时人的徐渭,作《高皇帝像赞》云:“上之岩也,天高以覆耶?下之丰也,地载以厚耶?扫孽胡而握汉统,维斯之与咮耶?眉采耶?目河耶?唐与虞之后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为我圣祖高皇帝之面耶?”[30]又如万历时人张萱之父在云南作知县时,曾于黔国公府“摹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后来张萱在京为官,“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为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31]。较之只有京官才能瞻仰的太祖正像,异相传播更广,留给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那么是否能为朱元璋异相的产生及流传设定一个时段上限呢?这里先提供一些与朱元璋相貌有关的旁证材料,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貌类高帝”[32]。宗室之中,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祐枢,也是“状貌类高帝”[33]。这两位王子都和朱元璋长得像,但没有他们相貌怪异的记载。臣子中也有“貌类”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山阴人陈思道,仕至礼部侍郎,此人生平“有二异”,其一就是“貌酷肖御容”。然查张岱《越中三不朽图赞·陈行父公像传》所存陈思道官服像,其面容并无奇处[34]。
成化进士陆容记:“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阖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35]此事祝允明《前闻记·天王堂土地》亦载:“姑苏阖闾子城之濠,设有东西二天王堂。其西堂东庑有土地祠,貌甚类太祖皇帝。相传张氏(士诚)僭据日,有道者潜塑此像,意谓此土地当属太祖云耳。道者失其名,盖异人也。或曰偶肖圣容,初无道者事。”[36]陆、祝二人都是明中期苏州人,在他们的记述中,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异;祝允明尤好记异闻,他说土地神“貌甚类太祖皇帝”,盖其心目中的太祖之像,本不奇异。
综合以上明初至明中期人“貌类高帝”的材料,似可推断,在明代中期前,朱元璋怪异之像尚未广为流传;朱元璋完成由“奇貌”向异相的转变,大约在嘉靖时期,其后始大量出现太祖异相之记载及绘画。
那么这些异类的画像是何时,又是如何流入宫廷的呢?
南薰殿入藏历代帝后像,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古今君臣画像,明代原贮于由印绶监掌管的古今通集库[37]。明朝帝后御容,则尊藏于太庙东北的景神殿[38]。易代之后,集中收贮于内务府库,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下谕重新装裱时,仍“沿袭前明以来之旧”,其保存状况是“扃鐍收藏,视同寻常图绘,未经启视,尘封蛀蚀,不无侵损”[39]。似乎这批图像在入清后从未有过更新,相关记载也无在这次整理中加进新的藏品的信息。
然而,对于南薰殿帝王像的轴数,相关文献所记并不一致:
造办处《活计档》所记修复、进呈情况,计历代帝后像77轴(乾隆十二年)[40]
《御制南薰殿奉藏图像记》:帝后像轴68轴,册7(乾隆十四年)[41]
法式善《陶庐杂录》:古帝后像75轴,册15(嘉庆七年)[42]
胡敬《南薰殿图像考》:帝后像98轴,册16(嘉庆二十一年)[43]
《大清会典》:帝后像轴100,册18(光绪二十五年续纂)[44]
从造办处修复进呈帝后像77轴(帝后册因连同历代先圣、功臣,细目不明),到正式入藏南薰殿,已少了9轴,这表明乾隆帝对于哪些图像应该尊藏,是有选择的,至于他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哪些图像应被淘汰,淘汰之后如何处理,则不清楚。此后南薰殿图像呈增长趋势,以立轴而言,嘉庆初年,已增7轴;到修《石渠宝笈三编》时,又增23轴,光绪年间复增2轴。
明太祖像的数量变化也较大。乾隆九年(1744年)三月,内务府曾对所藏图像做过一次调查,据《内务府奏销档》,太祖像为“大小像两轴”。到嘉庆初年法式善作《陶庐杂录》,已为12轴,至二十一年胡敬作《南薰殿图像考》时,轴数没有变化。
综合以上材料,乾隆九年,内府仅藏朱元璋像2幅,可能都是“正像”,即现存立轴中年坐像与册页老年半身像,《奏销档》“大小像两轴”之说,也许是轴、册概而言之。且据清初档案,原明宫太庙所藏帝后御容,在顺治元年(1644)七月间,经清点有391轴,加上册页、手卷等共计43椟,除御容每位量留一二轴外,全部送至晋王之寓。这说明此时清宫所藏,还没有太祖异相。
乾隆十二年重装“前明以来之旧”的历代帝后像,仅仅过去三年,应该不会有异相流入。乾隆帝对修复的帝后像,做过一定的裁汰(像由77轴减为68,淘汰率达12%,应该说不低了)。其后南薰殿并未锁钥封固,特别是在乾、嘉之际,对内廷秘藏做过系统整理,古代帝后像有了明显增长,计增30轴之多。笔者怀疑,朱元璋的异相,应该是在乾隆晚年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书时流入清宫,并且很可能是有意识收藏的结果。
民间绘画作品流入宫廷的路径,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同样是藏于清宫,与帝后像同批装裱的历代功臣像中,有姚广孝真容,据考证可能绘于洪熙年间,后藏北京潭柘寺,至明末犹在该寺,不知如何就进清宫了[45]。民间私绘私藏的太祖“御容”,也必然随这样一个路径,进达内廷。这条路径尚待通过史料发掘重新还原,而我们从黔国公邸尊藏“龙形虬髯”的异相、著名文士徐渭作歌赞美可知,这些画像至少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乃至勋戚之家的认可,这一心理基础和认知观念才是异相得以广为流传而不遭禁绝的根本原因。
三对朱元璋“异相”及其传播的政治文化考察
当代人依着今天的审美观,将朱元璋的异相称为丑像。过去的人却并不作如是观,如赵汝珍就用“雄豪奇伟”[46]四字来形容朱元璋的奇异之像,他不论美不美,只说奇不奇;这种意见,不是出自美恶之辨,而是基于术学理论的神秘主义世界观。今人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应可轻易判断异相皆非“写真”。本文的目的亦不在对这些画像作真伪的讨论,要在探析这些奇异之像之所以出现并广为人传信的原因,对这一人文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1、对朱元璋异相为“疑像”的简单辩说
异相中的朱元璋,一副弯月型的脸庞,容貌险奇怪异,有的还满脸布有黑子——这是一副惊人的相貌。对其真实性,历来讨论颇多,有信以为真容者,也有人视之为疑像。[47]
赵汝珍在《古董辨疑》第十四章《杂辨·明太祖御容之伪》中说:“朱元璋传世之御容有二,一为温文儒雅、五官端正者,一为雄豪奇伟、深目长颊者。二者均常见之,南薰殿各代帝王像,二像均有之。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明太祖亦同常人,绝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伪,惟孰真孰伪,前人未有纪录,凭空推想亦难确定。但以理推之,当以深目长颊者为真,盖此像迹近侮辱,含有朱豬之意,若非真像,在专制时代无人敢为之,况其子孙又奉祀之,其必为真像,盖可知也。”
赵汝珍之见其实存在罅漏,如谓“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已在清末,恐怕难称“(朱明)子孙又奉祀之”吧!一个人长那样一副尊容,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许多人虽然不做定论,还是倾向认为丑像“非真”,如明人王圻编集的《三才图会》,即不取异相[48]。
其实,与画像孰真孰假的推想之词比起来,对朱元璋一人而具两副容貌做出解释,更具价值;其中持“疑像”说者最多,又有三说:
其一,明末清初人谈迁说:“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一,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49]此说似难成立,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微行恐人识其貌,与赐诸王侯御容何干?难道“诸王侯”还会不识今上真容?且朱元璋在位,主要依靠公朝理政,经常临朝亲断政事,何曾担心臣民会认得他[50]!何况好多朱元璋“微行”故事,还是后世野史敷衍出来的。
其二,清初人宋起凤在《稗说》中说,他在南京二寺见到两种朱元璋御容,在灵谷寺者为一草本(大概指不设色的纸本),其像“望若龙状”;在鸡鸣寺者为“五官端好”“面无纤痕”的彩绘图像。“二处凡游者,必请主僧展礼。两地迥殊,不知其孰是。或曰灵谷者上令工为之,宣威外域尔,非真也”[51]。
其三,与上说近似,但不称“宣威外域”,说是朱元璋在得天下前为威服世人伪造的。
当元运已终,天下大乱之时,第一个以相貌之奇来主动承受天命的,是布贩子出身的徐寿辉。《明史·徐寿辉传》载:“元末盗起,袁州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52]似乎朱元璋也希望有一副徐寿辉那样有号召力的脸孔。此说很为人深信,因为它为朱元璋不合常理地拥有两种面容,且异相太过惊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一些研究古代肖像画的学者就认为,“此类疑像完全是按照朱元璋的主观意愿臆造出来的。在帝王个人生性和主观意愿驱使下,肖像画竟然能背离形似这一基本法则,这在历代帝王像中是绝无仅有的”[53]。将其称为宫廷人物肖像画的“变异”。
然此说实难成立。因为徐寿辉很快为部下所弑,朱元璋应该很清楚,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一副奇貌是靠不住的。如果说他欲借一副由天命符号构成的写意面孔,来传达他才是真命天子的讯号,就更不可信了。因为直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仍在名义上依附于韩林儿的龙凤政权,以其号令为圣旨,以己号令为令旨——尽管此时他已是江南兵力最盛的诸侯。他这么做,是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的政治策略,假造异像之说,有违于此。
以上三说皆认为异相出自朱元璋刻意的伪造。然而“异人”之像,“奇”固然重要,还须配一“伟”字,“奇伟”之像才是完美的。历代帝王画像,虽然都会在造型中融入一些符合相理的特征,如大耳、丰准、广额等,并且成为古代造像的基本手法;画师们在追求面容相似的前提下,都会表现渲染一下这些代表尊贵的符号。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大众基本的审美观,尤其是面容。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隆准而龙颜,美须髯”的美丈夫,他也有“七十二黑子”[54],但长在左股上,而不像朱元璋,满脸落花,实在破相得很。反观朱元璋的怪像,却是那样丑陋不堪,甚至十分猥琐,毫无贵气可言。朱元璋常常自拟汉高祖,甚至还觉其输于己,他会以那样的丑态来自贬吗?
2、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是其迥然相异外貌的基础
朱元璋的本像虽然绝不如此骇人,但其异相之出现与广泛传播,却正是“帝王个人生性和主观意愿驱使下”的结果。只是这位帝王,不是朱元璋,而是他的儿子朱棣。朱棣在篡位自为后,对“开国”历史进行了重塑,一个重要表现是:洪武朝的异人与异迹骤然增多。例如《天潢贵胄》中的诸多“异人”,伴随着太祖皇帝的出生、成长与奋斗;永乐以后,与朱元璋有关的各种圣瑞与“神迹”的传说更如井喷,一个神化、传奇的朱元璋逐渐从其平常人的面貌中脱脱而出。
通过前文对文献及图像的追踪,不难发现,这两种历史材料的演变大致是相对应的。从朱元璋的相貌被泛泛地形容为“姿貌雄杰”“异常人”,到符合相术上“辅骨插鬓”的特征,再升格为极贵的“奇骨贯顶”,体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整个的明朝中前期。其表现便是朱元璋的容貌越来越奇,也越来越“丑”。换言之,朱元璋的容貌在传世的过程中,经历了改造、加工,不断被添进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信息符号,如奇怪的脸型,突出的五官特征,以及12、24、36、72不等或“盈面”的黑痣等,最后变成一副“猪龙”之形。异相中朱元璋相貌并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就没有黑子),正是加工者手法、观念及心态不同的表现。它是民间的集体创作,远比宫廷画家的“稍加穆穆之容”要大胆和没有顾忌。
这个过程又与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朱元璋形象的迅速演变相对应。
首先应指出,朱元璋先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才会产生两副迥然相异的面貌。明中期以后,本朝太祖的形象,变异速度加快,在大众观念中的“人格”发生分裂:一方面,他是雄才大略的旷代圣主和明君,一方面,他又是超级嗜血的暴君和凶徒,在野史、笔记、口传、戏剧中出现了大量描写他无知、猜忌、多疑、滥杀的故事[55]。其情节或真或幻,或虚或实,但他残杀画工的众多传说,则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他真实容貌的怀疑。张瀚就猜测说:“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56]
与其正像为官方标准像,而异相多被民间奉为真身一样,朱元璋圣明的正面形象是官方、正史的语言,而那些掺杂了各种离奇、惊骇内容的故事形象,主要出自民间的演义与加工。当然,朝野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积极互动的,如本文指出的,朱元璋相貌之变,发轫者正是官方,但相貌如何继续演变,却成了民间的自由创作,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但宫廷和上层后来也部分地接受了太祖皇帝那张不同寻常的丑像,否则黔国公府也不会尊藏悬挂——由于相学思想对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性影响,即便朱元璋的子孙,对其祖先那些与正像不合、不雅,但是显出“雄奇”的异相,也不会感到不满,甚至还可能津津乐道。
朱元璋的形象塑造,其基础是人们对开国历史的集体记忆,而诱发其变的指针,则是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与需要。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怀旧之思成为人们宣泄不满的一个窗口(万历年间海瑞重提太祖以剥皮重典惩贪的旧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内矛盾重重,北虏南倭,交相来袭。当国家和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而人们又觉拯溺无力时,太祖皇帝“扫孽胡而握汉统”的开创之功,以及在位期间强力整肃吏治,实现政治清明的“伟大功绩”,就更令人称羡怀念了。太祖何以“不阶寸土一民”而得天下?成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久议不衰的话题。而对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只能用“天命”来解释。
如何察知天命呢?往往依靠包括相士在内的各类术士、方士的中介。
明代方术之风甚盛,尤其是成祖凭着一副龙颜得天下后,相术与政治的结合愈加紧密,愈为突出。如成化十二年的“侯得权之变”,侯得权本是一游方僧,止因有一副“奇貌”,就不断有术士奉承他是天子的贵造。他初时尚不自信,直到有术士拿也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来鼓励他,他才笃信,以为只要相貌足够“奇”,命中就一定有非分可希。侯得权迅速扩大了他的门徒队伍,就连许多宫廷宦官都甘心拜在他门下,奉他为“上师”[57]。
只凭一副奇像,就想做皇帝,侯得权并非独例。正德年间,封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是听信术士说他相貌奇伟,辄敢称兵造反。曾几何时,相人术被朱棣借来为自己篡逆披上天命的外衣,但他想不到,相术之理也会成为反抗皇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大量相术支配人行动的事例证明,通过相貌特征来研判人之祸福休咎,在群众中有着非常坚实的根基,是异常典型的群众心理。在此语境之下,朱元璋的面孔自然在变形中愈放愈大了。
人们总在试图探索朱元璋真实的相貌。其实,根据传播学理论,所谓真实,包括三个层次:客观真实、媒介真实和心理真实(即主观真实)[58]。媒介真实是借助符号再现的,根据相理“易容”的朱元璋,脸上集中体现了诸多的相学符号,如黑痣、龙形、虬髯、五岳特征等;尽管它离开朱元璋的真容(即客观真实)已不啻千里,但媒介真实比起原态之物更为饱满、精彩而多幻。在朱元璋面貌及形象的传播中,“真实”通过两套媒介体系传播:官方的正史、碑文、玉牒,以及陵寝、太庙等处悬挂的御容等;和民间传说、故事、小说、戏曲、口碑、私史、私绘帝王图像等。显然,两者都有各自的叙事框架,在传播中进行有意的选择、加工与引导,试图建立符合各自取向的观念架构。然而它们在议题和符号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交叉,这两条线索、两种真实,交相影响,积极互动,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大众认知上的“主观真实”(或称“受众现实”)——那就是一个谜一般的传奇皇帝朱元璋。
人们似乎更乐意接受朱元璋的怪异之像,即便到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文率国府众僚参谒孝陵时,所奉的仍是一幅朱元璋的异像。这或许是因为,正像中的朱元璋,只是一位器宇轩昂的封建帝王,而那些“丑”而奇特的面孔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隐含了更多的话语,更符合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心理(这也是民间秘密宗教设像的一般特点)。
“朱元璋”这位复杂诡谲的帝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按照自己的观念、想象和需要集体创造出来的。
作者胡丹,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微信:wohudan
[1]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二《郭子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79页。
[2] 《明史》卷一《太祖纪一》,第2页。
[3]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四,嘉靖十四年(1535年)刊本。
[4]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6页。
[5]《明太祖实录》卷一,壬辰年闰三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页。
[6]张来仪:《敕赐滁阳王庙碑》,《国朝典故》卷十,第195~196页。
[7]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2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
[8]参见杨永康:《<天潢玉牒>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9] 解缙:《天潢玉牒》,《国朝典故》卷一,第2页。
[10]碑文见《明孝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附录。
[11]从实录记事中“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以药傅之”“遂成骨隆然”等来看,笔法颇为写实,不能排除朱元璋中年后得了颈部包肿之类的怪病,使其外貌发生一些变化,官方对此做了神秘化解读。如是,则朱元璋的“奇骨”就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了。至于野史有无传闻,目前尚未看到相关记载。
[12] 《明太祖实录》卷一,第2页。
[13] 《明史·太祖纪一》,第1页。
[14] 《明太祖实录》卷一,第3~4页。
[15] 《明太祖实录》卷一,第27~28页。
[16]事实上,郭氏结局并不好,三子俱亡,唯有一女嫁朱元璋为妃。故郭氏命运之“吉”,只着落在郭子兴因识拔朱元璋于众中,后来被阴封为王上。
[17] 《明太祖实录》卷一,第6页。
[18]参见拙作《卖卜帝王家,术游公卿间——相士袁珙、袁忠彻父子小传》,《看历史》2014年第5期。
[19]袁忠彻:《古今识鉴》卷八《国朝》,明景泰二年(1451年)刻本。
[20]根据相术理论,眉上,前额天庭两侧,从里到外分别为日(月)角、辅骨、边城、山林。相学术语及对应部位,可参见《柳庄相法》(又名《柳庄神相全编》,清光绪十五年刻本)卷上“流年运限”等图。
[21]何乔远:《名山藏·典谟记·太祖皇帝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22]相术对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可参见万晴川:《明清小说中的人物形貌描绘与相人术》,《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小川阳一作,李勤璞译:《明清肖像画与相术的关系》,《美苑》2002年第3期。
[23]王耀庭:《肖像·相势·相法》(《美育》第99期,1998年)一文经与传统相法对比,认为朱元璋异相就是相书中所说的“龙相”。
[24]关于乾隆十四年这次对旧藏历代帝后名臣图像的重裱移藏,可参见赖毓芝:《文化遗产的再造:乾隆皇帝对于南薰殿图像的整理》,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26卷第4期,第75~110页。按:南薰殿图像中的13幅朱元璋画像,除一幅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余皆藏台北故宫。
[25]胡敬:《南薰殿图像考》,《胡氏书画考三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6]陈洪谟:《松窗梦语》卷六《方术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页。
[27]形似是肖像画的基本要求,明人陆容说某画工“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进。上览之,甚喜”(《菽园杂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0页),常被引作朱元璋掩饰自己真实面容的证据。然所谓稍“加穆穆之容”,可以理解为给朱元璋的容貌里加进一些显示其尊贵的符号,如长耳垂轮、面颊丰满等。这是中国古代肖像画及塑形的基本手法,未可理解为朱元璋喜欢不似己的画像。
[28]其实岂止帝王,就是民间画像,人物亦必契合其身份,重其场景,如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画人物者,必分贵贱气貌、朝代衣冠。”这等“气质”,在异相图画中是全然没有的。另外,在南薰殿图像中,有数幅显非明人所作,如1997年出版的《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名臣真迹》所收之像,左上题:“帝朱姓名元璋,江南句容人,国号洪武,在位三十一年。”据其题款,直犯御讳,不辨可知,必为清人所绘。它既非“写真”,当然更谈不上真容了。
[29]据王正华先生研究,朱元璋“猪龙”形的异相在明末清初已非常流行(按:惜王先生大作未尝寓目,转述于赖毓芝《文化遗产的再造》一文)。这类异相,近现代在民间犹有发现,如1986年3月3日《云南日报》载,在云南发现朱元璋绸缎画像,身穿龙袍,脸上生48粒黑痣,显系一幅异相。余不赘述,这类画作的量应该非常之大。
[30]王焕镳:《明孝陵志·艺文第七》,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4页。
[31]张萱:《疑耀》卷一“高皇帝像”,丛书集成初编本据《岭南遗书》本排印,商务印书馆,第3~4页。
[32]何乔远:《名山藏》卷四〇《靖江王懿文太子附》。
[33] 《明史·诸王传四》,第3642页。
[34]张岱:《越中三不朽图赞》,绍兴印刷局1918年铅印本。
[35]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第170页。
[36]祝允明:《前闻记》,《国朝典故》卷六二,第1394~1395页。
[37]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3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景神殿”,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39] 《清高宗实录》卷三〇一,乾隆十二年十月辛巳。
[40]《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41]鄂尔泰、张廷玉编纂《国朝宫史》卷一一“南薰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42]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按:该书刊于嘉庆二十二年,据赖毓芝前引文,法式善于嘉庆七年(1802年)以纂修《国朝宫史》而得入观南薰殿诸图像,故此定年。
[43]胡敬:《南薰殿图像考》卷上,《胡氏书画考三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第13页。
[44]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卷九〇,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第841~842页。按:南薰殿所收图像轴、策、卷的变化,可参见赖毓芝前引书附表一:《南薰殿图像内容的变动比较》。
[45]王征:《知公罪公,星有定盘——南薰殿<姚广孝像轴>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1期。
[46]赵汝珍:《古董辨疑》第14章《杂辨·明太祖御容之伪》,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
[47]参见索予明:《明太祖画像真伪辨——故宫文物札记之三》,台北《大陆杂志》1969年第6期;《明太祖画像考》,台北《故宫季刊》1973年第3期。较近的讨论有夏玉润:《漫谈朱元璋画像之谜》,《紫禁城》2008年第4期。
[48]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万历王思义校正本,第582页。
[49]谈迁:《枣林杂俎》智集《逸典·疑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50]参见拙作《明代早朝述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51]宋起凤:《稗说》卷一“御容”,谢国桢编《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52]《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附徐寿辉传》,第3687页。
[53]单国强:《明代的宫廷绘画》,《中国书画》2004年第3期。
[54]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2页。
[55]专家在对本文做匿名评审时,指出朱元璋在位时至少得罪过四种人:贪官、功臣、文人、富人。其相貌愈变愈丑,可能还存在一个刻意“丑化”“倒神”的过程,具有启发价值。也就是说,朱元璋相貌之变,同时存在两条线索,一个是“丑化”,一个是“神化”,但两者相互交汇影响,很难区分。由于涉及到“朱元璋形象”这个更大的课题,笔者将做专文处理。
[56]张瀚:《松窗梦语》卷六《方术纪》,第110页。洪武朝有名画家极多,以能画召到京师者也不少,许多人因艺蒙难,如王蒙、赵原、周位、张羽、陈汝言、盛著、徐贲等,都被处死。曾“传写太祖像”的画家,可考者有5人:陈遇、陈远兄弟,孙文宗,沈希远,还有一人,见丁自申:《府君丁仁庵公》(《明文海》卷四二六):“会有写真者,高皇帝召写御容,酷爱其似,忌复为民间传写,幽寘于狱”(按此条可疑,此人既知朱元璋不喜他再为别人画像,如何在牢中才见到丁仁庵,即“索纸,为公图小影片幅”?其人下狱的缘由,可能只是嘉靖时人丁自申的想象)。可参见马明达:《元代帝后肖像画研究》(《暨南史学》第4辑)之《明初的几位御容画家》一节。当时一些画家动辄因画触怒,如有名的周位因画水母骑龙而遭弃市,几等于文字狱,疑多出于后人附会。有意思的是,所知传写御容者无一人被杀,值得玩味。
[57]《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七,成化十二年九月己酉,第2867~2869页。亦可参见明末清初人东鲁狂生短篇小说集《醉醒石》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
[58]参见童清艳:《超越传媒:揭开媒介影响受众的面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