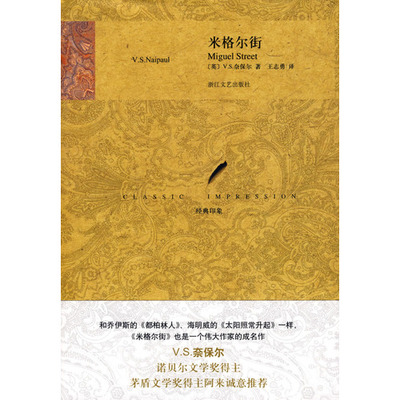告别米格尔街
作者:[英]奈保尔/王志勇译
我妈说:“你在这里变得太粗野了,我想你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去哪儿,委内瑞拉?”我问道。
“不是委内瑞拉,去别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委内瑞拉,也知道你,只要你一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他们就会把你丢进监狱。不,不能去那儿。”
我说:“那好吧,这事由您拿主意吧。”
我妈说:“我要去找加耐士.潘迪特谈谈这事。他是你爸爸的朋友。无论如何你必须离开这里,你变得太野了。”
我想我妈说得没错。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变野了。我喝起酒来像条鱼,还干好多其他的事。我是在海关时开始喝酒的,那儿有不少以各种理由没收来的酒。头一回喝时,酒精味令我头痛。我对自己说:“你必须挺住,就像喝药一样,屏气闭眼灌进去。”很快,我便成了海量,且为此感动骄傲。
后来,博伊和埃罗尔给我讲了不少玩的地方。我开始工作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他们带我去马里恩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爬上二楼,来到一间拥挤的小房间。房里挂着不少绿色的灯泡,像一串串珠宝,屋里有许多正在等候和观望的女人,墙上有条横幅,“严禁使用猥琐语言”。
我们在吧台上喝了杯香甜的饮料。
埃罗尔问我:“你喜欢哪个女人?”
我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感到一阵厌恶,我冲出房间回到家,觉得有些头晕和害怕,我对自己说:“要坚持住。”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个俱乐部,而后又去了多次。
我们搞了些疯狂的聚会,带着朗姆酒和女人到马拉卡斯海湾彻底狂欢。
“你变得太野了啦。”我妈说。
对她的话我一点儿没有在意,直到一天晚上我酩酊大醉,一直醉了两天。当我清醒后,我发誓再也不抽烟喝酒了。
我对我妈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特立尼达的错。在这里人们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大约两个月后,我妈说:“下周,你必须跟我去,我们去见加耐士.潘迪特。”
加耐士·潘迪特不当传教士很久了,并已经参政,而且干得挺红火。他好像是个什么部长,或是政府的什么官员,听人说他正在竞选议员。
我们来到坐落在卡莱尔大街上的他那栋大房子,我们见到了这位大人物,他没缠腰带也没扎头巾,而是身穿一套价格昂贵的西服。
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妈。
他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妈开始哭起来。
加耐士对我说:“你到国外准备学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学,就想离开这里,就这么回事。”
加耐士微笑着说:“政府还没有发过这种奖学金。你说的那事只有部长们可以办到,你必须学些什么才行。”
“我还真没想过这事儿,让我想想。”
加耐士说:“那好吧,你就想想。”
我妈哭着向加耐士表示感谢。
我说:“我知道我要学什么啦,工程。”我刚刚想起了比哈库叔叔。
加耐士笑起来,说:“你知道什么是工程?”
我说:“眼下还不知道,不过我能学会的。”
我妈说:“你为什么不学法律?”
我想起了齐塔兰加和他那套褐色西装,说道:“不,不学法律。”
加耐士说:“现在还有一份奖学金,是学药剂学的。”
我说:“可我不想学药剂学,我不愿意穿着白大褂,向女人兜售口红。”
加耐士微笑着。
我妈说:“崩理这孩子,潘迪特。他就学药剂啦。”又转身对我说:“只要你肯用脑子,什么都能学。”
加耐士说:“想想吧,那样就能去伦敦,就可以见到托马斯,看到国会大厦。”
我说:“那好吧,我就学药剂学。”
我妈说:“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报答你,潘迪特。”
说着哭起来,她掏出二百美元,递给加耐士,说:“我知道这不多,潘迪特,但我只有这些,是很长时间才攒起来的。”
加耐士神情凝重地接过钱,说:“你不必难过,你已经拿出了你的全部。”
我妈继续哭起来,后来加耐士忍不住也哭了。见此情景,我妈擦干了眼泪,说:“你知道吗,潘迪特,我是多么难哪,现在到处都要花钱,可我上哪儿弄钱呀,真不知以后我可怎么活。”
加耐士不哭了,我妈又重新哭起来。
哭了不一会儿,加耐士拿出一百美元,还给我妈,呜咽颤抖地说:“把这钱拿去,给孩子买件好衣服。”
我说:“潘迪特,你真是个好人。”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当你带着文凭和其他各种证书从伦敦回来,成为大药剂师时,那时,我会找到你,索取我应得的回报。”
我告诉海特我要走了。
海特说:“为什么,去当苦力?”
我说:“我拿到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去学药剂师。”
海特说:“是你捣鼓来的?”
我说:“不是我,是我妈。”
埃多斯说:“是件好事,我认识一个药剂师,我给他家倒了好几年的垃圾。那家伙可够富的,伙计,钱哗啦啦地往里进呀。”
消息传到伊莱亚斯那里,可把他气坏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门外,喊道:“贿赂,贿赂,你们就会干这名堂,贿赂!”
我妈反唇相讥:“只有那些穷得连贿赂的钱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才抱怨贿赂。”
过了约莫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离开的手续全部办妥了。特立尼达政府就我的情况给在纽约的英国领事馆写了一封信,英国领事管知道了我的情况。英国人让我发誓绝不用军队推翻他们的政府后,给我签发了签证。
我离开的前一个晚上,我妈搞了个小小的酒会,有点像遗体告别。人们进门便会满脸悲伤地告诉我会多么想念我,而且便把我忘到脑后,专心致志地吃喝起来。
劳拉亲了我的脸颊,还送给我一玫克利斯托佛大街的徽章。她让我把它挂在脖子上,我答应她把徽章装在口袋里带走。其实后来我也不知把它塞到那里去了,比哈库太太给我一玫六便士硬币,她说那是玫神圣的硬币,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就随手花掉了。泰特斯.霍伊特原谅了我所有的过错,还送我一本书。埃多斯送我一个钱夹子,他发誓说它绝对是新的。博伊和埃罗尔没送我任何东西。海特送我一条香烟,他说:“我知道你说过不再抽烟了,拿去吧,如果你改主意了就抽。”于是我又开始抽烟了。
比哈库淑叔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捣鼓那辆准备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的面包车,我不时跑去央告他别再折腾了,他说,他认为是汽化器出毛病了。
第二天一大早,比哈库就起来,又去捣鼓车。我们原打算八点动身,结果到十点时,比哈库还没搞完。我妈有些惊慌失措,比哈库太太也有点沉不住气啦。
比哈库在车底下吹着口梢,吹奏着《罗摩衍那》曲调。后来他从车下爬出来,笑着说:“怎么,害怕啦?”
终于一切就绪。比哈库对车造成的损伤不是太大,发动机还能工作。我把行李装上车,正要上路。
我妈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牛奶罐放在门口。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大门那么宽,足足可以通过一辆汽车,而放在门口中央的牛奶罐只有四寸多宽,我想从旁边过去,离牛奶罐还老远,结果还是踢翻了牛奶罐。
我妈的脸一下子沉下来。
我问:“是个坏兆头吗?”
她没回答。
比哈库按响车喇叭。
我们上车后,比哈库开车离开米格尔街,沿着大路直奔南码头。我没有向车窗外看。
我妈一直在哭,她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米格尔街上见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牛奶?”
她没答话,仍旧为洒掉的牛奶哭泣。
当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港的市郊后,我才向窗外看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男人和女人们在稻田里劳作,一些孩子在路旁的水管下冲凉。
我们正点赶到皮亚考机场。直到此刻,我才后悔得到那笔奖学金。机场候机室令我感到恐惧。肥胖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怪里怪气的饮料。戴着墨镜的美国女人趾高气昂地高声喊叫着。看上去,他们是太有钱,活着太滋润了。
后来传播中传来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播送的消息:“206航班将晚点6个小时。”
我对我妈说:“我们回西班牙港。”
很快我还要和候机里的人在一起,我想离开一会儿。
回到米格尔街,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海特。他腋下夹着一份报纸,拖着那双平脚板,从咖啡馆溜达回来。我挥舞着手臂喊他。
他答道:“我以为这会儿你已经上天了呢。”
我感到失望。并不仅仅因为海特的冷淡,而是因为在我命中注定要永远离开这里之后,一切仍像以前一样,我的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看着翻倒在门口的铜制牛奶罐,对我妈说:“这就是我永远不能再回来的兆头吗?”
她欣慰地笑了。
我和我妈,还有比哈库叔叔以及他夫人一起在家吃过最后一顿午饭之后,又沿着炎热的公路返回皮亚考。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我认识海关的一位官员,他没有检查我的行李。
播音员冷淡平静地宣布开始登机。
![[英]奈保尔:告别米格尔街](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53330t01e595dcc23d64d6f6.jpg)
我拥抱了我妈。
我对比哈库叔叔说:“比哈库叔叔,刚才我还不想告诉你,不过,我想你的车气门在响。”
他的眼睛豁然一亮。
我离开他们,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跑道上跳跃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