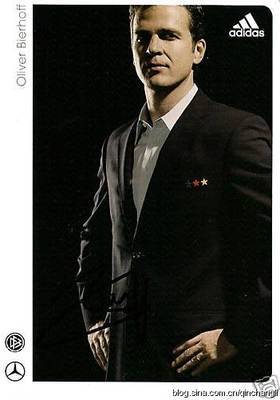后海龙囤时代
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降,海龙囤上又发生了哪些事?曾经壮丽的宫殿是如何渐渐埋于黄土下的?我曾尝试着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记忆,在脑海里一遍遍勾勒这400年光阴的轮廓,以期对囤之现状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建立起考古学在阐释海龙囤过往中不可取代的话语体系。现在,也许已到把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写下来的时候。
近400年来,僧人是海龙囤绝对的主人。
囤上有海潮寺,道光《遵义府志·古迹》:海龙囤,“播平后,兵备道傅光宅即其上建海潮寺。”同书“职官”又记:傅光宅,万历“三十年(1602)以兵备道副使任,三十一年(1603)四月升本省(四川省)提学道。”如果海潮寺系傅光宅在兵备道任上所建,则其建造年代应在万历三十至三十一年间。民间传说海潮寺的修建,是为超度阵亡将士的亡灵。这种说法可在《大清一统志》中找到依据,是书卷296载:傅光宅万历中“出知重庆府时,播贼方猖獗,总制李化龙莅郡,光宅督理戎马军饷皆有方略。播平,吊忠义、瘗遗骨、辑流亡、抚疮痍、修学宫······适遵义守缺,当事者委任之,遂星驰去,安抚夷汉大着功绩,寻擢遵义兵廵道副使,复迁提学副使。”其中“吊忠义、瘗遗骨”可能便与建寺有关,而此举明显在其出任兵备道之前,似在播平之后便立即着手。两相结合,海潮寺的始建年代只能笼统定在万历二十八至三十一年间。此后又至少在弘光元年(1645)、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民国十八年(1929)进行过重修,解放后拆除其两厢及下殿,今仅存上殿延续香火。前两次的修庙碑记均立在今海潮寺前,表明寺庙的位置应无变化,即镇于原新王宫中轴线上。海潮寺因此成为海龙囤时空完整性的一个重要补充。
根据碑刻,弘光元年(1645)的重修有两项内容颇引人注目:第一,扩大了海潮寺的规模。碑文称:“神宗朝,狐鼠盗弄干戈,此间遂为腥血之野。削平后,僧人建茅椽于其上,终草弗堪也。主宾相待炤月始来,遂举故迹昌大 颜,其寺曰龙崖”。知寺初为茅庵,40余年后方昌大其颜,而称龙崖寺。第二,扩充了海潮寺的庙产。碑文称:施主刘继文等“发愿上助城银三十八两六钱八分,得买正法叛逆喻志贤没官田三十六亩五分,以 五亩捨给本寺,乃立僧户耕种输差”。此时,主事的僧人为炤月。此后,海潮寺的庙产不断扩充。据当地老人回忆,民国时期,海龙囤城墙以内的山林土地几乎全为庙上所有,并有喻、向、吴、王、袁、祝、陈等七八家佃户租种其土。大约在七、八十年前,龙位坪、姚家凼、校场坝一带已是耕地。
龙位坪砖瓦废墟以上的堆积可分4层,底层堆积中发现崇祯通宝等遗物,表明大火后渐渐颓圮的新王宫大约在明末清初开始被黄土掩埋,而掩埋的原因可能与耕种有关。这与碑文所载囤上僧人的活动可大致吻合。
大约与此同时,曾经的土司禁地也逐渐变成坟山。囤上尚存明墓二座,均有墓碑,一为崇祯乙亥年(1635)罗斈茂墓,一为明福建晋江黄氏墓。二人事迹均无考。罗墓前不远处,有黄土一抔,民间传为“骡子坟”,内葬杨应龙坐骑。又传为“万人坟”,大集体时曾有好事者掘开坟之一角,发现累累白骨。“骡子坟”一名或与“罗斈茂”墓有关,“斈”(音“学”)字不常见,可能被念为“子”,而称其坟为“罗子坟”,久则讹为“骡子坟”,并移指此墓。因此,其为所谓“万人坟”的可能性更大。播平后,傅光宅曾“吊忠义、瘗遗骨”,其为当时所遗亦未可知。还有一种可能性不可排除,与下面一段往事有关。
据吴必伦之子吴久刚讲述:太平天国年间,桐梓久坝有个叫杨龙喜的,在黔桂交界一带做工,碰上广西农民起义,遂返回家乡,与芝麻人舒光富揭竿而起,一个称皇帝,一个称元帅,这就是黔北黄号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绥阳、仁怀、桐梓等地,久坝战役后,改久坝为新寨。围攻遵义城时则遇上了麻烦,久攻未下。时朝廷派敖宗光为钦差,沈从文之曾祖父沈宏富率湘军协同作战,大败号军,杨喜龙战死务川。舒光富率残部退踞海龙囤。朝廷以地方武装为主力,围剿号军。内有一大地主叫肖光远,是茅台人,其家曾被舒光富抢,怀恨在心,亲自领军围攻海龙囤。战争打得很激烈,舒部最终战败,逃离海龙囤。囤破时,一个怀有身孕的起义军家属在逃跑中被当地一个姓郑的男子收留,并向官军谎称系其妻子,逃过一劫。所以,当地郑家实际上是起义军的后人。起义军在海龙囤上驻了很久,当地留有很多传说,也留下很多遗迹。海龙囤北坡今水家屋基一带还有很多灶头,可能就是当时驻军留下的。杀人沟里,二三十年前,每逢发大水,都会冲出一些人骨,不一定是平播时的遗骸,倒可能是这次战役的遗迹。
因为一直住在囤上,手边资料有限,我没能查找到吴久刚所讲旧事的出处,但从传说的流行程度及其与今人的关联来看,这应是一段信史。因此,囤上部分遗迹应确如久刚先生所言,不能骤断为万历遗存,还需具体来看,其中便包括“万人坟”。
仿佛是历史的重演,为战事而建的古囤,宿命般再度成为血腥的战场。起义军溃败后,海龙囤重归寂静,海潮寺的僧众又回到幽谷一灯的桃源世界。囤之周边,人烟渐密。刘元光说,当地住的最久的是郑家,有两三百年了,葛家从四川迁来不过一百多年。绣花楼下有大量梯田,用石头砌的田坎,不知何时开垦的。对面的大河坝,现在仍能看到四五十户人家的房基,而人早不知去向。这些都表明,平播后海龙囤一度人烟灭绝,后来又再度繁荣。村民尚能记忆的租种庙土的喻、向、吴、王、袁、祝、陈等几家佃户,大约便是在此时逐渐迁入囤上的。71岁的杜金友说,其中王之友家住的最早,陈立举家是从黄钟山搬来的,他妈再嫁到王家,带来10多岁的陈立举。向家没人了,我奶奶就是向家的姑娘。喻家在喻清河死后,就无后了,一个儿子抱给杜家抚养。后关有喻家坟,但附近已经没有姓喻的人家。吴家没解放就搬下山了,现在还有后人。袁家死归一了。吴家是苗子,住在王武志屋背后,也死了。我家是在我父亲一辈从黄泥坝搬到囤上住的,“四清”时房子起火才搬下囤来到城门洞住。王武志家饿饭年间才搬来囤上。这样一去一来,现在囤上就只剩陈立举和王武志两家了。
如今,囤巅仅有陈、王两户,囤下白沙水两岸尚有几十户人家,有葛、张、刘、王、夏、杜诸姓。海潮寺前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修庙碑上,则还能依稀辨出吴、张、黄、何、岳、王、刘、赵等姓的捐款人,他们应该是当时周边的住户,许多早已不知去向。我怀疑,民国时尚住在囤上的喻家,可能与弘光元年(1645)“海龙山为天开胜地”碑上的“喻志贤”存有某种关联。海潮寺在耐得住清贫的和尚逐渐辞世后,也不复有人居住。
人来了,又走了,如潮起潮落,一切在时间的流里改变了容颜,而囤仍在那里,静静等待了412年。我们今天的来访,带着历史的使命,就是要唤醒这座埋藏文明的神奇山峰,令她开口讲述曾经在这里上演的或血雨腥风或缠绵悱恻的过往。
( 2012年7月30日,写于囤下海龙坝,一处传说中杨氏曾筑堰于此的肥沃之野,一处曾令郑珍魂萦梦牵的温柔之乡。)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8月7日“副刊”版。(李飞)
海龙囤:未消解的意义
最近几日,我常常被媒体追问:海龙囤的发掘有什么意义?对习惯从细微之处盲人摸象般观察历史的考古者而言,这不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生而有涯,总该使生命在有意义的志业中完成,而非在无聊中消亡。对意义和价值的不断追问,能唤起我们激昂的心。在海龙囤,对意义的追寻,是从废墟中开始的。
我试图用下面的表述来说服自己,说服他人。
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山地生态文化的杰出典范。文化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人对自然不断适应与改造的结果。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人文景观。山是西南大地的统治者,而人是山的征服者,这里的人们从来与山相伴,这里的文化因此有着山骨的印记。从山腰的洞穴,到险峻的山巅,都留下征服者的足迹。至迟从距今30万年以降,连绵不绝。最新的文物普查表明,贵州有被称作“囤”、“屯”或“营盘”的遗迹近千处,是名符其实的“千屯之省”。其中,海龙囤是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的古囤。
囤上所有的关隘、台基和踏道都是用加工规整的大石营建而成的,石之大者,重达数吨。如今石砌的雄关、古墙仍傲然屹立,残缺而美丽。这些坚固的石头,经历战火和岁月的洗礼,穿越时空传递着别样的讯息。没有人统计过她一共耗费了多少石材,只知其数颇巨。观者常常望石兴叹,追问石之来路及其被垒砌在十余米高空的技艺。或因难以想象,遂有美丽传说。传说杨应龙有一条赶山鞭,常在鸡不鸣犬不吠时赶石上山,石如猪奔,雄关遂成。调查表明,所有石材均就近开采,并以人工搬移、垒砌,而非出自神力,它们凝聚着山地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山的险峻,供给的近便以及取材之利,均应是海龙囤选址的重要条件。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遵义老城至海龙囤下,仅需半小时时间。停车再步行约半小时,即可抵达囤巅。遥想当年,奉命行事的选址者逆水而来,筚路蓝缕,该是怎样的艰辛?而当其在万山丛中与龙岩山猛然邂逅,再以职业的眼光反复打量这雄奇的山峰时,心头该是怎样的兴奋?三面环水,一面衔山的海龙囤,被群山簇拥,当地导游形象地将之描述为一朵莲花,群山为瓣,龙岩为蕊。我曾在一个月夜里,在飞龙关内听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聊海龙囤的风水。他说关隘上的每道门,都与远处的一座主峰相互呼应,形成四面来朝之势,仅此一端即可窥见海龙囤所蕴藏的深厚风水理念。经其指引,我们察看了飞龙、朝天诸关,确有此象,像西南山地的坟丘多有向山一般。我知道黔北的宋墓是讲求风水的,但居址如何却所知甚少,不敢骤断。风水是否也在海龙囤当初选址者的考量范畴,从学理的层面还需慎重考察;但在感情上,我愿意相信这是山地生态文化的必然选择。
海龙囤是中央与地方互动,家与国关系转换的重要场域。海龙囤是在1257年蒙军从云南逼近,播州告急的形势下,由南宋朝廷派出钦差,拨给银两并征调人力,与播州杨氏一道营建而成的。因此,她一出现,便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是一种国家行为。只是,这里自始至终都未成为抗蒙的前线,却在343年后成为杨氏土司对抗明朝廷的主战场。“抗蒙”与“平播”均是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海龙囤因此成为这两桩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发生地。同样是由播州人营建的重庆钓鱼城,却折断了上帝的鞭子,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是万历一朝的三大战役之一,数十万人参战,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方面,统治播州755年的杨氏土司被剿灭,结束了其长期在中国西南以国为家的历史,加速了国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战争的消耗也加速了已经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覆灭的步伐,44年后,握有中国276年的朱氏拱手让出天下。谁又曾想到,偏处西南一隅万山丛中的小小一囤,竟与几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有着如此不可割舍的关联。
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海龙囤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宋廷筑城理念。庆历四年(1044)奉敕编纂的《武经总要》,向被视为宋代筑城的指导性典籍。《武经总要·守城》:“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侍,兼此刑势,守则有余。”海龙囤筑于两溪交汇处的龙岩山巅,正合此守城之道,且她完全符合城池的结构,而与纯粹的军事城堡似还有一些区别。同书又记,“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曰露屋。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敌棚至城门”。海龙囤尚存的铁柱、飞虎、万安、西关诸关均设钓桥。囤后万安关外的月城、土城,实际形成两重瓮城。囤前飞龙关亦状如一小瓮城。自飞龙关逶迤而下一道外城墙,一端连囤巅主墙,一端接囤南山险,使囤之城墙整体略呈“9”字形,其在形状和功能上,均与宋元之际的“一字城”相近。虽然现在很难将宋代建筑和明代遗存截然区隔,但有理由相信杨应龙之重修海龙囤,应是在固有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现存海龙囤的整体格局可能在南宋末年始建时便已奠定,且她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城池在筑城理念上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因此,从一座古囤,可以窥见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家国关系的转化。
海龙囤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实物遗存,她完整见证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策从唐宋时期的“羁縻之制”,到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从兴建到废弃,杨氏“土司”一直是她实际的主人。这在新、老“王宫”的称呼中已经显露无遗。文献中多有杨氏衙宇僭越的记载,如《平播全书·献俘疏》称明军攻破海龙囤后,“录其关门之联曰: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所居之门匾曰:半朝天子”。又称“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这在发掘中的“新王宫”上是否有所反映?发掘显示,“新王宫”是一组有环“宫”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占地约1.9万平方米,她大致遵循了“前朝后寝”的整体格局,与明紫禁城存有某些相近之处。屋顶脊兽,多带有遒劲的三爪。“宫”内出土的大量来自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碎片上确有许多龙凤图案,其中相当部分为五爪龙。但这是“王宫”在规制和装饰上确有僭越之嫌的证据,抑或只是强势土司的应有之物,尚难骤定。
平播之后,这处曾经的土司禁地慢慢颓圮,壮丽的“王宫”渐渐埋于黄土之下,她的原貌逐渐不为人知。考古于是成为今人重新认知海龙囤的不可取代的途径,这也正是发掘海龙囤的意义所在。
在海龙囤巅度过的104个没有麻将、没有电视剧的日夜里,若无意义的指引,生活必将陷入巨大的空虚和迷茫中。然而我们并未迷失,因为意义就埋藏在那里,在黄土下,在废墟里,在我们心中,她从未消解,却在文明碎片的缀合中,被重新发现、诠释与建构。
(2012年8月4日凌晨1时,写于海龙囤巅。)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8月20日“副刊”版。(李飞)
火烧新王宫
新王宫毁于大火,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民间甚至传说,412年前的这把火,烧了数十天之久,滚滚浓烟遮天蔽日。我以为,这是对海龙囤壮丽恢弘的另一种表述。
这是一座建立在险峻山巅的城。据《杨文神道碑》,1257年筑“龙岩新城”的目的,是“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既作此打算,则选址必险,建筑必坚。而既称之为城,必是按照宋城的一般范式来营建的。这一点可以从宋代筑城的指导性典籍《武经总要》中得到验证,海龙囤的诸多做法与之契合。此后宋祚移于元,又移于明,播州却一直为杨氏所踞,和平无事,文献中也未见修囤御敌的相关记载。直至万历元年(1573)杨应龙即宣慰使位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对海龙囤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称:杨应龙曾“于囤前筑九关以拒官军”。如今囤前仅存六关,并囤后三关才得九关。其中,飞龙、朝天、飞虎、万安四关有杨应龙手书的匾额,为其所建无疑。朝天关匾额落款为“万历乙未岁中吕月乙卯日吉旦重建”,即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飞龙关为“万历丙申岁夹钟月未日吉重建”,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月。这应该是关隘竣工的时间,而其上的“重建”字样表明是在旧址基础上所进行的修建。换言之,海龙囤的整体格局,应在南宋始建时便已奠定。
杨应龙对海龙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平播全书·叙功疏》称杨应龙“彼其数年精力,用之一囤,前后重关,左右深谷,将自谓负隅之虎,莫可谁何”。此番重建,用杨应龙自己的话说,“今重辑之,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因此,修建时不惜代价。民间传说,建囤工人每日必须穿破三双草鞋,否则性命不保。高峻的城墙、雄伟的关隘、宽大的踏步、厚实的台基,表明杨应龙确实是将海龙囤视为“子孙万代之基”来经营的。从建筑风格及其所用石材判断,现存九关可能均是万历遗存。民间传说,新王宫亦为杨应龙所建。但目前除关隘以及与之相连的城墙年代可考外,其余建筑要准确判定年代尚有难度。新王宫内出土的有年代标识的遗物,最早的是带宣德年款的青花碎片,而大量的则是万历青花。排除“宣德”瓷器是晚期器物落早期年款以及精美瓷器的传世利用等可能,则宣德至万历大约便是新王宫的使用年代。但这一推论尚需更多证据的支撑。换言之,新王宫可以确定为杨应龙最后的官邸,但其到底创自何时仍是未解之谜。

有时候,我宁愿相信新王宫是一组经过严密规划、一气呵成的宏伟建筑,而非几个不同时期拼凑而成的衙署。或者,一开始所制定的完整规划得到了后继者一以贯之的严格执行,所以呈现出严整的布局,残存至今的废墟亦掩盖不住它缜密的规划。我们对它的认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而逐步深化。初步发掘显示,这组占地近2万平米的宏大建筑,有环宫的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屋宇因地就势,沿山脊层层抬升,器宇轩昂,气象万千。新王宫并未处在海龙囤居中的位置,而偏向西北,靠近后关。雄伟的石砌台基略呈“品”字形展开,中央轴线上的建筑可能为衙署,后端可能为“寝宫”,两侧则可能为府库、庖室、书房及役人之室。中央建筑有墙体与两侧屋宇相区隔,凡两组,一组居前,地势宽敞,被后之海潮寺所据,可能是囤上最高行政建制总管厅旧址;一组居后,为一面阔五间的大型建筑,其明间后部砌一石台,须弥座,传其上原有石雕龙椅,毁于1958年,“龙位坪”因之得名,应为土司议事处。中轴线左后侧建筑尚存五级相连的高峻台基,其中央有踏道贯通,当地人称“三台星”。须弥座风格的基座,便捷的交通,彰显了它非同一般的地位。初步推测这里应为杨应龙的“寝宫”。中轴线右后侧,紧贴西南段宫墙处,另有一组建筑略与“三台星”对称,可惜残破较甚,格局不明,可能营房或另一组“寝宫”。中轴线两侧的建筑或为单栋的屋宇,或为带有天井的成组建筑,曲廊迂回,错落有致。宫内排水设施整齐划一,有暗渠将水顺山势层层引向低处,至今仍在发挥着良好的功能。宫内道路彼此贯通,四通八达。布局的严密,令人相信这是一组一气呵成的建筑群;而规模的宏大,则令人怀疑这应非一人一时之作。我不确定,我们还能不能在大火之后的废墟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还历史以真实。
新王宫毁于大火,文献有明确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农历六月初六黎明,明军破囤,五路官军径奔新王宫,合而围之。《平播全书·破囤塘报》援引南川路总兵马孔英报告称:“我兵乘胜战夺二层飞虎关,严谕举火烧毁。我兵愈加精强,先登贼之大囤,举火延烧酋房”,“传令所部汉土官兵,不许一军进应龙衙宇,并不许夹带一物。其应龙见得前门兵已上囤,遂自缢死。应龙妻即领阖家人口尽从后门逃生,方将囤门一开,后兵方拥而入,随将应龙衙舍府库,合兵围之”。贵州右监军张存意的报告与此基本吻合,称破囤时“贼党开门倒戈,奔溃如蚁。我兵直围杨应龙住宅,遵守前禁,不敢径入宅内。官兵中有从宅后掘墙数孔而入者。比刘、李二总兵引兵入宅,则杨应龙已缢死卧房”。这些记录中,新王宫被明军称为“应龙衙宇”、“衙舍府库”或“杨应龙住宅”,它破囤之后,即被官军合围。从“府库”“衙舍”并举看,府库应在新王宫内。因为环宫有墙,加之前有禁令,所以明军不得径入,却有为利而动者“从宅后掘墙数孔而入”。此时,杨应龙已自缢。明军沿袭了凡攻克一处即纵火焚毁的政策,“延烧酋房”,但未言明所烧的是否为新王宫。贵州左监军杨寅秋的报告也提到了明军入囤纵火事,并称新王宫之火是应龙点燃的。他说:“贼倒戈奔溃,各路兵一齐登囤,拥入内城四面纵火。贼酋杨应龙将卧房发火,同爱妾缢死,要将自焚。时五路总兵官齐抵贼衙”。《叙功疏》对此过程的记述最详,称黎明时,应龙“自度不免,因抚膺顿足谓田氏曰:‘我今自焚死,断不落乱兵之手。’田氏牵衣号哭,酋捽去,入卧房将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何氏缢死。”吴广督兵入,“至后房,破门寻见酋尸,急出烈焰中。须臾,火烧楼房一空,如稍迟晷刻,酋尸俱成煨烬矣。”据此记载,应龙偕其妾,在“卧房”钉闭房门,纵火后自缢。而吴广在“后房”寻见应龙尸,知“卧房”在新王宫中居后,最有可能即今之“三台星”。而在另一条文献里,火为“左右”所纵。应龙见大势已去,“即同爱妾周氏、何氏悬梁自尽。左右放火焚烧间,总兵吴广、守备陈九经打开楼门,直登其上。吴广为首,陈九经为从,冲火取出全尸”。此“左右”,不详是应龙还是吴广之左右。种种迹象表明,宫内之火确为应龙先纵,而明军攻入后又“锦上添花”,于是须臾之间,“火烧楼房一空”。
考古清理出的满地灰烬、龟裂的石材、半灰半红的砖与瓦都清楚显示,新王宫确实毁于大火。曲房别馆,一炬堪怜!
新王宫焚毁前的诸多细节已经无法想象。万历十四年(1586),以进献良木而获赐飞鱼品服的杨应龙,一定不会放过在新王宫的木作之上大施拳脚的机会,令屋宇的装饰极尽奢华而有僭越之嫌。《平播全书·献俘疏》称:“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记杨氏大水田庄园说:“大水田庄宅制度,台沼亭榭,僭越非常,不惟雕刻彩饰龙凤等物,卧房一样黄色牙床三十六张,欺僭可知。”作为“子孙万代之基”的海龙囤,其装饰之精当不在其下。《献俘疏》中记录了一副已然不可考的对联,来证明海龙囤的超出常规及杨应龙的“目中且无海内”,文曰:“囤破而官军录其关门之联曰: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所居之门匾曰:半朝天子。”我很怀疑这副对联的真伪,因为留存至今的杨氏碑刻文献均称海龙囤为“龙岩囤”。但我丝毫不怀疑这座山巅的“宫殿”确因规模的宏大与装饰的精致而有着“半朝天子”的气象。
新王宫并未在大火中死去,而在大火中涅槃。
(2012年8月14日,写于囤巅。居囤第114日。412年前改变历史的114天里,明军“出师才百十四日,辟两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余年所得志于西南夷盛事”。)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8月28日D04版。(李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