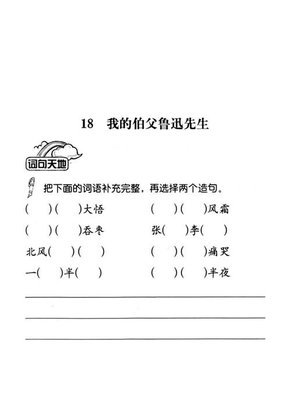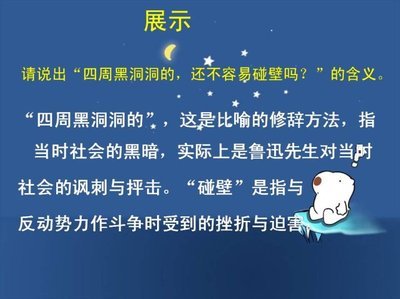前言
文学插图是文学著作的有机部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后,它就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久远,中外皆是,古今亦同。许多文学名著因插图的精彩而受到更广泛的传颂,文学插图也因与文学相伴而有了永恒的生命。为此,文学插图一直是艺术与文学内在关联和相互衬映的代表。
时过境迁,而今为文学作插图的画家烧了,在中国似乎更甚。尤其是以绘画的方式为文学作插图的优秀例子真的鲜见了。优秀的画家大概不再愿意在插图这种小画上费工夫,许多插图也由装饰性的数码图像代替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所谓“读图时代”图像的泛滥,一方面感到真正的文学插图的缺失。
所以,当张润世把他这些年的文学插图向我出示并说到要结集出版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他的作品里,我看到了一种从传统经典延续下来的精神,更看到了由他塑造的一个个有灵魂的生命。应该说,张润世的文学插图集是一本不仅属于文学也属于艺术的插图画集。他为将近60本文学作品画的插图,已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当这些画面作为文学插图时,它们是张润世感怀人生与现实的记录,是张润世性格、心理、遭遇和处境的缩影。面对为文学做插图的“任务”,张润世不是被动的做文学故事的“图说”,也不是做文学人物的“图解”,他总是在理解和消化文学内容的同时,将自己的情感和与文学的情节联系在一起,并且以文学人物为契机,展开自己对于生命与生活的感受。他的文学插图最突出也是最有价值的特征是表现了鲜活的人的情态,这种情态是一个个有情有欲的人物动态和相互关系构成的。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之中,他像一个导演拍小电影一样,将文学故事中的主人公当做演员,编排他(她)们的造型和动作,但与此同时,他自己又是一个演员,在插图的空间里扮演者真正的人物角色。这种“双重角色”的插图创作方式是饶有意味的。实际上,在他沉浸与创作的日子里,他的“演员身份”更加占有主导地位,他甚至就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在自己想象的虚拟的空间里变换着各种角色,喜怒哀乐都在其中。所以,他的作品让人看到了一种中有情绪、有动态、有灵魂的形象。
张润世为中外多种主题的文学作品做过插图,有的是小说,有的是寓言,有的是神话。他在形象创造上的路子非常宽,能够让自己的想象走进不同的文学作品的世界,但无论何种内容,突出人物的身份与状态,集中刻画人物的表情与性格,是他不同作品共有的特性。紧紧围绕“人”和人的“情态”,为“人”和人的“情态”造型,是他艺术创造的立足点。因此,他最精彩的作品是那些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做的插图。这部分文学作品切入都市,直呈人性的当代属性,使张润世更加会心。在这部分插图中,他淋漓尽致地调度了远近跌宕的空间关系,使人物间的关系如同超现实主义绘画流派般多变,他通过最能体现视觉造型特征的“肢体语言”,把人的动作表现的十分强烈,甚至推向极端,将人性和人的灵魂深处中潜在的欲望释放了出来,他的有些作品气氛晦冥,如是探向情感的神秘空间,有些作品色调优美,人物尽在缠绵之中。总之,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再一次接近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地带,那里有灯红酒绿下的复杂意绪和晃晃悠悠的感觉,也有超越现实的向往。
张润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铜版画的方式创作的。这首先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期间主攻铜版画专业经历有关。作为科班出生的画家,他已经在铜版画的表现上掌握了娴熟的技巧。但是,他在文学插图创作中大量使用铜版画或类似于铜版画效果的图绘方式,则在于他与铜版画这种特定的语言特征有强烈的心理应和与情感默契。铜版画的干刻、腐蚀,着色等技巧造成的视觉效果是十分丰富的,既可以细致入微地刻画形象,又可以整体浑然地营造氛境,不像用线描勾勒,只能抓住物象的外轮廓,也不像用其他的绘画方式,展现可能只是造型手段本身。在我看来,铜版画这种具有“素描”效果的特征有着十分朴素和纯粹眼语言的属性,又有显示出明暗、层次和画面肌理的材料质地属性。当一种绘画方式在物质性和精神性两个方面都与画家的性格和创作欲求形成内在关系的时候,它就自然成了画家的选择,乃至着迷的事物。在欧洲古典到现代的绘画历史上,铜版画一直是画家乐于使用的技巧,甚至构成了许多大师级名家的艺术世界,例如荷兰的伦勃朗、西班牙的戈雅、德国的门采尔。他们在以油画创作为主业的同时,无不运用铜版画作为更直接的手法表现具有连续性的主题,表达从自己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感觉。系列的铜版画作品——其中有不少是文学插图——是这些画家的个性更为真实和更为丰满,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铜版画在欧洲之所以从传统一路延续到当代,就在于他维系了画家的真实回忆,承载了一种近乎喃喃自语的叙述。由此可以说,张润世将同伴画的效果大量运用于文学出插图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他的作品展开的就是具有回忆和想象色彩的叙述。
张润世而仅是一个著名的插图画家,他作品的大一暑假手臂一非同寻常,我相信他会愿意驻守在插图这个属于他的小千世界里,不断地实现他的理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