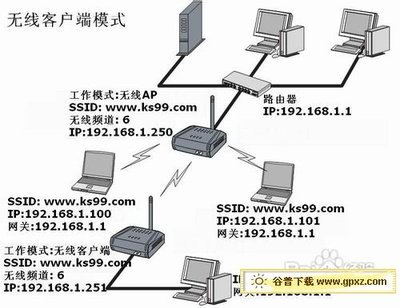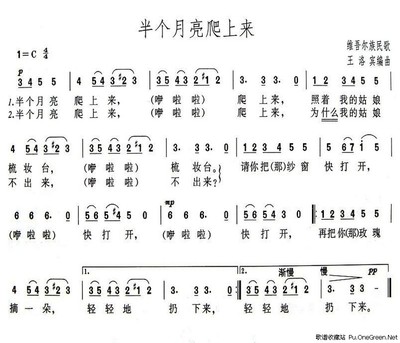作者:刘连枢
一
地道里的阴暗潮湿吸食了手电的光亮,微弱的落点还是照清了两扇石门,上面漾着细小的水珠,泛着幽幽的光。钌铞儿和一把老式锁锈成了铁疙瘩,只一拧就酥碎得失去把门的
作用。试探地推了推,石门竟然开了,一道道黄光白光红光蓝光刺目耀眼。定睛看了,闪黄光的是金条,发白光的是银锭,泛红光蓝光的是宝石。这些金银珠宝原本装在箱子里,可箱子板已经朽成末儿,宝贝堆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小山。回身看看,不见有人,这才把手伸向一根金条———啊!金条似乎是刚刚浇铸的,烫得大叫一声……
王一斗醒了,手掌上虽没有灼伤的痕迹,但分明感到火辣辣的疼。
满囤妈被惊醒了:“又做你那发财梦了吧?”
王一斗认真地说:“这回梦得真真儿的,比过去哪次都清楚。”
“再清楚也是梦,有能耐真的拿回一根金条来,让我过过眼瘾也行呀。”满囤妈翻过身去,亮出发面饼似的圆滚后背。
几十年来,王一斗重复地做着同样的梦,有时清晰,有时朦胧,内容大同小异,几乎一成不变,结局都是被金条烫醒,每次醒来,手掌都感到火辣辣地疼。王一斗请过不少睁眼的瞎眼的睁一只眼的瞎一只眼的算命先生,但都无法解析这个梦,也说不清这些年为啥总做同样一个梦。只好认同满囤妈的话:“都怪你不开眼的爷爷给你起了个一斗的名儿,你这辈子顶多就是一斗粮食的命,穷疯了就做发财梦呗。”
起风了,院门口老槐树的枝杈借助月光把影子投到院子里,映到窗户上,不停地摇啊摇,摇得王一斗神情恍惚,好像躺在漂泊的小船里。二十岁那年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他和现在的满囤妈在河北定兴老家的小河边幽会,躺在船篷里,相互拥抱着。怀里的姑娘可不是现在发面饼似的圆滚后背,一条家织布的大红裤腰带在她细腰上系了三圈,他给她宽衣解带,一圈圈地觉得是那样繁琐和漫长……第二天,王一斗就来到北京城一家煤铺送煤拉脚。就像如今四川、安徽盛产小保姆一样,早年的沧州、静海常出太监,三河、乐亭常出老妈子,北京城里送煤的、摇煤球的大多来自河北定兴,这都是因为彼此引导推荐介绍鼓吹的结果。有了糊口的营生,没有住的地方,王一斗请“跑房纤儿”的租下三小间东厢房。安个家,不容易,一切都要现置买,可哪有那么多富余钱呀?于是从煤铺借来一块铺板,没有铺凳,就找来四根木桩两块木板,木桩一头削尖砸进地里当立柱,木板按铺板的宽窄长短钉在木桩上做横梁,代替铺凳使用。有一根木桩砸进地里不到半尺就咚咚地钉不下去了,心想遇到了砖头,就没有再往下钉。闹得他睡觉时,一翻身床就摇晃,一摇晃就感觉是躺在船篷里,就想起大红裤腰带在细腰上系了三圈的姑娘。也就是从躺在这张摇摇晃晃床上的那天夜里开始,王一斗做起了在暗道里发现金银珠宝的梦。
这天夜里却不然。也许是因为即将搬离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宅院的缘故,也许是第六感觉此时此刻发挥了神灵作用,也许是命运的使然注定要让“一斗粮食的命”的他梦想成真一回,冥冥中,王一斗想到了如同躺在船篷里的那张摇摇晃晃的床,想到了那根砸进地里不到半尺就钉不下去了的木桩。可为啥发出“咚咚”的空声,应该是“噔噔”的实声才对呀,莫非砖头底下盖着……啊,王一斗不敢再往下想了。他从褥子边摸出一盒清凉油,打开,用食指抿了一块,涂抹在太阳穴两侧。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遇到急事烦事愁事或后悔的事不顺心的事想不开的事,太阳穴两侧的大筋就突突,一突突脑子就炸开似的疼,一疼就必须赶紧涂抹清凉油。但只是起麻木作用,脑子不一定有多清醒。
王一斗摇着发面饼般的圆滚后背:“哎醒醒,别睡了。你说咱住的这个院子,早年间会不会是太监的暗宅?”
满囤妈起身拉亮电灯:“你不是还在做梦吧?”
王一斗忽地坐起来:“睁开你俩窟窿好好瞧瞧,我是做梦吗?”
满囤妈索性也盘腿坐定:“那好吧,有话说有屁放,二踢脚摇铃铛,是带响儿的我都听着。”
“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事,你听说过吧?”
“前些天,电视上还演了呢。”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前,慈禧太后把皇宫里的金银珠宝装了八大马车,藏到一个太监暗宅的井里,这你也听说过吧?”
“这一片儿上了年纪的谁不清楚呀,就差地球上的人都知道了。”
“后来,八国联军撤了,八大马车金银珠宝藏在井里,直到慈禧太后归天也没挖。”
“那都是人穷疯了瞎传,要是真的还能留到今儿个让你惦记?”
“要是瞎传,天下大乱时,为啥把南屋的夏五爷整成神经?”
“整成神经的多了,又不是夏五爷一个。”
王一斗有些恼了:“你娘那臭脚!我没工夫跟你抬杠。你想过没有,藏着八大马车金银珠宝的那眼井,就埋在咱家南屋地下。”
满囤妈一点儿不觉得惊讶,张圆了嘴巴打了一个哈欠:“这样吧,我睡我的觉,你自管在南屋地下挖地三尺,反正要不了几天一搬家,这房子也就拆了,当心老胳臂老腿儿的别扭着。要真是挖到金银珠宝了呢,叫我一声,我帮你拿,省得金条把你的手烫破了皮。”
满囤妈的挖苦和贬损没能阻止王一斗对梦的解析,他打定主意非要刨开南屋地看看当年挡住那个削尖木桩的东西到底是啥,要是一块砖头也就死心了,真要是那……别说自个儿后悔一辈子,儿子孙子重孙子祖祖辈辈都要悔断肠子。难道这辈子一轮到他烧香,灶王爷就调屁股的事还少吗?
王一斗起身下床,提了提大裤衩子,穿过堂屋来到南屋,拉亮电灯,搬开紧挨南房山的破木箱子,露出水泥地面。其实,王一斗不止一次地想刨开屋地看个究竟,但都鬼使神差地错过了机会。到了京城煤铺送煤拉脚,那个大红裤腰带在细腰上系了三圈的姑娘要进城来看他。他在当铺买了一张双人床,摆放在北屋,就将南屋那个用木桩和铺板搭建的单人床拆了。当拔出那个摇摇晃晃的木桩时,他本想刨开屋地看看。就在这时,从院子里传来夏五爷一句“王一斗有人找”的喊声。他出屋一看,是细腰姑娘。半年不见,干柴烈火,一阵亲热,一番云雨,哪里还顾得上刨开屋地看看呀。再一次想刨开屋地看个究竟,是把砖地改成水泥地的时候。这三小间东厢房地面铺的是青砖,一到夏天就返潮,王一斗求房管所在砖地上抹了一层水泥。当房管所工人师傅用大木抹子将和好的水泥铺摊开来的那一瞬间,王一斗又冒出把靠房山的那个地方刨开看看的想法,可当着几个外人的面,不便暴露自己心思。就这么一犹豫一恍惚一愣怔,水泥在大木抹子的挥舞下把青砖地严严实实地覆盖起来。这以后好长一段时间,王一斗莫名其妙地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没着没落,而且至少有一年工夫没有再做那个发财梦。
王一斗从工具箱里找出錾子和锤子,蹲下身刚要操作,又停下来,走过去拉上窗帘。夜深人静,偶尔有一辆载重汽车呼啸而过,震得窗户微微地颤抖。尽管轻手轻脚,不敢用太大劲,但铁锤子砸在钢錾子上发出的清脆而尖利的声音,足以惊醒睡梦中人。这样下去怎么了得,满世界的人都会听见。王一斗找来一只破鞋底子垫在錾子上,锤子再砸下去,只有地颤动,声音小多了。
窗户忽然亮了,西厢房白炽的灯光映过来。
王一斗停下手,专注地听。
“哗啦啦……哗啦啦……”,尿水注入尿盆发出的声响,清晰地钻进王一斗的耳朵。这个娘们儿!王一斗心里骂着,一时走了神,脑子里闪现出枝子妈大脸庞大嘴巴大眼睛大耳朵的形象。妈的,那窟窿眼儿肯定也大,不然撒尿不会像老母猪似的,也不会掏空了丈夫的身子要了枝子爹的命,自己老早巴早就守寡。
西厢房的灯灭了,东厢房暗下来。王一斗重新操起錾子锤子与水泥地较劲。不一会儿,两三厘米厚的水泥地就酥了碎了被橇开了,露出原来的砖地。掀起一块块砖,用铁锨挖不到半尺就发现当年挡住木桩的一块青砖。这青砖很大,王一斗一圈圈儿地扩挖着,亮出青砖的真面目,竟有二尺见方、三寸来厚。活了六十多岁,王一斗还没见过这样大的砖。他用力一撬,青砖裂成了几块。他不知道,此时他犯下一个大错误,损坏了一块说不上是国宝级至少也是极有收藏价值的文物。不然,王一斗起码也少吟诵一次“后悔哟后悔死喽,后悔哟后悔可喽”的咏叹调。
搬开裂成几块的青砖,露出一个口有水缸大小的黑窟窿,王一斗激动得几乎窒息,一时竟不知所措。这就是那眼藏有金银珠宝的井吗?这不会又是做梦吧?王一斗静了静神儿,猫腰想看个究竟,一股阴冷的潮气撞在脸上,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蹲下身来,颤兢兢地打量着黑窟窿,似乎这不是一眼井,而是一头张开大嘴的怪兽。让王一斗不解的是,这眼井的井壁不是砖砌的,而是用弧型大瓦构成,四周夯的是三合土,土里白灰的颗粒依稀可见。王一斗抄起一块碎砖头,试探地投进井里,发出“嘭”的一声响,好像落在了木质的东西上,也不是想像的那样深。
王一斗回到北屋,刚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就被满囤妈一把按住了。
“你拿它干啥?我新换的电池。深更半夜不睡觉,叮叮咣咣闹耗子呢?”
王一斗压低声音说:“我挖出井来了。”
“井?出水没?赶明儿咱吃水不用交水费了……”
不等满囤妈贫完,王一斗把老婆子死鸡拉活雁似的扯到南屋,指着黑窟窿说:“睁大你那狗眼好好瞧瞧!”
满囤妈的眼睁得大大的,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王一斗打开手电筒,照向黑窟窿,一束光柱穿透翻滚着的团团雾气,照亮了井下三四米处铺着的木板。他让满囤妈找来支蚊帐的竹竿,伸进井里,竹竿的一头杵到木板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听见了吧,是空声儿,木板底下一准儿还有井。”
后来证明,王一斗的揣测是对的。在用弧型厚瓦衬砌的井壁中间,横铺着一块块木板,而且是一水儿的柏木,足有半尺多厚,木板下掩盖着一眼青砖白灰砌的大口井,井底部还有卧井,卧井把口安有两扇石门,打开石门,里面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与王一斗梦中的景象几乎一模一样。
满囤妈缓过神来:“即便木板底下有井,你敢保证有金条银锭?”
王一斗说:“咱挖开它瞧瞧不就知道了。”
满囤妈说:“咋挖?这么深,你我都老胳臂老腿儿的。”
王一斗说:“你是绝户呀?咱把儿子从老家叫来。”
满囤妈说:“满囤能听你的吗?媳妇打个嚏喷他都哆嗦。”
王一斗想了想,编出个主意:“就说这次房子拆迁补偿了好几万块,媳妇立马儿会给满囤插上翅膀飞来。”
满囤妈有些犹豫:“再过十来天咱就搬家了,破东烂西的我还都没收拾呢。”
“要不说你头发长见识短呢!挖出金银珠宝来,家里那些破东烂西的你还要哇?卖给收破烂儿的还要看我有没有工夫。”
满囤妈低声说:“老头子,咱这么干,犯法不?”
王一斗说:“犯啥法?犯谁的法?咱在这屋子住了几十年,埋在地里的东西就应该是咱家的。再说了,人不知鬼不觉的,只要咱不说,神仙也不知道。”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喵———”的惨叫,长长的,怪怪的,鬼哭狼嚎一般,划破了整个夜空。王一斗吓得心惊胆战,头发根子都立了起来。满囤妈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这让她正好看见老头子大裤衩子的松紧带不知为什么绷断了,大裤衩子出溜儿滑下来,露出了黑乎乎的一嘟噜玩意儿……
奇耻大辱啊!一个堂堂几万万人的泱泱大清民国,让区区几千个洋毛子就给整治了……噢,对了,不是大清民国,还不到民国呢,男人还留着辫子,是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几千个洋毛子,还是八国联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凭着船坚炮利,没费吹灰之力就攻陷了天津卫。北京离天津二百多里地,快马也就一天的路程。京城皇宫里一下子慌了神,真是慌了神。宫里的大臣太监娘娘妃子可以跑,金銮殿的金银珠宝可没长着腿儿,万一洋毛子攻进北京,闯进紫禁城哄抢怎办?李莲英鬼点子就是多,伏在老佛爷耳朵边嘀咕了几句。老佛爷一听,骂开了,你们这些狗东西,别看没了坠着身子的秤杆秤砣,花花肠子一点儿也不少。就说你吧,瞒天过海在宫外建了两三处暗宅,还娶妻纳妾,收养继子。没有冤枉你吧?李莲英小脸刷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佛爷圣明,奴才该死!天下事甭想瞒过老佛爷您。老佛爷只好依了李莲英的主意,火烧眉毛,兵临城下,屎堵屁股门,不依不行了。吩咐马上装箱,金银珠宝连夜转移出宫。这时候,有探马来报,八国联军出了天津,直奔北京而来,先头部队已经过了武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