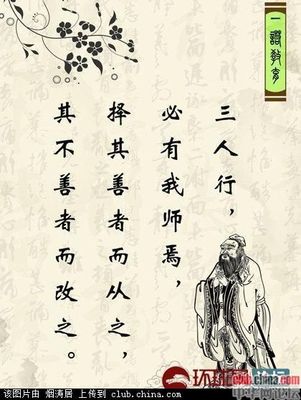史成芳是罗田三里畈人,华师中文系82级的。名字挺女性,但绝对纯爷们。他身材高大,头发天然卷曲,还有一脸络腮胡子。与人说话,总是满脸堆着笑。因为都是罗田人,又都是学中文的,我们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史成芳毕业后,分到湖师中文系,教写作。交往没有多久,就让人感觉他挺另类。他研究八卦,练气功,和别人聊天时,如果在寝室里,就喜欢打着坐说话。那年月,湖师中文系资料室在三角塘附近的教学楼一楼,老史没事就去那儿,一呆就是一整天。他不研究专业参考书,而是将系里刚买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摊在桌子上,探究在我们看来似天书的《周易》,偶尔还帮人算卦,因为说的头头是道,年轻老师喜欢围着他,让他预测自己不可知的未来,每次他都挺认真地计算着。有一次,中文系参加歌咏比赛,时间是晚上,下午他就预测说,中文系这次能拿第一,但过程会出点小问题。到晚上果然统计算分时出了纰漏,经过交涉,很快被纠正,我们真拿了第一。这事经办公室的冯老师一宣传,老史算卦的名气更大了,渐渐地,他有了“大仙”的美誉。老史人洒脱,颇有老庄之风,我那时为前途焦虑,而他似乎干什么事不紧不慢,给人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即便教写作,也和别人不一样,1986年冬天,快放假时,地处江南的黄石,下了场大雪。课程结业考试,老史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是《窗外雪野白茫茫》,空灵洒脱之气尽显。
大学老师,看似风光,其实压力挺大的。特别是年轻人,教学、科研、职称、提升学历,样样都不是省心的事。老史尽管洒脱,也必须面对这些。有一天,我去资料室,他也在那里。
咋不看《易经》啦?
他抬起头,说:不看了,要考研究生。
我说,考什么专业,哪所学校?
他的回答让我惊讶,考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
他手上翻看的,是1986年《比较文学年鉴》。那书挺厚的,绿色封面。
后来我去他母校华师读硕士,专业是世界文学。因为是定向委培,我的关系还在湖师,每次回黄石,我们都要见面。我还跟他介绍女友,女孩子是银行的,家庭条件优越,他去和人家见了一次面,但没有下文。一天,他提出请我吃饭,他借住在师院品字楼二楼的一间卧室,我住湖师的九平方单间,两地很近,就隔着一个小坡,我去了,他人不在。走廊上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似乎还留着火种,屋子里乱糟糟的,到处是英语书和复习资料。过了会儿,他匆忙进来了,我问,你请我吃饭,饭菜在哪儿啊?
“立刻,马上”他说,抽开炉子的风门,放上锅,将洗干净的藕和排骨,一起放进去。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着藕炖排骨。
与那些经常和他在一起厮混的青年教师比,我和他这样深入交流,还是第一次。我谈到华师学习的感受,还有自我想象的玫瑰色的未来:有可能出国,不出国呢,将来回黄石也不错,在湖师教书离老家近,偶尔可以回家看看父母,也挺好的。但老史说,这要求太低了,要是这样,他早就去读研究生了,他告诉我,他考上了复旦,当时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上的,但他放弃了。
为什么不去呢?
他还是强调,要读研究生,就要读最好的学校,他铁定心考北大,而且将来要到北京工作。
有仙风道骨的老史,志向如此远大,这让我刮目相看。那次吃完饭后,他练习打坐,我也跟着学习,但是坐在脏兮兮的床上,将两腿盘起,人极度不舒服,只好放弃。
1990年,我回到湖师。在系里教书,结了婚,一年后,有了孩子,教学科研外加班主任工作,忙而且充实。和老史的交往也是平平淡淡的。1993年,经过几年艰苦努力,老史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入北京大学,成了知名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他也是委托培养的,关系还在湖师,所以,去北京读书时,他让我代他领工资,按月帮他寄到北京。
老史人缘好,经常有湖师到北京出差的朋友去看他,我们也偶尔听到从北京带回的一些消息。他谈朋友了,女孩子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女儿,“老史潇洒啊,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女孩子穿行在北大校园”。回来的朋友给我描述。想象着一米八的老史骑在矮小的自行车上,带着一个女孩,总感觉浪漫中有些滑稽,但和老史的气质还是相符的。
1996年老史硕士毕业。夏天,他和女朋友小周,去了青海一趟,然后回罗田看望母亲,在回罗田之前,到黄石,我邀请他和女朋友在我家住了一晚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小周,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说话细声细气,言谈举止中透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那几天天气格外热,我家条件有限,但是小周很淡然。我招待他们吃饭,老史话格外多,给人感觉似乎与以前有点不同,仙风道骨之气少了,他兴高采烈地说到青海之行。“好远啊,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一坐车,就一天”。他说,“不过,那儿藏民淳朴,晚上饭后在帐篷外唱歌,无论唱多久都不收钱”。我很惊讶,第一次听说老史会唱歌呢。
我考取博士不久,老史又考取了博士。还是北京大学,导师还是乐黛云先生。不过老史有了一个新光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生!
老史,这位从罗田山乡走出的读书人,不断创造奇迹,北大、比较文学博士、娶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女儿为妻。大家都为老史高兴,无论如何,老史的前途都是光明的,知名的导师、新兴的专业、北大的牌子和学习氛围,加上他的聪慧和努力,老史有可能成为世界知比较文学专家,甚至可能是周游世界的名学者。我们都认为老史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这个罗田三里畈农村走出去的读书人,遭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光。
我那时在武大,苏州大学王钟陵先生邀请我的导师陈美兰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精粹》,先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师弟小刘。为了找北大陈平原等先生编纂的《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汇编》,我想到在北京的老史,想叫他帮我买一套。
“你要快点给我寄过来啊”。
我火急火燎地催他。
他说,我病了,行走不便,我叫小周去帮你办。
我没有细问病情,只是说,要多保重,不要太拼命啊。因为在我看来,健硕如老史这样的人,身体不会有大问题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老史得的是绝症:直肠癌!
老史知道自己的病后,明白死亡随影随行,但他非常镇静,一边治疗一边以顽强的毅力撰写博士论文。他研究的是一个艰深的理论问题:《诗学中的时间概念》,我不知道老史会怎么对时间那么敏感?论文完成了,他还带病参加答辩并且获得了优秀。当生命结束时,老史应该在悲凉中有一丝安慰吧,他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他无愧于这个称号!
老史是在北京去世的,当时湖师的好友一起为他募捐,中文系几个朋友的钱是我寄出去的。老史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八宝山办的,骨灰由他母亲带回罗田,她母亲我见过,干练、大气、善良,当时黄石有一个退休的女老师办了一个读书会,倡导青年人多读书,为增加读书会的吸引力,她邀请湖师的年轻老师参加。老史可能参加过几次,老史的母亲得以认识这位热心的女老师,87年春节,老史的母亲邀请这位独身的女性到罗田过年,在车站,老师还在犹豫,老史帮着母亲做老师的工作。
当一个才华横溢的、为人洒脱的朋友突然就要离去,这个事情给我的震撼是无法言表的。我总是问,老史怎么会死呢?才36岁,年纪轻轻的,连中年都称不上啊。大家惋惜的同时,也有些疑惑。老史的死,在他的同学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当年有他的学长、师兄弟、同学留下了文字,这些同学而今都是知名的专家,比如孔庆东、旷新年等。旷新年写了《想起史成芳,想起了那些事》,从旷新年的文字中,似乎能找到一点根由:
史成芳的死令许多人感到惋惜和心痛,也使人许多同学因此对北大失望。他是死于癌症,死于爱情,更是死于这个社会的势利和偏见。他和他的一位师妹恋爱。在许多人看来,这是甜美的一对恋人,他们同一个专业。可是,他们的恋爱却遭到女孩父亲的反对,而她的父亲就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我们自己的老师。直到许多年以后,同学们还感慨,女婿都读到北大博士这个份上了,如果说地位的差别,能差到哪里去呢?如果说史成芳是农村出来的,然而,中国所有的人上数两代三代,有几个不是农村的?看到他们恩爱的样子,我们无法想象,今天的父母会忍心拆散他们,而且拆散他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许多同学都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像我自己,由于从农村出来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都已经忘记了我本来的农村身份了。在20世纪末的北大校园,一场感天动地的爱情被我们自己的老师踏碎了,随之被踏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的心和他年轻的生命。一个年轻的生命倒下了,那没有倒下的未亡人,又是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即使他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吧,然而,最后被毁掉的还有他自己女儿一生的幸福。可是,这就是今天的世道。哪怕我们的生命倒下,也要让他们的偏见通行。我们命如草芥,被任意践踏,无声无息,化为泥土。
而今,旷新年是知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评说尽管掺杂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愤懑情绪,但还是说出了某些真相。我以为老史英年早逝,是死于一种责任和担当,他爱一个人,他要证明自己有给对方幸福的能力。他想在中国顶尖的学校和新兴的专业里有自己的位置,那是确证自己价值和幸福的基础。他一直在努力,既为了表达自己对学术宗教般的虔诚,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对爱情的承诺,还是排遣内心郁积之气方式。但命运似乎不给他机会,他过早的走了,只留下我们这些人空洞的猜想和感叹。
前年暑假,已经是一所大学书记的幼金老兄电话我,说想去看看老史,约我同行,可惜当时我在江西。幼金说,他几次在梦中见到老史,那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人啊。
是的,今天写这篇文章,也是为纪念家乡英年早逝的才子,希望人们还记住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