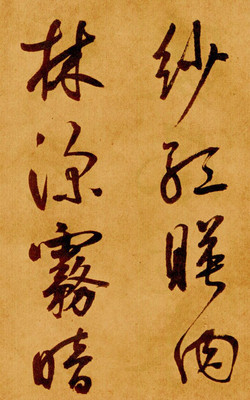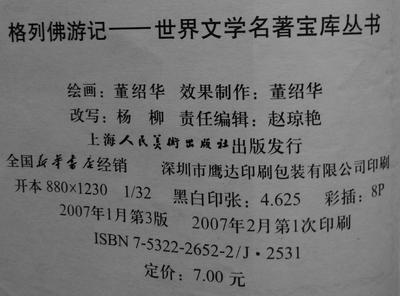《诗经·秦风·无衣》注解及释义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①。王②于兴师,修我戈矛③,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④。王于兴师,修我矛戟⑤,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⑥。王于兴师,修我甲兵⑦,与子偕行。
①袍,长衣。行军者日以当衣,夜以当被。朱熹《诗集传》“袍,襺也。”襺,纯用新丝绵所铺的袍。同袍,友爱、互助意。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至其死。
②王,指周天子。春秋以前惟周天子得以称王,诸侯则否。故此处非指秦国国君。王先谦《集疏》:“秦自襄公以来受平王命,以伐戎所兴之师,皆为王往也,故曰‘王于兴师’。”
③戈,古代的一种曲头兵器,横刃,用青铜或铁制成,装有长柄。中国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朱熹《诗集传》“戈,长六尺六寸”。矛,长柄,有刃,用以刺敌。是古代军队中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朱熹《诗集传》“矛,长二丈”。《考工记》“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长二丈也。夷矛则三寻,长二丈四尺。
④泽,一说同“襗”,里衣、亵衣。诗集传“以其亲肤,近于垢泽,故谓之泽”笺云:泽,亵衣,近污垢。正义曰:衣服之暖于身,犹甘雨之润于物,故言与子同泽,正谓同袍、裳是共润泽也。
⑤戟,又作“棘”。合戈、矛为一体,可刺杀也可勾啄。出现于商、周,盛行于战国、汉晋各代。《诗集传》“戟,车戟也,长丈六尺”。
⑥裳,下衣。此为战裙。上曰衣,下曰裳。《帝王世纪》:“黄帝始去皮服,为上衣以象天,为下裳以象地。”《说文》“常,下裙也。裳,常或从衣。
⑦甲,总称甲胄。兵,总称武器。《东周列国志》:“收天下甲兵,聚于咸阳销之,铸金人十二,每人重千石,置官庭中,以应‘临洮长人’之瑞。”
对于此诗的主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毛诗正义》认为《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另一种则以《诗经原始》、《诗集传》为代表,认为《无衣》,秦人乐为王复仇也。而我则赞同后者,通读本篇,丝毫没有刺用兵之意。
诗中“王于兴师”可知,此王必是周王。春秋之前惟周天子为王。楚虽僭称王,然北方周地只称楚子(周封楚子爵)不称楚王。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受王命攻打犬戎。王封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歧丰之地。”秦始为诸侯,封于歧丰故周之地。则此王为周平王。周王兴师讨伐犬戎,故曰“同仇”。周人长期受犬戎侵扰。幽王时,犬戎攻克镐京,屠掠周地。故周人苦犬戎久矣。而秦人居于西戎,必然与犬戎有间隙。兴师讨伐犬戎,何来不满?必是同仇敌忾,互相召唤、互相鼓励,舍生忘死。《诗经原始》有云:“夫秦地为周地,则秦人固周人,周之民苦戎久矣,逮秦始以御戎有功,其父老子弟欲修敌忾,同仇怨于戎,以报周天下者,岂待言而后见哉?”且秦与犬戎有仇。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人君主死于犬戎之手,故上下一气,为其君仇,所以能同仇敌忾。所以《诗经·无衣》唱道:“与子同袍,与子同仇;与子同泽,与子偕作;与子同裳,与子偕行。”何来秦人讽刺其君好战与?
再者说,秦人与戎狄杂居久矣,故其民风彪悍,好战、喜战。《诗集传》有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秦地本身水土厚重,其民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汉书·地理志》有云:“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由此可知,秦人尚武之风浓烈。魏源《古诗微》云:“《无衣》,美用兵勤王也。秦地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尚力气,故《秦风》有《车邻》、《小戎》之篇及‘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之事。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至其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之先世与戎仇,屡有勤王敌忾之事,至后世民俗犹存。”又因为秦人长期与犬戎有间隙,纷争不断。由秦仲到庄公再到襄公。三代与犬戎有战争。再结合此诗背景,乃秦响应周王西征犬戎,国仇家恨在一起,其人民又怎么会因征讨犬戎而讽刺君主好用兵呢?
再从诗本身来说。全诗共三章,用“赋”的表现手法,在铺陈复唱中直接表现出战士们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首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言明我秦人与戎狄既有国仇,也有家恨,故曰“同仇”次章“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都是以“岂曰无衣”开言,正如前面所述,并非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递进至“与子偕作”。既然已经是同仇,之后必然要复仇,如何复仇?定是“与子偕作”。最后尾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多说无益,此仇不共戴天,唯有与子共赴沙场,一雪前耻。越往后读,气血越沸腾。读完最后一句,气血沸腾,豪气冲天,不上战场厮杀一番不痛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泽、同裳。此并非真的共用一件袍、一件泽、一件裳。而是通过写共用衣服,表达出同生共死,同仇敌忾,相互扶持之意。为什么诗中的秦人可以与子同袍呢?正如第一句所说“与子同仇”正是有共同的敌人才能同生共死。既然都可以同生共死了,那么必然可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了。袍、泽、裳并无特定意义,但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重沓复唱中表达出秦人不畏死亡,大无畏的精神。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读之不禁受到强烈的感染。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可推断出,此诗有可能是秦人的军歌,表现了秦人并肩作战的无为气概,充满激昂的精神。唱着如此同仇敌忾之战歌奔赴战场,百战百胜也不足为奇了。谢氏枋得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天下无复知有复仇志,独《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此诗富有浓浓的复仇之意,即为复仇,秦民又怎会讽刺其君主好战用兵呢?有云:“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能及。”
与《邶风·击鼓》篇相比较《秦风·无衣》篇就更无刺用兵之意了。《邶风·击鼓》写了一名士兵被迫南行,与妻别离,却无归期。诸如“我独南行”的“独”,与无衣篇中反复出现的“同”字有着强烈的对比。“独”写出了,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擅动刀戈,与民意相悖。而“同”不单单则写出兵与兵之间的同生共死,还写出了上下一心之意。《击鼓》中所写的士兵,与其妻立下契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后自己却被迫远赴战场,背离自己的誓言。此非我愿,却无可奈何。每读至此,哀伤之情油然而生。夫妻分离,也许再无相见之日。反观《无衣》也是奔赴战场,却没有儿女情长,而有同袍之情。此因《击鼓》乃讽刺其君用兵,导致家破人亡。《无衣》乃上下一心,同生共死。《击鼓》中的“不我以归”“不我活兮”道出了浓浓的厌战反战心理。而《无衣》中的“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则反映出了好战,喜战的心理。与之相比较,《无衣》是赞扬了团结对敌,保家卫国之意。并无刺其君用兵之意。
从诗本身的背景,民族风俗,诗歌艺术角度都没有讽刺其君好用兵之意。与诗经其他反战、风刺用兵的诗篇相比较也无讽刺其君好用兵之意。所以《秦风·无衣》篇是表达了当时秦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团结对敌之意。依据其诗的风格和激昂的气势,也极有可能是秦人奔赴战场时所唱的军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