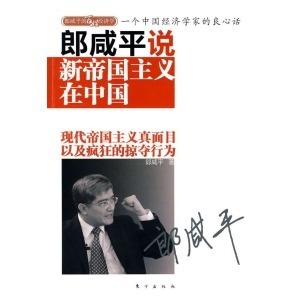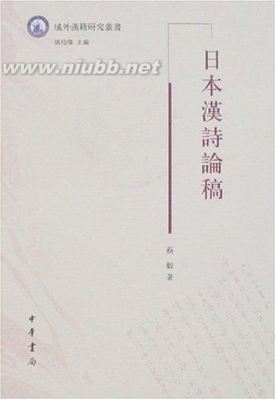
日本汉诗在中国
(日本)南山大学教授蔡毅
蔡毅,1953年12月5日出生,江苏南京人,京都大学博士毕业,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南山大学外国语学部亚洲学系主任,现任南山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有《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君当恕醉人——中国酒文化》(日文,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6)、《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编著,日文,勉诚出版,2002)等著、译多种。长于域外汉籍,以及中国诗学在东亚文化圈的研究。
上海师大古典文献学“文学与文献”第23次讲座(2012年4月),请日本南山大学的蔡毅教授讲日本汉诗。以下是他精彩的发言:
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中国古典诗歌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反之“学生”的习作,也曾摆上“老师”的案头;“支流”的活水,也曾对“主流”有所回馈——这种日语称之为“逆输入”的现象,因其数量甚少,作用甚微,迄今似乎无人问津。本文拟从文化交流双向互动的视点出发,对日本汉诗传入中国的历史轨迹作全方位的扫描和评述:1、日本汉诗人的在华足迹及其创作活动;2、日本汉诗人为实现作品跨海西传所作的努力;3、日本汉诗对中国诗歌反转性影响的可能性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通过对这种“逆向反馈”文学现象的解读,揭示东亚汉文学史上罕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并为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提供一个重新认识的崭新视角。
日本汉诗作为中国文学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条支流,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所谓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在漫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有一些日本汉诗以各种方式传入中国,并获得了或隐或显的种种反响。尽管其数量和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靡东瀛相比,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但作为一种“逆输入”的文化现象,同样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笔者对这一课题产生兴趣,其实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缘。
在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汉诗,江戶時代末期释月性的《将东游题壁》: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
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作者月性(1817-1856)为幕末志士,这是他离别山口故乡时的述志之作,后来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立志诗”。但笔者赴日留学之初读到这首诗时,却觉得似曾相识,于是立刻判定这是对中国古人某首诗的“剽窃”,一百多年来日本学者竟然无人指正,实属疏漏。可是,当我想证实自己的“断案”时,却怎么也不能如愿。惟一可补日本各种注本不足的,是找到了后两句的出处: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以遗子由二首》之一“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后来陆游《醉中出西门》诗又用东坡语“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明代都穆《南濠诗话》已指出苏、陆之間的继承关系。然而这不过是极其正常的用典,和我最初的“剽窃”印象毫不沾边。
带着这个疑问,1993年末,我回国探亲。当时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国内正热播电视连续剧《少年毛泽东》。为了了解文艺家们是怎样把这位昔日圣主请下神坛的,我也顺便看了其中一集。突然一个画面跃入眼帘:朝阳喷薄欲出,长天一碧如洗,少年毛泽东站在翠绿的山冈上,高声朗诵的,正是这首诗。
原来如此。它被当成了毛泽东的作品。
据有关资料,1910年秋,毛泽东请亲戚说服一心想把他送到县城米店学徒以继承家业的父亲毛顺生,让他到湘乡东山小学校继续读书。临行前他抄录了这首诗,夹在父亲的帐簿里,让每天必览帐簿的父亲能够看到。建国初期征集革命文物时,毛泽东母亲文氏的家族把诗上交给地方政府。但因为诗并未写明原作者,后来便以讹传讹,被非正式地当成了毛泽东的作品。毛泽东是从何处读到这首诗的,目前尚不明。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注,该诗还曾刊载于此后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五期,依中文习惯,原作的“坟墓”被改作“桑梓”,“人间”被改作“人生”,与毛泽东抄录的相同,只是作者被误署为“西乡隆盛”。对这位明治维新的英雄,少年毛泽东出于崇拜之情,录其诗以明志,当然不可以“剽窃”断罪。问题在于长时期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中,研究者失于详考,舆论界疏于澄清,以致直到90年代,还被堂而皇之地用于有关毛泽东的影视作品。笔者当初不知就里,反而武断认定月性为抄袭者,正缘于曾经在国内看到过这首诗,但因它并没有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故而印象模糊,闹出了一个欲证其伪而始知己误的笑话。
这个误会,其实意味颇为深长。20世纪初内地湖南偏僻的乡村,居然也印有日本汉诗的足迹,那么在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创作的汉诗作品传到了中国?它们又获得了怎样的评价和反响?对这个几乎从来无人关注的“逆向反馈”问题,笔者开始了一场近乎大海捞针的艰难跋涉。
一、日本汉诗的西传轨迹
根据现有资料,中国人最早给予评价的日本汉诗作品,是空海的《在唐日示剑南惟上离合诗》:
磴危人难行,
石险兽无升。
烛暗迷前后,
蜀人不得过。[1]
空海(774-835),即弘法大师,是日本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作为遣唐使的一员,曾于唐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元年(806)入唐求法。其《性灵集》序云:
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夫泉州别驾马总,一时大才也,览则惊怪,因送诗云:何乃万里来,可非炫其才。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2]
按,离合诗本来是一种文字游戏,基本方法是切取前句首字的偏旁,作为后句的首字,再把剩下的部分加以组合,来构成一个新字,而这个字往往就是这首诗的主题(空海诗为登+火=燈,马总诗为人+曾=僧)。中国现存最早的离合诗是汉末孔融的《离合作郡姓名字诗》(《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所收,该卷还收有其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若干离合诗作品)。而如果把话题扩展到拆字游戏的话,与孔融大致同时代的东吴薛综嘲讽西蜀张奉之语,亦可纳入我们的视野:“蜀者何也?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另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诸葛恪语,作“有水者濁,无水者蜀”)这里关于“蜀人”的戏语,或许亦为空海所本。可是,离合诗在孔融以后尽管绵延不绝,但直到空海入唐之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不过是文人兴之所到,偶或为之,完全谈不上人气所锺,流行所至。另一方面,在日本除空海之外,现知最早的离合诗是收于《文华秀丽集》(818年成书)的小野岑守《在边赠友》,题下自注“离合”。诗为五言律诗(略有失律),各句首字“班”、“夕”、“衿”、“衣”、“弦”、“弓”、“绵”、“帛”,可离合为“琴絃”二字。小野岑守(778-830)比空海小四岁,从年龄上看空海在入唐以前似乎有可能接触过这种体裁,但如果考虑到空海入唐时才三十岁,此前仅为一介学僧,尚未与平安宫廷汉诗人多有过往,而小野岑守仅二十六岁,与空海之间也并无接点,因此这种可能性应属微乎其微。再看小野之作题为“在边赠友”,当作于他810年之后任地方官时,其时空海已经归国,反过来说他是受空海影响,也未可知。何况小野此作亦属昙花一现,之后又过了大约一百年,才开始出现收于《本朝文粹》的橘在列的离合诗,以及字训诗、回文诗等游戏之作。就是说,空海的这首离合诗,在日本汉诗史上,非惟空前,在相当长的期间除小野之作外亦属“绝后”,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问题也由此而生。空海此作,难道是他突然心血来潮,想落天外的产物吗?如果不是这样,又是什么机缘,使空海对离合诗这一特殊体裁产生了兴趣的呢?笔者认为,下述重要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在空海抵达长安前一年,唐贞元十九年(803)秋,以所谓新台阁诗人权德舆为首的文人唱和集团,掀起了一阵小小的离合诗以及其他游戏诗体的创作热潮。其成员为权德舆、张荐、崔邠、杨於陵、许孟容、冯伉、潘孟阳、武少仪等八人,被离合的文字为“思张公”、“私权阁”、“咏篇”、“效三作”、“好”、“五非恶”、“词章美”、“才思博”。这些作品收于《权载之文集》卷八,《全唐诗》则分隶于各人名下。我们知道,在中国诗歌史上,离合诗尽管早已出现,但至此时为止,一直是文人率尔操觚的即兴之作,如此众多的官僚文人的集体唱和,尚属首次。而综合考察空海的在唐行迹,如他在长安的广泛交游,编纂《文镜秘府论》时对唐代典籍的大量接触,对新潮文学的敏锐反应,以及与权德舆及其离合诗创作集团成员的接触可能,我们大致可以认定,空海的离合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
这一史实的认定,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实不可等闲视之。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于空海等遣唐使来说,其最高的文明成果,不是当今时代的科学技术,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唐代达于巅峰的文学样式——汉诗。空海竭尽全力搜罗整理的汉诗作法大成《文镜秘府论》,就是他对这一文明巅峰崇拜景仰的结晶。离合诗也许是因为初露峥嵘,当时的诗论家还未及予以关注,《文镜秘府论》对之没有道及,但“反音法”,“回文对”等细微的文字锤炼功夫,已为空海所瞩目[3]。当然,离合诗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故向无佳作,但对刚刚接触汉字文明、刚刚尝试汉诗创作的当时的日本文人来说,这无疑是汉字构造和汉诗艺术的最巧妙的组合,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极为困难,也极富挑战性。空海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并获得了成功,因而受到唐代文人的高度赞赏,使他们对这位来自文明后进国的文化使者刮目相看。这份光荣,无异于当今时代的一个小国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了金牌。正缘于此,空海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告之于弟子真济,并使其书之于自己文集的序言。
第二,从日本汉诗对中国诗歌接受的历史来看,空海的离合诗也具有特殊意义。如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汉诗的流行诗风,往往比中国本土滞后二百年左右,例如相当于唐代后期的平安时代前期,流行的还是六朝诗风。而空海此作,却感应着当时最时髦的文学风气,表现出与时代同步的创新能力。尽管空海在平安时代汉诗人中,显得颇为“另类”,比如他不像其他诗人那样一味专写近体诗,而垂青于日本汉诗人并不擅长的古体诗、特别是七言歌行,对当时几乎无人知晓的李白等盛唐诗人的作品也有所眷顾,因此离合诗之于空海个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独特性,或许属于一种例外,但惟其如此,也就益发显示出它的可贵。
第三,唐代中日文人之间的汉诗往来作品,多达一百二十九首[4],而其中真正的唱和之作,仅此二首。《性灵集》序云“兼摭唐人赠答,稍举警策,杂此帙中,编成十卷”,但第八、九、十卷均已散逸,这些“唐人赠答”的实情,已无从知晓。因此,空海和马总的离合诗,就成为一千多年来中日汉诗人丰富多彩的唱和往来诗中现存最早的作品,同时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文人对日本汉诗的评价记录,大辂椎轮,垂范可谓久矣。
踵武空海,终唐之世,中日两国诗人陆续有所交流。894年日本废止派遣遣唐使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使命,便主要落在僧侣肩上。日僧在入华求法时,于汉诗也有所眷顾,如入宋僧成寻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抄录的杨亿《杨文公谈苑》中,就收有日僧寂照的诗作。但迄于元代,这种日本汉诗的西传形迹,大都是零散、片断的,中国典籍对日本汉诗的集中著录,实始于明代。
明代因倭寇问题,对日本的关注大大高于前代。虽然较之于政治、经济、地理等关乎国运的情报,日本汉诗仅为附庸而已,但作为一种文化的表征,中国文人仍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明代典籍如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王昂《沧海遗珠》,乃至清代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以及《御选明诗》等总集中,都辟有专栏,收录日本汉诗。这些作品因为缺少日方资料的佐证,目前尚难遽断真伪,但其如此批量登场,无疑是需详加考察的课题。
与清代几乎同时的日本江户时代,因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中日文人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流,日本汉诗要通过特殊的途径,才有幸摆上中国文人的案头,对此本文第二章拟作详述。中国文人得以大量接触日本汉诗,并对之作有意识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要到明治维新海禁大开、两国重启人员往来之后。
19世纪后半,以俞樾编选《东瀛诗选》为代表,日本汉诗作为一个东亚汉文学的整体存在,被正式纳入中国文人的视野。该书收作家548人,诗5297首,不但是中国研究日本汉诗的奠基之作,在日本也是规模空前的一部总集。其编选所用日人诗集多达163种,堪称日本汉诗最大规模的西传。作为晚清大儒,俞樾对日本汉诗的平章月旦,现在已成为研治此业者的必备参考。但有违俞樾初衷的是,由于他的选材局限于日商岸田吟香所提供的资料,在诗人和作品的入选上与日本一般认识多有乖违,所以当时在日本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其实,真正的第一部中国人编选的日本汉诗集,应为旅日文人陈曼寿所编《日本同人诗选》。该书出版早于《东瀛诗选》,但因编者属无名之辈,内容也限于陈氏“同人”,故罕有人言及。其他如李长荣《海东唱酬集》、叶煒《扶桑骊唱集》、聂景孺《樱花馆日本诗话》,也都是晚清文人对日本汉诗在华传播所作的有益尝试。
除了这些选集之外,清末诗话类作品中也屡见日本汉诗的身影。如当时尚属罕见的具有赴德任教经历的潘飞声,因在柏林与日人多有交往,其《在山泉诗话》中不仅收有多首日本汉诗,还记录了他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其间隐含了对东西文化冲突的隐忧,颇具时代特色。下面介绍一则可略发史实之覆的实例:
孙橒《馀墨偶谭》正集卷五“日本诗人断句”条云:
日本诗教甚盛。近有词人江户百户藤顺叔(宏光),不远数万里,航海至柳堂从李
子虎光禄问诗,自称海外诗弟子。其别子虎有句云:“他日倘寻江户宅,白莲秋水夕阳
边。”亦殊有美思也。[5]
文中所云藤顺叔者,实名八户宏光,字顺叔(“百户”当为“八户”之误,而“藤”之姓,则应为顺承江户文人习惯,把自己的姓氏临时改为单字,以获取中国文人的亲近感)。这个八户顺叔,曾于1866年前后访问香港、广州、上海、南京等地,但因他1867年1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刊载了一条署名记事,揭露日本已经暗地里做好战争准备,图谋侵略朝鲜。这个消息随即经由北京清廷传到朝鲜政府耳中,乃至发展成為日朝之間的外交问题。也许因为捅了这个纰漏,他后来便隐姓埋名,以致在日本几乎找不到他的任何信息。端赖上引诗话,特别是王韬、李长荣等人的有关记述,我们才得以知晓其人的存在。中日两国文献的互补,也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由唐至清,一千多年来日本汉诗在中国的流布,虽不能说触目皆是,却也斑斑可考,不绝如缕。这些史实的廓清,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日汉诗往还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全貌。
二、日本汉诗人的西传努力
日本汉诗人在对中国诗歌学习的漫长过程中,从最初的单纯模仿,到有所创新,再到自成一体,经历了艰辛甚至痛苦的蜕变过程。江户中期以降,日本汉诗开始了“日本化”的探索,即在遵守汉诗基本规范的同时,也力求体现岛国风情,东瀛特色。这一动向,与当时日本开始增强文化自信、倡导国粹思想的潮流,是一致的。而在汉字文化圈的总体框架下,文化宗主国的认可,便成为周边各国争取对等地位的重要前提。具体就汉诗世界而言,则是力求获取中国文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汉诗的“本场”在中国,主流和支流,老师和学生,是中日之间无可置疑的历史定位。因此,支流如果能对主流有所回馈,学生如果能得到老师首肯,显然会极大地助长弱势一方的底气,尤其在日本民族本位意识抬头之际,这些来自彼岸大陆的赞语,就不啻春风化雨,加速催生此地独具风姿的异卉奇葩。
当然,在江户时期,还有一些渡日僧侣以及来往于长崎的清朝客商,他们为日本汉诗留下了不少序跋评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人对日本汉诗的理解和认识。但这些都发生在日本国内,并未回传中国,而且长崎清客均属商贩贾人,其评语多为逢场作戏,每见溢美之辞,当时日本有识之士也不以为然,故本文对此不予论列。
可是,西土虽然只有一海之隔,受制于锁国之限,也惟有望洋兴叹。怎样才能承受“正宗”中国文人的青睐呢?这里介绍两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事例。
一是伪造沈德潜等人赠诗事件。
这是日本汉学史上一个著名的笑话。据东条琴台《先哲丛谈后编》卷五、原田新岳《诗学新论》卷中等书的记载,其大致梗概为:
沈德潜于乾隆十八年(1753)为吴中七位诗人编定的《七子诗选》(共十四卷,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黄文莲、赵文哲、钱大昕、曹仁虎各二卷),不久就传到了日本。长崎汉诗人高彝(1718-1766,实姓高阶,字君秉,号旸谷)对之加以节选,各人二卷删为一卷,仍名《七子诗选》,复刻于日宝历七年(1757)。高彝向来自负诗才,以此为契机,便欲托人请沈德潜为自己的《旸谷诗稿》作序。他找到了来往于长崎、自称可出入沈德潜之门的杭州人钱某、尚某,以重金请他们转交自己致沈德潜的一封长信、五首七律,以及分别题赠七子的七首七律。二人归国后,谎称高彝为“侯伯执政者”,携厚礼叩访沈德潜,却被沈以华夷有别、日本入清以来未作朝贡、商贾之人不得私与其事为由,严词指斥,拒之门外。对此沈德潜《归愚诗钞》余集卷五〈日本臣高彝书来乞作诗序,并呈诗五章。文采可观,然华夷界限不应通也,却所请而纪其事〉诗以及《自订年谱》乾隆二十三年(1758)条均有明确记载。
碰壁之后,钱、尚二人苦于无计,杭州一老商以“日本人资性悫实易欺”,建议他们请寄寓杭州的落魄文人龚某作伪。龚某乃与五六学究合伙炮制沈德潜答书、和诗以及吴中七子次韵之作七首,钤以朱印,精心装裱,由钱、尚带回长崎。高彝得之,自然欣喜若狂,不仅重谢二人,还把伪沈氏诗中“才调能胜中晚唐”一句刻成印章,大肆炫耀。可惜好景不长,数年后沈德潜诗钞传日,其他长崎清客也纷传钱、尚欺诈之事,骗局终于败露。
现录伪沈德潜和诗二首如下:
奉题琼浦君秉高先生诗集并志遥注
昭代声华四表光,国风十五大文章。
尚教人杰锺旸谷,犹遍歌谣译越裳。
万里银涛飞锦字,百篇玉戛奏笙簧。
元音自是盈天地,酬唱相思叹望洋。
大雅如林今古芳,原无人不可登堂。
文鸣得似东西汉,才调能胜中晚唐。
读到君诗堪击节,谁言我论示周行。
多缘四海同心理,渺渺锺情忆大方。
归愚沈德潜草(钤印二方:“沈德潜印”,“归愚”)
诗格卑微,遣辞拙劣,岂能出自以“体格”自高的沈德潜之手?其伪不辨自明,徒为笑柄耳。关于这段公案,北京大学陈曦钟先生已论之甚详[6],兹不赘述。笔者只想补充一则轶闻:这些伪造的沈德潜及吴中七子诗原件,两年前赫然现身于日本古董拍卖网(上引二诗文本即据网络照片),听说已被东京一位专攻中国文学的学者买下收藏,可谓得其所哉。
二是赖山阳《日本乐府》的快速西传。
赖山阳(1780-1832)是江户后期日本汉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汉诗日本化的倡导者。他著名的〈夜读清诸人诗戏赋〉,逐一评骘了明末以来十五位诗人,或褒或贬,纯出己意,丝毫没有以往日本汉诗人因过于尊崇彼岸先贤而显出的谦卑之态。诗末云:
吹灯覆帙为大笑,谁隔溟渤听我评?安得对面细论质,东风吹发骑海鲸。[7]
对一海之隔的清代诗人,他已不满足于亦步亦趋,而是渴望他们也能听取自己的声音。他的《日本乐府》,就是这种日本民族意识高涨的集中体现。
赖山阳于文政十一年(1828)岁末,仿明代李东阳《拟古乐府》和清代尤侗《明史乐府》,一气呵成了分咏日本历史的《日本乐府》六十六首(其中有部分为旧作的改写),与当时日本六十六州之数相合。在日本汉诗史上,咏史诗夥矣,但大都是题咏中国古史旧事,如此全面、系统地抒写日本本国历史,以及运用乐府诗形式咏史,赖山阳均为第一人。其创作动机,如该书〈后记〉自述“我国风气人物,何必减西土”,即凸显日本的独立地位和存在价值。该书文政十三年(1830)冬刊行,一年多后就得到了中国文人的评论,在日本汉诗的西传史上,这也许是最快的一例。其传送何以如此之速?数年前在长崎发现的清朝客商江芸阁、沈萍香的书简,可以为我们破解这个秘密。
这些书简由兰学专家、京都大学松田清教授首先寓目,乃嘱笔者予以考察。书简现藏长崎县立美术博物馆,共52通,虽有部分破损、蠹蚀和缺页,但近两百年前的中国普通商人的书信文稿被如此妥為保存,仍不能不使人对日本人珍惜文物的热情肃然起敬。
以下略举数函为例,文字悉依笔者判读。江芸阁致水野媚川13号书简云:
今春所托评阅赖乐府,携归即送晚香主人。奈伊即日起程往浙江儿子署中去矣,
此书带去未还,且待伊归向索也。
水野是长崎“唐人屋敷”、即清客住居之所的管理者;“晚香主人”为吴县文人顾铁卿;
“今春”当为天保三年(1832)春天,其时距《日本乐府》刊行仅仅一年稍过,水野的动作可谓迅速。
不幸的是,在水野拜托江芸阁请顾铁卿评阅《日本乐府》一事尚无结果时,传来了赖山阳于该年9月辞世的噩耗。此后江还数次致函水野,字里行间似有难言之隐。所幸水野并没有惟江芸阁是求,他还同时悄悄地另觅高明,这个人也果然不负所望,他就是沈萍香。
沈萍香16号书简,其实并非信函,而是沈与水野的一段笔谈:
(水野):日本乐府赍归乞翁先生雌黄一件,深为拜托。
翁先生、榕园先生同学人。
(沈):翁海村,知不足。
我有微物,未曾检出,正月内奉赠,乞恕之。
翁公本来相好,榕园却不认识。当到吴门访托,勿负见委。
(水野):所赐科场书,看过毕瞭然。多谢。
(沈):缓日我尚有事奉托。
花月楼小集重刻否?
(水野):已告成,他日应上呈。
游记山阳批径电览否?
(沈):缓日我再要做跋。
(水野):敝邦一佳话也。
这份笔谈未署时间,从文中言及赖山阳“游记”(不详)而未言及其死,以及后文要谈到的钱泳题咏时间来看,当作于天保三年(1832)上半年。在新发现的江、沈书简中,这份笔谈也许最具有史料价值,下面且对此稍作详考。
水野首先拜托的“翁先生”,大概出自沈萍香的推荐。翁广平(1760-1842),字海琛,号海村,江苏吴江人。他的《吾妻镜补》作为中国第一部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该书引用日本资料多达41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堪称洋洋大观。而翁广平科举不第,仕宦无成,一生蜇居故乡平望,几乎足不出户,其资料何所从来?这里的奥秘,在于当时中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浙江乍浦,距其家乡不远,那些往返于长崎的吴门清客,他也多有交往,因此他才能享有别人不可企及的研究日本的便利条件。沈萍香是否了解《吾妻镜补》的写作,是否有将《日本乐府》纳入该书的希求,现在无从考证,但作为“本来相好”的同乡人,他知道翁广平是当地的“日本通”,才向水野推荐其人的,却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沈萍香瞄准的目标似乎更高、更大,这就是笔谈中的“翁海村,知不足”六个字。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因收入太宰纯校《古文孝经孔氏传》等书,在日本名震一时,林述斋的《佚存丛书》,即多为鲍氏所取资;市河宽斋编《全唐诗逸》,也以厕身其列为最高理想。而翁广平和鲍廷博交游甚深,《全唐诗逸》就是因翁广平推荐,在鲍廷博去世后,由其子鲍志祖于道光三年(1823)收入丛书第三十集的。该集还收有翁广平自撰记其族叔事迹的《余姚两孝子万里寻亲记》,这篇文章仅不足三千字,内容、体例与《知不足斋丛书》其他诸作迥不相类,可见他和鲍氏父子的交情非同一般。尽管《知不足斋丛书》至三十集已寿终正寝,但沈萍香并不一定知道详情,通过翁广平把《日本乐府》纳入丛书,会不会是沈萍香向水野许下的宏愿呢?
另一位拜托对象“榕园”,则出自水野之请。榕园即吴应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九经籍二十三云:
《榕园吟稿》十卷,吴应和撰。原名宁,字子安,号榕园,浙江海盐人。
吴应和既非达官显宦,也非文坛巨擘,更不像翁广平那样和日本有特殊的因缘,水野为何同时还选中了他?原来赖山阳天保二年(1831)秋于归省旅途中,曾抽暇评点了《浙西六家诗钞》,而这部诗集的编选者,就是吴应和。吴选编成于清道光七年(1827),而赖山阳的评点直到十八年后、嘉永二年(1849)才正式出版,当时并未流传,水野远在长崎,却如此迅速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可见他对赖山阳关注之切,了解之深。
也许因为沈萍香“不认识”吴应和,“访托”似乎并无结果,而翁广平那里,却不仅确确实实送达,翁还特意为之撰写了一篇洋洋近千言的《日本乐府序》,载其《听莺居文钞》。此外,该书又被送到了另一位与日本汉学颇有关联的清末文人钱泳手中。钱泳(1759-1844),字立群,号台仙、梅溪,江苏金匮人。曾与翁方纲等交游,娴于诗书字画,对日本文史亦颇感兴趣,因其家居今无锡一带,故可和翁广平一样从清客们那里观览日本典籍,赖山阳《日本乐府》即因此得以寓目。《赖山阳全传》天保三年(1832)十月廿四日条:
(清道光十二年)该日,清国钱梅溪,得沈萍香见赠其于长崎来舶时所获《日本
乐府》,乃作五律二首,追慕之馀,添书于小屏风,送来京都赖家(三年后送达)。中
川渔村云此由梨影见示。支峰又将其诗冠于《乐府》,并自添跋文,刊于“增补”本(明
治十一年二月)。
沈君萍香尝游长崎岛,于市中得《日本乐府》一册,持以示余,为题其后二首:
文教敷东国,洋洋播大风。传来新乐府,实比李尤工(自注:谓李宾之、尤西堂也)。
稽古联珠璧,斟今考异同。天朝未曾有,还拟质群公。
诗才真幼妇,史笔表吾妻。日月无私照,风云渐向西。
雄文标玉管,彩笔敌金闺。闻说扶桑近,高攀未可跻。
道光十二年十月廿四日,句吴钱泳题。[8]
钱泳的题咏,大概是中国文人对《日本乐府》最早的评价。正因其难能可贵,山阳之子赖复(支峰)才于明治十一年(1878)《日本乐府》改版增补时特意附于书后,并作跋曰:“而其诗,先考易箦后,经三裘葛,始寄送京师。”[9]钱氏作诗的“道光十二年十月廿四日”,正值赖山阳辞世后整整一个月,未知山阳冥冥之中,可曾对这异国知音发出一叹?值得注意的是,翁广平说“此册沈萍香先生得于长崎岛市中”,钱泳也说“沈君萍香尝游长崎岛,于市中得《日本乐府》一册,持以示余”,都未提及此乃日本人水野媚川特意嘱托。而无意得之,与有意为之,其在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实有天壤之别,因前者往往止于随心采撷,而后者则系自主推介,由此我们也更可感知新发现的沈萍香书简尽诉原委之可贵。尽管赖山阳本人或许出于自尊,或许鉴于前述高彝被骗的教训,其著作中并未提及这件请托之事,但从他与水野的密切交往来看,他是完全应该事前知情,并乐观其成的。《日本乐府》后来在中国也获得赞誉,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曾选其中〈蒙古来〉、〈骂龙王〉二首,评曰:“此二诗绝高古,不似日本人口吻。……意朱舜水之徒为之润色者欤?”[10]
上述二例告诉我们,江户时代的汉诗人为了突破锁国的封锁,获取彼岸贤达的只言片语,曾付出了怎样艰辛曲折、甚至走火入魔的努力。正因为有他们持续不懈的隔海诉求,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才得以桴鼓相应,蔚为大观。
三、日本汉诗西传的文化意义
日本汉诗对中国的回传、亦即日语所说的“逆输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首先,它再次印证了汉诗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纽带,是怎样把语言互异、国别不同的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历史上朝鲜文士访华时留存的《燕行录》、朝鲜通信使与江户文人的唱和往还,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但中日间直至明治时期之前,这种文士们的大规模同场竞技、一争短长的壮举,可惜并未出现。正缘于此,上述日本汉诗通过不同渠道的回流,哪怕只有一星半点,也如同空谷跫音,弥足珍贵。它说明文化交流尽管有主从、高下、强弱之分,但同时也是彼此渗透、双向互动的。特别是在强势一方已被充分认识之后,对弱势一方积极回馈的确认,便非惟拾遗补阙,更可相得益彰。
其次,它对过去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也起到了相对正面的作用。自《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迄于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大致经历了蒙昧鄙野(魏晋南北朝)→知书识礼(唐宋元)→凶残暴虐(明、清代前期)→文明开化(清末)的嬗变过程。其间虽因时势迁移、岁月流转而屡有变化,但日人能诗这一印象,始终使中国人能以温情的目光,注视着遥远东海中那块神秘的土地。因为“华夷之辨”的基本准则,并非地域人种,而是礼乐文化,如韩愈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1]吟诗作赋,则文野判然可别,史不绝书的中日之间的汉诗赠答,即其明证。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诸如传递信息、增进了解、刺激想象等社会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的相关话题。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即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国文人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认知的材料,以致难脱搜奇猎异、以助谈资的畛域。笔者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日本汉诗可曾对中国诗歌产生过直接影响?
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伪命题”。核之中日文化交流史实,如日本刀、折扇、和纸之类日本器物制作之精良,的确曾在中国引起过不同程度的赞赏,但如果语涉汉诗这一“家传宝典”,或恐难容异域之人反客为主。因为中国诗人面对日本汉诗人,长期以来一直以祖传正宗自居,在先生巨大光环的笼罩下,弟子们似乎唯有俯首听命,而毫无置喙的余地,遑论“逆向反馈”?然而,当我们瞩目中日文化交流发生逆转的清末、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会发现其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先说结论:笔者认为,与当时大量“日制汉语新词”回馈华夏故土,促进中国早期启蒙运动的时代气运相呼应,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在清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八年(1882)任清朝首批驻日使馆参赞期间,也曾受到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
众所周知,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创作成就最为显著者。其新体诗的一大特点,即梁启超所说的“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12],代表作如他使英时写的〈今别离〉四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东西半球时差,当时就得到了诗坛大家的交口称赞。陈三立评之曰:“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13]。此外,黄遵宪“百年过半洲游四”[14],他的大量记录日、美、欧出使行迹的诗篇,也被认为是开辟了诗歌领域的新境界。陈衍《石遗室诗话》有云:“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英簜与敦槃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迹之作,颇为夥颐。”[15]
诚然,上述评价如果仅仅准之中国诗史,黄遵宪的确当之无愧。但如果我们拓宽视野,把目光投向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话,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种景观了。早在黄遵宪赴日之前,东瀛的汉诗人就承维新之际西学蜂拥而入的时代风会,作了把西洋文明新事物、新语汇纳入传统诗歌形式的率先尝试。明治以后,国门大开,具有汉学素养的日本文人得以亲赴海外,看到他们以前只能通过书本神游的外部世界,并诉诸吟咏,形诸笔墨。众多漫游中国大陆的诗作姑且勿论,明治六年(1873)成岛柳北周游欧美归来,其《航西杂诗》在记述西方世界异域风情方面,已着了先鞭。明治八年(1875)森春涛编辑的《东京才人绝句》,则汇集了明治初期题咏“文明开化”的代表性成果。川田瓮江序云:“昔者咏物,花鸟风月;而今则石室电机、汽车轮船。耳目所触,无一非新题目。”“森翁此编,作诗史读,可也;即作文明史读,亦无不可。”[16]且略举其诗题、内容及作者如下:
航西杂诗咏“伦敦”等成岛柳北
夏日病中作咏“中外新闻”等铃木蓼处
横滨杂诗咏“瓦斯灯”等关根痴堂
杂咏十题咏“女学校”等藤堂苏亭
赠新闻记者某(如题)铃木半云
博览会(如题)八木萃堂
……
森春涛于同年创刊并主编的汉诗文杂志《新文诗》,则以每月一期的速度,不断推出标榜“清新”的汉诗近作。这份刊物虽然本以在维新大潮中“独守旧业”、即坚守汉诗园地为宗旨,但能顺时应变,在已显落伍的汉诗这一文学样式中吹进“文明开化”的新风,也称得上是“化腐为新,工亦甚矣”[17]。阪谷朗庐因日语中“新文诗”与“新闻纸”发音完全相同,更赞之为“吾家吟坛新闻纸”,“新闻纸示劝戒于新话,而新文诗放风致乎新韵,皆新世鼓吹之尤者”[18]。下面且捃拾数例,看看他们是怎样用“新韵”来作“新世鼓吹”的。
铃木蓼处〈题风船图〉:
西人技术亦奇哉,舟在青空尽溯洄。
见得谪仙诗句是,孤帆真个日边来。[19]
诗有想像,有情韵,用典也恰到好处,因而被视为明治汉诗的代表作,入选各种诗集。但与之相反,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扞格难通者,也在所难免。如芳川越山〈明治九年十二月设海底线于阿波州,竣工有作〉:
非因要害碍楼船,一锁投来万信传。
休道相思南北隔,偷从海底两情牵。[20]
诗前半颇为稚拙,几近不文,但后半称扬电线暗递相思,与黄遵宪〈今别离〉礼赞电报遥寄情愫,在借科学技术昌明写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这一点上,就不无相通之处。
森春涛不仅以《新文诗》为阵地,为这一汉诗新潮推波助澜,他自己也时时挥笔上阵,鼓噪呐喊。他于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将作新潟之游,友人杉山三郊作序送之,称新潟其地“西洋各国亦争辐凑,于是火轮之船,电机之线,山水人物,殆有与昔时异观者,而从未尝见有艳笔描其形胜,写其风俗者,岂不昌平一大遗憾乎哉?岁之辛巳夏六月,春涛森先生将启新潟之行,赋诗曰:此行要问今风俗,吾意将翻古竹枝。”[21]收于《春涛诗钞》的《新潟竹枝》组诗,虽然传统意象仍然在唱主角,但“铁轮”、“火井”、“邮签”、“巨舰”、“人力车”等新名词,也时时现于笔端[22]。用“古竹枝”写“今风俗”,正是当时汉诗坛流行的一种风尚。
最为集中的例证,是黄遵宪赴日前夕,明治十年(1877)八月上野博览会开幕,《新文诗别集》第9号为之特辟专号《上野博览会杂咏》,其诗题全部直接标举展示名目,依次为:制丝机器,谷种,矿种,漆器,陶器,酿造品,织造品,文房三具,写真翁媪匾额,写真女子匾额,洋法画匾,盆松。和洋杂陈,琳琅满目,新鲜事物的诱人魅力,扑面而来。对此当时诗坛泰斗小野湖山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在评松冈毅轩〈上野公园博览会开场……〉诗时说:
事新,则字面亦不得不新。能用新字面以作稳雅诗,非毅轩翁决不能也。[23]
这里的“能用新字面以作稳雅诗”,和陈三立所说的“以新事而合旧格”、梁启超所说的“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如出一辙。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文明大潮,东瀛西陆汉字文化的子孙们为拯救祖传家业开出的药方,竟然如此不谋而合,实在是意味深长。
到黄遵宪抵日后,这一热潮依然有增无减。《新文诗》第30集卷末载“皆笑社月课文题”,即明治十一年(1878)该诗社的每月共同课题,四月为“气球船喻”,八月为“电线说”,而不是惯例的赏樱、玩月,追新逐奇风气之盛,不言而喻。而这一年,正是黄遵宪开始与明治汉诗人广为交流的重要年份。
综上所述,在黄遵宪赴日前以及在日期间,日本汉诗坛以《新文诗》为中心,正劲吹着一股“文明开化”之风。以“采风问俗”的“古之小行人、外史氏”[24]自任的黄遵宪,面迎这一古典诗歌王国前所未闻的巨变,怎么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
进而论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黄遵宪与明治“文明开化新诗”之间,确实有着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以开风气之先的森春涛为例,黄遵宪就与之多有交往。明治十一年(1878)清使何如璋特访森春涛,森作诗志其事,黄遵宪次韵,并于题下注云:“髯翁素工香奁,戏仿其体。”[25]来日仅仅一年,就对森诗风嗜好了然于心,可见过往之密。黄遵宪致森春涛的个人信函,还分别刊载于《新文诗》第55、57、62集,其中并谈到对春涛之子森槐南所作戏文《补春天传奇》的指导,父子两代,交谊深厚。黄遵宪因为这种特殊关系,对《新文诗》杂志以及森春涛所编所写的其他诗作时有寓目,当为情理中事。不仅是森氏父子,黄遵宪与上文涉及的小野湖山、川田瓮江等人,也均为酬酢甚勤的友人。石川鸿斋《日本杂事诗跋》说他“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这些登门求教的人士手上,想必也经常捧着“文明开化”的诗篇。何况黄遵宪为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曾广泛浏览当时报刊杂志,登载的汉诗文固不必说,即使是日语的“新闻纸布令”,他也自称“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26]因此,在他触目可及的大量日本文献中,明治“文明开化新诗”这株刚刚破土而出、沾着新鲜露珠的诗苑奇葩,必然会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其实,黄遵宪在日期间,对这种新体诗可以说已经初尝鼎脔。《日本杂事诗》第53、175、178、181首分咏新闻纸、照相、博览会、人力车,就已显示出他驾驭此类题材的娴熟功力。《日本国志》里日人新创的西文译语,即所谓的“和制汉语”,更是纷至沓来。可是,《日本杂事诗》作为叙事性的大型组诗,最初的写作目的如黄遵宪所说,是“仆东渡以来,故乡知友邮筒云集,辄就仆询风俗,问山水,仆故作此以简应对之烦”[27],与专以某一新奇事物为对象、即传统意义上的“咏物”之作,毕竟还有区别。这里且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黄遵宪对引舶来文明入诗所持的积极态度。
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的石川鸿斋编《芝山一笑》,收有清朝驻日钦差副使张斯桂的《观轻气球诗》,对这“泰西气球新样巧”的新奇事物,作者发出由衷的感叹。石川自己也和了一首《戏次其韵》,其诗中有云:
闻说洋人始新制,图敌瞰营施奇计。
或历宇内捡广狭,又阅舆地极微细。
对此黄遵宪评曰:
奇思异想,真入非非。亦广大,亦精微,是不可思议功德也。[28]
按黄遵宪在来日前作于同治九年(1870)的《香港感怀》中,已提到了“气球”,若论《人境庐诗草》用新名词,这也许可算作最早的一例。而咏赞气球的张斯桂,也是一个自称“心地尚若少年,意欲纵观天下奇形怪状一切事情”[29]的好事之人。因此,在他们治下的清使馆中,便不时有此类“新诗”的具体实践。如使馆之首何如璋,在一次与黄遵宪以及日人的共同唱和中,就曾以当时最摩登的电话为题:
近西人有电器名德律风,足以传语,故以此为戏:
何须机电诩神通,寸管同掺用不穷。
卷则退藏弥六合,好扬圣教被殊风。[30]
黄遵宪自己也并非徒作旁观。《戊寅笔话》记大河内辉声在新买的一把“洋伞”上题诗,并请黄遵宪也题一首,黄乃作《戏作四言铭》:
亦方亦圆,随意萧然。
朝朝暮暮,可以游仙。
替笠行露,伴蓑钓烟。
举头见此,何知有天?[31]
按《日本国志•礼俗志》叙日本女子所持之伞,“伞仿西洋制,名蝙蝠伞,谓张之其翼如蝠也”,《日本杂事诗》第103首自注亦云日女子“出则携蝙蝠伞”,足见其对这一舶来生活用品的注意。这首诗虽然属于“戏作”﹐用语也纯然古风,但既然题在洋制“蝙蝠伞”上,也就可以视为黄遵宪“奇思异想”的一种尝试。
那么,为什么黄遵宪使日四年有余,上述新潮诗人可谓时相过从,新事新语也几乎每日耳濡目染,却始终没有写出《今别离》那样的杰作呢?对此我想试作以下三点解释。
首先,黄遵宪如其《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所说,对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因危惧传统汉学消亡,常作指责讥议,到知其乃大势所趋,理所必然,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同样,对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新诗”,作为一名年轻时就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革新派诗人,他自然会深感兴趣,备受启发,甚至跃跃欲试,但真正操刀染指,却尚需时日,有待观察。而在当时日本汉学界,保守势力仍居统治地位,黄遵宪就自称“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32],这些旧学宿儒出于对维新事业的抵触,视汉诗中阑入新名词为浅薄庸俗,诘难非议也时有可闻。明治十三年(1880)城井国纲编《明治名家诗选》,就秉承其师村上佛山遗愿,有意不选这类“新诗”。五年前对森春涛《东京才人绝句》的“耳目所触,无一非新题目”称扬备至的川田瓮江,这时也不得不韬光养晦,三缄其口,川田序引村上之语云:“近日作者投时好,如气球、电机、轮船、铁路,争入题咏,奇巧日加,忠厚日亡,今而不救,恐有流弊不可胜言者。”[33]黄遵宪也应邀为这部诗选作序,听到如此痛心疾首的呵责申斥,不会不有所避忌。何况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对日本汉诗人本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指导地位,“新诗脱口每争传”[34],这些被“争传”的“新诗”,实际上还负有示范本土标准、乃至整肃诗坛纲纪的重要使命,如果他也随波逐流,加入世俗称颂“奇巧”的行列,或许将有损于他国粹护法神的形象。而到了英国之后,他显然已经没有这种多余的顾虑了。
其次,黄遵宪对西洋文明事物本身,也还需要理解消化。日本因同属东方国度,在此所见所闻,毕竟只是中转贩卖的“二手货”,真实的欧风美雨,还有待今后的亲历。再说像地球东西时差那样的“国际知识”,不做亲身体验,是无从真切感知的。
再者,黄遵宪作诗的谨慎态度,也可能使他不愿率尔操觚。“公度诗自命另开一新面目,最不肯轻易落笔。”[35]黄遵宪在致宫岛诚一郎信中,也嘱其作诗务必推敲再三:“四库目论陆放翁,讥其作诗太多,故伤冗滥,通人当知其意,无俟仆喋喋也。”[36]《今别离》四首,也许正是因为经过长期孕育、终于瓜熟蒂落的缘故,才能想落天外,与古为新,意环笔绕,穷形尽相,较之明治诸公,无疑堪称后来居上。
毋庸讳言,黄遵宪的新体诗也并非登峰造极,无懈可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在赞扬黄遵宪的同时,曾批评“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37];而钱钟书《谈艺录》则认为黄遵宪也不免此病:“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38]令人抱憾的是,随着二十世纪以来旧体诗本身的全面衰退,怎样才能真正获取、自由表现“新理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大概今后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范畴的话题了。
以上所论,尚仅限于黄遵宪一人,其他如梁启超等人与明治汉诗的关联,还需继续深入探讨。因此,晚清“诗界革命”受明治“文明开化新诗”影响这一命题,目前似乎还难作定论。然而,即便笔者的臆说能够成立,我们也大可不必为家传灵丹竟曾“师夷之技”而感到沮丧。汉诗一道,尚且能面向海外,博采众长,这正说明了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开放性,显示了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汇纳百川的强大生命力。本文的写作目的,其实正在这里。
[1]《拾遗杂集》,《弘法大师全集》第三辑,密教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614页。
[2]《遍照发挥性灵集序》,《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六卷,筑摩书房,1984年版,729页。
[3]参见兴膳宏:《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五卷《文镜秘府论》注释23页,335页(筑摩书房,1984年版)。
[4]据张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台北)大立出版社影印小醉经阁丛刻本,1982年,12页。
[6]《关于“大学头”及其他》、《再谈高彝与〈七子诗选〉》(《北京大学学报》第41卷第6期、2004年,第43卷第1期、2006年)。
[7]《赖山阳全书·诗集》卷十九,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22年版,573-574页。
[8]《赖山阳全书·全传》,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22年版,614页。说明部分原文为日文。
[9]《赖山阳全书·诗集》所收《日本乐府》,46页。
[10]《中华国学丛书》所收,中华书局(台北),1970年版,91-92页。
[11]韩愈:《原道》,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五),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664页。
[1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四十五(上)《诗话》,《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2页。
[13]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今別离》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517页。
[14]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所收《己亥杂诗》第1首,中华书局,2005年版,153页。
[15]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125页。
[16]森春涛编:《东京才人绝句》,明治八年(1875)刊印,1页。
[17]川田瓮江:《读新文诗》,《新文诗》第1集,明治八年(1875)刊印,1页。
[18]阪谷朗庐:《赠春涛老人》,《新文诗》第1集,明治八年(1875)刊印,11页。
[19]《新文诗》第5集,明治九年(1876)刊印,9页。
[20]《新文诗》第14集,明治十年(1877)刊印,7页。
[21]杉山三郊:《送春涛先生游新潟序》,《新文诗别集》第14号,明治十四年(1881)刊印,4页。
[22]《春涛诗钞》卷十五《新潟竹枝》,富士川英郎等编:《诗集日本汉诗》第19卷,汲古书院,1989年版,126-128页。
[23]《新文詩》第21集,明治十年(1877)刊印,1页。
[24]黄遵宪:《日本国志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2页。
[25]《新文詩》第42集,明治十一年(1878)刊印,6页。
[26]《黄遵宪全集》(上)所收《戊寅笔话》第170话,680页。
[27]黄遵宪:《与森希黃》,《新文诗》第62集,明治十三年(1880)刊印,10页。按该文《全集》失收。
[28]王宝平编:《晚清東游日记汇编》第1种《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71页。
[29]小野湖山:《题张副使彤管生辉次韵诗后》,《新文诗》第56集,明治十二年(1879)刊印,2页。
[30]《黄遵宪全集》(上)所收《与宮岛诚一郎等笔谈》,722页。
[31]《黄遵宪全集》(上)所收《戊寅笔话》第159话,665页。
[32]《日本杂事诗自序》,《黄遵宪全集》(上)6页。
[33]城井国纲编:《明治名家诗选》卷首,明治十三年(1880)刊印。
[34]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別日本诸君子》,《黄遵宪全集》(上)105页。
[35]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一,《古今文艺丛书》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重印版,1212页。
[36]《黄遵宪全集》(上)308页。
[37]《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40页。
[38]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3冊,中华书局,1984年版,23-24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