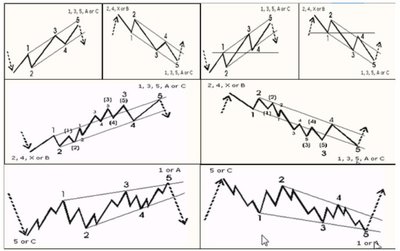文 存
今天是铁列克提战斗42周年,目前专程前去的柘城兵参战者、后来任该团副团领导、业已转业的董兰志战友,正在铁列克提战斗的主战场无名高地的“忠勇山纪念碑”前代表战友们给烈士致哀。烈士英名永存,让我们共同纪念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由于这场战斗失利,几十年来国家对此保持沉默,我们的烈士、勇士们的业迹和英名至今没有官方的公开报道,2009年4月当我们得知半年前建成揭碑的无名高地“忠勇山纪念碑”的碑文正视了历史,提到我们是100余人参战,并非是几十年来官方媒体披露的是一个排的人全部牺牲,极大地激发了已经默默沉寂了40年的战斗幸存者们。紧接着受他们委托,我在网络发出了《纪念铁列克提战斗四十周年聚会活动联系启示》。正当万事俱备、只待届时前往之时,被新疆的“7.5”事件泡汤了。然而激情不减,其中柘城战友在自己的家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铁列克提战斗40周年大会”!
今天是战斗42周年,让我们以柘城战友的纪念40周年大会的实录,作为对战斗42周年的纪念吧!
主持人:
战友们,同志们,铁列克提战斗40周年纪念会现在开始。
会议进行第一项:全体起立。向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尹清启、张开志、王承贞、刘义新、贺宗义、杨世怀、李瑞增、袁国振、王永仁等战友默哀三分钟……
主持人:礼毕,请坐。
会议进行第二项:有县人大黄副主任讲话。因正在会议中,来后进行。
会议进行第三项:有慈圣镇李书记讲话,大家欢迎。
慈圣镇李书记:
今天很有幸来参加这个会,由于领导正在县里开会,首先有我代表慈圣镇党委政府与咱们共同纪念这个日子。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1969年8月13日上午9点10分在新疆塔城铁列克提无名高地发生了一场苏军袭击我们巡逻队的战斗,当场牺牲28人,其中我们镇参加了14人,牺牲两人。有慈圣镇慈圣东村尹清启,战士;慈圣镇后台村张克志,战士。虽然他们牺牲了40年,但他们为国家的安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英勇事迹我们怀念在心。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隆重的仪式上缅怀他们,我们为他们这样的为国家献身感到光荣和骄傲。谢谢大家。
会议进行第四项:介绍铁列克提事件有关记载。
丁殿勋:这份塔城军分区他们军史上的记载,是比较正确的,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
铁列克提事件:
铁列克提边防连位于裕民县西南边境,巴尔鲁克山西部,和扎拉纳什科尔湖、阿拉套山相望。阿拉套山中段为中苏界山,山脊线以南属中国博乐地区,以北属苏方管辖。铁列克提地区东面靠山,西面靠湖,是前苏联纵深通往阿拉山口的走廊,其铁路有的地段在中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苏联对铁列克提地区极为重视,在附近地区驻有装甲、炮兵部队。长期以来在这一地区苏方非法铺设松土线,对中方非法蚕蚀,多次出动大批军人、装甲车辆强行阻拦中方巡逻,私设国界标志,并伺机蚕食中国领土。
1969年3月,苏军在中国珍宝岛失利后,伺机在西北新疆边界挑衅报复,企图挽回损失。6月10日,在塔斯提方向一手制造了塔斯提事件,被中方边防军人击伤6人(文存注:当时50米距离的数十名苏军骑兵全部打倒,具体伤亡人数不祥;我军排长李永强和带领的9名战士毫发未损。此事发生后,受到追查,周总理下令“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之后又在中国丘尔丘特边防连当面集结兵力伺机报复,新疆、北疆两级军区和分区对此极为重视,曾利用第八师23团驻托里一线,其中一个加强营约500余人布置在丘尔丘特附近地区(文存注:还有从沈阳军区紧急调来的炮兵部队。双方剑拔弩张、重兵压境)。苏军发现中国纵深兵力,前苏福基克臣市同丘尔丘特当面回撤(文存注:塔斯提事件是造成双方战备高度紧张的源头)。后苏军又在铁列克提地区私设国界标志,并构筑工事,侵入中国实际控制线纵深一公里。
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外交部、总参谋部批准,新疆军区于1969年7月6日对伊犁军区和分区下达了“按中国习惯线进行正常巡逻”的指示,7月8日中国新疆军区上报了巡逻方案,7月16日分区作训科参谋尹效智带两个步兵班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协助组织实施巡逻。经过一个月准备,原决定8月11日开始巡逻,后因8月13日在巴克图与苏方会谈,为配合会谈,上级决定于8月13日巡逻。(文存注:还有6月20日肖发刚带领分区骑兵营一连的部分骨干驻铁列克提;6月25日杨振林带领分区步兵营一连的一个排驻铁列克提;7月20日分区骑兵营三连的一个排调驻铁列克提。8月12日午后,范进忠带领分区步兵营一连的排长等骨干来铁列克提支援。原站老人员约20人。)
当时的巡逻战斗编组是:
担负这次巡逻任务的官兵有109人,其中巡逻组编成11人。其中干部3人,记者1人,报务员1人,战士6人,由铁列克提边防站副站长裴映章负责指挥,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李连祥随队拍摄,携带手中武器和一部电台,隐蔽配置在40号界桩附近地区。其任务是沿40号至39号界桩约10公里中国习惯巡逻路线,由北向南巡逻。(文存注:109人算错,是:11+ 20 + 11 + 17+ 36 + 15 =110人;隐蔽点不是40号界点,是在40号界点北9公里的695高地;由北向南的沿40号至39号被颠倒;40号至39号界点不是约10公里,是约两公里。)
掩护组47人,下分三路掩护小组。
左翼掩护小组编成20人,其中干部两人,记者3人,战士15人,由分区骑兵营一连副连长肖发刚指挥,隐蔽配置在708.6高地西北800至1000米之间地区。
中翼掩护小组编成11人,其中干部1人,记者两人,战士8人,由分区步兵营一连副连长杨政林指挥,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温炳林和新华社摄影记者王一兵随处采访,计划隐蔽配置在676高地南侧无名高地。(文存注:中翼组分两个组合计13人,即676高地和南侧的无名高地。676高地4人组杨振林负责;无名高地9人组李建班长负责)
右翼掩护小组编成17人,其中干部两人,战士15人,由分区步兵营一连连长范进忠指挥,隐蔽配置在695高地东南600米附近地区。
三路掩护小组均实行分段掩护任务,预备队编成36人,其中干部3人,战士33人。一个班12人,随指挥组配置在708.6高地东侧附近地区。主力位于铁列克提边防站,主要担负增援任务。(文存注:实际情况变化;主力位于铁列克提边防站不存在)
指挥组领导有营长康有福,政委蒲西武,分区司令部作训科参谋尹效智等15人。其中干部8人,记者4人,战士3人编成,配置在708.6高地东侧,主要担负献计、指挥、组织任务。(文存注:实际情况变化)
会议进行第四项:由袁国孝介绍铁列克提战斗经历。
去年10月份我和杨俊奇战友回到了当年战场,看到了无名高地的纪念碑,很激动。以前的边界线是一公里一个洒了石灰水的石头堆,现在是铁丝网。回故当年,一阵心酸,山上我们22个人,牺牲了21,为保卫祖国领土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我们是8.13凌晨从铁列克提出发,之前领导们作了很多的军事动员,讲边防政策72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理、有节、有利……”;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按照1883年中俄伊犁、爱辉、北京三个条约,苏俄剥夺走了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两个法国、六个江苏省的面积,当时战士们听到这些,怒火万丈,在8.13凌晨,带着这种愤怒走上了战场,走上了无名高地。
无名高地那时是争议地区,按照条约线边界线在无名高地西,在69年6月份,苏联偷偷摸摸的把边界线挪到了无名高地。我们是第三掩护组,由李建班长为第三掩护组组长。
8.13凌晨从边防站出发,69年8月13号是七月初一、星期三。七月初一的凌晨以后是大月黑头,虽然漆黑瞅不见什么,但是战士们心里的恼怒已经压倒了一切,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了无名高地。
那时我是枪榴弹射手,副射手是尹清启,还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温炳林,我们三人是一个战斗小组。我们小组是隐蔽在无名高地东南角、山脚往上大约50米位置。隐蔽了不到半小时时间,上面又传过来话,我们转移到无名高地东北角,这时天还没亮。
在太阳刚要出来时,苏联的两架直升飞机从西南的塔里库里湖(应该是扎拉纳什科尔湖)方向飞来,通过无名高地上空,飞向卡头山,纵深有30公里。到卡头山后,又返回到无名高地。
也就是飞机开始飞过来的同时,有三辆大卡车从湖的西北角出发,我们在无名高地往西看,看的很清晰,他们下来一个我们数一个,一共126人。
那时我和尹清启只是个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说是上战场,一腔怒火,可对于事情不懂;温炳林是个记者,干哪行讲哪行,他光想着拍有价值的镜头。他说“小袁和小尹,你们站起来,掂着枪,怒视敌人的飞机,我给你们照相,拍苏修侵略我们的罪证。”
我们俩就站起来,挎着枪,昂着头,怒视敌机,还让我们朝敌机挥拳头。这时温炳林说了四句话:“横眉冷对新沙皇,赤胆忠心守边防,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保边疆。”
就这样,他和王一兵一个摄影,一个拍照,直等到敌机走了才罢,其实我心里想,这不是违反战场记律吗?可是这是拍摄电影的需要。
照完相时间不长,巡逻队从钢管山由裴映章站长带队出发,走到离无名高地大约二三百米地方,敌人开火。敌人打的第一枪,就打着裴映章,在脖子上贯穿。当时我也不明白,200多米的贯穿伤他竟能爬过来,他带领的是11人,我们在无名高地的是11人。他爬上来离我的距离不过10米,不能说话、不能动弹,颌下前脖的贯穿伤我看得很清楚,可他怎么能够爬到山上?当时也没时间分析这事。
与此同时,骑兵四排排长李国贞爬到离我3米处的射击位置,他是巡逻队的,我们是在无名高地的最北端,他是从北来,他坐在那里休息。
这时,敌人的装甲车从无名高地西南角过来,绕到北头掉头,大约50米下来人,离我的射击位置大概400米左右。李国贞的枪法很准,只一枪就打倒一个。当时这个人从装甲车下来,还没有站稳,就被打倒了。
从李国贞打倒这个人后,战斗就激烈了,像是五盘鞭炮同时点着爆炸,分不清点了,子弹急风暴雨式地射向无名高地。
我是枪榴弹射手,我在前面,尹清启在后面,相距1米左右,我打完了,他能及时地把榴弹递给我。当时我离装甲车有400米,枪榴弹的射程150米,有效射程是100米,根本够不着。69到49年,我们才建国20年,运动不断,武器发展比较落后。
枪榴弹一共8发炮弹,我带4发,尹清启4发,我只是打了3发。因为阵地上只有我带的武器才能威胁到他们的装甲车,是个打击对象。打3发后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我嘴皮上面和眼下面的伤疤,里面还有弹皮,就是那时炮弹爆炸以及爆飞的石块给打着了,就是觉得头顶“轰”的一下,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已经在他们的火车站,这里离他们的边防站很近。当时我看到有裴映章站长、温炳林、景长雄和我并排躺着,裴站长的伤最重,是脖子上的贯穿伤,他静静地躺着,从始至终都没吭过气。
靠着裴站长的是温炳林,他很勇敢,旁边挨着景长雄,景长雄旁边是我。当时我们非常渴,景长雄伤很重,老是在呻吟,喊“水、水”,要喝水。温炳林那时也不知道景长雄名字,就说,“小战士,坚强些,宁可死,不能向敌人求什么。”就是不能要水喝,景长雄就不再要水喝了。
我们四人一起,在车站停了一个小时后,先带走的裴映章,景长雄是第二个被带走的。随后温炳林又和我说:“‘小伙子,坚持住,我们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苏联人要给他看伤,他就骂“不要动老子,滚开!”,带头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到苏修!打到新沙皇!”他是第三个被带走的。我在最后,在拂晓前被他们的一辆小吉普拉到一个在戈壁滩上的简易飞机场。
那时我受伤了,被敌人弄走了,反正什么也不想了,只是想死、死、死。时间不是太长,又在一个机场降落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医院。后来知道,这里是阿拉木图市。
他们用剪刀剪开我的衣服,给我做的手术,做罢手术后,我那个病房里的记者、军官、卫兵等等,从房间到走廊,都挤满了人。我的军装因为动手术,被剪子绞坏了,整天就只是穿个裤头。
他们问我叫什么?为什么要当兵?那时我们上战场前有教育,领导有安排,就是假如被强行绑架了,不能暴露自己的名字,不能泄露机密。我是个新兵,不知道啥叫机密,咱们的边防站还是知道的,我什么也没有说。
那时我们人人都有语录本,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李连祥,在我们边防站住了一个多月,对士兵很好,给我们理发,钉扣子,喜欢我,和我关系最好,和我挨着铺睡,还在我的语录本上写了“向袁国孝同志学习”。
在14日凌晨,我住的病房两张床,中间有个小桌,不到20平米,后面有个窗户,猛然有人在窗后喊“袁国孝!”我认为我一生当中脑子反应最快的就是那时,有个翻天覆地的转折。在那样一种地方,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是何等的激动,我一想,不对,敌人不知道我名,肯定是从语录本上看到的,试探我是不是那个人。我就用被子蒙住头,始终动也没动。
那几天,他们的记者、军官、翻译天天要给我照相,我向国家保证,向边防领导保证,我没有一张照片丢在苏联,我的办法是天天蒙着头,睡觉也蒙着头,要睡着了就用头把被子压着,不给他们照相的机会,防止他们给我照这么个只穿着一件裤头的丑像发出去。虽然我只是一个才十七八岁的青年,是个新兵,可我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几亿人民的形象。
有一个军官,问我叫啥,非要和我照相,我说可以,就举起手,拉出打他的架势,这样的照片就不能发表的,我说我叫理通道直,后来他们就叫我李道直。他们始终不知道我叫什么。
也是一人一个脾气,有个苏联士兵,他每天拿个方凳在门口坐,用两手在头两边支着,说“萨,萨”。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一次还拿几块糖要给我吃,我反正是不吃。那天他又比划“萨,萨”,接着有个苏联军官提着照相机进来了,我知道了,他是要我蒙头的意思。
我在苏联整整41天,8月13号到苏联,9月22号回来。也受过拷打。我是农村人,犟脾气,他问啥,我不说啥,怎么也不说,他们急了就打我,打呗,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这是实话,不管是谁,那时只能随便他们了。
后来又换了一个翻译,不带苏联口音,东北过去的,说是山东人,姓张,和我口音差不多,有两个星期左右。
之后又换个翻译,是苏联人,翻译的似懂非懂,他问我“想爸爸吗?”“想”“你那么小,家里你妈妈一定很难过,想妈妈吗?”我说“我想妈妈,想也没用。”问我“想不想回去?”我说“想,可是你们得许我几个条件,不答复不回去,给国家献丑了,回去也没意思。”
他说“你有什么条件说吧?”我说“一、还我毛主席语录;二,我要见我的战友,我们同时在火车站的那三名战友,我们要见一面;三、还我军装;四、还我武器。”我这四个条件一个没答复,每天都是这样他问我,我问他,除了这四个条件,多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一次还来了各国的许多记者,一人问我“你到底是红卫兵,还是边防兵?”我说“我当然是红卫兵,也是边防兵。红卫兵是年轻人,边防兵还是年轻人。”回来以后听说,当时在场的一名日本记者在报纸发表了我是红卫兵的报道。
万万没想到,到了9月21日下午,苏联翻译告诉我,“你明天可以回去了。”还告诉我那三位被俘战友因为伤势严重已经不在世了。我说“不回去,起码你得还我军装。”回国以后我才知道是9月21号,在那我是黑了白,白了黑的,也不知道几月几号。
到22号那天,他拿的衣服,有西服、领带、鸭舌帽、皮鞋,强行叫我穿上,强行送上车,到飞机场,又坐车,每次前面都用毛毯挂着,叫我瞅不着。等车到达地点巴克图停下后,我一下子精神焕发,我看到了我的老领导,看到了我的同志们,看到了我们的国旗,看到了我们的国土,我就飞快地跑过去。也就是刚要到边界时,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对,都给脱了下来,浑身精光,只留下一个短裤头。
我过了边界线,随即穿上了军分区领导给我准备的新军装还有衬衣等等,上了救护车。从巴克图到塔城还有8公里,两边都是工农兵学商的欢迎队伍。我精神好了,思想也好了,要求驾驶员把车开的慢些,我说40天来,我又见到了我的同胞,不要开的快。
把我送到军分区卫生所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就过来看了我,在一起座谈,记者很多,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解放军报的,解放军画报的,新疆军区战胜报的等等。我回报了在苏联的这41天的经过。
9月27号,塔城军分区举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两名战友搀扶着我走上主席台,全场鼓掌;9月30到乌鲁木齐,10.1参加国庆观礼,10月20在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军区第三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会前,战友们在交流
会后,参会的战友们和县、镇领导合影
2008年10月参战者袁国孝和杨俊奇在当年战场
2011年清明节参战者袁国孝和常书林在当年战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