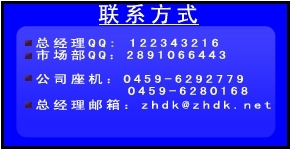近日四處講論,殊覺游轡無歸,意亦倦之。講記蕪雜,難以整理,尤為煩惱。今且附錄一篇以就教於師友。其餘游上饒、過鉛山、在寧波開國學院、赴濟南辦國際古琴研討會等,另詳微博微信等,不復贅及。
禅宗史新研
龚鹏程
時間:2015年4月10日
地點:江西宜春寶峰寺寶峰講壇
各位大德、各位菩萨:
我想稍微介绍一下目前禅宗史研究的进展。但这並不是整个学界的情況,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探索。
由於禅宗的祖庭和早期传播都在江西、湖南,因此我们很少关注西北地区。所以我今天想从西北佛教谈起。这是个比较特殊的角度,各位不见得熟悉。
一、
新疆、中亚、西亚一带,从9世纪到15世纪,广泛流通回鹘文。回鹘,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维吾尔民族。他们当时的回鹘帝国,跟唐宋朝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安史之乱時,中原混乱,在维系唐朝政权时,回鹘出了很大的氣力。而且,回鹘当时的国教是佛教,所以,它也是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后来,他们也编了回鹘文大藏经,跟我们的汉传大藏经相当,规模非常大。所以,當時西北地区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整个新疆、特别是维吾尔人,都信奉伊斯兰教。
至今還留存有大量的回鹘文献,多達几万件,分散在世界各地,德国最多,約有八千多;其他像日本、芬兰、英国等地也保存了不少。
这些文献內容非常有意思,例如有《易经》的卦文。
在北疆伊犁靠近哈萨克、乌兹别克边境的地方,有个小县城,叫特克斯。各位听这个名称就知道,它是哈萨克族人的聚集区。但是,整个城是按照八卦的卦象建的,所以又叫八卦城。在中国南方有很多八卦村,但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城。所以这个县城很稀奇。而且,这地方的人都非常相信《易经》。我曾在该地发现过蒙古文的《易经》以及道教流传的一些经书,而回鹘文献中恰好也有易卦跟符箓。
例如在交河古城(吐鲁番地区,唐人诗“黄昏饮马傍交河”的地方)发现的残片上,可以看到的大概有十三卦。在其他地方还发现了一些符箓,如说女人发烧怎么样治病,这一类保佑人体的符箓,或是免于迷路的符箓——这是第一批可以说明回鹘跟中国关联非常密切的材料。
第二批材料,是跟中国星斗信仰、星占有关系的。这批文献也很多,如在吐鲁番出土的星占,跟《开元占经》、《协纪辨方书》等汉人占星书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這大概就是汉地八卦和星斗信仰传到那边去、对他们产生影响后出现的产物。
另還有一些五行、八字和天文历法。
回鹘文献中除了道教外,还有大量佛教文献,最特别的就是《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这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佛经非常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从印度传來的,而是汉地僧人所造。後來汉地已不太流行,很少人听过,也没什么人传习,一般的大藏经也多没有收它。但它在西域特别多,在敦煌也有,抄本、刻本和残卷加起来竟有186种,在当地非常流行。
由於它的版本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的转变:早期拜火教的思想比较浓,表示它受到印度跟波斯的影响;可是越到后来,中国的思想就越来越深,最後源于波斯的東西几乎完全被排除了。其中有很多讲五行、八字的内容,还有很多天文的术语,而术语基本上都是从汉语借过去的。如太岁,还有一些其他的观念。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影响是二十八宿。在我们中国人的天文观裡,二十八星宿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回鹘文献中也有反映。跟二十八星宿相关的名词,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各位要知道,在清末民初,國際学界有个共同的观点,认为二十八星宿、十二时辰和十二生肖,都不是中国本土创造的,而是由西方传来。从西方哪里传来呢?有人认为是印度,有人认为是巴比伦,有人认为是埃及。當時大家认同“中国人种西来说”,人种是从西方来的,文化当然也从西方传来。像二十八星宿,就是個例证,因为它的名称都很奇怪,当时人认为這是译文,是对照着西方的语言翻译过来的。到现在的研究,才確定它的起源还是在中国本土,而且年代非常早。所以,二十八星宿在新疆出現,乃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另外,中国的星斗信仰,最重要的是北极和北斗。北斗是转的,而北极星不动。北极星和北斗互相配合,成了我们中国认识天体最重要的一个标准,这在回鹘文献里也是有所反映的。
再就是十二月、十二支、十二生肖,这些也很常见。例如回鹘文献《玄奘传》,在用回文纪年纪月时,就采用了跟中国一样的方式。干支纪年法是我们汉族所创,十天干跟十二地支相互配合形成了六十甲子。公元前后,汉人才把每个地支跟动物相配。也就是说,十天干、十二地支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把它们配上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等等,要到汉朝。回鹘人接受了汉人的干支纪年法,他们大概在九世纪中叶迁到高昌。
另外还有七曜历。就是一周七天分别属日、属月、属火、属水、属木、金、土。这种纪日方式,早期我们也认为可能起源于埃及,是闪族人创造的,后来慢慢向东传播进入印度,再傳入中国。但是,最近的研究认为它应该还是发源于中国本土。
回鹘使用的这種历法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不过它在各地的面貌不完全一样,如在敦煌的和在吐鲁番的文献就不太一样。有的是先五行,后面加十二属相;也有的用十天干加五行加十二属相,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它们和中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这一点在五行的排列方式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的五行顺序,习惯讲金木水火土,但是汉朝的排列顺序是木火土金水。高昌的五行排列方式,和汉代就很类似。这历法,後来还影响到了西藏的十轮历。可能是十一世纪以后,由高昌影响過去的。
回鹘的医学和中国的医学也非常类似,不仅基本的药方和中医类似,它们的很多医学用语也来自汉语。在晚唐、五代到宋元,回鹘医术和中医的交流非常多。现在中药裡的木香、安息香、鸡舌香、羚羊角等等,都是从西域传进来的。
以上是个大背景的介绍。这些现象,呈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从吐鲁番、高昌一直到伊犁,这整条线上,汉字和汉文化的影响是很盛的。高昌的语言,有很多语汇是从汉字或者汉语读音翻译过去的,有些甚至就直接借用漢字。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回鹘文献里面有大量的汉字和回鹘文对照的读本,这表示这个地区的人在学习汉字,因此出现了很多教材。
还有史料记载,中国把大量的佛经,如大藏经、般若经等,当成了外交礼品。回鹘人来进贡,就把这些佛经回赠给他们。所以《北史》记载说河洲、沙洲的寺庙,都像中原寺庙一样,诵著汉字佛经。
除了僧人,一般民众使用汉文也非常普遍,因为大量的地契、房契、档案、家庭文书,都有汉字。有些是回鹘文穿插、夹杂着一部分汉字,或者是用回鹘文书写一些汉字的专有名词;还有很多完全采用汉文书写的文献。
这在回鹘文的佛典裡就更明显了。我们刚刚提到,中国人一般的思想,什么五行、八字、天文、星占等这些,在回鹘的影响是很普遍的,至于佛教,就更不用说啦。回鹘文的佛典,基本上都是根据汉文佛典翻译过去的,所以佛典中经常夹杂着汉文(这有点像现在很多学者写文章,要使用一些英文,在特殊术语上起一种强调的作用,或者表示这个术语在中国还没有相对应的语词)。这是当时很重要的现象。
他们的佛典基本上是大乘系统,小乘佛典很少,可见的仅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其他密教的经典也不多,主要只有《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有一些中原高僧的传记也被翻译成了回鹘文,比如我刚刚跟各位介绍过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远传》。另外,有大量的佛经是我们汉地的僧人自己造的,这些经的数量很多。在道安法师跟僧佑在南北朝期间所编的佛教文献目录中,就专门有伪经的介紹。
有一些我们平常觉得非常重要的经典,像《法华经》、《华严经》、《金光明经》、《金刚经》或者《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净土三经》等等,这些在印度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经典,在回鹘文献中就没有,或者非常少,这跟它们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像《金光明经》在回鹘文献中只有7件,《金刚经》只有9件,《法华经》有15件,《大乘大般涅盘经》只有3件,《地藏经》只有1件。而且最特别的是《首楞严经》和《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件都没有。有人可能会问,7件、9件、15件,看起来数量也挺多的嘛。但是各位想想,刚刚跟各位介绍過的《八阳神咒经》,现在能看到的有将近200种呢,相比起来,這几种经就非常少了。
另一些不被历代大藏经所收的中土伪经,在回鹘文献中却极多,比如《父母恩重经》。《父母恩重经》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这部经是漢僧造的,强调孝道,還有一套相关的法会、活动、观念。光敦煌所出的《父母恩重经》就有五六十件,在回鹘文献中,这部经也很多。此经从来没有被收入过《大藏经》,但在民间很受欢迎,后来也就被翻译成回鹘文,在西域广为流布。
还有一部经,叫作《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这经我们平常也不太讲,但在回鹘地區流传也很广,在敦煌发现的就有40件,吐鲁番也出土了十几件,图文并茂,非常考究。
还有一部汉文经,叫作《佛顶心大陀罗尼》,这也是伪经,回鹘文写本也多达27件。
《金刚经》影响着汉地佛教,在中国有很多译本,是我们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但是,回鹘文献中的《金刚经》卻不是从印度来,它是依玄奘译本回頭翻成回鹘文的。它的依据应该是敦煌的一个汉文本子。應当是梁朝底本的玄奘本,每品正文后面都附有偈语,最后还有议论,议论部分是回鹘文译者自己发挥的。
还有一部《颂金刚经灵验功记》,现在都是附在《金刚经》里让我们一起读的,它也被译成了回鹘文。
更妙的就是回鹘文的《阿含经》,也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夹杂着很多汉字或汉語词组。
各位,佛教是从印度经慢慢传进中国的,主要的管道,一条是海路,一条是陆路。陆路是从中亚到新疆,再进入汉地。回鹘以佛教为国教,就是受这样的影响,所以它扮演的应该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由他们把这些佛经传进中原,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证据,却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因为它所呈现出来的佛教传播路径,乃是把汉传的佛典再翻译回去,而不是把印度的佛典翻译过来。所以,佛教呈现出一种由东边向西传的趋势。
汉地佛教是整个汉文化的一部分,它本来是从西方传入的,可是实际上,佛教传进来以后,很快,它就开始从东往西回传,而且整体趋势上是汉文化在向西传播。我们刚刚介绍的易学、象数、道法、天文等等,之所以能普遍地在回鹘文献中看到,也需要放在这个大趋势、大背景底下来看。
為什么要讲这个呢?过去我们谈中西文化交流时,谈得比较多的是佛教如何从印度、西亚、中亚传进中国。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发展起来非常兴盛,加上当时汉文化传播力量十分强势,所以,本来是这些地区向我们输入佛教的,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佛教向他们输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做佛教研究的人好好思考。
因為我们自己虽然觉得佛教发展得非常好,但是,目前国际上研究佛教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国际上还是以梵文、巴利文为主,覺得其他地方的文献都是通过贵霜王朝等慢慢传进中国。我们虽然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但終究是翻译。就好像我们学术界,如果有人完全不会英文,只能读翻译本,那么他来讨论西方的学术史,很多人就会质疑,说你根本不懂英文,怎么能谈西方的哲学、历史呢?同樣,我们只读汉文文献,就常常被批評,说你不能读梵文、巴利文,不懂西域文书,其實就没办法真正做研究。西方人做佛教研究也特别注重语言部分,所以对于我们的汉传佛教便不免看轻了。
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现象,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汉文化才是强势文化。这就好像现在我们都要去学英文一样,这个地区的人们都要学汉文。现在很多知识阶层的人都能读英文,一如当时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只要识字,就都能读汉文,同时也会接受很多中国的观念。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接受西方的观念一样。这时,汉文佛典的地位,就反而取代了印度来的。使用的佛经,多是直接从汉文翻译成回鹘文。
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献只是一小部份,當年整个回鹘文《大藏经》的规模卻是很大的。而它又是从汉传《大藏经》传播过去。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并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为何敦煌会有那么多的《六祖坛经》。
平常我们讲禅宗史,大家都知道六祖是在广东弘法的,圆寂於韶关;故後来唐宋間禅宗的主要传播地只在江西,湖南一帶。但是,我们现在卻从敦煌石窟裡发现了很多《六祖坛经》。最早是日本的探险队,领队大谷光瑞,在敦煌得到了一个本子。后来,这本子被放到了旅顺博物馆。现在已經下落不明,只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它首尾两页照片。
大家很遗憾,很想知道关于《六祖坛经》的更多资料,後来就发现大英博物馆有斯坦因带过去的另外一个《六祖坛经》,而且首尾完整。这本子後来收进了《大正藏》,它的缩微胶卷也公布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是对敦煌本《六祖坛经》进行研究的主要依据。
但後来在北京博物馆也發現一卷《六祖坛经》,是卷轴装的。但不全,只有后半部。这是第三个本子。
第四个,是敦煌县博物馆收藏的,首尾完整。是从敦煌的千佛寺山上得来的。这一卷特别重要,因为它抄了很多禅宗文献,《六祖坛经》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还有很多東西,有一篇很重要,是独孤沛的《南宗定是非论》。当时南宗北传,北方还是神秀北宗禅的势力范围,南宗传过去以后,在北方引起了重大的辩论。推动这次辩论的主要人物是神会和尚,他写有《坛语》,还有净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注解,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本子的抄写质量、校勘质量都很好,研究价值最大。
第五个是后来在北京图书馆又发现的另一件,只有一页纸,是个残卷,没头没尾。所以大家猜测是原来抄了一段,后来废弃了,或者是抄的过程中遗落了一页。这是个残卷,但也有校勘的价值。
这五种敦煌本,实际上属于同一个脉络,并没有不同的来源。敦煌《六祖坛经》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不断推陈出新,有很多新的成果。現在我们認為这五个本子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有详有略,来源則是一样的。
此外,还有西夏《六祖坛经》的残片。现在这个残片分藏在很多地方,总共有12页。这12页被很多人收藏,因为敦煌的材料,每一片都很珍贵,很多图书馆就只收藏了一页、两页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西夏文《坛经》是根据汉文《六祖坛经》翻译的,它的底本应该就是敦煌本,这个底本的流行年代相对更早。现在我们发现的敦煌本,基本上都是唐末北宋时期的,这个西夏本非常接近当时的敦煌本,所以也蛮重要。
西夏本和敦煌本重要的意义在哪?北宋时期,敦煌孤悬西北,在各种势力交错的情况下存在著。那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曾经是唐的辖区,但又曾经被西藏统治过,被西藏吃掉了,后来又收复了。最后,瓜沙地区的老百姓自己形成了一种地方保卫力量,一方面表明我是宋朝的領地,可是西夏强大了之后,又要向西夏称臣朝贡,实行等距外交。當時北方,如辽王朝就盛行华严,禁止禅宗,禁止《六祖坛经》,可是敦煌却仍流行禅宗和《六祖坛经》,采用北宋纪年。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敦煌的佛教跟辽的佛教不是一回事,不一样,它还是受汉地佛教的影响比较大。
这是很有趣的例子,为什么呢?说明了南宗禅在敦煌地区十分流行,南宗禅向北传播到了这么偏远的地方,从东南传播到了西北。所以,我们不能以為禅宗在当时仅仅局限在东南一隅,它的传播范围非常广,而且神会和尚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对于早期禅宗史,教界和学界向来意见不一。如學界胡适先生的禅宗研究,就點出了早期禅宗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不可忽視。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敦煌《六祖坛经》比今本《六祖坛经》少了12000多字。而现在的《六祖坛经》总共才20000多字呢,可見它們有很大的差距。胡适的研究,特點就是推崇神会,他认为神会和尚是禅宗能够立足的关键性人物。当时神会在北方大开辩论,打败了北宗禅,才确立了南宗禅的地位。甚至于,胡适推论,所谓《六祖坛经》恐怕就是神会和尚的语录,不是六祖的。这里面有很多争议。
但是,教界很少人谈神会。在我们教界,六祖以后,整个禅宗的宗派史中是没有神会的,神会和尚的寺院、法脉传承,後来都很少有人讨论。但很显然,神会和尚有《南宗定是非论》,可见他在当时是起过作用的,我们也不能忽略他。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从西北的文献上来看,为什么在西北敦煌这样的地方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六祖坛经》。是有个大的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就是汉地佛教的反影响。这种反影响中,最特别的当然是禅宗。禅宗是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然后从南方传到北方。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目前还比较少有人关注,所以我在这里特别介绍。
三、
以下要谈的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且是个国际性的话题。
禅宗在近代引起了一个重大争议,争议的核心是佛性思想。禪宗说人都有佛性、众生平等。所以人只要明心见性,便可以立地成佛,这是《六祖坛经》的核心思想之一。
所谓佛性,我们也把它稱為如来藏性、如来性或者觉性,指佛陀的本性,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一般理解。有些时候,我们又把它称为心、本性、法性、真如等等。我们最早讲人皆有佛性、人皆可成佛,是从竺道生开始。当时他讲“一阐提人皆能成佛”的佛性理论,大家都不相信,因为当时的理论认为人不都有佛性,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一阐提就没有。没佛性的人是不能成佛的,就好像我们种一颗丝瓜,決不会长出葡萄来,人种不一,佛性自然不同。但是从竺道生以后,汉传佛教都慢慢地接受了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论,到了禅宗,尤其讲得透彻。
这个思想,在六祖见五祖的时候便有明确表示:“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众生皆有佛性,人是平等的。
第二,佛性是人本来的自性,佛性本来清静,我们之所以不清静是被客尘所染。只要能够彰显本心,染就去除了。所以说本性清静,只要用此心,直了成佛。
第三,我们自性本来自足,含藏一切,万法都是从心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自性含万法,万法就在人性之中。“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所以自性是万法、一切的本源。
这些是中国禅宗的基本想法,不必多介绍,應該都是常识了。
但是这種想法在近代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佛教,违背了佛教的根本道理。
最近的质疑是1986年日本兴起的批判佛教的思潮,代表著作包括:(1)《本觉思想批判》(1989年),(2)《批判佛教》(1990年),(3)《道元之佛教:十二卷本正法眼藏之道元》(1992年)。还有松元史朗的代表作,包括:(1)《缘起与空:如来藏思想批判》(1989年),(2)《禅思想之批判的研究》(1994年)等。这些批判,認為自性、心性、本觉的说法是错的。
这很快在国际佛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北美佛学界在1993年的美国宗教年会裡,就有一组特别针对批判佛教的讨论,收集了23篇相关文章,后来出版為《修剪菩提树》。菩提树在禪宗有很重要的寓意,故这書名就表示是一次批判禪宗的风暴。
其它相关的研究還很多。由于在国内,禅宗的力量很大,所以对于这些批判不是很在意,反应也比较少。但是在台湾,有傅伟勋〈道元与批判佛教〉(《道元》,东大图书,1996);林镇国〈佛教哲学可以是一种批判哲学吗?〉(收于释恒清编《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东大图书)等。
其实这是个有意义的话题,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研究佛教到底是什么、禅宗是什么、真常心系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大的争论,引发了一个新风暴。
批判佛教的主要观点认为:真常心系的如来藏想是伪佛教,不能称为真正的佛教,因为它违背了佛教的根本意义——“缘起”和“无我”。而它之所以有违这两个佛教的基本教义,乃是因为它带有强烈的神我思想。松元史朗将它称之为dhaatu-vaada(基体论),即是指单一实在的基体(dhaatu)生起多元的诸法(dharma)。所以他们强烈地批判本觉思想,甚至指出禅宗、《维摩诘经》的“不二法门”等,都不是真佛教。
因为本觉思想主张一切“法”根于一个“体”,或者一个“真如”,从一个“本觉”生出来。所以他们觉得這是一切要回到“本心”这一最主要的权威,不承认一切文字、一切外在的東西,不承认概念,也不承认知性、推理、逻辑的有效性,收摄到单一的“本觉”上。他們认为这和印度的“梵我论”相同,在中国則是跟道家“自然”相结合的,偏离了佛教原来的思想,违背了缘起观。因为,假如讲缘起,就是无我,无我才能真正达到“利他”。若講本觉,讲「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有情非情皆具成佛道」等等,不外乎是一种欺骗。真佛教不是这样的,真佛教比较接近西方哲学,是一种知性的推理,而我们中国却强调开悟与体验。
以上是个简单的介绍,各位可以根据我讲的线索把他们的著作都找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觉得其批判可能不准确,因为禅和神我论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如来藏思想。我们能不能把如来藏思想理解成基体主义?恐怕不行。如来藏不是生出生死,而只是说生死会依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来藏在染,就是生死;如来藏在净,就是涅槃。我们一般人会把如来藏看成一个实体般的东西。可是《胜鬘经》说:“如来藏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乱意众生,非其境界。”我们这些众生、一般人,颠倒夢想,会把如来藏看成一个实体,可实际上如来藏不是。
对如来藏的理解,非常困难,过去確實有很多人把如来藏当成一个实体,像《大般涅盘经》的《狮子吼菩萨品》里面就谈到了佛性和缘起法的一个关系:一般人看万法,要不就是持神我论的“常见”、要不就是虚妄的“断灭空”,这两者都是佛教所反对的。佛教讲的是无常无断,既不是神我论的常有常见,也不是断灭空。这个义理很难解释,因为它是“真空”,但是它有“妙有”的趣味,所以很多人会怀疑它是不是含有神我论的气味,即使是印顺法师。
他的研究有个重点,要说明如来藏思想不违背佛陀,只不过它早期在印度不是主流。但对于如来藏,他也有批评,认为如来藏的讲法是受印度神学影响,因为如来藏和梵我论还是很像的。像印顺法师的这种怀疑,其实早在《楞伽经》里,大慧菩萨就曾经提出过。大慧问佛说:“世尊,为什么你和外道一样,都说有一个如来藏呢?”佛陀回答说:“我说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的我。大慧,有时候我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等等,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我是以种种智慧善巧来说,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有时说如来藏,有时说无我。只不过说无我,一般人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所以我有时会讲如来藏。”佛的目的是“为断愚夫畏无我句”,一般人听到“无我”害怕,一般人总是执我,所以要开导他们,讲如来藏。可是它和外道讲的“我”不一样,是一个“无我”的如来藏。从佛陀的本意上来看,如来藏绝对不像批判佛教的人所说,是一种基体主义,或者是“有我论”、“神我说”或“梵我”思想。
四、
禅宗的另一个特点是“顿悟说”。但最近我們发现,顿悟思想很有趣,還涉及到西藏佛教和唐密的传承。
在吐蕃时期,西藏非常强,势力范围是现在的西藏、一部分四川,青海,一直延伸到蒙古、新疆。力量非常大,整个河西走廊都被并吞了。而且,他们曾攻入长安,占领长安40天呢!正因为这样,所以敦煌曾经沦陷过,归吐蕃统治半个世纪之久。当时敦煌的僧人被带到了西藏,其中最重要的是摩诃衍。
摩诃衍是个禅僧,他被迫入藏十多年。去了以后,影響極大。赤松德贊的王妃及貴族婦女三十多人甚至隨他受戒出家當了尼姑,成為西藏歷史上第一批比丘尼。
可是他的講法和西藏当地的、从印度传过来的僧人的讲法不一样,終於引发了辩论。前后有好几次,发表了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非常重要。法国的戴密微最早对这场辩论作研究,称之为“西藏诤论”。後来意大利、日本都有人做研究,也称为拉萨诤论、桑耶诤论(因为是在桑耶寺举行的)。诤论不止一次,所以後來统称为西藏诤论。
我已介绍过,当时在敦煌地区流行的禅宗,乃是南宗禅,摩诃衍就是。后来他和“婆罗门僧”发生辩论。那並不是真正的婆罗门,而是印度过来的大乘佛教,特别是中观论一派的学者。
关于这次的辩论,汉文资料除了《顿悟大乘正理决》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藏文资料,则有莲华戒的《修习次第论》。我们从篇名上就可以发现,一个講頓悟一個讲次第。传统佛教的修行是讲次第,而禅宗是讲顿悟的。
根据《顿悟大乘正理决》记载,摩诃衍到西藏後非常活跃,引起了印度来的僧团抗议,認為他传的禅宗不是佛教,应该禁止。所以摩诃衍就起来辩护,双方有过几次交手。
最终结果怎么样呢?双方的记录不一,漢僧说:“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至今已後,任道俗依法修习”,表明摩诃衍胜了。可是另外藏文的《布顿佛教史》记载完全不同,說:摩诃衍这些顿门的禅师无言以对,只好献花给印度来的僧人,承认自己失败,而且摩诃衍的徒弟当时还自杀了。後来,藏王命令:以后,見解应该依龙树菩萨的讲法来做、行应该根据“十法行”来修学,不再依顿门的规矩。所以和尚就被送回汉地,著作則被窖藏起来,禅僧退出拉萨了。
因双方记载不一,我现在认为大概是这样的:辩论互有胜负,但最後汉地的僧人离开西藏,是因西藏内部政治复杂,佛教教义的争论和内部政治斗争是结合的。所以他们最后离开西藏并不完全是因教义辩论失败,而是政治环境逼迫他们离开了西藏。
但这个争论并不是禅宗跟密宗的争论,而是禅宗跟印度中观派的争论。其中特别有趣的點是什么呢?−−−−中国早期的禅宗思想,实际上就是以龙树传进来的中观思想为基础,慢慢发展起来的。可是,同样是龙树中观思想,在印度继续发展的结果,却跟在中国产生了冲突,有了差異,这是很值得思索的。
五、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禅密关系。
這是另外一种形态,禅家北宗在北方兴盛的时候,也是密教兴起之際,他们的时间非常接近。我们这里说的密宗,是以善无畏、金刚智跟不空为代表的唐代密宗。唐密先于藏密,藏密是一部分唐密入藏以後形成的。
北宗门下有很多著名的禅僧,像神秀的门人,会善寺的景贤禅师,就曾经跟善无畏交往,而且也常被认为是善无畏的门人。神秀的另外一个门人义福,也相传是金刚智的门人。普寂的门人一行法师,后来也师从善无畏跟金刚智,而且还翻译了很多的密教经典。
一行則是非常重要的密教大师,曾修了一種历法,就是著名的大衍历;他也做了《大日经疏》,是当时密宗龍象。
此外,嵩岳一向是北宗的大本营,而担任金刚智翻译《瑜伽念诵法》、《七俱胝陀罗尼》笔受的温古也号称"嵩岳沙门"。善无畏住持圣善寺,而普寂最重要的门人弘正后来也长期住持此寺。因此两宗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研究密宗的朋友,也有些人認為密宗特别像北宗禅,特别是宗咯巴,当然这是後话。但是密宗跟北宗禅的关系是现在一个热门话题,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
现在《禅要》这一套书,虽然是善无畏的说法记录,可是在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北宗禅的影子。例如各位看这几段,“今所发心,复当远离我法二相,显明本觉真如”,又要“如人学射,久习纯熟”,还是需慢慢熏习。这一修法在《楞伽师资记》所述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说得更加具体。还称“所言三摩地者,更无别法,直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名为大圆镜智。上自诸佛下至蠢动,悉皆同等,无有增减,但为无明妄想客尘所覆,是故流转生死不得作佛。行者应当安心静住,莫缘一切诸境”,“行者久久作此观,观习成就不须延促,唯见明朗更无一物。亦不见身之与心,万法不可得,犹如虚空。亦莫作空解,以无念等故,说如虚空,非谓空想。久久能熟,行住坐卧,一切时处,作意与不作意,任运相应,无所罣碍。一切妄想,贪瞋痴等一切烦恼,不假断除,自然不起,性常清净”,这与北宗禅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
总之,敬贤与善无畏的对谈,开启了禅密两家之会合,对佛教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这是密宗与北宗禅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到了善无畏门人一行这儿,却又有了转化。一行现存的《大日经疏》中其实就包含着南宗的想法。
一行认为此经宗旨是“顿觉成佛入心实相门”,与禅宗一向强调的顿悟成佛一致。据《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一〈入真言门住心品〉:“此品统论经之大意。所谓众生自心,即是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者。是故此教诸菩萨,真语为门,自心发菩提,即心具万行,见心正等觉,证心大涅槃,发起心方便,严净心佛国。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故曰入真言门住心品也。”所以他认为只要发菩提心就能够修成正果。
底下这些讲法也都是:“初发心就可以得无上菩提,便得法轮”。这些讲法跟禅宗已经很接近了。禅宗是以心传心,六祖听人诵《金刚经》,“无所住而生其心”,即从这一句開悟。一行呢,强调的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是“想无所住而住心”。这两者是有所不同。但是,他特别强调初发心便成正等觉、顿悟成佛,跟南宗禅已经很接近了。
这是禅跟密的关系。这关系现在我们研究得还不够,但它很有趣。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释说:顺着某种思路发展下去,也许它最後一样會發展成像南宗禅的形态呢?
這也间接的回答了前面那個说禅宗不是佛教的讲法。很多人都说佛教中的国化背离了佛教原意。可是佛教继续发展,可能也就會发展成中国佛教的这种形态。
要知道,批判佛教之類论點,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晚清佛学復兴之后,这争论即一直存在。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及其门下呂澂先生等,就觉得我们佛教跟印度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讲佛教,所信仰的常是伪经、伪论(伪经就像《楞严经》这种,是原来印度没有的。伪论就像《大乘起信论》这种,也不是印度有的)。中國人讲的“本觉”的思想,跟佛教的“本寂”思想也大不相同。故大乘非佛说、“真常心”这个讲法也不是佛教的,禅宗尤其不是佛教。
对这些留下来的争议,我们现在可以說:一,从理论上看,佛教不是神我论,也不是基体主义。“真常心”讲法在印度当然不是主流,但在后期发展中,这个含义卻越来越凸显了,所以“真常心”在印度是支流,在中国是主流。
禅宗是在中国创造的,可是密教跟禅宗之间还是有很多关联。密教是佛法在印度的最后阶段,假如密教還能继续发展,它应该也会发展出一些跟禅宗非常接近的讲法。
當然,从教相上看,西藏密教有很多仪轨、法器,跟汉地佛教不一样。但那是因为地方的风俗不同,或受了苯教的影响,还有其他一些因缘,所以才变成这样。如从理论上说,其中就确实有很多可以互相讨论的,值得深入探索。
六、
我还要讲一个禅和易经的关系。−−−−我這個演講,从发现回鹘文的《易经》残片开始讲起,最後仍以禅宗内部理论與《易经》的關聯作結束。
六祖之后,禅宗内部理论还是頗有发展的,发展的線索是什么呢?就是禅跟易的关系。
各位,佛教在东汉传进来時,中国人乍听之下很难理解。所以,在魏晉南北朝初期,我们要介绍佛教,主要靠什么呢?靠“格義”。就是拿中国人所熟悉的若干观念来跟佛教做比附,以便瞭解。比如佛教讲的“空”,中国人不能理解。中国人總認為“空”就是没有,但是佛教讲的“空”不是没有,而是有,且是有之所以为有的原理。這實在太難懂了,所以早期讲的“空”,都只好拿道家的“无”來阐述。
當時最常被拿来“格義”的就是老子、庄子跟《易经》。支遁、法称、法通,另外还有梁武帝他们,都用《易经》来解释佛教。唐朝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时還说江南对《易经》的注疏有十几家,頗論“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呢!这表示用《易经》来解释佛学,是一种风气。这风气,唐代以后不但没消失,且继续扩大。一行法师写过《大衍历》,用《易经》的大衍之數来讲历法;另外华严长者讲《华严经》,也用《易经》,後來甚至成了个传统。
禅宗在发展过程中,也常利用《易经》来解释修行的方式。如圭峰宗密是华严宗五祖,又是禅宗荷泽的四传弟子。他就曾经用《易经》来讲佛法,有《十重图》,讲修炼过程中的净染之象,与易学的月体纳甲颇为接近,也受了《参同契》的影响。
为什么说跟月体、纳甲很接近呢?纳甲是汉代易学,《易经》在汉代易学是讲象數的,其中《参同契》用之以讲修炼。修煉重視火候,进火、退火,就跟鼎炉烧製丹药一样。如何进火、退火呢?那就要隨月亮的变化了,把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和一个月的朔、望结合起来,形成一套体系,就可以讲修炼的过程啦!
禅宗南岳怀让一系借“圆相”说禅。跟我刚说的月亮一样,也是用进、退来讲用功的情况。传到仰山,更是大规模地使用圆相,到了慧忠以后,竟有97种圆相。易学家陆希声很佩服他,因为这把《易经》的道理发挥到极致了,他特别想去拜访他。
马祖道一以后,到临济义玄这一系,又借阴阳来说禅。他创立临济宗时,就用阴阳的观点提出了“四宾主”、“四料简”和“四照用”。
青原行思一系也用《易经》来说禅。曹洞宗石头希迁還模仿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而作禅门《参同契》五言诗,以纳甲炼丹解说参禅之法与坐禅的不同阶段、境界,用以调和禅宗南北两派的争议;同时,他利用易学阴阳明暗说,融会诸家,提出“回互”理论。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录,《参同契》的内容是这样的: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
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碱醋。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
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
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这篇讲: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明暗像月相一样,有黑有白。他们经常用到《易经》的卦,比如说乾卦,阳卦为白,阴卦为黑,在这个基础上谈。
有关《参同契》具体在讲什么,争议是很大的,洞山良价在此基础上,又作了《宝境三昧歌》,其中有著名的“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十六字偈: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护。
银盌盛雪,明月藏鹭。类之不济,混则知处。
意不在言,来机亦赴;动成窠臼,差落顾伫。
背触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属染污;
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为物作是,用拔诸苦。
虽非有为,不是无语;如临宝镜,形影相覩。
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
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
终不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
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刚杵;
正中妙挟,敲唱双举。通宗通途,挟带挟路。
错然则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属迷悟。
因缘时节,寂然昭著;细入无间,大绝方所;
豪忽之差,不应律吕。今有顿渐,缘立宗趣。
宗趣分矣,即是规矩;宗通趣极,真常流注。
外寂中摇,系驹伏鼠;先圣悲之,为法檀度。
随其颠倒,以缁为素。颠倒想灭,肯心自许。
要合古辙,请观前古;佛道垂在,十劫观树。
如虎之缺,如马之馵;以有下劣,宝几珍御。
以有惊异,黧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
箭锋相值,巧力何预,木人方歌,石女起舞。
非情识到,宁容思虑,臣奉于君,子顺行父;
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用,如愚如鲁;
但能相续,名主中主。
这完全是根据《易经》的卦象,因为六爻是离卦的六爻。“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像荎草味,又像金刚杵,它有宾有主。
有关这个,歷來解释很多,像《宝镜三昧玄义》,宋代云岫禅师所编。《宝镜三昧本义》,清代行策所编,包括六爻四十六种图说。另外还有《宝镜三昧原宗辨谬图说》,清代云淙净讷,讨论历来对宝镜三昧的不同解说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曹山本寂,他又修改了汉代京房的“五位君臣”。京房是汉代易学家,他结合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假借君臣,以彰内外”的思想,后来曹山本寂則发展出了《五位君臣颂》,叫做:
(1)正中偏 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
(2)偏中正 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觌面别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
(3)正中来 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
(4)偏中至 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
(5)兼中到 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五位君臣”也是“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是洞山大师所创,后来曹洞宗都讲这些。
曹洞宗的后学慧洪法师,写了《宝镜三昧》十六字偈。但他的解释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因为慧洪不知道“兼中至”是什么意思,故把“兼中至”改成“偏中至”,用来跟“正中来”相对,后来元贤禅师认为他的讲法有五种错误:
一,“正中来”是前后四位的枢纽,前二位入此位,后二位出此位,属于正象至尊之位,不能与他位互相对待。
二,如果以“偏中至”对“正中来”,则前边有两位,中间有两位,后边只有一位“兼中到”,这就不是金刚杵首尾阔、中间狭的形象了。
三,“正中来”是内黑外白之相,“偏中至”是全白之相,这两位图相完全不能对称。
四,“兼中到”是全黑之相,与“兼中至”的全白之相正好相对,不能让“兼中到”孤独在后而无伴。
五,从三爻五卦看,以正为阳爻,偏为阴爻,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变成三爻,变尽为五卦。其中以上三爻变成水火既济卦,表示“正中偏”;以下三爻变成火水未济卦,表示“偏中正”;以中间三四五爻变成风雷益卦,表示“兼中至”;以二三四爻变成山泽损卦,表示“兼中到”。损益二卦,均出自于中间回互,也就是兼带之义。风雷俱动,象征着兼至的生发作用;山泽俱静,象征着兼到的回归于体。离卦二阳一阴,中虚外明,具有“光明正大”的含义,象征着“正中来”,刚好可以用内黑外白的图象表示。五位配五卦,不仅含义完全相合,而且未济卦与既济卦正好相对,损卦与益卦也正好相对。
总之,無論用黑白点或者阳爻阴爻来讲,主要都是在讲修行的功夫。
曹洞宗临济宗这些祖师们,當時都使用这一套。这表示用《易经》来解释禅宗的修为是一种普遍手法。而且,他们所采用的不是汉魏以来我们读的《易经》。我们现在读的都是王弼的注解,他的特色是扫除象數,而这些禅师讲《易经》时,卻都使用汉人的象數易学,而且用得最多的就是《参同契》。
《参同契》是一本很奇妙的书,道教内丹和外丹學都参照《参同契》,是他们的共同经典。曹洞宗临济宗在发展的同时,道教的内丹也同时在发展。
道教早期都是把金石矿物炼了去吃。唐代中期开始有了内丹的讲法,主要大师就是吕洞宾和钟离权,他们有本书叫《钟吕传道集》。认为我们不需要吃丹药,我们身体就是鼎炉,最好的药材就在我们身体裡面。把我们身体内部的元素调理好,到最後水火既济,内在成丹,就可以成仙了。
道教在中晚唐兴起这套理论的影响很大,後來全真教出现,被认为是内丹的北宗,江西、福建这带流行的叫做内丹南宗。南宗有七真,七个祖师,北宗也有全真七子。明朝晚期又发展出东派,清朝則发展出西派,中间还有个中派。这些内丹派的共同祖师就是吕洞宾,所有道教宮觀,只要有内丹传统的,都专门有个吕祖祠。吕洞宾是晚唐人,他这一套讲法就结合了《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在唐代中晚期還有一个彭晓写的注,他讲的“五位君臣”就跟宝镜三昧很像。彭晓和吕洞宾的内丹学,可能和禅师用《易经》来讲禅宗修炼是有关系的,也许他们是从禪宗这边得到了启发,才开启了内丹学。
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可以说明后来的道教的内丹,為什麼都叫做性命双修。性命双修的命指我們要活久长点,这部分是用道教的功法,而性功則都是用禅宗。只修命不修性是不行的,怎么样才可以修性呢?采用的就是明心见性的禅宗功夫。道教的内丹,基本就是结合禅宗的道学。这样的发展,中间當有个过渡,那就是禅宗从唐代到北宋大量地、非常娴熟地使用《易经》来解释禅门修行方式的做法。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做的报告的几个部分,希望能给各位带来新的思考。感谢各位聆聽!
附答問:
問:日本批判佛教、批判禅宗,目的是不是要否定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答:日本的批判佛教,不要孤立地看,它其实要回答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谈佛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佛教在明清是很衰落的,所以近代佛教有个复兴运动。复兴的形態很多,像支那內学院,或太虚法师所提的“人间佛教”等等。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明清以来佛教状况的担忧。所以近代有很多大僧人大学者,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像弘一法师,認為要振兴佛教,应该从戒律着手,因为僧团的戒律已经松弛了。印光法师則觉得我们要接引大众,让大家重新对佛教产生信仰、信心,應該从净土的角度。太虚法师又觉得佛教的格局应该更开阔,在汉传佛教之外,也应该包括藏传。他对佛教本身的僧团改革、佛教跟社会的关系著墨很多,所以社会不觉得佛教是脱离社会、只知山林清修过自了汉生活的群体。他们都各有主张,但是其中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佛教到底应该如何定位,这是一直没解决的。
中国汉传佛教到底怎么定位?我们自己当然觉得我们的佛教很興盛、是正宗,但你若把眼光放到世界看,你就知道,别的地區,佛教跟我们大不相同。例如汉传佛教当然都吃素,但其他大部分地区佛教徒卻不吃素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觉得很奇怪,但其實我们才是特例。世界各地研究佛学的人,比如欧洲叔本华这些哲学家,都受過佛教影响,这是大家知道的。欧洲人老早就研究佛学,而他们跟印度的关系更密切,但他们看不懂汉文佛典,只懂梵文、巴利文、藏文,所以更会觉得汉文佛典是个特例,認為中原地区的佛教是很特殊的佛教形態。
刚好中国的佛教跟西藏、南传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大乘,南传只是小乘,不重要。然而从南传的角度看,什么大乘佛教?我是上座部佛教,你是大众部佛教,你比我低啊!
从这些角度看,我们中国的佛教本身应如何定位、如何说明我们的特性,不是問題嗎?我们確實有很多特性,可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你这些確實是特点,但你有了这些特点以後,还是原来的佛教吗?
於是清朝末年,出现了一种思潮,其想法就是回到印度、回到佛祖的时代。因为後面的发展可能走偏了、走错了,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回到佛陀。在中国,就是先回到玄奘,因为玄奘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又是汉传佛教跟印度的中间一个接头。但玄奘的佛学已经中断很久了。他虽然名望很高、贡献很大,但他的法相宗只傳两代就绝了,直到清朝末年才恢复。
回到玄奘的意义就是回到印度。这一条路不是只有支那內学院在走,实际上有很多人。在民间,現在还有很多讲佛学的人标榜我是原始佛教,我讲四念处、我讲四阿含,說大乘是佛教后期的歧途,禅宗更是中国人後来自创的,跟佛教没关系。
这是近代学术上的大问题,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批判佛教只是这大脉络底下的一种思潮。
这类思潮为什么值得我们提出来討論?因为它不是泛泛而谈,谈一些仪式啊、规矩啊什麼的,它是在追问我们信仰最核心的部分,佛性、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等等。明心见性,这性到底是什么?明心见性的性就是我的心,我的心是什么意思?一般人的理解是:我的心就是有道德的一个主体。如果这样理解,那就跟佛陀讲的不一样了。世界不是万法皆空吗?那至少有一个不空,我的心不空,我的心又生万法出来,很多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可是佛教之原義不是这样的。这个我應該也是空的。法、我皆空,而空又不是断灭空,不是没有的空,所以它难懂、难以理解。
禅宗的讲法最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因为中国人讲主体性,故禪宗的讲法和儒家道家都很接近。但是它毕竟是从佛教发展下来的,它所提出的“真常心”的理论,并没有违背佛教的缘起观或中观,它只是展开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现在要重新去辩护,证明批判佛学的批判不对,替禅宗做一个理论上的辩护和说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个头等大事。
我们自己認為是佛教,但還有許多人认为它不是佛教,这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要说明它是佛教,和释迦牟尼的思路是不违背的,是一个思路的很好的发展,而且这種发展并不仅仅在汉传地区才有,它还曾经影响过西北、回鹘等一片广阔的区域。而且并不只是单方面地从印度传过来,还有我们传过去的東西,包括西藏也受我们的影响,或者说,它发展出了一个和我们很接近的思路。同時,禅宗的影响,還不仅仅在禅宗内部,它后来还影响到了道教等其他方面。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不是宣讲式、弘法式的,我想从理论上来解决我们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和我们现在禅宗的处境有关的。禅宗只有面对这些理论上的问题,才能发展得更好,才能明白在整个佛教中我们的定位和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要談到密教,說明它和禅宗是可以有交集的。佛教从小乘、大乘发展到密教。密教是一个没有完成就中断了的体系,因为印度被侵略,所以佛教消灭了,这导致它的发展中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則是大乘佛教理论的继续发展。
这也回答了刚刚的问题,日本人要否定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其实不,日本人在佛教上不太看得起中国。因为日本的佛教比我们厉害多了。我常常开玩笑说,中国的佛学研究落後日本一百年都不止。很多人都不服气,因为我们对日本有抵触情绪,但是你想想也就知道了:刚刚我讲了很多《大藏经》的事,中国现在还存有十几二十种《大藏经》,但是学界是不会用这些书的。全世界研究佛学的人,用的都是日本人编的《大正藏》。而《大正藏》收录的汉文佛典中,日本人的著作比中国還要多。所以全世界的佛教研究者都认为日本佛教比中国佛教重要。
禅宗,我们自己認為了不得,但是世界上说禅宗,日本铃木大拙的影響比我們大得多。所以西方世界讲禅,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我们现在的佛教还在恢复过程中,还在休养生息。所以日本在佛学研究上开发一些论题,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
反之,现在我们要恢复中国佛教的声望,要作研究,就要关注、吸收日本人的论题、想法和研究成果,这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问:我们学佛需要了解刚刚这些问题吗?
答: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吗?修行就可以了。当然!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每个人学佛的原因也不相同。
知道一个道理以后就奉行它。奉行以後,觉得身心安泰,能够获益,这样当然很好,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我们相信了一个道理,卻自己又不安心,那就别谈了。但有些人会说,我相信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的历史发展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还有些不同的说法?我们若要了解这些,那就还要做一些历史的考察。
还有,我相信这个道理,但是不是道理就是这样呢?我相信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值得奉行呢?是不是还有争论?我是不是还可以想得再深一点?这就需要再做一些理论上的辨析了。
換言之,修行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层次即有不同的理解。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想这么多,但是如果能够多知道一点、多想一点,当然就更好。
问: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困惑,我不知如何才能进入佛学的殿堂?
答:感谢你的问题,你也说出了很多人在学佛过程中的困惑。我的建议是这样:我们不是在讲禅宗吗?禅宗有個有名的偈语:“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你到处去找什么上师、到处巡山拜佛,有什么用呢?佛在汝心頭,自己明心见性时,哪还需要你跑到西藏去?找很多的上师?那都是徒劳,本来就是没用的,所以你找不到也是当然的。
佛教的道理,千言万语,分开讲,非常复杂。简单说,又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讲的:“明心见性,自证本心”,所有的道理,收归到你的本心上,不需要对外去寻找,如果还需要印证,可以从佛教的经典中得到一些印证。佛教的道理并不复杂,无非“三法印”、“四圣谛”,这是它的根本道理,最多再加十二因缘。各宗各派讲得这么繁琐,都是以这为基点发展出来的,如果你能够对“三法印”、“四圣谛”有所体会,自然就可以了。你所要学的就是这个,其他的,不用到处去找。
现实的人都是有缺点的,所以拜誰為師都不牢靠。佛陀他最后印证的是那些道理而不是誰。我们学佛,也是学他发现的这个道理,“依法不依人”。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總觉得找个人才可以依靠、要找到某个人可以去追隨。其实不用的,因为法就在那裡,非常简单,只要你能如法去做,那就对了。法,其实大家都知道,没什么秘密,明心见性有什么秘密?不需要另外去找,当下即是,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问:我平时也修行,可是也有很多困惑,我应该去看什么样的经典?
答:《六祖坛经》还是有用的。《坛经》有个故事,說有人去问六祖,坐禅可以吗?六祖说:“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重点还是在于你心不定,心还是乱的。
问:用什么途径让心安静呢?
答:从外相你不可能静,从外相怎么可能静呢?我们宜春不是有马祖道一吗?马祖道一禅师有个最有名的典故,就是說磨砖不可以成镜。外相怎么可能静呢?静是心静,越是利用这些外在的形式,越是不可能静。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本。
问:那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答:根本就在于心上,心不静所以才要静心。你再用一个别的东西来让心静,那是不可能的。心外求心,何时了结?古人讲:以水济水,只会更乱。
问:印顺法师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中国禅宗应该是一种应机说法,你说到马祖道一禅师他用阴阳说禅,它的内容是什么?
答:您这是两个问题。印顺法师是要解决我们刚刚所讲的问题,因为有人认为大乘非佛说,如来藏也不是佛教思想,所以后来印顺法师判教,认为佛教可以分为三系: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真常心,我们要承认它是佛教理论中一个合理的发展,它在印度、在佛的说法中是有根据的,他要确定这一点。后人之所以会觉得它可能不是佛说、违背了佛教道理,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在印度是个支流,真常心系统到中国以後才发展得比较好;第二,真常心的讲法,可能被认为受印度教的影响,有似“神我”说。印顺法师分别这两点做了说明。真常心系的思想在原始佛教中就有,只是在印度发展得不够好,在中国发展得比较强,所以它算是中国和印度佛教发展的不同取向。我前面要讲的也是这个。
后面所谈的是应机说法。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应机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谈佛法与科学,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相信科学,所以我要让你相信佛教时怎么办呢?我要告诉你佛教不违背科学,或者说佛教非常科学、佛教不但科学而且超科学。这其实也是一种方便说法。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个时代的人相信这个,所以我就用这个跟你解释。在唐代那时的读书人,对《易经》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那个时代的祖师们,如洞山、慧洪、曹山等,几乎都使用《易经》来作解释。这是他们当时的应机说法,当时社会的知识界就跟我们现在相信科学一样,知识群体相信《易经》、熟悉《易经》,所以法师们就用《易经》去解释它,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说法。
我们过去在解释禅宗史和禅宗理论时,看这些东西看得特别头疼,实在不知道他们的譬喻解释是怎么回事。这其中可能有一些元素是当时人对《易经》的解说。这些禅师,是针对当时人对《易经》的解说再做一些解释。我们脱离了当时的语言环境,孤立地去看那些解释,虽然作了很多注解,可是还老是讲不清楚,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今天看这些东西时,我也建议其实不要看得太实。很多人在他们的举例和譬喻上辩论不休,我觉得没太大意义,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当时而做的配合就可以。就像现在圣严法师写《佛法與科学》,我们针对这个去辩论他寫得對不對,佛教是科学吗、佛教超科学吗等等,有啥意义?我们應知道这只是这个时代的应机说法呀!
现在很多人讲佛教打坐参禅,跟能量、跟量子物理、跟医学如何相关,打坐的时候身体的能量就会如何如何,那都是因为我们现在相信能量,所以借这些东西去解释。难道它們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我们只是用这些东西去解释,去增加知识阶层人士的信任,认为打坐挺好的。其实他不是相信打坐,而是相信能够增加能量。这些都是属于应机的,不可以执着来看,所以说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简单地聽我的介绍就可以了。或者你有兴趣,再去找一些资料,晓得当时有这么多的讲法,或利用这种方式来劝化对于佛法还不理解的,特别是对于修禅的方式还有很多困惑的人,也是可以的。
问:老师你好,现在有很多学佛的人会买一些小动物去放生,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你买了东西去放生,卖家还是会去进货卖给别人,这种行为是不是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灵安慰。我觉得如果你有一颗慈悲心的话,去看看孤寡老人,做做慈善之类的就很好。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答:“放生”是明朝提倡的一种伦理态度,因为觉得杀生太多,提倡放生,同时也伴随着一些仪式。但历代都面临着你这样的质疑,有一些商人专门捕动物来给你放生,还有就是放生有时没有考虑到环境,影响生态。这些都可以斟酌,如果我们觉得现在放生引起了不好的結果,當然可以做些调整。但还是刚刚所讲的,这些形式都是外在的,放生的目的是提倡人應該有慈悲心,所以它的重点是呼吁人有慈悲心。
放生这种仪式,可能不足以启发这种慈悲心、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就可以开发別的方式,像你说的照顾孤寡老人啊、维护生态等等,都很好。
假如我们不采取放生的仪式,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慈悲心,只是我们觉得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某个地方是可以放生的,某些地方不必放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再做调整。
问: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净土?释迦牟尼佛会不会去那里呢?人死后会去哪里呢?
答: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确实是不去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净土。不同的佛有不同净土,有东方淨琉璃世界、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法华净土、有華嚴淨土等等。不管什么净土,我们一定不要执着。因为净土的讲法只是相对於我们五浊恶世来说的,不是人死了以后才去净土,我们活着也要追求净土,不要活在一个污秽的环境里面,要追求清净世界。
后来的佛教,不是常有人说“心净佛土净”吗?净土会应在什么地方?净土在心上。“心净佛土净”,这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哪里是净土,不是说死掉以后再去净土。现在让我们自己心净,从而创造出世界,成为净土,这比较实际。死掉以后去哪,很难说,对不对?
问: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答:其实没有原则的不同,只有些形式上的差異。
西藏佛教,我们现在一般都说是密宗,其實密宗最早先传进的是中原,在长安等地極盛。後来传到日本,称为东密。日本密宗空海大师就是到唐朝来留学以后,回日本去开创真言宗的。而藏密是一部分唐密进入西藏,还有一部分由莲花生大师从尼泊尔进西藏,综合开创的。

但是後來曾经有一段时间,西藏灭教,所以西藏的佛教曾经中断过,当时曾把佛教的经典都藏起来,号称“伏藏”,後来才又挖出来。所以西藏的佛教分为前传期和後传期两段。
不管阶段如何,藏传佛教基本上是以密教为主体建立的。密教在汉地只是所有的宗派中一部分,例如寺院中有千手千眼观音的,就是有密教淵源或受密教的影响。只是在汉传地区,有独立传承的密教比较少。在西藏的密教是集中的,在汉传地区,密教往往融入其它宗派中。
第二,西藏本来有宗教,叫苯教。苯教有一部分受波斯影响。所以佛教进入以后,它和本地信仰有严重的冲突,但又有融合。例如吸收了苯教的一些神,視为佛教的护法,所以西藏佛教有一部分是苯教的传统。
三,西藏佛教還接收了一部分印度密教的影响,这主要是后期密教,如“金刚乘”。这部分佛教法器比较多,而且比较强调手印和口訣。由于神系不太一样、法器比较多、又强调手诀咒語,所以从形相上来看跟漢傳很不一样,但从理论的内涵说,还是一脉相承的。
问:北传、藏传、南传三系佛教最完整的是哪系?
答:三个系统都不完整,各有所长。汉传《大藏经》中有一些是西藏《大藏经》没有的,藏文《大藏经》中又有一些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各有所长。
南传没有大乘,基本上属于上座部佛教,所以三个系统要综合起来看的。現在和过去不一样,古代人认为大乘比较好、密教特别神秘,和显教不一样,有秘密法。我们现在看,則觉得三个体系各有所长,!
问:您在台湾工作过,现在却接受北师大、清华、北大等大学的聘请,您为什么来到大陆?
答:我的目的还不清楚吗?我是来播種的,弘扬文化。大陆如果要复兴国学,没有我,能复兴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