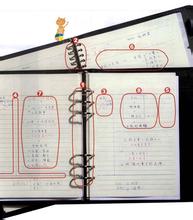春末,褐海这座城市一片青葱,欣欣向荣。我依旧安安静静地潜伏在褐海中学的一隅。校园角落里的叫不上名字的小花,粉的,黄的,大马路上的杏花,全都绽开了,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我忽然潦倒起来,有时候,半夜起床,喝一点酒,头晕脑胀地又睡过去,醒来时,天就亮了,窗外的树上驻着麻雀,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学校里的事情杂而琐碎。
我已经有些厌倦了。厌倦这里的古板和压抑。更多时候,我愿意在下午的时候坐到艺体馆门前的台阶上看操场上的孩子们踢足球。张卓群越来越少地出现在那群男孩子中间了。有几次,他站在操场边,湿漉漉的眼神看着跃动在操场上那些生龙活虎的身影。
批改高三学生作文的时候,我批到了一个叫卢榛榛的学生的作文。我边读文章边向她的语文老师请教:“你看这个文章写得是不是很好?”
坐在我斜对面的同事皱起了眉头,问:“谁?”
我说:“卢榛榛。”
他说:“她啊——”声调拉长,有不怀好意或者是轻蔑的意味。
“她怎么了?”我迫不及待地追问。
“哦,没什么。”
我埋下头,又去读文章。题目叫做《依然站着》。办公室的窗外爬满了绿色的藤蔓,生机勃勃。这个季节的生命总是旺盛且充沛地生长。在不经意间,一切已成蔚为壮观的景象。生机盎然的夏就要降生了,我摆弄着红笔,内心草长莺飞,一片狼藉。
我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女孩。
我不觉得自己哪里好,不觉得自己的名字好听脸蛋好看,也不觉得上天非要垂青或者拯救我什么,我是一个看上去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没人知道我心里那个洞,黑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可阻止地成为我生命的疼痛所在。铭心刻骨。
我很年轻,在大街上,总是有很多很多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模样清爽,朝气蓬勃,她们成群结队地出现,麻雀一样掠过街头。我和她们如此格格不入,遥远得恍若隔世。我想,我不是一个天使,我是一个幽灵,或者魔鬼。许多个夜里,我梦见一匹白色的马拉着灵幡驶过我的窗前。姐姐和以往一样,突然出现在客厅的沙发里,蜷在那儿,像一只疲惫安静的猫,我背着大大的书包,弯下身子来,叫了一声:“姐姐。”她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为什么没有按时回家。两条腿悠闲地交叉在一起,与她上半身的激动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百无聊赖。
进自己的房间,打开书包,把课本拿出来,坐在书桌前温习功课。门微微敞开着,厨房里飘出晚饭的气息。爸爸在门外晃了晃,又走开了,坐下去小声地同姐姐说话。姐姐似乎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窗外的天空晦涩滞重下去,空气中混杂着油腻甜腥以及夜晚来临之前微凉的枯涩味道。姐姐总是如此神出鬼没。有时候,妈妈提起她,就无奈且懊恼地摇起头,说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泪花。从小到大,姐姐一直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离家出走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最长的时间是出走一年半,一年半之后,当她破衣烂衫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妈妈几乎不能辨认出她是自己领养的女儿了。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去年SARS风头最紧的时候,因为姐姐,妈妈哭了几次,她打电话给姐姐,叫姐姐回家,姐姐不肯。她说她在澹川,一切都很好。可在妈妈的印象里,那一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城市,有战争、瘟疫和无休无止的死亡。后来姐姐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被确诊为SARS疑似病例,被隔离了,不能回家。她说这些的时候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而电话这端的母亲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她那么大的年纪,为了这么大的一个女儿,折腾成如此模样,我真为此有些憎恨姐姐。
弟弟与姐姐如出一辙,一样的不听话,从小到大,让父母为他们操透了心。他理着根根竖立的毛寸,走起路来左摇右晃,把家里的东西摔得叮当作响,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怒火。他常常毫无礼貌地指责妈妈的聒噪和唠叨。很小的时候,爸爸总是舍不得打他,也有例外,他十二岁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抽烟,被父亲抓住,皮开肉绽地打了一次。可他本性桀骜,是不可更改的性情。后来,爸爸再教训他的时候,扬起的手被他架在了半空,他大逆不道地说:“你太老了,留着点力气撑着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吧。”然后狠狠地一推,爸爸踉跄地退了几步才算站稳。
弟弟叫潘景家。已经十八岁了。姐姐叫陆曼娜。而我叫卢榛榛。这是一个奇怪的家庭。
弟弟是父母领养的最后一个孩子。弟弟的妈妈因为生弟弟大出血去世,而他的父亲拒绝认领这个孩子,因为弟弟不过是他和那个可怜的女人的私生子。他是一个没有一点责任感和怜悯心的男人。所以,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弟弟就失去了双亲,他就亲身历练着人情冷暖,没有爱,没有呵护,什么也没有,光溜着屁股躺在一张小床上,他本能地伸开双臂,粉红色的肉乎乎的小手在空中抓着些什么——连刚出世的孩子都知道寻找爱,可是他注定什么也抓不到。自己的命运仿佛是一团被揉捏的废纸,任意抛弃在世界的角落,等待陌生人来翻云覆雨。这就是弟弟。从一降生,陌生和疏离就成为他命运中解不开的结,他只有生活在自己用隔膜做成的世界里才感到安全。
后来,弟弟被送到孤儿院。
我九岁的时候,爸爸有一天下班回来郑重其事地坐在我的对面。他和蔼慈祥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不安和慌张,他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他小心试探着问我:“榛,你不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睁着明亮的眼睛,略微有些恐惧地望着父亲,父亲有很大的鼻子。更小的时候,我被他抱在怀里的时候总是没完没了地拿捏他的鼻子。我其实已经有些隐约。
在我更小的时候,大约四五岁的年纪,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他们总是刻毒地喊我是“私生子”。有一次,我哭着鼻子去问幼儿园的阿姨什么是“私生子”,她停下手中的活,俯下身来,紧紧地贴住我的脸,对我说“私生子”就是没人要,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你有爸爸也有妈妈,有温暖的家,还有一个姐姐呢!最后她直起身来,照例拍拍我的头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下了一个结论,你不是私生子!我安心地看了看幼儿园的阿姨,快快乐乐地走开了。
可是那样容易被美丽的谎言所欺骗的年纪早已灰飞烟灭。
姐姐说:“榛,你是私生子。”
姐姐交叉着光溜溜的大腿坐在我的对面。麦当劳店里人来人往,她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咬牙切齿。面目狰狞。我突然停止了咀嚼,手里还捧着一个汉堡,两条腿晃晃悠悠地吊在半空中,忽然就停止了摆动。
我说:“姐姐,那你呢?”
她说:“我也是,我和你,我们都不是好东西,是私生子!”
——姐姐那一年十六岁,正式从学校退学。因为她和一个男孩子在自习课上拥抱和亲嘴,且拒不承认错误。她还打架、抽烟、说脏话,是个女流氓。她被学校开除了,狠狠地开除了。她离开学校那天连头都没回一下。
她带我来麦当劳,这钱是她从妈妈那儿偷来的,她就坐在我对面,阴郁着脸,看我,警告我:“不许说你吃麦当劳了!”
她是一朵半途而废的花,猖獗且不顾一切地怒放。
我觉得姐姐美丽极了。
——爸爸把我的手攥在手心里。我觉得很温暖。
我说:“爸爸,我不想知道。”
爸爸说:“不,榛,你迟早需要知道。”
第二天,爸爸带我去了孤儿院。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弟,他理着平头,穿着一件小白衬衫,纽扣系错了一颗,睁着大而灵动的眼睛,双手狠狠扯住栅栏的栏杆,向外张望,同时,身体不停地向后荡去。
还有很多孩子,可是我却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
我走过去,隔着栅栏摸他的脸,冷,有雨后润凉的气息。我雀跃着叫他“弟”。他定定地看我,忽然开口说:“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吗?”
我说:“你不喜欢这里吗?”
他回头看了一眼,我的目光被牵引过去,看见了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小男孩,安静地站在那儿,他又转过头看我,凶巴巴地说:“我恨透了这里!”
爸爸告诉我,六年前,我就是从这里被他和妈妈抱回家的。现在他和妈妈想收养最后一个孩子,想要一个男孩,姐姐让他们太失望了太伤心了。我被爸爸拉在手里,沿着栅栏在一条石板小路上走过去。之后,我们见到孤儿院院长。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女人。
她似乎和爸爸是老朋友了。
她坐在茶几后面,笑容满面:“老卢啊,要我说你就带这个叫沈小朋的孩子。”
她欠过身,递来一张照片和一沓资料。照片是黑白的,小小的,上面一个瘦小的男孩子,有点惶恐的样子,嘴唇紧咬住。
院长接着说:“这孩子天性温顺,从不惹是生非,而且脑子聪明。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也不容易,收养一个将来有指望的孩子吧。”
父亲笑着说:“这孩子的身世?”
院长说:“一个女人送来的,她说她是从一个垃圾箱旁边捡来的,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送到这里来了。做父母的也真够狠心的,或者是走投无路了吧。这些事谁说得清?只可怜了孩子。”
父亲翻来覆去地把那些资料和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看了又看,笃定地点头。他对院长说:“就沈小朋了!就这个孩子了!”
我们三个人沿着栅栏在那条石板小路又走回去。春天的上午,阳光明晃晃的,几只燕子停在电线上,又扑棱着翅膀飞开,一些女孩子发出了美丽的尖叫。幼儿园的小操场上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两个六岁的男孩子大打出手,一个穿小白衬衫的男孩把一个穿蓝颜色T恤的男孩骑在了身下,同时,手持一块小石头重重地拍下去,下面的男孩即刻头破血流,他先是抽搐了几下,不久就爆炸一样哭了出来,哭天抢地。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小男孩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用陌生疏离的眼神看着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的男孩,不说一句话。
院长大声叫着,声嘶力竭:“潘景家!潘景家!潘景家!”
她给气得脸色煞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应声扭头朝我们瞥了一眼,是那个穿小白衬衫的男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潘景家。而倒在地上的那个,血流不止,他就是爸爸准备领养的沈小朋。
我扯了扯爸爸的衣角,他弯下身,拍着我的头顶,说:“榛,别怕,男孩子打架而已。”
我指了指手里还拎着小石头的潘景家,我说:“爸爸,我要他做弟弟。”
透过栅栏,可以看见小操场上惶恐的人群,所有的小孩子们像是惊恐的小兔子三三两两地蜷缩成一团,胆战心惊地看着跑道上的两个小男孩,风吹起了他们的衣服,鼓鼓的像一片迎风飘扬的旗帜。潘景家面不改色地站在那里,怒气冲冲,而倒在地上的沈小朋这会则坐了起来,泪眼婆娑,他身后的天空笔直着倾斜下去。
我绕过栅栏走到他的身旁,我比他高出一头,我拉起他的手说:“弟,我们回家。”就是那时,沈小朋的哭声戛然而止。
潘景家就这样意外地走进了卢家的院门,但从始至终,都无法融入这个家庭。
十几岁以前,我们总是无休无止地战争。很多次,他抓破我的脸,把我打哭。之后,又喃喃地叫我“姐姐”。我总是试图对他好,可他总是拒绝,或者厌恶地将我打哭。这似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漫长游戏,我们都乐此不疲。但注定终究会有厌倦的一天。
夜晚,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经常是他的两条胳膊绕住我的脖子,越绕越紧,像系在我脖子上的绳索,将我从黑暗中勒醒,我在暗夜里看他的脸,总是有些惶恐。额头上凝满了汗,熠熠闪光。
再长大一些,我们分床而睡。相互之间很少说话、交流,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他才叫我一声“姐姐”。读小学的时候,我一直送他到学校,看着他背着书包晃进教室之后我才安心地离开。我总是说,弟,你要让姐安心。
可我却一直怀念以前的日子,我甚至从未曾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情愫有何异常。亲情之外,我们在最初的相遇中就已注定了一些纠葛,可是却无处逃逸。
从小,弟就没有让父母省心。他总是没有尽头地打架,总是不断有“仇人”找上家门或者偷偷地砸碎家里的玻璃。我终日胆战心惊。一起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有时会遭到一群男孩的围攻。我知道他们是弟的敌人。可弟毫无畏惧,他和他们厮打像头凶狠残忍的小兽。似乎生下来,他就天生一副打架的坯子,即便被打倒在地,头破血流,他也不哭,从不哭。我书包里总是备有创可贴,每次打完架,我都给他处理伤口。
弟的身上,早已是伤痕累累。
有一次,他的额头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横流。我用酒精棉止血之后,用蘸了药水的纱布将伤口精心地缠住,绷紧,用牙齿咬住纱布,系紧,当我全神贯注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坐在床上的弟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双手已经揽住了我的腰,他把头探进我的怀中,我蹲下去,看着他,他冰冷的唇凑了过来。才十几岁,他还太小,我们的亲吻,有力而仓皇。
可是,从那以后,弟再也不肯同我多说话,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形同陌路。
弟在十四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女朋友。那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脸面有些单薄,经常是叉着双腿,嘴巴上叼着棒棒糖,背着一个大书包在马路对面等待她的小爱人。弟会拉她的手,一起匆匆走掉,像两只纯良的小白兔,转弯消失的瞬间,我安慰自己说,榛,这样是好的。弟一直是一个孤单的孩子,两个人在一起,就会觉得暖了。
可我依旧是不能自抑地悲伤。
站在黄昏的马路尽头,看到清洁工将风吹落的枯叶扫成一团,又用火点着,树叶的燃烧发出一种古怪的味道,腐朽般清香,我抽动着鼻子,不知道是被烟呛到了,还是真的想哭,心隐约有疼痛之感。
弟这一年进了褐海中学的高中部。而我刚好由前楼搬进后楼,开始读高三。
我所在的褐海中学有尖尖的屋顶,小且精致的红色塑胶跑道。弟开始穿橙色的球衣在操场上踢球,大汗淋漓地。即便是只有他一个人在玩,依旧如此。足球在他的脚下奔来突去,更像是另外一个生命,和他追逐嬉戏。我亲眼看见他在挥霍和透支着自己的体力,汗水齐刷刷地从额头跌落。他站在黄昏的入口,像一个英武而忧郁的小王子。我习惯坐在艺体馆门前的台阶上看他踢球,那里可以躲雨,这是弟弟告诉我的。我就坐在那儿,安心地抱着一瓶矿泉水,等着他踢完足球跑过来拿。
弟开始抽烟。
最开始,我在他脱下来的牛仔裤里掏到了半盒烟。外面是冬天。姐姐因为意外的流产住进医院,已经有一周时间了。父母都去照料她了,家里又空落起来。弟才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心存有微微的恐惧,像落在他头上的几片雪花,知道在这样的温度中势必融化,这是我的命运,只能在激烈的对峙和彻骨的寒冷中向往爱,可一旦爱降临了,我就会死,因为爱是有温度的,是暖的。
——我如此害怕,又渴望与弟和睦独处。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呆呆地看着时钟的指针一圈一圈划过去,双眼红肿。弟走过来,他在我的身边坐下,探手够过茶几上父亲的烟。我说:“弟,你不能抽烟!”
他没吱声,也没看我,似乎这句话十分荒谬。
之后,他进了自己的房间,书包扔在了沙发上。很难揣测我怀着怎样的心理,双手颤抖着打开了弟的书包,我在里面翻到了一个小维尼熊以及三个避孕套。那一刻,心突然乱了,从窗口吹进了冷冷的风,我觉得自己在沉陷,像一枚最不起眼的鹅卵石,最终被包裹在海藻中间,不复被人触摸的可能。
我站起身,走到弟紧闭的房门前,抬起一只手,就在扣门的瞬间,又犹豫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他十八岁了,个子已经蹿到了一米八○。站在我面前,更像是一个哥哥的样子。似乎每时每刻他的身体都在生长,雨后春笋一般旺盛茁壮,站在我身后,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叫“姐”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心跳。这就是潘景家吗?多年前那个手里攥着小石头,穿小白衬衫在风中傲然站立的小男孩?是他吗?我竟然有些不确定。
门被打开了,我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弟换了一身衣服,崭新古怪的。
我忍不住:“弟——”终究是欲说还休。手中握紧那三个烫手的避孕套。
他用一只胳膊推开我,对我说:“姐,我出去了。”
不及我问话,他提起书包,连奔带跑出了家门。
一夜未归。
我整个夜晚守在电话机旁,看着天色一点一点黑下去,黑到无边无际,黑到天光大灭,黑到绝望,然后再一点点转为微蓝,边缘处有炭火般的闷红,转白,转亮。我手里拿捏着从弟的书包里偷出来的小维尼熊和三个避孕套终于在稀薄的凌晨抵达之时靠在沙发上睡过去。
从那时候开始,弟的身影很少出现在操场上了,他不再来踢球,可我在艺体馆门前看球的习惯却意外地保留了下来。
——我是一个乐于怀念的人。就是这样,我的天空累积了很多忧郁的云朵。
那个叫张卓群的男生总是在踢球休息的间隙向我跑来。第一次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无比荒唐的借口搪塞,他挥汗如雨,指着我抱在怀里的矿泉水恭恭敬敬地说:“我好像认识你,可以借你的水给我喝吗?”
我犹豫了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过矿泉水给除了弟以外的其他男孩喝。
我抬眼看看他,多少觉得这个人有些明目张胆了。
记忆这张网,网不住阳光了,水一样漫过来,我在记忆的水面上寻寻觅觅,终于看到这样一张脸,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一个瘦小且神情惶恐的男孩,紧抿嘴唇。最后的形象是,他穿着蓝色的T恤衫头破血流地躺在地上,几只麻雀从天空飞过去,他在哭,在抽泣,可我听不见任何声音。我把手中的矿泉水递给他的时候,试探性地叫了一声:“沈小朋?”声音小小的,我看见他恍惚了一下,仿佛在听别人言说一个陌生的名字。我的心又沉了下去。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肯定是记忆出了错误。我垂下头,看自己并拢在一起的双脚。倦怠。很漫长的时间,我以为他离开了,可他还在。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
我又确认了一次:“你是沈小朋?”
他点头,说:“是。”
“在孤儿院里的那个沈小朋?”
“是。”
他笑着,笑容融化在阳光里,像个天使,第一次觉得男孩子可以如此干净、纯良,像水一样温润。他静静凑在我身边坐下。
“我想我知道你是谁了。”他说。
我说:“对,我就是。”
他皱起眉毛问我:“当初,你为什么不带走我?”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我更喜欢桀骜的孩子吧。我弟就是。”
“潘景家?”
“是。”
他喝了几口水,还给我,说:“谢谢你的水。”
我没有说“不客气”,而是问他:“这些年,你一直在孤儿院长大?”
他说:“不,我很快就被亲生父母找到了。我现在已经不叫沈小朋了。我叫张卓群。”
望着一脸迷惑不解的我,他笑笑说:“其实,我也不明白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为什么如此离奇,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人叫我‘沈小朋’这个名字了。这不过是送我进孤儿院的那个陌生女人随口说出的名字而已。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出门,之后把我弄丢,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我被人送进了孤儿院,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最终被父母找到,才重新回到了家。所以,我一直是张卓群。‘沈小朋’不过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小插曲。”
我说:“你是幸福的,你比潘景家幸福。我当初选择了潘景家没错。”
他说:“我宁愿你选择我。”
说完这句话,他起身向操场跑去。绝尘。
我瞥见他红了脸。“我宁愿你选择我”这句话是可以有很多解释的。比如说,这“选择”并非多年前意义上的选择,而是意味着现在,甚至将来。因为毕竟潘景家已是我的弟弟。或许是我的心思太过密集了吧,我定定地望着操场上的那些矫健的身影,男孩子们,我所喜欢的男孩子们露出了健硕有力的大腿,在奔跑,像踩在我的心头,沉重而有力,我多希望其中有弟的影子,我在梦里一再见到他,还是毫无杂念的小孩子的样子,可是我已经到了用舌头去舔,去碰男孩子牙齿的年纪了。
弟越来越不像话,他酗酒、抽烟、打架、找女朋友、夜不归宿。他像个桀骜不驯的小流氓隔三岔五地出现在街头。爸爸悲伤极了,从没见到他这样难过,每个黄昏,他都站在阳台上一声不吭地向外眺望,他希望看见弟。
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弟的生日,家里照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爸爸还从蛋糕店买回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全家人都等着他回来吃晚饭。后来,爸爸挥挥手,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榛,吃饭吧,别等他了。”
我不肯吃,硬撑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头也不回地出门,下楼,一来到大街上,我就再也抑制不住了。我边走边哭,毫不顾忌路人见到自己的失态,即使是掘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到。在路边的投币电话那儿,我不停地投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拨出去。午夜的时候,我敲开了郊区一幢平房的门,弟只穿着一件裤头,赤裸着上身,见到我的一瞬间,脸上的表情异常古怪。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并且脸庞浅浅地红着。弟弟忽然意识到什么,折回去加了一件平角裤,再次出现在门口。
“弟,我可以进去吗?”
他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犹豫了一下,有点无奈且厌倦的样子,“好吧。”
是一间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狭小逼仄得可以,除了放下一张大而凌乱的床之外,似乎再也放不下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墙上有玛丽莲·梦露的黑白招贴画,性感得活色生香。床上有一个女人,眉眼单薄,眼梢的地方流淌出淡淡的妖媚,有一点像“鸡”。可明显还是未成年的少女。床下有一大堆纸巾和两个用过的避孕套。
弟对躲在被单后的女孩说:“这是我姐。”
她如临大敌般地笑了一下,很小的声音叫道:“姐。”
弟说:“你走吧。”
这是弟的朋友租住的房子。
那个女孩走后,我问他:“怎么不是你的第一个小爱人了?”
弟说:“早就吹了。”
我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他漠不关心地追问。
我忽然有点心疼。
“弟,你该回家了。不能把日子这样过下去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似乎并无反应,淡定地“哦”了一声算作回答。
我想我是疯了,劈手夺过弟手中的烟。叼在嘴里狠狠地吸上两口。在弟瞠目结舌的时间里,我把半支烟抽成一小截烟屁股,然后狠狠地掐灭。我被呛得头昏脑胀,直流眼泪。
我说:“你不是疯吗?不是放纵吗?那让我们一起来好了。”
我拥住弟,把滚烫的嘴唇递给他。他慌张,毫无准备地喊我“姐”。我停下来,对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叫我榛。”
他顿了一下,用陌生的目光打量我,试探地叫了一声:“榛。”
——这是我的“第一次”。交织着犹豫不决。彻骨的疼以及泪水,我濒临死亡般地绝望地抱住弟,木然地承受着来自他的重量和抽插。他伏在我的身上,终于像个孩子对我讲害怕。
我说:“你害怕什么?”
他说:“榛,你知道吗……”
“什么?”
“其实,我一直……”
我用一只手掩住他的冰冷的嘴唇。
他埋在我的身体里:“我觉得自己在犯罪。我在乱伦。我一直在警告自己,这是不可能。我们是姐弟。可我还是不能克制地想你。所以,我才会肆无忌惮地出来疯,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拯救自己。没有人可以帮我。”
我说:“不是的。弟,我从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你,就想把你带到身边,看着你长大,到这一天……”
他含着泪,颤颤地叫了一声:“榛。”
除了紧紧拥在一起,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对抗命运的姿态,可拥抱这么难,非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我看着弟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想知道他如何生出这样英俊迷人的面庞。我一再地鼓足勇气,试图问他“你喜欢我吗”。可自始至终,我也没有说出口。并拢的双腿间,有暖暖的东西在流淌,是血。
有时候,我想,我也许宁愿选择继续站住,接着站下去,依然站着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