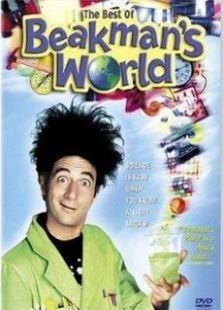编者按:
作为位于欧洲最后一道大师之堤的电影诗哲,安哲罗普洛斯以其作品的舒缓悠长,兼具大气磅礴的历史深度与清醒深刻的哲学气息,深受国内数以万计的影迷所爱戴。这位在世的大师一生囊括柏林、威尼斯、戛纳、萨洛尼卡、布鲁塞尔电影节等几乎所有欧洲电影界殊荣奖项,以自己的作品对20世纪的希腊电影、欧洲文艺电影进行定义。陈凯歌、贾樟柯等国内导演亦曾坦承自己曾受安哲作品影响。2010年春季,安哲热潮再次席卷中国。几乎同一时间,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为安哲罗普洛斯特设纪念影展单元;而内地电影图书重镇北京世纪文景,也出品了华语世界第一本全面论述安哲罗普洛斯的原创性研究著作《尤利西斯的凝视:安哲罗普洛斯的影像世界》。
清风徐徐的午后,“凤凰网读书会”邀请《尤利西斯的凝视》一书作者诸葛沂先生,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知名学者杜庆春先生,北京电影学院的美女导演姜丽芬女士,与青年读者影迷朋友一起漫话安哲。诸葛沂在读书会现场分享了他在写作当中的心得感悟。姜丽芬结合她的影像作品《新娘》、《乡兮》解说长镜头的魅力,而杜庆春将剖析安哲游弋性凝视的电影语汇、及其在中国的接受现实展开批判性的思考。
《尤利西斯的凝视》诸葛沂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安哲的拍摄手法解决了中国电影直面“真实”的困境
凤凰网读书:欢迎各位来到库布里克书店参加“凤凰网读书会”,本期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我们将一起探讨电影大师安哲的镜头极其背后的隐喻。无论是对于看电影的人,还是安哲的影迷,都具有意义。今天的嘉宾有著名影评人,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名师杜庆春先生,有曾受邀参加过柏林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颁奖礼、获得意大利远东国际电影节十佳影片奖的姜丽芬女士,还有本书作者诸葛沂先生。
杜庆春:大家好,今天我们借《尤利西斯的凝视》一书来谈下世界电影大师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艺术及其当下反思。首先,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出现的费德里科·费里尼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建立在一种写实的情况下,非常主观的一个领域,非常内心化的手法去创作,不是去表现一个完全写实的、对某事件的拷贝,而是通过时间和空间延续的使用来展现。但是安哲罗普洛斯用这种方法表现的整个主题却和费里尼、安东尼奥尼非常不一样。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也只是说去表现现代的身体的禁欲或者说欲望的状况,但安哲罗普洛斯把这种方法拉回到一个很庞大关于希腊历史、现实的叙述和表述过程中间。它表现一个个体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虚拟状态,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他的作品有很强的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东西,带有很强的社会面,一种时间性的思考。这是和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非常不一样的。
安哲罗普洛斯对长镜头美学,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是什么?或者说他在1990年代中期被中国电影人发现,被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电影人发现之后,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共鸣?长镜头将安哲罗普洛斯的主观性更往前推了一步,因为长镜头带有一种很强的隐喻性,甚至是通过一些隐喻性的产品出现。比如说,他通过天上出现下雪,古希腊雕塑的残肢被吊起来等等这些产品,来强化隐喻性的色彩。另外一个对电影人更大的冲击是,他开创了一种(风格)--当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导演试图做这个突破--即,当我们的镜头不做切换的时候,镜头内部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能够突然发生改变?也就是单镜头内部的时空转换。这也是安哲罗普洛斯给很多电影人带来的非常强烈的冲击。
因为我们说电影的记录本质上是一个单价值的,这个镜头拍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东西的此时此刻,不可能说那个东西一会儿是80年代,一会儿是90年代,一会儿是2000年,你拍唐朝的时候,那就是唐朝时期,这个镜头前一半是唐朝,后面变成北京了,这个很难做到。除非你用大型旋转舞台那种方法来做。但是安哲罗普洛斯却试图来做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不通过大型的美工的方法来改变的。他就像一个人在一个镜头前能够自由地穿越这时空,让一个现代人慢慢可能就变成了100年前的样子。
这样就带来了非常强烈的主观性和诗意,这是非常有趣的东西。1990年代中期,大概是1995年左右,北京电影学院在自己内部的教学参考里面就引用了安哲罗普洛斯的材料,我们都看到了安哲罗普洛斯的介绍,其实绝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他的片子。大概引入了一、两年之后,通过台湾的录影带大家开始看到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我觉得对当时正在学校学电影的人,是有非常强烈的冲击感。当时我们把他看成是在遥远国度的艺术的偶像。
随着时间到了1997、1998年,电影学院学电影的人离开电影学院,当然,我留下教书。最著名的是贾樟柯的作品,明显是带有这样一个产品美学的特点。这其中有两块东西起作用,就是当年在学的时候,一个是安哲罗普洛斯,一个是台湾的抠像系统,对他们的电影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两个东西对当时体制外的独立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首先,去做创作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其次,医疗物质、技术条件等等都非常简陋,面对这样一种简陋的状态,其实写实长镜头是一种救赎,因为(这样)他(还)可以做电影。如果我技术很差的话,我想拍一个好莱坞电影是不可能的,但写实还是可以拍的。另外,写实主义对独立影像来说是政治正确的。对电影,大家都说不够真实,那么写实主义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因为我是在面对中国的现实。
要知道对我们那个时候来学电影的人,这其实是非常大的问题所在。我们是作为艺术青年进入电影学院,而那个时候电影学院也是标准意义上的(艺术)院校,我们在内心当中其实很难把纪录片性质的写实主义看成是美学性、艺术修复性的,(因为写实主义)那个东西太简陋,太直接地去面对现实。那么它的审美性来自哪里?这是一种很大的痛苦。当我有一台便携式的摄影机,去面对一个完全没有加工的现实的时候,我的美学修养体现在哪里?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问题。通过这一点,可能大家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长镜头美学被这么多的电影人拿过来了。我有这样一个武器,我可以找到所谓的审美性。我用很简单的设备去拍一个未加工的现实的时候,我依然可以表现出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所在。我不是这样拍像家庭影像那么粗糙(的作品),我还有一种艺术家的审美性在里面。这非常重要。
在这一点上我们改造了侯孝贤和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头美学的实质,我们用长镜头美学来包裹着一个艺术心灵,不可磨灭的那种艺术追求,然后又用它去面对那个现实。这里面当然会带来问题,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可能是假的,我们的长镜头也可能是假的。后面如果有时间我再跟大家来讨论。
我先开始用很快的速度介绍了安哲罗普洛斯长镜头美学的基本状况,也介绍了我所了解到的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美学和中国电影人创作的一个连接的基本状况。下面有请诸葛老师来出场。
中国电影需要“拿来”和“送出”
诸葛沂:大家好,我是《尤利西斯的凝视》这本书的作者诸葛沂,前面杜老师已经说了很多关于长镜头在中国的影响等话题。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希腊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可能在中国有想去写一本关于安哲罗普洛斯书的人,可能不到十个。由此,我自己感觉很纳闷,我怎么会写这么一本书出来?这本书是我在07年的时候写出来的,但我觉得这本书是迟来的。就像杜老师所说,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电影了,但是我们关于对他的阅读,对他的批评,包括西方对他的评论,包括他自己的评论,他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电影,以及西方怎么来看他的电影,又如何带动了西方电影心灵的一种转向?我觉得这些都还没有移借过来。
有时候我回想到鲁迅先生原来写过:“拿来主义”还是“送出主义”?我们拿来的过程都还没有做完。我们还有很多“拿来”的工作要做,这时,我觉得很多事情也要“送出”。当时可能默默无闻的在那边写,也没有几个人会给你一些支持。这就是我写这本书(时的状态)。
刚才听杜老师所说,包括我们中国现代的导演受到了来自于西方、欧洲电影的这些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当时中国的这些导演们可能也有人找到一个途径,觉得长镜头是可以不要用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这样看的,我发现也有一些电影人或者是读者、观众,他会有一种潜在的想去钻研、研究一下或者是想知道,(安哲)为什么想要用这个镜头语言,可能性是怎么诞生的?
我当时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在大学里没什么课,我刚参加工作,20几岁,整天就在家里,工资可以糊口,每天就是看片。安哲的电影,你看得时间久了,会感觉有一点难受,为什么?有些电影时间太长了,像《流浪艺人》,会有四个小时。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写了一篇关于安哲的日志,说这个受不了,看到一个小时后他就已经睡着了,两个小时后他就开始骂了。所以现在我回想写书的那个过程,觉得其实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沉浸在整个环境当中,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看到书中配出这么好的剧照,这个太棒了,可以给学生看看。
当时没有太多的条件,我搜集了很多的书,国内能找到的是法国有关于他的一本书,台湾也曾经出过一本,但是这本书是法国人写的。关于他的外文著作也不是特别多,英国可说的著作有两本,谈话录有两本。我必须通过很多的渠道,才能把它搞到手里:亚马逊、北大图书馆,想方设法把这些书都拿到。我觉得我没有达到可以批评他的程度,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在这本书里语含敬畏。确实是这样,当时就带着这种心情在写,所以尽量找到更多的资料。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在浙大,一个研究生也想做安哲罗普洛斯,在杭州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些东西,虽然可能人不会很多,但是我们会凑在一起讨论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别的目的,也没有参加太多的活动,但是我们时常会来讨论这些东西,相互交换资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安哲罗普洛斯访谈录逐条逐条地看,每一条我都会事先翻译过来。我会去体会他自己怎么样看他的电影,他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镜头语言。包括他为什么要拍一个系列的电影。他说过这一句话,他一辈子就拍了一部电影,现在这部电影还没有结束。他说如果要是去世的话,他希望是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去世。其实他说这句话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拍电影了,但是现在他最新的一部电影出来,还是延续了他的那种风格。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镜头更为清晰,我感觉这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大陆没有人认真写安哲的电影
诸葛沂:很多资料拿过来以后,就开始看(关于)他的书,包括台湾出的那本,看完之后我再去搜集中国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著作,发现很少,几乎就没有。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可能这个工作我可以来做,是怀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首先是初稿,后来又经过编辑提出的很好的意见,我们又修改,修改以后得以更为体系化。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度理论化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观看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时,有些东西是看不懂的。不知道在讲什么样的故事,或怎么样去理解它,我觉得这本书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
我觉得当安哲知道我们在这里开这么一个读书会做交流的时候,他肯定觉得很诧异。回头一想,又觉得或许他并不会诧异,台湾早就在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过。今年香港也在组织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回顾展。当我们现在再去从事创作,再去追寻一些(新工作时),可能需要人们很好地看一看前人走过的历程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许适逢其时,它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还有一个(可谈之处),我觉得他使用这些语言时,可能并不像我们一样,我们是在拿他的镜头语言来用,但他(自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包括他的家庭经历的时代,四几年的时候希腊解放战争--我们这边是解放战争,他那边不知道什么说法--人民战争或是什么战争。当时,他自己的家庭也经过了一个颠沛流离的过程,曾经他和他的母亲在尸横遍野的郊外,去寻找他父亲的尸体,在尸体堆上翻来翻去,结果没有找到。后来突然有一天,爸爸回来了,在一个下雨天,这样的场景一直呈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也就是父亲的归来。
姜丽芬老师曾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安哲罗普洛斯是在用诗歌影像语言来写作的一位电影诗人,同时又兼有哲学的深度。所以我的工作可能只是让安哲罗普洛斯跟中国的读者、观众见了面,或者说跟中国的观众有了交流,有些人可能从中发现了一点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是迟来的。它对于安哲,对于我自己都是一个迟来的礼物。这是我想说的关于写作这本书的过程。
下面,我们请姜丽芬老师来谈谈对长镜头的看法。我看过姜老师的电影,非常的好。因为她不是完全引用或者是直接使用了长镜头这样一种语言,它有一些语言背后的文学、艺术,以及一些情感层面的东西潜藏在当中,这要请姜老师来谈谈。
安哲的拍摄特点是对时空的诠释
姜丽芬:大家好,大概两周之前接到邀请,有这样一个读书会,要谈安哲罗普洛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无论什么时间去谈论他的电影和创作,我个人都是带着一种特别敬畏的心情。怎么讲呢?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是学习导演的,大概是在2003年时候开始了我做导演的创作,从此,我就对长镜头美学产生了一种特别浓厚的兴趣。我拍了两部长片电影,一个短片,也都是延用这样一种电影美学来做的,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对长镜头美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一种理解,或者说诠释的想法。
我第一次接触到安哲电影的时候是《永恒一日》,然后逐渐看了《雾中风景》,从他一些早期的作品,再到最近的作品。我个人觉得因为在20世纪电影史上的大师影像中,其实用长镜头美学来做影片的非常非常多。像日本的沟口健二,还有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另外像塔尔科夫斯基,我们中国的侯孝贤、贾樟柯,等等。这些都是世界知名的导演,他们都是用这样的电影美学来拍电影。我个人觉得,对于现在的电影语言,你要么就选择蒙太奇,你要么就选择长镜头美学来拍。因为我不是做理论出身,所以我可能是用自己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谈安哲的电影,我觉得如果将安哲的长镜头和其他一些电影大师的长镜头美学来比较的话,其实安哲自己也谈过,他也受到像日本的沟口健二这样的大师的一些影响,主要是在他的电影语言当中。
我个人觉得他的影像,在很多长镜头美学电影导演当中,也很有它自己特点的。现在说起来那么多导演在做长镜头,这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事情,包括很多年轻新锐导演都是这样来拍。我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一部长片和一部短片,一会儿和大家来交流一下长镜头美学。我个人觉得安哲罗普洛斯从他年轻时候接触电影、学习电影,一直到现在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电影大师,他的这一切,不是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们之间的距离很遥远,我们只能通过他的影像去理解,看待他的人生,看待他眼中的世界。安哲的长镜头最大的特点是他对时空的一种诠释。他做得一贯到底,他用一生的作品在做这件事情。这是他毫不犹豫的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然他永远是那样特别高贵的影像,还有他诠释的历史、文化、民族等等很多的工作。
凤凰网读书:三位老师都怀着对大师尊敬的一种心情,讲得确实都比较低调。可能喜欢安哲的影迷,生活当中也是比较低调的状态。因为喜欢长镜头的人,其实都会有一点闷,但是这种闷当中,带有着一种有质量、强度的沉默。下面姜老师也许可以结合影像来讲一讲,然后大家再进行互动。
姜丽芬:我说我自己拍了长镜头的片子,其实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在谈安哲罗普洛斯,我只能说拿出我的创作长镜头的感受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提出意见和想法。我先给大家放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2005年,正好中国电影百年,请了八位年轻的导演,每个人拍一个三分钟命题电影,用三分钟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你自己来创作,但是给了中国电影百年这样一个命题。当时我拍了一个故事叫《新娘》,我就是用一个长镜头把它拍下来。
(《新娘》播放)
姜丽芬:我简单说一下,大家应该都看清楚了,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即将跨出闺房门的新娘,想起了她当年的男友,然后她背后站着憨憨厚厚的丈夫,最后她前男友来了。我刚才谈到安哲的长镜头,其实是对时空的把握,我个人觉得安哲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具有特质和特点的,我也毫不掩饰的说,我深受他的影响。我觉得技巧的东西实际上学来是有益的,怎么做,怎么变化,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学一学,我个人觉得不难。但是这样一个长镜头美学,如何来诠释我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感受,我的文化教育和历史背景,我的故事。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在做长镜头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内在的节奏,这个节奏是他个人独有的。我拍这个的时候,还不太成熟,因为时间也比较仓促,只有两天时间拍,我排练就排了一天,后来拍摄的时间,整个光线的变化的控制,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在看起来,如果说还有机会再拍的话,我可能会更成熟一点。
但是艺术当中这些冒出来的东西,我知道只有在那个瞬间有,现在也就没了。全场长镜头的语言运用,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当时这个活动说是中国第一部手机电影,要放在手机上播,所以不允许你超时,也不能太短,规定你至少两分半,三分零五秒就容不进去了。从喊“开机”到喊“停”,必须得卡在三分一秒或者是三分两秒,前后掐头去尾刚好卡在那个时间。所以这个故事的节奏,必须是卡在这里,这给当时拍摄带来了难度。时间紧。再有,大家刚才看到,小伴娘一甩过来的时候,现场是一个婚礼很喜庆的场面,很多人,然后屋里所有的摆设都是很光眼亮丽,视觉感很丰富的。但是这个镜头再过来的时候,就变成很肃静的感觉。这个变化,实际上所有在现场拍摄的人,都觉得像打仗一样,这些人一开始很高兴的在这里演着,然后我镜头整个出来的时候,所有人安插在哪个地方,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我自己做过这个事情以后,再去看安哲这一生的电影。我们看到他的影像永远是在雾里、雨里、雪里,或者说是特别恢弘的场景里面,有多少人的控制,我们现在看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实际操作是非常非常艰辛的,而且要等时机的。大家都知道希腊是一个非常阳光明媚的区域,但是偏偏安哲的影像里面是那样的肃静,那种调子有点冷冷的,很宁静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谈一谈。
每一个镜头都是磨人的等待
读者:姜老师,因为您拍摄一直是在做长镜头的方式来进行,让我们想起曾经看过黑泽明先生助理野上照代女士的一本书《等云到》,其实是说电影作品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要等特殊的光线,特殊的一个天气,可能大家就会用悠闲的心态去等待那片云彩从山坡那边过来的时候,但是可能实际在拍摄电影当中,这种很悠闲的状态并不是常常会出现的,尤其是在长镜头这种大的调度和安排中,肯定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故事。您在拍摄过程当中有类似的故事吗?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姜丽芬: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到的短片,大概是拍了七遍,第七条时,等到我跟摄影师说OK,就这样了,就可以了,当时是五月份,窗外一阵暴雨就下来了。你要晚一阵,等十分钟就没了。我还带来一个长片,那个长片我拍的是黑白的,我们再谈一下黑白的影像。
安哲的影像即便是彩色的,它也是将整个颜色都滤调,或者是做的特别安静,颜色非常简单,都不会是特别绚烂的色彩。我第一部电影是胶片拍彩色的,第二部电影就把它做成黑白的。而且第二部影片我全片是做的34个长镜头,全部是黑白的,我个人觉得一下进到那个里面以后,精神气质就出来了,你想要的东西、内部世界,可能就更容易凸显出来了。但恰恰越是黑白的越难,而且长镜头语言大家都知道,像安哲的影片影像总是360度,或者再来一个180度,他带到的范围(非常大)。我后面做了一个长片,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像我个人我做完第二部电影的时候(非常疲劳),肺部严重的感染,因为在现场要控制的东西太多,拍摄镜头360度可能已经转了280度了、290度了、300度了,就差一个角,突然出了一点意外,然后,你就得停止,得重来。
我们可以看到开片的第一个镜头,我希望演员悄悄地从雾蒙蒙的早晨走出来,那个雾,拍了两条就没了,阳光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所谓的“等”就是这样,你望着这个天气,没有办法,只能说等待来日,而明天是什么样的雾(也不好说),因为江南的天气十月份也是挺秋高气爽的,那个等待之后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好多东西有时候是天赐。你觉得真是天公如果给你作美,能比你想像的还要好。天公没有太配合的时候,你就达不到你那个(想法)。其实拍长镜头影片,导演这方面就是要有最大的耐心去等待你期待的那个影像。
读者:刚刚您放这部电影中的长镜头里的东西,跟安哲的也不太一样,安哲罗普洛斯有一部电影叫《鹳鸟的踟躇》,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他的长镜头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他那时候只是把镜头放在卡车外面,然后一个小女生被野蛮的拖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交代,也没有任何配置和声音,唯一的声音就是高速公路上面车子的声音。其实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压力,这给了我们很大想象的空间。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安哲罗普洛斯的地方。所以我想了解,您刚才说那个长镜头的方式是导演调动很多人的情绪,因为他不停地在等,可是我所理解的长镜比较像是他把你带着跟他一起去感受那个时间,这一分一秒地过去,比较像是两者的一种沟通。我比较想了解您关于这个区别的想法。

姜丽芬:你刚才谈的是使机器固定拍摄,让观众没有看到实景的东西,但是你完全能明白这里面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其实长镜头,有固定长镜头和运动长镜头之分,今天我给大家放这个是用运动长镜头来表现的,当然我个人也很喜欢不要更多地去解释这个东西。长镜头的魅力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就是让大家跟着一块去进入,一块去感受,我在设计这个故事的时候,要三分钟之内表现出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选择了运动长镜头的表现方式。在我带来的长片里面也有完全是固定(的长镜头),一会儿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尝试实际上在我的创作里面也有,更多的是在试。
另外我想谈一点,我觉得安哲里面有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就是你看它的运动都是缓慢的,实际上它镜头内的张力是很大的。有的时候他带出历史、人文、生命,带出很大的事件。这些张力是在镜头的结构里面解决的。每一个导演拍长镜头都有不同的对长镜头的诠释、把握和理解。但是对于美学角度,我个人觉得是一种非常有魅力并很吸引你去尝试的一个方式。
艺术家不要消失掉对生命、社会、人生的追求
诸葛沂:刚才你说卡车那一幕,让我很有亲切感。那是《雾中风景》你的镜头。你说到这一点,让我突然回想到我当时看电影,同时在写作时的那个过程。你觉得它虽然是固定的一个长镜头,但是它给你一种压迫感,或者是沉默当中的力量感,这既是按照他与生俱来的很稳定的思维,同时他又很直面这个社会或者生命当中碰到残酷的现实,他没有回避掉。有人说艺术是生活的缩影,其实可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是在那样一个世界沦陷的,或者说在那样一种状态下受到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一旦你进去以后,看到那种沉默的力量,我们是感同身受的。
所以,你说这种感触我觉得很亲切,你看到这部电影最本质的一些东西,我认为在《雾中风景》里面,两个小孩子实际上在表现两种不同人生的道理。电影里的姐姐其实受尽凌辱,一直想追求一种东西,但是她没有得到,包括她很喜欢那个男的,她希望救赎。弟弟是扮演一种救赎者的身份,包括他看到那人在雪地里打滚,镜头里他做的抚慰的动作。其实他给你一种遭受凌辱后,你去救赎的启示。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电影,可能不能就电影荧幕上呈现的去理解,有时候你要了解他哲学的思想,要了解他文化的背景。
实际上安哲罗普洛斯很喜欢文学,很喜欢诗歌,包括希腊的历史、神话,再如很多其它作品,一些古希腊留下来的历史著作给他带来的影响,同时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无论我们讲长镜头语言,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利用长镜头语言,是固定的,还是运动的,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不要消失掉自己对生命、社会、人生的一种追求,这才是最重要的。维特根斯坦讲:艺术就是谎言。虽然他说的是一个谎言,但是有真理推出来。
杜庆春:这个问题提不是一种东西。但是安哲罗普洛斯的作品里面,其实有固定的长拍,也有移动的长拍,所以安哲罗普洛斯用了两种长镜头,我觉得长镜头的区别不能是运动,还是固定。运动的和固定的是两种,也许是一种。我觉得根本不在于这些。我讲几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其实是戏剧性的。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头首先是很强的戏剧性需求。他们传递出来的那种叙事性的力量是有叙事性的需求。
第二个是隐喻性的东西。这个隐喻性在安哲罗普洛斯里面有一个必然的维度,这个维度是说在镜头里面有种很大的历史,所以说他的这个长镜头,不管是固定,还是移动,他都试图带出一个历史维度的问题。这个历史维度到了某种形态,变成时空的一个转换。
还有另外一种长镜头,我觉得完全不是这种风格的东西。它是一个永远记录单向性的东西,所以我哪怕拍一个历史片,其实我关心的也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单向性,其实侯孝贤也是这种。侯孝贤也经常使用长镜头拍摄,但是他是了解单向性的。实际上,那里面的隐喻性和镜头内部的时间维度不重要,我是说镜头内部时间是不是能够和一个历史事件(相联)。比如说《悲情城市》,它本身是表明一个很大的历史跨度的事情,但是每一个镜头诉求、镜头内部的历史跨度,已经到极致了,固定长拍已经到极致了。但是单个镜头内部,依然是一个单向性问题。这是对单向性记录强烈的需求,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静静看着这个世界的此时此刻的心态。
我讨厌盲目崇拜大师的人
杜庆春:我刚才前面留下了一个话题,就是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大陆像贾樟柯等人来使用长镜头的时候,非常有趣,他们很多时候是用移动的过程来完成侯孝贤式的单向性记录。就是说他们在这里面“搞鬼”,把两个东西一块使用。即使这样,在中国,我看到的华语电影里面是很少呈现出来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导演都不愿意做,因为它的技术太外化了。如果你里面的时空转换维度,这个历史的维度打得不透的话,它就完全成了一个炫技,这是个技巧。摇到这儿变成一条鱼,再摇过来是一个现实,再摇过去又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时间的维度没有足够强,(没有达到像)安哲罗普洛斯这样的历史隐喻性的话,这种做法会让人感觉太害怕了,就是你技巧太外露了。但是像贾樟柯,不管是《世界》还是《三峡好人》,他都不采取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会让人害怕。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这非常有意思,安哲罗普洛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因为安哲罗普洛斯在精神气质上很像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经典时期。他把文化的思考奠定在一个寻根性和对文化、历史的反思性上。但是中国大陆的第五代是做一个造型隐喻系统的电影,而安哲罗普洛斯是通过这种长镜头美学来做一个在单镜头内部的时间穿越。用现代的一个词--穿越,来完成一种隐喻性的思考。而贾樟柯他们是六代和六代后,六代和六代后整个气质不是一个历史反思性的和文化反思性的,他们是非常个人史的写作和个人家庭状况的写作。所以这种东西拿过来以后,他没办法用这种方法去做安哲罗普洛斯电影的主题。
这种美学对他们来说太高兴了,它可以把自己的个体粗糙现实转化为一种审美化的表态,转化为一种诗意,所以这种美学成为一个糖果纸或者一个包装术,把自己粗糙的现实和粗糙的现实感受,直接升华为某种诗意的东西。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现在是很讨厌“诗意”的,因为这个词经常意味着它只不过是一个包装术。我刚才讲它既没有真正的让你进入写实,同时也没有让你进入一种某种意义上像安哲罗普洛斯那样巨大的历史感受中。因为这一代人不承担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的是,贾樟柯在学校里的时候,想拍的第一部作品是《站台》,然后他出去以后做的第一个东西是《小武》。《小武》成功了以后,他马上做《站台》,《站台》当年一出来,大家说这是“史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得很崇高,其实这背后是思维。其实在中国老讲“拿来主义”,我个人觉得中国电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多的“拿来主义”,而且是在历史性的层面上,在表面上修辞意义上来做“拿来主义”。比如,我们也拿来搞3D嘛。我觉得安哲罗普洛斯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在于他把整个GEO电影脉络(编者注:GEO是指英文GeostationaryOrbit的缩写,即对地静止轨道。对地静止轨道是轨道倾角为0°的对地同步轨道。)里面的东西运用出来。他在法国留学,学的标准法国电影的语言脉络。
从安哲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历史。这个历史视角是可以通过缓慢的移动带出的,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原因。为什么《小城之春》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经典性的作品,而现在很难有人在这个领域跟它比肩?除了作品本身之外,更在于拍摄《小城之春》的时候还没有转递美学的视点。《小城之春》为什么用那种拍法?它不是说我要做长镜头美学的电影,而是说,那样的节奏才符合我的情感和内在的节奏,完全是中国最古典的、戏曲式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一个节奏。这个和整个孤岛时期,人家做传统戏曲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所以,我说我挺讨厌艺术大师的。就是说,我讨厌那种“文艺青年”,因为他们喜欢大师,他们把大师看成可以去露脸,而没有根源性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电影界很麻烦,就是没有根源性的东西。电影,归根到底是看世界的东西。
凤凰网读书:杜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接着问你,因为杜老师有句名言说,拍的太漂亮的都不是好电影。我不知道你主要指的是画面的感觉,还是指整部作品做得足够完美,拍得太精致了,让咱挑不出毛病的就叫太漂亮了?你对漂亮的定义是什么?
杜庆春:我现在说话都特别不负责任,因为不负责任,所以也往往要得罪人。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得罪人。因为当老师当多了,老师要负责任,我就想我怎么不负责任来说话。我说电影拍的太漂亮的都不是好电影是什么意思呢?刚才大家讲的很明白,那片云过来了以后,我才能拍。为什么那片云过来我才能拍?是因为那片云过来以后,或者那片云走了以后,光线会漂亮,光线会进入这个空间,或者说那片云在的时候,大地上有一片阴影,它会让空间更有层次、有气氛,然后很漂亮。什么玩意儿?我们拍电影的时候要光线进来,我觉得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重要的,就像刚才我讲的,面对现实有一种审美的态度,有一种艺术修辞的修养去看这个世界。比如这个书店装修的还挺艺术的,反正我有审美,色彩搭配得很素雅,我有视觉修养,觉得读书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说法是安哲罗普洛斯的诗意只能面对他所看到的现实,但还有更大的现实,是他的“诗意”已经不能再面对了,或者说有一种痛苦是可以用诗意来承担的,而有些痛苦是超越了诗意可以承担的(范围)。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说为什么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诗意这个玩意儿,它太让你有自己有优越感了,觉得不可得到。因为现实很多的情况下,其实根本就不可以用诗意这个词来面对,比如说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优美的、慢慢的长镜头去面对这个诗意,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而安哲罗普洛斯恰好是用他的那种方法去面对痛苦,他是很痛苦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哲罗普洛斯在很多情况时是在(属于)现代之前的,所以这几年中国的独立电影创作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和可能,可以摆脱诗意的长镜头。新的一代人,可能需要一些新的表达方法。另外,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中国现实已经不是小“我”的那种现实,你再用诗意的长镜头去面对的时候发现很困难。如果你拍一个人出去,然后砍小孩,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不是可以用诗意的写实性的长镜头来描述?安哲恰恰不是写实出名的,我们在突破这个东西,就是把长镜头美学的诗意和莫名其妙的这种混合体在更深的程度上突破,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电影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去做的。
长镜头不能承载现实的所有残酷
凤凰网读书:通过不负责任的杜老师不负责任的言论,让我们感到杜老师还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只不过他的责任感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面对不同的内容,可能要有不同的美学方式去表达。杜老师讲的是,有些东西不是说拍出来很漂亮就对了,可能是需要用其他的方式拍得更有力度一些。
诸葛沂:我有时觉得长镜头未必都是诗意的东西。比如说跳楼、砍人等社会事件,难道我长镜头拍出来,一定是诗意的?好像也未必如此。最重要的不是你用了这个镜头或者那个镜头。我写安哲时有一种状态,我在家里,生活节奏和安哲一样,整个都是慢动作,每天跟人接触也少。这可能是类似一种诗意的长镜头状态。但是,当我们思考,为什么总是有人跳楼,不断有砍人事件发生?为什么地球现在变化这个样子?这时,未必说我的语言就一定要用一个长镜头来表示诗意,它表现出来或许是残酷的。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老师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杜庆春:我是说,中国太多的创作者用长镜头的一个很大的出发点是觉得它很“诗意”。我没有说长镜头一定很“诗意”。比如说闭路监视系统,它无休无息在记录状况。如果你把它当一个实验品的东西,你会认为它是诗意,否则你不会认为它是诗意。但是为什么中国目前有太多的创作者愿意说,我用长镜头,证明我有诗意。这个问题在慢慢发生变化。当年为什么我们要诗意?是因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用长镜头和诗意,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纪录片因素。当年,纪录片也是体制外的。现在中国的纪录片,已经了不得了,每年的国际上纪录片大奖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拿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这点事,你拿进去拍就能得大奖。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漫长的长拍,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实验的东西。比如说安迪·沃霍尔拍的《帝国大厦》,那个东西更惨,一个机器搁那拍八个小时,什么都不动,带子没有了,换带子,我们在那儿喝啤酒,等着,拍完走人,这种东西,算是实验一下。但是纪录片运动和实验运动,在中国基本都是漫长的缺席状态。就是所谓学电影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依然想--我要成大师,拍电影就得去戛纳拿一个奖。比如一个导演回来就说,哎呀,今年我在电影节上遇到安哲罗普洛斯,跟他合影了。另外一个导演说,什么呀,你没有去的时候我就跟他合影了。我们应该明白这种意思了,我不愿再多讲。
那么,有的长镜头就被搞成那样了。比如《三峡好人》,那种现实是可以用诗意的长镜头。但那么面对,大家觉得足够吗?我觉得那种现实肯定不是三峡的真正现实。它成为了我们电影(的一个借口),我们可以不那么接近现实的一个借口,而我又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我是艺术家,我要搞一套美学出来。我觉得,麻烦的事情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说长镜头一定是诗意的。
镜头长不是“长镜头”
姜丽芬:我要补充一点。刚才两位都说了对长镜头的诠释。我个人觉得,比如,一个小区有一个投影,就是一天24小时记录,或者说安迪·沃霍尔拍这个《帝国大厦》。这个镜头的长度,我个人认为是镜头长,而不是长镜头,在我看来这是有区别的。因为电影语言里面的具有一种时空的变化,像我无论用固定长镜头,还是运动长镜头,里面都有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像侯孝贤,有的时候,他也会把镜头非常的凝固、静止在那里。但这个里面,它有蕴藏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片子,叫《蓝色》,好像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银幕上一个蓝屏,然后全部都是在一个画外音在叙述,当然我觉得这是先锋、实验的一个做法。
但是你说我们三个人在做这个读书会,然后有一台机器放在这儿,把我们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你觉得这能称之为一个长镜头吗?这不是。我个人认为,无论是运动,还是固定拍摄,都还算是长镜头的一种表现方式,只是两种不一样运动的方式而已。在我带来这个长片里面,也有固定长镜头,它是在一个车里面拍摄的,机位整个是固定的。这部片子的34个长镜头,除了2个固定的,其余32个全部都是运动的。
还有一个关于技巧的问题,我也想说一下。我是看费里尼的长镜头,看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头,而产生了某种理解。最后我用长镜头美学来表现我的影片。但我自己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不可能说先把这个运动和调子全设计好了,或为了这个技巧而去写了这个,那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剧作在前,剧作完了以后去选景。选完了景后,我想,在电影美学里面,这个形式是一定要遵守了。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当然有这样一个想法,希望用长镜头美学来表现。但是每一场戏写出来以后,落实到真实的场景里面的时候,比如说对于这个家的描写,是文字。然后我到了现场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会感受整个的气场,我的状态,怎么走,怎么来表现,包括时空的运用。其实有时候,写作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我觉得,(用长镜头的方式)比我去分切,用蒙太奇的手段来组织起来,可能在我看来,我的内心感受会更深,更难过。所以,这是拍这样的电影的时候,我的内心的感受,而不是说,我早就已经要用这个技术、技巧,一定要超越什么东西,全部放在这个上面。
凤凰网读书: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姜老师的《乡兮》片段。
姜丽芬:这个是影片的结尾部分。
(《乡兮》播放)
好电影要融入导演的个人情绪经验
姜丽芬: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三个长镜头,第一个是说,这个故事里的姐弟两人在北京上学,然后工作,父亲突然病故,他们返回家里奔丧。这一段,是这个女儿对于小时候生活的感受。
诸葛沂: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把三个镜头一气看下来,在创作过程当中,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你当时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这不是一件很讨好的事情,你是怀有什么样的情绪做这样的东西?
姜丽芬: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个人生活的阶段的感受。其实,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一日》给我带来很多影响。《永恒一日》是说一个小孩和一个老人的故事,时间上,他有的时候把这个人的一生,(当成)就像一天一样。真的是瞬间,时光就这样流逝过去了。我在写剧本的时候,突然觉得生活已经走到了这个时间段,或者说这个年龄段。我是93年到北京来上大学,再过三年,可能就20年过去了,这20年对我来说,也真的像是一天,或者一瞬间一样,我没有太多去回味。所以,这个剧作就通过镜头把我从懂事起,我感受到的,我的生活、生命里,所有周围的一切都融入进来。比如有一场奔丧的戏,它就是这样的气场,这样的声音、感觉。当我写到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种痛,但是单独看这个长镜头是不会有太多情感的感受,没有看长片,很难从感觉上去理解这个东西,你现在只是看到了几个简单的镜头。这几个镜头中,最难的就是拍摄奔丧场面。大家都知道当地的一个奔丧的习俗,他们都是普通人,完全没有感觉你们在拍电影,因为平常就是为人家在奔丧。你跟他去讲,我要这个里面诸多的控制,怎么做,最后一个情感怎么呈现出来。他不管,他只管你说要我把这个棺材抬起来就走,走多远,走那儿停,他只管这个。所以,我这场戏只拍了两遍,拍完以后,我看了一下回放,当然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就说,OK,就是这样了。我要的东西,它已经在里面了,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理解。
凤凰网读书:今天,我们共同分享很多感触,既有以一种宏大叙事的角度去考虑一个电影人应该去表现什么样的内容的问题,又牵扯到一个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段去表现需要表现的内容的问题。但抛掉这些理论性的问题不谈,我觉得在实践上,像姜老师拍的作品,有一点是和安哲在精神上暗合的,就是返回到自己的人生、生命的体验当中,去感受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或者说自己和自己背负的一段回忆之间的关系。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活动已近尾声,最后我想向三位嘉宾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看安哲的电影,其实是一件很辛苦,也很奢侈的事情。因为需要拿出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充沛的精力才可以看。如果能够给你只看一部安哲电影机会的话,你们会选择那部电影?
姜丽芬:我会选择《永恒一日》,我觉得看那个片子,我很有感受。
诸葛沂:最早打动我的是《流浪艺人》,可能我会跟学生看。但就像你说的,太奢侈,要有时间。
凤凰网读书:好,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我们的“凤凰网读书会”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每一位来宾的到来,因为在这样的天气聚在一起享受一下午实在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谢谢大家,再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