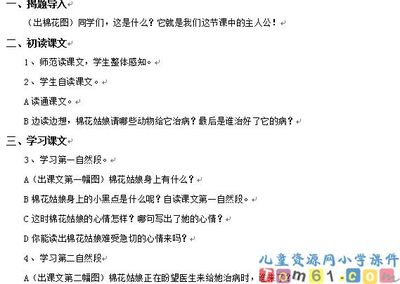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我为什麽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己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於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兄弟三个,孤苦伶盯,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於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日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麽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後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後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於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祥,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
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信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仅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恐怕要成为永远的谜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黄的),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
“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建在。家境依然很好。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打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麽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麽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乘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己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後,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於是就大块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灾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
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後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内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於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侍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於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麽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後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拿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
“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麽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呵!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於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侯,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麽名誉,什麽地位,什麽幸福,什麽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永久的悔——摘自张光璘《季羡林先生》
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母亲在家乡病逝。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
他从六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亲,可是,现在还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便永远地去了,怎能不使他悔恨万分呢?
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在家里,守候在母亲身旁,有时也到村子里走走。他“看见院子里的树上,有母亲亲手砍伐的痕迹,在被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母亲吃饭用的饭碗,随时用的手巾,都留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上每一块砖上都印有母亲的脚印,不觉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夜里,他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念儿子时,不知流过多少泪,不禁又泪流满面,泪水沾湿了枕头,彻夜难眠。
他不断地责备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母亲?为什么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荒僻穷困的村子里?为什么八年时间没有来看望过母亲?他感到自己实在愧对母亲,无地自容。他狠狠地责骂自己:“我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回忆,内疚,自责中度过。他感到,随着母亲的死,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空虚和冷寞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感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空白。自己整日像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
下葬的日子到了,别人给他穿上白布袍子。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一个人东走西走,跪下又起来,泪眼里看见来来往往的吊丧的人,感觉脑子有些麻木。突然,看到一群人去抬起母亲的棺材,这时才醒悟到真的要和母亲永别了,顿时嚎啕大哭起来。”以前,母亲的棺材放在屋里,母亲虽然死了,但只隔着一层棺木躺在里面,他每日陪伴着母亲,心里还稍感安慰。现在母亲将要埋到永恒的黑暗的地下去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想去阻拦抬棺的人,但人们把他拉开了。他糊里糊涂地跟在抬棺人群的后面走着,绕过了熟悉的大水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墓地。他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然后是下葬,填土,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个土包,他又被人拖回到家里……整个下葬的过程,他脑子里都是空虚和麻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任人摆布。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尘封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棺材,空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屋外小院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墙头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阴沉的秋天的长空变得更黄,更黄。他心里感到无限的落寞和寂寥。
第二天他便离开故乡返回北平。临行时,他回望官庄,“在云天苍茫中,触目的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
回到北平以后,他仍然日夜思念死去的母亲,常常在夜里醒来,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l933年l2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
l934年5月3日日记写道:
因为想到王妈又想到自己的母亲。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时间,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
六十年后,1994年,报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并且出了题目:“永久的悔”。季羡林看了题目后说:“题目出得好,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于是,提笔写就《赋得永久的悔》这篇著名的散文,文中写道: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是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一生中,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过面。他对母亲的爱超过对任何人的爱。他说过,母亲死后,他便再没有过真正的欢乐。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直至200l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来到母亲墓前,百感交集,“扑通”一下便跪倒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此刻,他“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故乡行》)
东方赤子——季羡林访谈录摘
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是名扬四海的东方学者,也是现代中国学贯中西的文化巨擘。他对文化的贡献,首先当属他所专攻的当今国际东方显学之一──印度学及中亚古文字学。此一学科在中国所谓「先生独关而自立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此外,佛学、九译之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季先生都有经典者作,故被称颂为「二十世纪中国东方学之重镇、印度古学之泰斗、九译之学之大师、中西交通史之大家」。
值得探究的是,季先生做的虽是出世之学问,却充满人世之情怀。他「心击家园,每作出位之神思;感时忧世,鸣旁通之秘响」。他关注人类命运、东西方文化发展、着力于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尤其是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杂记。
可以说,认识季先生,不能不读他的散文。张中行先生曾言: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而先生的深情,不仅予亲人、予师友、予人类,而且给予了大自然、给予了自然界一切有言与无言的生命。宗璞先生说,是季先生描写夹竹桃的一篇散文,使她「忽然认识季先生之所以为季先生的」。她写道:「作为夹竹挑知己的季先生,实际上不止写活了夹竹桃。对海棠的怀念,对牡丹的赞叹,写马缨花令婴宁笑,写紫藤萝使徐渭泣,他对整个大自然都是心有霊犀,相知相通的」。的确,先生对自然的热爱和非凡的领悟,不仅成为他散文的一大特色,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感受他的赤子童真,感受他对人生、对世界的追寻和理想。
认识季先生,又不能不读他的《牛棚杂忆》。在这部「因文化劫难、人性泯灭,为回挽人心世道」而作的血泪之书中,先生不仅捧出一面真实的「镜子」,让人们认识「文革」「这一场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永为警戒,而且,季先生以罕见的真诚,剖露出自己的心路历程。没有赤子之心,怎能写出这样披肝沥胆的文字?
总之,无论是作为一代学术大师,还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季先生的一生都能给人许多启示和教益。也许,下面的访谈能让我们走近季先生,聆听季光生的心声。(问为本刊特约撰述王辛,答为季羡林先生)
灰色的童年灰色的故乡
问:记得有篇文章写您,说您是一位「非常本色的人」、「始终保持了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能否谈谈您的故乡、您的童年?
答:我的家乡在山东省清平县(现在并人临清市)官庄,是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我们家又是贫中之贫,可以说是贫无立锥地。所以,我写过一篇回隐童年的文章。叫《灰黄漫忆》,说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只有一片灰黄。
我祖父母早亡,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我父亲和另一个叔叔(九叔),食不裹腹,衣不遮体,饿得到枣树林里去拣落在地上的干枣来吃。于是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在济南,九叔最终站住了脚,我父亲则回到农村务农。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面,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肝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了。大概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就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和最大的快乐了。
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我就会被大人领着,走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回来给母亲,打一打,压点面,这样吃顿白的。
有一年,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母亲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饭后,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总之,童年的贫困生活,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大概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六岁离开父母投奔叔父
问:从您的回忆文章中可知,您六岁离开故土,到了济南,从济南走上成材之路。现在回想起来,离开故土,来到济南,该是您一生一个幸运的转折吧?
答:我六岁那年,春节前夕,公历可能是一九一七年吧,离开父母,离开故乡,被叔父接到济南去。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们兄弟俩就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就只有去济南这条路。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可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多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总之,一个人的生活难免稀奇古怪的。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光大道,也曾走过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真是一言难尽!
问:据知您从小学习英文,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学习德文,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远见,当属不易。而且,您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传统文化都有很深造诣,看来您从小就在中西文化方面打下基础?
答:叔父对我期望很大,要求极严。到济南后,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小学,九岁的时候,在叔父的安排下,课余开始学英文。小学毕业后,进了中学,叔父又出钱让我在课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等,每天连轴转,一直学习到深夜。叔父还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数都是些理学的文章。叔父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的本领。他能作诗、填词、写字、刻图章,尤其是,凭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不仅发生了兴趣,而目兴趣极为浓烈。那时候,每当看到他正襟危坐读《皇清经解》之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至于「远见」,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永久的悔
问:读过您写的一篇文章《赋得永久的悔》,谈您对母亲的追念,令人十分感动。我想,这一定是您离开故乡后的最大遗憾了。
答:我是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光明日报》一位记者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早就想写的。的确,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一生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距」,曲曲折折,坷坷坎坎,我的经历可谓之多;要讲后悔的事,那是俯拾即是。但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也就是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的母亲娘家姓赵,她娘家穷得同我家差不多,所以她一字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娘家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地。这五里地,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我是母亲的独子,六岁离家后,两次回家奔葬,呆的时间也很短。后来听人告诉我,母亲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简短的一句话,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逐渐理解了,心中暗暗下决心,一旦大学毕业,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了我,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了。
一生考场得意十九岁 同时考取清华与北大
问:您在文章中经常提到自己「少无大志」,我想那是自谦,或可说明,您原是被动地接受叔父为您制定的严格的基础教育,有了这样的基础,一旦勤奋向学,自然超群拔类,一鸣惊人了。
答:我的确少无大志,小学和初中,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对此,我毫不在意,仍然热衷于钓鱼、摸虾。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上了高中以后。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刚上高中,由于受到国文教员的表扬,努了一把力,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各科成绩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成为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受到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积极攻读,高中三年,六次期考,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不过,这并未改变我少无大志的情况。我照样鼠目寸光,胸无大志,从未发下宏愿,要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甚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渡过一生而已。
一九三零年,我高中毕业,又同时考上清华与北大。可以说我一生考场运气好,一辈子从小学一直考到最高学位,从来没有失败过。
陈寅恪学风影响一生
问:您同时考取北大、清华,为何选择了清华?据知陈寅恪先生是您在清华的老师,您对他非常崇敬,能否谈谈他对您的影响?
答:一九三零年,我同时考取北大和清华,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入清华。原因并不复杂,据说清华出国留学方便些。当时的「留学热」并不亚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所以「吾从众」,在留学的历史潮流推动下,上了清华。清华当时的校风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了四年,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清华的培养,我大概会是一事无成的。
在清华,我入的是西洋文学系,但是,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与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我搞-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而且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此外,寅恪老师朴素无华,经常掖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匆匆来上课。不认识他的人,决不会想到,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方面,他也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留德十年 苦攻绝学
问:负笈德国,是您人生的重要一站,您在德国确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专攻印度学、中亚文字学,不知您当时选择这些「绝学」,有些甚么深意?
答:留学德国,是我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一九三五年、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定了一个互派研究生的合同。我当时从清华毕业已一年,在故乡济南省立高品中任教,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报名,很快通过了。于是,这一年的夏天,我离别老亲、少妻、幼子,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前面谈到,在清华时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我就有志于梵学,到了德国,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我当时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梵文,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在哥廷根大学,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别的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还意外学到了吐火罗文。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老实话,找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甚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绝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二战爆发后,我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被微从军,他的老师,已经退休、年逾古稀的西克教授出来代理他。西克对我这个异域青年寄托极大的希望,一定要把他的绝学传授给我,要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我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想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
总之,我是学了这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了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重操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是生了根。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梵文学者,是已故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以及我们的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
问:您刚才谈到人生的偶然性,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的: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您没有清华的准备,就不会想到学梵文;您作为异域学子,如果没有杰出的表现,德国老教授也不会执意收您为弟子,主动教授吐火罗文。尤其您留德期间,正是二战时期,处境一定十分艰难。听说您在德十年,每天都记日记,有人誉之为「一部中国留学生求学奋斗史」,不知后来可否发表?
答:没有,没有时间整理和考虑。
三十五岁任北大教授兼东语系主任
问:据知您留学回国后,三十五岁就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评为全国可数的一级教授之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等。回顾这段经历,不知您有些甚么感想?
答:二战结来后,我离开德国,于一九四六年夏辗转回到阔别十一年的祖国。
通过陈寅恪先生介绍、胡适之先生与传斯年先生和汤用彤(钖予)先生的同意,来到北大工作。同时,我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须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正教授。可是,大大出我意料,至多不过十天,用彤先生通知我,我被补聘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前二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都是饱学宿儒,我一个三十多岁、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真是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我知道这是前辈师长对我的提携和爱护,这对我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一直起着激励的作用。
四九年后,我继续「鸿运亨通」,可以说,刚过不惑之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和利益,我都已稳稳地拿到了手中o
但是,我是一个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如此,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至今我在燕园内外有颇令人满意的口碑,好像我真是淡薄名利,与人无争。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我的道德真就这样高吗?不,不是的。我虽然不能把自己归于坏人之列,因为除了替自己考虑之外,我还能考虑别人。但我也决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两个方面,我已达到了顶峰,我还有甚么可争呢?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一生,虽也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灾难,我也不幸「躬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
俗话说:「一个禽笆三个桩,-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在这方面,我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
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定德国与清华交换研究生合同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另外是胡适之先生,汤用彤先生,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
总之,我生平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几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牛棚杂忆》不出对不起子孙后代
问:您刚才谈到「文革」遭遇,读过您的「牛棚杂忆」,给人震憾很大。据说您认为,这本书非出不行,不出对不起子孙后代。您是怎样考虑的?
答:把文革的遭遇写出来,我认为,是对后世子孙负责。我们不写,对不起后世子孙。一个这么伟大的民族,发生这么大的悲剧,这是一个空前的悲剧,我希望它绝后啊!从一九三二年我二十一岁时起,我几乎每年都写点东西,可是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为甚么会成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而且,岂是我一个人如此,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如此。由此可见,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的吗?所以我认为,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写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它会告诉我们,其么事情应当干,其么事睛不应当干。
拥怀「原罪感」四十多年
问:您在《牛棚杂忆》中多次谈到「原罪感」这个词儿,您是甚么时彻底摆脱了所谓「原罪感」?
答:解放以后,我是有一种「原罪感」。我从德国回国以后,仅仅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兴奋、愉快,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而且,反观自己,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摘桃派」: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可是我做了甚么贡献呢?当国内人民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抗战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追求自己的名声事业。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需要改造,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诚心诚意地接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背着这样沉重的「原罪」的十宇架,我经过解放后大大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虽然也有想不通、弄不明白的时候、但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最奇怪的是,经过文革九死一生的灾难,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没有把我的个人遭遇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国家的悲剧联击在一起,一直怀有「原罪感」。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所以,我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里说过: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
问:文革那段残酷的经历,是甚么信念支持您渡过难关,是否想到会有今天?
答:文革中在揪出来被斗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和文革中许多自杀者一样,我也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当时,就在我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到圆明园的芦苇丛中自杀的时候,红卫兵冲进我家,解押我去批斗。在这场批斗中,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下子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
至于是否想到会有今天,根本没有。当时已是破罐破摔,牛棚里,大家普遍的想法是到新疆建设兵团那样的地方去过一辈子,没想到会平反,会有今天。
不过,虽然活下来了,但是,刚从牛棚出来的时候,我己经虽生犹死,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束西,不知道怎么说话;不习惯抬起头来走路,不习惯同人打交道,几乎「异化」成「非人」。
而且,正如我在《牛棚杂忆》中谈到,现在,我一面「庆幸」自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在我后来「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辞之余,我的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这大概算是我的「文革」后遗症吧。
问:《牛棚杂噫》出版后有甚么反应?有人给您写信表示忏悔或其它吗?此书一版即出八万册,目前市面似已买不到,是否还出第二版?
答:《牛棚杂忆》出版后,确有不少人写信来,表示你说的这类意思,但是写这本书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所以一切向前看。这本书已经出了第二版。(未完待续)(本文刊载《中国评论》2001年6月号)
东方赤子——季羡林访谈录(下)摘
问:读过许多赞颂您的文章,其中张中行先生的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季先生就以一身而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因为,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这是他人的评价,那么您对自己怎样看待?答:谈到看待自己,我写过一篇《我写我》,里面说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古希腊哲人曾发出狮子吼:「要认识自己!」可见这问题之重要。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
的确,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而且剖析得有点过头。或者说,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比如拿写文章为例。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好。
又比如文学作品。自己写散文,而且已经写了六、七十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不通伦理学,也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的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多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着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精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录,退休无日,路穷有期。
总之,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光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甚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