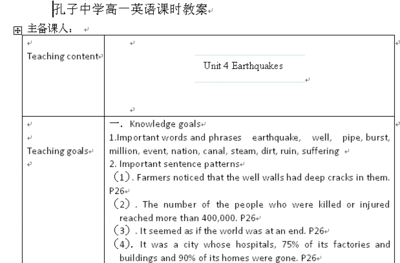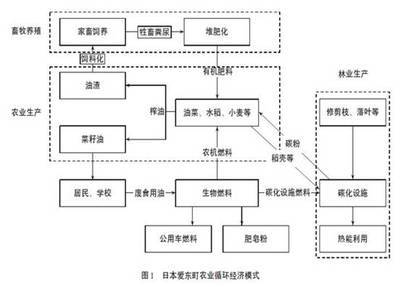内容提要近代上海被认为是中国最黑暗的城市,却寄寓着中国人对未来社会最天真的幻想,为中国乌托邦叙事提供了尺度与向度。上海模式的中国乌托邦叙事所提供的未来世界是现实上海的再造,包含更好的空间和更好的时间,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进化论的色彩;也是现实上海的反转,尤其是租界与华界状况的反转,反转叙事交织着中国作家的现实忧虑与未来愿景。上海式乌托邦叙事受到租界文化杂糅性的影响,提供的是中西杂糅的乌托邦。
一、黑暗城市的乌托邦之光
上海租界光怪陆离、藏污纳垢,是臭名昭著的“罪恶的渊薮”,又是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它的繁荣亦属不正当,因为租界的繁荣与中国的战乱动荡、经济颓败“互为因果”,“国内愈纷乱,租界愈繁荣;租界愈繁荣,内地愈衰落”[①]。如此上海,为谴责小说、狭邪小说、黑幕小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但同样是这个上海,为近现代文人的乌托邦叙事提供了灵感与背景。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相当一部分幻想未来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是以上海为生发点,凭借上海经验来虚构理想世界。“未来上海”成了各界人士、各种期刊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了乌托邦叙事的主要对象。
被认为最黑暗的城市,却寄寓着中国人对未来社会最天真的幻想。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仔细推敲,又在情理之中。
首先,不同的人眼中的上海形象是有差别的。“乡下人看上海,看到的是繁华。道德家看上海,看到的是罪恶。文化人看上海,却每每看到的是文明。”在晚清民初时期,好些新型知识分子把上海看作是“文明渊薮”[②]。“文明渊薮”自然可以作为想象未来中国的底本。其实,由于上海具有文明与罪恶、殖民与现代的双重特性,因此,同一个作家对上海的书写,有时也呈现出黑暗地狱与理想乌托邦的两副面孔。热情建构上海乌托邦的毕倚虹、陆士谔、包天笑都是上海的双面写手。毕倚虹的《未来之上海》(1917)封面标“理想小说”,讲述了“中国之鲁滨孙”2016年回到上海的见闻,但他又写有六十回长篇小说《人间地狱》(1924),“人间地狱”是指上海社会。陆士谔的“未来小说”《新中国》(1910)以上海作为“新中国”的想象基础,可以看作他的《新上海》(1910)的姊妹篇,两者具有互文关系,分别提供了现实上海与理想上海的镜像。包天笑既写《上海春秋》(1922-1926),把上海当作罪恶的染缸,又写《新上海》(1925),想象上海“世界博览会”的盛况。有意思的是,陆士谔和包天笑都是左手揭露上海的丑恶,右手畅想上海的未来,两者同时进行。实际上,近现代的乌托邦叙事,包含“过去”与“未来”的一系列比较,“未来”的文明社会以上海为底本,“过去”的丑恶社会则直接指向现实上海。这就是近现代的乌托邦叙事选择上海的情形。

其次,上海“商埠是个人造世界”[③],适合被“再塑造、再想象”,“复兴那种隐蔽的乌托邦理想”[④]。
再次,对替代世界进行想象的热情,是乌托邦叙事的原动力。替代源于不满。租界化上海被认为是一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⑤]天堂与地狱的辩证关系体现在“上海是富人的乐园,穷人的牢狱”[⑥]。当人们幻想未来上海已没有穷人,“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⑦]。最“野蛮”也最“文明”的上海[⑧],最能激发作家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力。
最后,“上海是个缩本中国”[⑨],作家能够在上海乌托邦与中国乌托邦之间实现直接沟通。“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租界拥有的“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⑩]元素,为近现代中国的乌托邦叙事提供了尺度与向度,故作家们乐于借上海来想象未来中国,或者说想象未来上海也就是想象未来中国。
对理想世界的热情幻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就已存在。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王绩的《醉乡记》、宋代苏东坡的《睡乡记》,都构设了理想社会。这些篇章所构设的理想社会都是“桃花源”式的,其共同点为:化外、自然、和谐、小国寡民、天下为公。“桃花源”反映了小农社会的大同梦。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保留了这一古老的梦想。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世界的热情幻想,亦受到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启示。“乌托邦”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广泛传播。严复1897年译述的《天演论》“导言十八篇”中的第八篇为“乌托邦”。《天演论》影响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的“乌托邦”理想也为诸多知识分子所热衷。这种影响从晚清到30年代,一直非常强劲。例如:1930年代初级中学使用的《国文》课本就选入了“乌托邦”篇[11]。1931年出版的《新文艺辞典》也列有“乌托邦”词条[12],并对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进行了介绍:“这是一部描写理想共和国的作品。据云,在那一个国土中,既没有咖啡,也没有律师,没有虚饰,也没有时髦。居民欲望颇少,每日仅劳动六小时等等,很有些社会主义的色彩。”[13]莫尔的《乌托邦》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叙事提供了灵感,《月月小说》连载的“理想小说”《乌托邦游记》[14]就提到的莫尔《乌托邦》的相关内容。
在新旧交替时代,在遭遇挫折与祈望再度强大的民族境遇下,中国的“桃花源”与西方的“乌托邦”寄寓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诉求。而上海成了知识分子想象未来世界的焦点。中国的乌托邦叙事无论观念形态还是叙述形式,大都建立在上海租界状况的基础上。中国乌托邦叙事的基本模式是上海模式。
二、上海式乌托邦叙事的空间与时间
乌托邦分为空间意义上的乌托邦与时间意义上的乌托邦。中国古典的“桃花源”在性质上属于空间意义上的乌托邦。古典文人在脱离现存社会秩序的隔离性空间建构起理想社会,表现出对礼法制约、阶层分化、社会动荡的现实社会的规避,对自然自为、安定富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向往。近现代中国的乌托邦叙事在多数情形下借上海租界空间来生发,因此修改了古今中外乌托邦叙事的常规,虚构的既不是单纯的空间意义上的乌托邦(如:世外“桃花源”,荒岛、太空上的理想城邦),也不是单纯的时间意义上的乌托邦(如:遥远未来的中国社会)。多数乌托邦叙事没有虚构现实社会不存在的乐土,提供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现实社会空间的再造,包含更好的空间(去除租界性质,并赋予政治道德理想后的上海/中国空间)和更好的时间(未来上海/中国)。上海租界的特殊性质与地位规约着中国乌托邦叙事的模式。庄乘黄《新上海未来记》、毕倚虹《未来之上海》、包天笑《新上海》、徐卓呆《未来之上海》、程瞻庐《牛渚生重游上海记》、无咎《未来之上海》、吴闻天《三十年后之上海》等题目中标有“上海”二字的小说,自然是关于上海的,就是标明“中国”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也是以上海为想象的起点和基点。
中国古典“桃源梦”囿于自傲的中原心态所衍生的天下观,因此只能以原始儒家、道家精神在中国疆域内虚构隔绝性的理想净土,复兴知识分子隐秘的集体梦想,其“桃源梦”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都是古老的中国样式。古典“桃源梦”的叙事动力属于内发型。近代中国乌托邦叙事的动力则属于外发型,落后挨打的屈辱感所唤起的民族自强意识,很快就转向“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度变革、“新民”的强烈诉求。夷技、夷政成了效法的对象,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突破了古典“桃源梦”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拘囿。除了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旅生的《痴人说梦记》、鲁哀鸣的《极乐地》等少数小说构设了“与世隔绝的孤岛的空间乌托邦类型”[15],大部分近代小说的乌托邦叙事借助上海租界空间来再造理想社会。吴趼人《新石头记》的空间叙事策略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上海租界所具有的空间政治意义。小说沿着“上海租界—自由村—上海租界”的游历线索来构设乌托邦图景。在小说前半部,贾宝玉遭遇的是上海租界摩登、繁华、堕落的殖民性空间,小说后半部写贾宝玉进入“自由村”的所见所闻。“自由村”是吴趼人虚构的乌托邦,是真正的“文明境界”。“自由村”街道整洁、秩序井然,科技发达,民风淳朴,信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自由村”看作是对上海租界进行政治消毒,并赋予传统儒家道德观念后的结果。“自由村”为东方强一家所创造,东方强的三子、女儿、女婿的名字分别为东方英、东方德、东方法、东方美、华自立。华自立出生科学世家,其父雅号“再造天”[16]。由此可见,所谓“文明境界”,乃东方道德与西方科技联姻的结果。在小说最后一回,吴趼人又把贾宝玉调遣回上海,提供了抹除殖民性后的上海租界的形象:“果然立宪的功效,非常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17]《新石头记》的乌托邦空间,是以上海租界空间作为镜像加以想象的结果,而且不忘把现实租界纳入中国乌托邦的整体景观。
蔡元培的《新年梦》也是以上海作为想象的初始空间和主体空间。1901年至1907年的六年时光,蔡元培基本上呆在上海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新年梦》[18]是蔡元培唯一的一篇小说,全文用白话,连载于1904年2月的《俄事警闻》。《新年梦》就是“中国一民”在上海做的一个梦,这个梦是中国的大同愿望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的结合。“中国一民”的“新年梦”明显受到租界体验的影响,例如,在区域空间(包括道路、医院、学校、工厂、公园等)的规划上,上海租界景观提供了赖以想象的直接经验;取消家庭、性爱自由的观念,虽然来源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但上海租界的情欲状况无疑为之提供了语境支持。小说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非常重视租界问题,把它作为三大议案之一来叙述,并介绍了收回租界的详情。可见,租界的文化空间性质影响了蔡元培的中国乌托邦想象。蔡元培提供的是革命派的上海/中国乌托邦。
尽管“乌托邦是对人的一种可能性生活方式的描述”[19],但是古典桃源梦与中国近现代的乌托邦叙事存在观念上的本质分野。正如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所写到:“只要用宗教的和封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中世纪秩序还能在社会之外,即在超越历史和缓和其革命锋芒的某种彼岸世界,设置它的乐土,那么,关于乐土的观点就仍然是中世纪社会的组成部分。直到某些社会集团把这些意愿变为他们的实际行动、而且试图实现它们,这些意识形态才变成乌托邦。”[20]近现代中国的乌托邦书写属于后者。在空间上,上海式的乌托邦叙事不像“桃花源”那样构设现实社会之外的闭锁空间,而是以世界主义的开放视野,在世界大势的格局下来畅想未来中国。关于未来中国的畅想,最终落脚于“去租界”后的上海空间。这是因为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现代中国而言,理想的社会图景必然涉及对现代文明和民族自主的渴求,所以,最具现代气象与殖民气息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就成了重塑中国的最佳空间。上海梦与中国梦之间有着最为深切的联络,在乌托邦叙事中,二者具有合二为一的效应。无论蔡元培的《新年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是其后通俗作家的作品,皆是如此。
在时间上,近现代中国作家的乌托邦叙事,讲述的不是桃花源式的“同时代”故事,而是面向未来,带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近现代乌托邦叙事进入未来时间的基本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直接定位为未来的某一时间点,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开头即写道:“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21]包天笑的“未来小说”《新上海》省略了穿靴戴帽的“入话”交代,一开头就进入未来的时间点——中华民国四十四年(1955)的三月三日,叙述未来的事件——“上海正开了一个世界博览会”[22]。这两部连载小说都未写完。第二种为“梦见”未来世界,如蔡元培的《新年梦》、陆士谔的《新中国》都以主人公在正月初一所做的梦来承载作者的乌托邦理想,梦醒之后的时间点依然为小说创作时的“当下”。这两部小说提供了系统的乌托邦社会图景。以上两种时间类型,通常为清末力倡维新立宪和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所采用,未来中国与未来上海的叙事被糅杂在一起,构设出“理想主义者改造社会的蓝图”[23],洋溢着富强中国的乐观期待。第三种为“重回”上海,置身多少年之后的上海,如徐卓呆的《明日之上海》、程瞻庐的《牛渚生重游上海记》、毕倚虹《未来之上海》、无咎的《未来之上海》。这四篇小说都选择让主人公离开上海后重回上海,以“重游”的方式感受未来上海。时间的距离,巨大的变化让“重游者”成了这座城市的陌生人。“重游者”依旧抱着多年前的“成见”,对新上海的一切感到不解。为此,徐卓呆、程瞻庐、无咎在小说中提供一位见证上海巨变的人物陪其游览新上海,为之解惑。“重游者”记忆库中储存的是上海的罪恶形象,伴游负有解说的责任,对新上海的新景观、新制度、新气象进行解说。两人的对话构设了未来上海与“过去”上海的对照,在对照中,上海的乌托邦面目清晰地浮现出来。以“重回”上海的方式设置乌托邦时间的小说,在时态上是错位的,“过去”的罪恶上海实际上就是“当下”的上海,“现在”的理想上海则是指未来上海。陆士谔的《新中国》以梦的方式来开启未来中国的叙事,但梦中内容的叙事策略与上述作品类似,包含了重游者与伴游的人物关系和新旧对照、时态错位等叙事策略。这类小说的幻想逻辑为:“欲言未来之上海,当先明瞭现在之上海。”[24]
三、上海式乌托邦叙事的反转策略
上海式的乌托邦叙事是现实上海的反转,尤其是租界与华界现实状况的反转。反转涉及物质文明、城市景观、华人素质、行政权力等。福柯认为:“乌托邦也就是非真实的位所。这些位所直接类似或颠倒地类似于社会的真实空间,它们是完美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的颠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乌托邦本质上或基本上都是非现实的空间。”[25]上海的乌托邦叙事自然包含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是真实社会的颠倒。但是,租界的特殊性质——殖民性的城市,使得上海的乌托邦叙事与古今中外的乌托邦有着较大分野。这种分野主要表现在上海的乌托邦叙事常常以租界内的文明气象为理想蓝本,通过修改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署名(改为中国人)和地点(大部分为上海),并加以想象夸张,来构设乌托邦;同时,作家们非常在意租界的权力归属问题,以及租界和华界的对照问题,以反转的策略重建未来上海的城市图景。
反转源于华界和租界的反差。正如晚清的竹枝词所云,“出北城趋新北门,洋场景别一乾坤。洋泾浜至头摆渡,商务兴隆铺户繁”[26]。从1930年代的飞机上鸟瞰上海,看到的是“繁华绮丽之区,仅在租界一隅之地。一至华界,情状顿异,街衢狭隘,建筑简陋,与租界之文明程度一相比较,则相差当在数十年以外”[27]。上海绅士李平书论到租界与华界的反差状况时,既义愤又忧虑:“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28]华人既承认外国人缔造了租界的文明气象,又因租界文明对民族主权与尊严构成了威胁而愤愤不平或“惴惴然不可终日”[29]。这种忧虑不仅指向当下,也指向未来,陈布雷的《未来之上海都市》(1921)一文就表达了对华人能否“享受未来都市之福利”的担忧[30]。而租界与华界的反转叙事,交织着中国作家的理想与忧虑。
对上海租界现代景象的惊颤与对殖民性的不安,使得关于上海未来的构想被拖入现实问题中,构设出上海乌托邦形象,以疏解现实的焦虑。在这种心态下,近现代中国作家的乌托邦叙事从民族意识的角度对上海城市空间进行重建。让乌托邦中的华界在文明程度上压倒“过去”(当下的)的租界,让华人成为未来上海的主人。《新中国未来记》以模糊的表述,暗示整个上海已政权归一:由我国国民决议在上海开设的“大博览会”,“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31]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亦有类似的笔墨。在蔡元培的《新年梦》中,租界已收回,外国人在上海已没有生意可做。程瞻庐的《牛渚生重游上海记》构思简单,以反转作为故事线索。牛渚生是上海“素负盛名”的社会小说家。“海上为万恶之窟,波谲云诡,不可思议”[32],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凭着洞察社会与描写世相的能力所创作的社会小说大为畅销。其后厌倦写作生活,往南洋群岛。三十年后,返回上海,思重拾旧行当,以书写黑暗腐败上海的社会小说来谋生。然而,三十年前作为“游戏中心”的上海于今转变为商业中心、工业中心、科学与文化中心,赌窟、妓寮、秘密社会、政客机关,都已在上海字典上找不到了,社会小说乃大破产,牛渚生的打算落空。陆士谔的“理想小说”《新中国》对“新中国”的幻想,同样依赖于租界、华界的反转叙述策略。《新中国》讲述小说家陆云翔1910年的正月初一喝醉了酒,睡在床上梦见与好友李友琴女士一起来到大街上,见到宣统四十三年(1951)的上海已改天换日:外国人很谦和友善,外国巡捕全部换成了华捕,治外法权已经收回,租界的名目已久不存在,警政、路政都由地方市政厅主持;原来僻陋的徐家汇,于今比当年租界最繁华的马路还要热闹;……陆云翔梦中的上海景象和故事,是外侨控制租界情形的反转,也是华、洋生存境况和租界华界状况的反转。反转的叙事策略得到人物关系的支持。陆云翔是“过去”(当下)上海的“回叙”者,一个自感惭愧的、时光倒错的回叙者,以“旧”观念来揣度“新中国”/“新上海”的一切事物,被李友琴看作顽固迂腐;李友琴则是中国/上海乌托邦的解读者,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解读者。在两人的见识对比和思想交流中,摧毁殖民权力后的民族自傲感得到释放。
《新上海未来记》[33]的反转策略更有意味。该小说标“寓言小说”,作者为《快活世界》月刊的编辑庄乘黄,可惜这个刊物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该小说也因此未能连载下去。已发表的两回颇有新意。第一回为“楔子”,我们撇开不谈,第二回“重游沪海关尽沧桑过眼繁华都成梦幻”构设了未来上海的图景:不知到了哪一年,万国和平会议定取消上海租界,改为上海商场。从此外人受中国法律支配,华人得享平等权利,可以大踏步自由出入公园,中外人士和睦相处。上海因此中外人口剧增,人满为患。十六铺议事厅的议员开会决定,将南京路、静安寺路下面挖空,开辟一条地下马路,建造房屋,开设店铺,以便上海做个经商殖民的尾闾所。庞大的地下工程竣工后,取名为“地中天”,地皮掮客纷纷购地造屋,运货设肆。议事厅发表公告,允许活夜叉、野鸡、小脚老妈、叫花子、亡国大夫先行迁入,允许藏污纳垢的小客栈、牟利害人的土膏店、专收黑货的当铺,优先选地段,允许伤风败俗的小房子、男女同台演出的新剧社、造谣生事的侦探在“地中天”自由行动。“地中天”成了上海的一大著名景观,来上海的人无不去游地中天。小说关于“地中天”的想象,非常奇妙。作者把租界移到地下,取名为“地中天”,并把罪恶全部迁入其中,构设了一黑暗世界。这一世界在空间上的降格,寓意深刻,暗喻上海租界是黑暗世界,是罪恶的渊薮,是见不得人的世界。把租界贬谪地下,也算是华人在空间上取得了胜利。小说对此有两处批注,表达的就是这种感想。一处评曰:“开了新天地,容那旧社会。”一处评曰:地中天“是乾坤颠倒天地易位的影子”。面对“地中天”的乱象,华人又引入“木巡警”进行整治,取得成功。小说因此感叹:“上海这一次的大变迁……中华一部新历史上,是最有光彩的”。这最光彩的一幕还包括上海庄严矗立的三座铜像:黄浦滩前的叫“苦力中之奇男子”;虹口里的叫“面头大王”;泥城桥西的叫“翠英姑娘”。这部小说的反转策略,独出心裁,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华人对租界的隐秘复仇心理,既重构了外侨与华人的种族关系,又赋予象征性空间(雕塑)以民族意识与平民性质。
虽然反转是上海式乌托邦的基本叙事策略,但是对未来上海(中国)的描绘,很大程度上还是以租界景观为底本。无咎的《未来之上海》[34]安排主人公许懋功1925年离开上海,十年后再回上海游览。此时的上海已成为“模范商埠”,其繁荣发达程度已远超纽约、伦敦、巴黎。租界已实行中国与各国共管。小世界改成了俱乐部,免费为公众提供洗浴、理发等服务。城隍庙改成了公园,比外国公园好得多。华界的马路比十年前租界的南京路还要宽阔整洁,让“老上海”许懋功误以为是租界。这篇小说关于未来上海的叙事,处处以现实租界为蓝本,不过对之进行一番去恶存善的“消毒”;处处以租界为参照,不过把租界的繁华进行空间移植,移植到华界。《新中国》对未来上海街景的描绘更是直接来源于对租界马路的想象:“但见马路宽阔,店铺如林。电灯照耀,如同白昼。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十多里间,店铺没有间断过。绸缎、磁器、银楼、酒馆、茶肆,没一样不全备。”[35]类似的描绘,在当时的纪实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陆士谔不过把现实租界的繁荣程度稍加夸张而已。上海/中国乌托邦的建构,过于依赖上海经验,可以看作租界景观的仿写。未来上海/中国的想象,主要采取空间移植策略,把租界文明秩序化,换成中国(华人)主体,变成华界的现实。所谓未来上海/中国图景,很大程度上是租界社会的良性放大。
反转的策略,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有着现实的趋向。192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牛渚生重游上海记》,想象三十年后的上海已“刷新”,成立了“特别市”,“自治程度,一日千里,增进至速”[36]。两年后,国民政府成立上海特别市,程瞻庐的愿望得到部分应验。国民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包含反转的动机。蒋介石和上海市市长的态度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蒋介石在成立大会上的“训话”强调:“盖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中外观瞻所系,非有完善建设不可,如照总理所说办理,当比租界内,更为完备……彼时外人对于收回租界,自不会有阻碍,而且亦阻止不了,所以上海之成绩,关系内外至大。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37]首任市长黄郛在就职演说中亦指出上海乃“中外观瞻所系,关系实为重要。”[38]让上海来担当“中外观瞻”的重任,并希望上海特别市比租界更完备,是因为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贸易、金融等方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因为强大的上海租界不受中国控制,并对中国尊严、利益构成了威胁。因此,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最重要之目的,在使今日之租界,日渐衰落”[39],把上海的中心转移到上海特别市,反转租界、华界的落差,改变中外观瞻的成见,证明党国的力量,证明中华的强盛与尊严。可惜国民政府的反转策略收效甚微,后来收回租界,也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反转效果。
四、未来的嘲讽与杂糅的乌托邦
乌托邦叙事虽然可以天马行空地畅想未来世界,但也是颇见性情的一种创作。“文学家的乌托邦,与他的品格思想,却有密切的关系”,如果陶渊明没有超越尘世的品性,“断没有那样高尚的乌托邦呵”[40]。因此,不同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各有其品格,就小说门类来说,就有“未来小说”、“理想小说”、“政治小说”、“寓言小说”、“滑稽小说”等名目。
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想象,都执着于理想乌托邦的建构。在上海式乌托邦叙事中,徐卓呆的《明日之上海》、毕倚虹的《未来之上海》、吴闻天的《三十年后之上海》,既是对未来上海社会的猜测,又是对现实社会的嘲讽——以未来时间的上海嘲讽现实时间的上海。毕倚虹的《未来之上海》虽然封面标“理想小说”,且带有淡淡的科幻色彩,但总体来看,作者对未来上海的想象,不是朝着理想上海的方向发展,而是借未来的时间点,来抒写对20世纪初殖民性上海种种怪现状的嘲讽。《三十年后之上海》[41]以反讽的笔调,对贪图享乐、着装暴露、男女关系混乱、缺乏安全感的上海进行了嘲讽。小说虽然写三十年后之上海,但在进入故事时,却把“未来时”当作“现在时”使用,把“现在时”变成了“过去时”来讲述,在最后才点明:“滔滔的一大篇,都是民国纪元后四十四年上海的事情,怎么被我现在已记出来呢”。到此,所述故事回归应有的时态。这是把未来拉入当下来叙述的一种特殊方式。但其实质,仍然属于把现实的不满与焦虑带入未来社会的想象。
徐卓呆的《明日之上海》是一部以“明日上海”来映射、嘲讽“今日上海”的“滑稽小说”。小说在徐卓呆自己编辑的《新上海》月刊连载时,第一期之后所刊登的内容,每次都在题目右边附上一段几乎不变的文字:“【已刊大略】有一个从小离开上海的华侨之子,一朝从南洋回到进步的上海,遇见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样样都很有趣。”这段文字透露了几个关键信息,一是小说采取“重游”上海的叙事模式,归国华侨之子莫敏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莫名其妙”)遇到的事是“料想不到”的,且“很有趣”。二是莫敏棋再次进入的是“进步的上海”。在这里,“进步的上海”是作者对“明日上海”的总体确认。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莫敏棋俯看这个城市时,“觉得竟与自己理想中的新上海,大不相同,更与自己幼时所见的上海,也不大相同”[42]。小说所描绘的未来上海不是朝着理想状态迈进,而是朝着荒诞离奇的方向“进步”。《明日之上海》分十一部分在《新上海》连载,最值得注意的是“(一)舶来车夫”和“(三)惊人的古董店”这两部分。“舶来车夫”讲述上海的外侨养尊处优,出门有车,后因恐惧老不用腿会变成蜗牛模样,便把拉黄包车当作时尚的健腿运动,免费载客。莫敏棋刚回到离别多年的上海,便遭遇了白种外国人身穿晚礼服免费拉车送他去旅馆的事,很为不解。这个故事既是对租界外侨生活奢华的攻击,又把往日狂妄的外侨置于低眉顺首的臣服状态,满足了民族主义的意淫心态。租界是外国人的天下,崇洋是租界的一贯风气,小说对这种状况进行了反讽。在“惊人的古董店”,莫敏棋看到货架上摆的竟然是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倍感疑惑。好友陆芝谷(伴游)告诉他,由于上海人崇拜洋货,样样都用洋货,使得中国产品在市场上几乎要绝迹了,故都成了价格昂贵的古董,高价购买这些古董的却是洋人,他们或买来当装饰品,或买来当珍贵礼品送人,闹出不少笑话,如把中国夜壶当花瓶摆在客厅里,把饭桶当荣誉证明[43]。“惊人的古董店”具有双向反讽的意味,既讽刺了外国人对东方文化的误读,把污秽当宝贝,还自以为领会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又讽刺了上海人盲目崇洋的心态,弃国货不用。而讲述这个故事的行为,则包含了作者以民族主义的方式所进行的自我解嘲。
上海式乌托邦叙事受到租界文化的杂糅性的影响,提供的是杂糅乌托邦。梁启超把“大博览会”与孔子后裔论道糅合在一起,“大博览会”起源于西方,符合上海租界的“商埠”性质,但是在欧化的“大博览会”的中心安排孔子后裔论道,仿佛展示了一幅“中体西用”的漫画。在构设乌托邦时,中国作家念念不忘“大同”理想,梁启超把“大博览会”看作是商务、技艺、知识、宗教汇聚的“大同”盛会。包天笑同样以上海“世界博览会”为载体,来经营他的世界大同理想[44]。蔡元培在《新年梦》中期待战争消失、国家消亡、语言统一的“真正的大同世界”的出现。陆士谔的《新中国》也把未来中国描绘成没有战争、财富平均、人人小康的大同世界。就其实质,他们都是把中国的“桃花源”搬到上海租界,把乡村模式的“桃花源”修改成都市“乌托邦”。
在西方,“‘城市’形象和‘乌托邦’形象长久以来一直纠缠在一起。”[45]近现代中国作家借助上海空间所构设的大同世界是“桃花源”与“乌托邦”的杂交,具有中西杂糅的特点。这个大同世界不是封闭的,而是面向全世界。这个大同世界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由中国现实社会衍化而来,而是对殖民性的上海租界进行一番“清洗”的结果。理想世界的叙述包含中国文化的元素,如未来中国梦总是从正月初一开始,保持青春的药取名为返老丹;也掺杂了西方文化元素,如代议制的议会形式,最先进的工程技艺。包天笑的连载小说《新上海》第一回介绍的“世界博览会”场景和描绘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交通地图,从中能嗅到洋场繁华绘影的余味,与“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46]之类的现实书写有着类似之处。但小说接下来把桃花源搬入上海大都市,以现代的博览会来容纳古典的桃花源:“博览会的公园内,有一处地方,是一带清溪,回抱着两面堤岸,上面搭着几个茅亭,一大方草地,碧茸成茵,两岸却都种了桃花……已经熳烂地开放了。那清溪中也有几只小船,铜栏綵幔,放乎中流,好似身入桃花源一般。”[47]小说中的人物、场景、科技所组合的情境,非常奇特,反映出租界文人中西古今杂糅的知识趣味。
如果注意作者的身份,会发现民国后从事乌托邦叙事的小说家都是被称为“通俗作家”(鸳鸯蝴蝶派)的一帮人。他们在上海卖文多年,有着扎实的旧学功底,又通过各种途径受到西学的熏陶,思想观念半新不旧。他们的生存环境与经验见识决定了中国的乌托邦叙事是中西杂糅的,是上海式的。通俗作家之所以纷纷进入乌托邦叙事领域,一个方面缘于他们骨子里有着传统文人的诗性情怀,而“凡富于诗的精神者都自有他的理想世界”[48]。另一个方面,他们对上海租界的态度,有着“城”与“人”的区分,对“城”(欧化的城市景观与市政管理)持文化认同的态度,对“人”(违背儒家伦理规范的名利追逐与欲望放纵)持道德批判的态度。换而言之,从器物、制度层面来看,上海租界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欧化的繁华气象;从儒家道德理想来看,上海租界则是黑色染缸和罪恶渊薮。当通俗作家专注于物质性与知识性的现代文明,并对租界、华界的状况进行反转后,上海就成了理想未来的模拟空间。当通俗作家同时把中国传统精神趣味加入其中,最终泡制出来的产品就是上海式乌托邦。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SW1309115)的研究成果。)
[①]新中华杂志社编:《上海的将来》,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9页。
[②]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第3期,第139-153页。
[③]乘黄稿本、神我批注:《新上海未来记》,《快活世界》1914年9月,第2期,第1-11页。
[④][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⑤]穆时英:《公墓》,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第194页。
[⑥]世杰:《如此上海》,《陕西旅沪学会季刊》,1935年10月,第2期。
[⑦]新中华杂志社编:《上海的将来》,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2页。
[⑧]陆士谔:《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⑨]乘黄稿本、神我批注:《新上海未来记》,《快活世界》1914年9月,第2期,第1-11页。
[⑩][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11]付东华、陈望道编:《国文·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66-270页。
[12]顾凤城、邱文渡、邬孟晖合编:《新文艺辞典》,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第220页。
[13]顾凤城、邱文渡、邬孟晖合编:《新文艺辞典》,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第465页。
[14]萧然郁生:《乌托邦游记》,《月月小说》1906年11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第1期,第87-98页。
[15]耿传明:《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76-190页。
[16]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糊涂世界两晋演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5-287页。
[17]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糊涂世界两晋演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4页。
[18]蔡元培《新年梦》,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0-242页。
[19]李永虎:《乌托邦的现代性困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24-29页。
[20][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7页。
[21]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第1卷第1期,第51-76页。
[22]天笑:《新上海》,《新上海》1925年5月,第1期,第191-203页。
[23]耿传明:《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76-190页。
[24]赵君豪:《明日之上海》,《旅行杂志》1930年1月,第4卷第1期,第1-6页。
[25][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的空间》,米歇尔·福柯等著《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6]张春华、秦荣光、杨光辅:《沪城岁事衢歌上海县竹枝词淞南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27]赵君豪:《明日之上海》,《旅行杂志》1930年1月,第4卷第1期,第1-6页。
[28]李平书:《论上海》,转引自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第3期,第139-153页。
[29]赵君豪:《明日之上海》,《旅行杂志》1930年1月,第4卷第1期,第1-6页。
[30]陈布雷:《未来之上海都市》,罗炯光、向全英编著《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31]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第1卷第1期,第51-76页。
[32]瞻庐:《牛渚生重游上海记》,《新上海》1925年5月,第1期,第67-70页。
[33]乘黄稿本、神我批注:《新上海未来记》,《快活世界》1914年9月,第2期,第1-11页。
[34]无咎:《未来之上海》(小说),《新上海》1925年11月,第7期,第35-44页。
[35]陆士谔:《新中国》,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第39页。
[36]瞻庐:《牛渚生重游上海记》,《新上海》1925年5月,第1期,第67-70页。
[37]《国民政府代表蒋总司令训词》,《申报》1927年7月8日,第13版。
[38]《黄市长就职演说》,《申报》1927年7月8日,第13版。
[39]赵君豪:《明日之上海》,《旅行杂志》1930年1月,第4卷第1期,第1-6页。
[40]刘柱章:《陶渊明的乌托邦》,《艺林旬刊》1925年5月,第4期,第3-4页。
[41]吴闻天:《三十年后之上海》,《新上海》1925年12月,第8期,第79-82页。
[42]卓呆:《明日之上海》,《新上海》1925年6月,第2期,第89-94页。
[43]卓呆:《明日之上海》,《新上海》1925年10月,第6期,第127-132页。
[44]天笑:《新上海》,《新上海》1925年5月,第1期,第191-203页。
[45][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46]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
[47]天笑:《新上海》,《新上海》1925年5月,第1期,第191-203页。
[48]刘柱章:《陶渊明的乌托邦》,《艺林旬刊》1925年5月,第4期,第3-4页。
作者:李永东;载《文学评论》2014.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