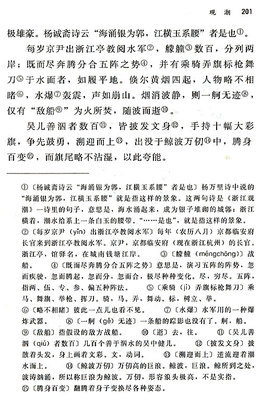陈孝荣中篇小说《荞麦》连载一
1
荞麦坐在吞口的阶沿上,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峰和天际的交汇处。此刻,黄昏正在无可挽回地逝去。四周的一切正在渐次模糊。所有的物体也都在黄昏里选择隐退,大踏步地陷入混沌之中。惟有天空还在做出最后的努力,在天际与大山的交汇处用力地睁着眼睛,保持一点点薄羽般的亮光。但它也不可能止住时间的手指。时间无可抗拒的力量会轻易地按下天际的眼帘,让黑夜顺利地抵达。公公和婆婆就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乘凉。没有发出哪怕一丝轻微的细响,一如他们的呼吸被阻塞了一般。但警惕的触须却布满四周,随时都在监视着荞麦的一举一动。
公公今年五十五岁。名叫丁四宽。身体还一如山里那些圆滚滚的石头,异常硬朗。行动也是异常敏捷。略微显出老态的,只是硬撅撅的头发和胡子里参杂着的少许白发。模样与山里那些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也是大山结出的一枚果实。中等个头。脸膛饱满。有一双粗大的胳膊和粗壮的双腿。那双讨生活的手也是出奇地大。不大不小的眼睛里,看上去似乎也装着善良。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装着千万吨的能量。愤怒时的咆哮几乎能淹没整个村庄。他搬了把木椅,坐在稻场里。上身打着赤膊。下身穿着一条淡黄色的西装短裤。看上去,恰如一只青蛙潜伏在那里。一双塑料凉鞋被他脱了,放在脚前。脚则放在凉鞋上。脚尖向上。那十根乌黑的脚趾,似乎是在向天空讨要着什么。坐在那里的他,尽管看上去一如一只懒猫,身上的每一处都放置在悠闲里。然而,那却是一只真正的老虎。现在的样子,不过是一只吃饱喝足后处于休闲状态的老虎而已。那些狂风暴雨般的凶暴就躲在那种悠闲的背后潜伏着。
婆婆今年五十二岁。叫杜红芝。她连一根白发都没有。脸膛红润。身材中等。面相看上去,与山里那些普通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经过大山打造之后的家庭生活主宰者。略显微胖的脸上,张贴着穿越生活之后的和解。身体里透出的活泛,一如一只呼噜呼噜转动的陀螺,时时都在表明她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激情。那对羊眼里似乎装着母性的温柔,荡漾时也能看到她的宽阔。然而荞麦知道,那都是假象。她那张脸其实就是个魔术箱,里面能根据需要,随时变幻出符合情境的表情。尤其是她那张嘴,能根其所需随时掏出锋利,或是温柔来。她就坐在吞口下。上身穿一件罗汗衫,下穿一件灰色的薄裤子。脚上穿了一双红色的拖鞋。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看上去,恰如一只灰色的母狼守候在利益的门口。那份刀子般的凶狠就隐藏在休闲背后安睡。
荞麦就坐在婆婆另一侧的阶沿上。她是丁家刚刚进门半年的新媳妇。娘家离这里约三十多里。她今年二十四岁。模样不说一如刚刚出水的芙蓉,起码也一如山里那些饱满的水果。饱满、匀称、晶莹剔透。那份美丽能瞬间让见到她的男人失去知觉,好半天才能回归现实世界。苗条的身材和娇好的五官,把她放进美女丛中,即便她算不上出类拔萃,起码也能独立成林。青春的气息一如亮光,从她的身体里冒出来,也能点亮她身边的一切。当然最亮的部分属于她的双眼。那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双眼皮,宛如成熟的葡萄那样诱人。那里随时随地都装着无邪,一如清澈的河水,河底的一切粒粒可数。她穿了一件极为普通的灰白色连衣裙,坐在寂寞的深处,接受着公公和婆婆的监视。
此刻的她,并没有关注眼前的黄昏,也没有对天空的努力产生任何兴趣。此刻,她的思维与情感正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向下坠落。因为她怎么也弄不明白,新婚不久的丈夫刚刚一走,家里曾有的和谐就成了易碎器,那么轻易地就被打破了。
打碎和谐的原因其实很小。就是她的丈夫离开之后,公公和婆婆怕荞麦耐不住寂寞,跟别的男人睡了,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或是她的思想开了小差,偏离她的男人,沿着一条他们所不熟悉的小路,依附到其他男人身上。而且最初也不是以打破的形式出现的。公公也没有参与。记得当时是丈夫离去后的第二天,荞麦吃过晚饭之后,去百合家玩。百合也是从外地嫁到这里来的新媳妇,只是时间略比荞麦早一些。模样也长得好看,经历也大体与荞麦相形。因而,她与她之间就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给紧紧地系在一起。尤其适合打发寂寞远离,两人在亲热里一点点靠近心灵取暖,并在交流之中积累生活经验和穿衣打扮的心得。而且两家离得近,大约半地里的样子。荞麦的双脚迈出大门的时候,太阳早从西山的山口归了巢,睡觉去了。乡村也在傍晚里按下骚动,准备洗脚休息了。没想刚刚一出大门,婆婆的声音就跟着她的脚后跟赶了过来:“荞麦,晚上你到哪里去?”语气的背后依旧是一如往常的温柔,不愉快的东西一件也没见到。
当时,荞麦的心里也是空白一片,并没有提防之类的东西爬出。哪怕一只小小的蚂蚁也没有,只有新媳妇的无邪。所以她便回答说她要到百合家去玩。
婆婆接着说:“一个女人家,晚上出去做什么?”
这句话,让荞麦捕捉到婆婆话背后的意思了。就笑起来:“我又不做坏事。”挂在脸上的笑,一如开出的一朵艳丽的花朵。
“牛娃子不在家,你晚上不要出去了。”
“我行得正,怕什么。”说过,荞麦还是去了。
但荞麦万万没有想到,她的那双脚一迈出去,就是迈进了一个万恶的深渊。
这天晚上,当她从百合家回来之后,一推开大门,就发现公公和婆婆并没有睡,而是坐在堂屋里等她。灯影里的他们,一如坐在那里守候着猎物的凶猛动物。脸上凝重的色彩一如岩石,生硬、冷漠、毫无生命力。堂屋里的一切也似乎在灯影里屏住了呼吸。荞麦一出现,他们就轮番地对她进行了教育。
一开始,他们的语气里也塞满了好言相劝,并没有恶意。所说的话语也无非是谆谆教导她,要爱护自己的名声。女人必须行得正,坐得稳。女人的护身法宝就是好名声。有了这个法宝,女人一生才会风调雨顺,平平安安。所以女人必须小心地把这个法宝呵护在手心里。当然还包括农村的现实。因为现在农村的单身汉多,那些臭男人对女人都是虎视眈眈。即便你荞麦有保护自己的意识,而且那意识钢铁一样强硬,但外来侵略都是虎狼之师,一点小小的破绽就会弄出天大的事来。但荞麦却实在听不下去。在她的意识深层里,那种相劝,一如把不存在的污水往她身上泼。劝说的情形,也一如他们站在一个高高的山岭上,对她指手画脚。即便他们的出发点一如软虫一样善良,但结果却是对她自由的严重侵犯。所以她就顶撞了他们几句。也就这样,家里的和谐就被打破了。从此,他们恶语相加,什么“骚货”“你痒呀?”“你过不得呀?”等等之类的话就如恶浪一般将她深深地淹没。公公咆哮的声音犹如响雷,爆炸在乡村的每一个空间里。婆婆刀子一般的嘴,划得荞麦的心里鲜血淋淋。倘若如此倒也罢了,他们除了恶语相加之外,还严格地把她看管了起来。他们规定,她的身影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晚上睡觉之后,他们得在她的门前放上一把铁锹。那把铁锹就是他们设置的第一道防线。只要荞麦从屋里一出来,一拌动铁锹就会给他们发出信号。他们就会根据信号做出相应的反应。除了这第一道防线之外,他们还加了最后一道,也是最为保险的防线,那就是公公和婆婆就睡在她的屋外。倘若荞麦要逃出,必须首先经过他们那一关。也就这样,荞麦一如被包裹在壳中的核桃仁、或是花生仁之类的东西,被紧紧地看管了起来。哪里也动弹不了。
所以,这件事情让荞麦明白,尽管打破和谐的引子极小。但背后所隐藏的动因却很大。那个动因就是自私。顺着那个线头,荞麦朝深处走去,结果却让她大吃一惊。因为她发现自私那东西可不一般,它们并不是长在人心里的植物,而是恶性肿瘤。那个恶性肿瘤到底是从母腹里带来的,还是后天长成的,荞麦也一无所知,但她知道它们却是万恶的根源,可以把一点小小的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而且它们的力量也宽大无边,一如宇宙一样覆盖了生活的所有区域。力量一旦施展起来,就一如隐藏在人性之中最锋利的剑,可以轻易地摧毁一切。至少眼前的事实告诉她,表面上,公公和婆婆是为她好,而其实是为他们的儿子好,为他们自己好。倘若荞麦真的一旦出轨,伤到的只能是他们的尊严,荞麦从此或许会过上另一种新的生活。而且农村的现实也确如他们所言,不仅是那些单身汉,包括留守的女人在内,全都是虎狼之师。他们耐不住寂寞的膨胀,全都张开虎口狼牙。任何藩篱都形同虚设。
然而这种看管,却严重地伤害了荞麦。在他们那种一日严似一日的看管里,荞麦逐渐发现,她已不再是荞麦,也不再是丁家的媳妇,而成了他们眼中的一件私人物品。他们可以随意地处置、监视、看管、甚至伤害她。因为现在的农村,娶媳妇的难度是夼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块天。养儿子的家庭,均会被这块天给塌得弯下脊梁。生命也会在那种压迫之下,一日强似一日地被摧毁。所以一旦拥有了媳妇,那种看管就必得如同生漆焊接一样,牢牢地焊住。原因在于外面的诱惑是一张无形的、宽阔的、同时又是如此甜蜜的一张大网。他们怕荞麦经不住甜蜜的勾引,而心生翅膀,跟着别的男人振翅而去。所以他们就轻易地揭去那张虚伪的和谐面皮,用另一张更加严密的网把她严严地看管起来。
由此看来,原来的那些和谐不过是装出来的一张虚伪的面皮,经不住任何考验。它一旦破裂,那种爆炸比现实之中的任何炸裂都要惊心动魄。听不见一丝游丝般的声响,它们就一如炸裂的气泡,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片碎渣也不曾寻见。或者一如一条虚拟的蛇,消失进了历史的天空。但它的杀伤力却比现实里的炸裂要严重得多。现实里的炸裂最多不过血肉横飞而已,可那种炸裂却伤及神经、尊严和人格。内心的鲜血血流成河,却看不见现实的伤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荞麦的思维与情感就一日日开始坠落了。
那种坠落自然也非现实里能看见的那种坠落,而是一如飘在空中的柳絮,缓慢地,同时又是钝刀子割肉般地坠落。她能明明白白地看见鲜血、刀子缓慢进展的进度,但就是不能痛痛快快地解决问题,一刀到底。坠落的四周,也全都是那种没有软乎乎的质感、没有黑洞洞的黑暗,更毫无温暖与拥抱感可言的沼泽。它们类似于一种透明的、悬浮的、无底的,同时又连着血肉与精骨的一种沼泽。那样宽阔,那样的白雾茫茫,怎么也找不到分割的边界。在这样的一种坠落中,她觉得她的呼吸是越来越细了。仿佛谁用一种她不明了的方式,正在一点点收缩她呼吸的通道。怒火也正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隐隐地燃烧。意识的视线能清晰地看到那些山头上的怒火。它们就那么明目张胆地,同时又是温吞吞地燃烧着。一点点烧毁她的生命植物和绿色的激情。淡淡的烟雾笼罩上空。而她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更让她不能承受的,则是神经正在一点点接近极限。似乎那里有一双巨大的手,分别捏住她神经的两端,朝两边用力的拉扯。神经在那样一种拉扯中,只有一根细细的丝线相连了。那种丝线细得宛如蚕吐出的蚕丝,随时都有可能挣断。
这样,当荞麦心头的怒火在坠落中慢慢地旺盛起来,她便没等天空的眼帘合下,就忽地一下站起来,返身回到她和丈夫独有的房间里。
2
房间是新婚不久的新房。粉得雪白的墙壁、大红的囍字、洁白的蚊帐、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隔绝外界的淡绿色窗帘、头顶的日光灯,以及她的一些私人用品。凡此种种,都在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荞麦。因为丈夫离去多时,房间里再也不储存他的任何气息了。就如同房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保管,没能把他的气息保管住。现在这个空间里,剩下的惟有荞麦的体香。它们从荞麦生命内部的涌泉里涌出来,塞满每一片细小到看不见的空气细胞中。淡淡的,又浓浓的。时值盛夏,从外面涌进来的热气,又带着火热的热情推波助澜,使它们更加活跃与激动。每一丝、每一缕都似乎带着火红的、昂扬的激情。
打开灯后,荞麦便返回灶屋,提了一桶温水过来。然后关严房门,开始脱衣服,准备洗澡。
可是当她把自己完全剥光的时候,荞麦却停止了下来。一如她在不经意间触动了一枚制动的按钮,她便犹如一根木头,直直地站在了那儿。那个只对少数人展示过的优美祼体,静静地止立在时间之中。雪白的肌肤一如刚刚剥出的竹笋,鲜艳欲滴。梨形的乳房坚挺地站立着,宛如两只美妙绝伦的精美瓷器在幽暗之中发出的神秘光芒。娇美的身体曲线似乎来自于天工之作,每一处起伏,每一笔细小的线条,以及线条的变化、走势,都是那样的恰到好处。但她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却被某个看不见的刹车给制在了那儿,与前面的那个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紧紧地连成一条直线。尽管那里的神采依旧,但成了一副凝固的画。青春的脸上也似乎僵直了,置了大片的荒凉。仿佛一座停在那儿的钟,不再对这个世界呈现出喜怒哀乐。
房间里塞满了寂静。它们一如听话的猫,呆在空气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荞麦。房间的物件也都一动不动,似乎傻了一般。乡村坐在静谥里,一如听话的孩子。通过空气传播过来的邻家的日常性话语,以及偶尔插进来的几声狗吠,更是增加了寂静的厚度。鸟也歇了,睡在它们的巢里歇息累了一天的嗓子。但这一切均没有进入荞麦的内心,只是擦过荞麦的意识边缘就消散了。此时的她,正沿着思维的绳索,回到了事情的原点。
荞麦是在东莞同现在的丈夫认识的。丈夫叫丁松,小名牛娃子。今年二十六岁。是一个长得还算标志的男人。将近一米八的个头,还算周正的五官,以及那浑身劲暴的肌肉,都能给人一种牵引般的引力。当然这一切,都没在荞麦的内心里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占据那个最高峰的,则是牛娃子会木工和水泥工,以及他的眼里和行动上透露出的汩汩诚实。就木工和水泥工来讲,它既是牛娃子的二门手艺,同时也是荞麦可以依靠的一个靠山。当时,他正在东莞一带帮人装修房子。荞麦则在一家电子厂做普工。就辛苦程度而言,她似乎比牛娃子还要累,然后结果却完全相反,他每月的收入几乎要比荞麦高出一倍。做为一个女孩子,以身相许之前,必须先让男孩子用稳固的生活相许。所以她不选他的家,不选他的父母,单单选中了他的人。至少那两个手艺让她看到了,他们通过双手可以驾驶生活驶向光明。
当然更为主要的,则是牛娃子的诚实。那是女孩子最好的一座靠山。牛娃子的眼睛并不大,也不算小。任何缺陷也没有。安装在他那张略显消瘦的脸上,算是恰到好处。当然那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的那两只眼睛里,时时露出的诚实。那诚实一如水中的鹅卵石,无须特别注意,就清晰可见。在他们交往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从来都没从他那两只眼睛里看到过虚伪的影子。
还有,尽管他的嘴并不会说,但他的行动却是灵敏的天平,随时都知道讨荞麦喜欢。他既舍得为她花钱,也知道讨其所好。吃的、穿的、用的,都能送到她的心坎上。所以跟他在一起,荞麦总是觉得潜藏在她内心的快乐一如风,从深处吹来,让她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这样,她就认定他了。
不过严格说来,认定牛娃子时她内心深处有过异常痛苦的纠结。因为荞麦一开始,就没打算找一个鄂西山里人结婚。从鄂西大老远跑到广东,漂泊数年,最终还是回来吃窝边草。这让她觉得她真的一如兔子,漫山奔跑之后依旧还是回到旧窝。几年的时光算是白白地浪费了。所以她有点不甘心。但当时恰逢荞麦的爱情遭遇了阴雨天。一个与她相爱的小伙子突然和她吹了。那个小伙子是湖南人,与她同一个厂工作。所不同的,只是那小伙子是大学生,在厂里从事管理工作。而荞麦不过是一个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大专生而已,两人的地位隔着一条鸿沟。那小伙子之所以看上她,原因还在于他看上了她的漂亮。所以,当另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现的时候,荞麦就被她的漂亮击败了。同时被击败的,还有她的地位。因为那女孩子也是大学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荞麦经过同厂女友的介绍,认识了牛娃子。很快,她就被牛娃子占据了她内心的那块空白,驱走了连阴雨。再加上相识一年多以后,一一验证了牛娃子的勤劳与诚实,荞麦就不打算再选择了,便把希望的准星对准了牛娃子,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这其中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她的年龄也在背后催促她,让她不能再等。她已经二十四岁。这个年龄对于山里的女孩子来讲,已经是大龄青年了,再也经不起折腾。倘若放走了牛娃子,再重新认识一个男朋友,起码又得花去几年时间。那种无可把握的折腾,一如懒婆娘的缠脚,说不定会拖到二十七八,甚至三十岁都未可知。所以去年从东莞回到鄂西之后,他们就办了结婚手续,并于腊月十四办了婚宴。
婚宴自然也说得过去。无论是她的娘家,还是婆家,均倾其所有,为他们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因为她和牛娃子均是独生子,父母积累了大半辈子的人情世故,也都是指望在这一铳药上放个大的响声。响声自然很大,亲朋都到了场。门槛也差点挤破。那种热闹、排场、浓浓的亲情、做新娘子的美好,都成为最美好的回忆,被她牢牢地收藏进了她记忆的房间。有时,还常常被意识拿出来晾晒一番。
婚后,她也坐在幸福里陶醉了一段时间。与牛娃子的痛快而又温馨的缠绵,也被意识刻在了记忆的底板上,一如太阳一样鲜活。
可是今年开春之后,牛娃子与村里的建筑队出去的时候说什么也不再带荞麦了。而且他的理由也一如那些大山一样很充分:“你就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生孩子。”因为当时她的例假停了。
“那不行。”荞麦不同意。“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不要把我困死呀。”
“你说你跟着我,我怎么照管你?”牛娃子说,“我们搞装修,没个固定的地方。”
“谁说要你管了?”
“还进那些破厂呀?”牛娃子说,“能挣几个钱?”
这样,荞麦就只好留了下来。
可是没有想到,当牛娃子的身影一如大雁从山口消失之后,荞麦的灾难也就接踵而至了。
3
“荞麦,你洗个澡怎么洗这么长时间呀?糊的些什么洗不干净呀?”
婆婆的声音一如摔碎的沙罐,生硬地从屋外传来,一下子就切断了荞麦的思维。随即而起的怒火也瞬间就在她心里燃烧起来。然而荞麦并没有回嘴,而是回到现实之中,坐下洗澡。因为她知道,她的单纯还是一对娇嫩的翅膀,无法应对现实的复杂与人性中的凶险。别说接嘴,即便行动上做出反抗的姿态,都会被他们凶猛地打压下去。一如将一颗鲜嫩的菜苗放进开水锅里,根本就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所以在经过了他们凶猛的打压之后,荞麦一方面在痛恨她的单纯,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出路。
单纯并不是荞麦的错,错的是这个现实。是这个复杂而凶险的现实,让她的单纯没有生长的土壤。
当然,荞麦的单纯与她的年龄有关。人生那东西,总是在时间里的一种由单纯到复杂,又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任何一个个体总是从单纯起步,逐步认识这个世界,又逐渐知晓人生是怎么回事的。荞麦也自然不可能跳跃过去。没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经历,没在复杂那口大锅里煮上几回,她不可能步上复杂的颠峰,也更是无法学会用简单应对复杂。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然与她的善良与经历有关。荞麦出生在一个叫壶口嘴的地方。那是鄂西大山中最普通的一个村子。百十户人家犹如一张面饼,张贴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白墙青瓦的房屋一如被谁不经意间洒出的一把种子,散落各处。有的依山而建,有的临水而居,有的被绿树包围,有的则高高地炫耀在某个山包上。海拔约在一千米左右,算是半高山。出产油菜与水稻。主粮也还是以苞谷为主。荞麦的家在村子的中部。算是单家独户。与邻居最近的距离也在半里地左右。荞麦的真名也叫覃荞麦,因为她出生在荞麦生长的季节,她的父母就望着山间那些绿油油的荞麦随手捡了这个名字。所以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再加上又是独生女,荞麦更多的时候就只能与独孤为伴。因为孤独那东西位于生活的另一侧,从来不与生活搭界,它不可能教会她复杂。
她父亲叫覃世好。五十二岁。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也是个善良的好人。父亲中等身材。生得秀气,一如烟杆一样精精瘦瘦。只是笑容也时常如山里的野花一样,开在那削瘦的脸上。脑子里也从来没有算计别人的那样一根弦。对女儿也是百般宠爱。所以父亲不会教给她复杂。
比较而言,母亲周兆红则对荞麦要严厉得多。与父亲相反,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胖胖的,现在年已五旬,脸上还有两团红晕。模样也算好看。在村子中人缘极好。母亲对她的管教一如粉刷墙壁,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细小的角落也不曾放过。不过,母亲的严厉是慈母那厚厚的土壤里长出的参天大树,送给荞麦的是绿荫般的保护伞。因为她怕女儿受到伤害,就强行地给她灌输生活经验和学会保护自己的意识,也并非教会她如何狡猾,怎样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就信息而言,公路也通到了山里。卡车、轿车的引擎声也时常与山里的鸟儿们遥相呼应。电视作为连通外界的桥梁,也铺设了数年。但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最多也只是牵引出荞麦的羡慕与向往,并没有教给她任何复杂。
所以在她的成长道路上,荞麦从来都没有被灌输过“凶狠与复杂”。她的内心深海之中涌动的全是善良朴实、勤奋好学、努力向上等等之类正面的能量。
高中毕业后又去一所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大专院校读了两年书。之后就随人去广州、东莞一带打了几年工。所结识的也都是与她年龄相仿的青年人。那些年青人中,或许有着接受过复杂信息的人,但并没与荞麦行走在同一轨道上。即便发现有这方面的影子,她也能本能地回避。所以就其生活而言,过去她几乎算浮在生活的表面之上,一如飘浮在水面的一层油,并没有深入里层,不知水深与水浅。在她的意识深层里,认为这个世界是无邪的。即便有坏人,那也只是少数。他们最多也如同掺在米饭里的砂粒,一旦挺了牙齿,就会被毫不客气地吐出。所以那些坏人也无须她担心。
当然爱美之心她也不弱于其他女孩。同其他女孩一样,别的女孩就是自己的镜子。无须动多少脑细胞,就对着那镜子学会了一切。衣服的样式、色彩、面料、质地,都会有风向标给她指引。头发该整理成什么样子,也有着榜样摆在前面,无须刻意。花时间去整理出来的新式头型既要保持不另类,也不要太过朴素,反正在中游的水平线上游荡不会招来麻烦。化妆品一样也不少。尽管购买不起昂贵的,但种类齐全。常常化点淡妆,让人一看看不出化过妆的样子。手指甲、脚指甲也常常涂油,但不至于招摇。模样娇好,无须整容。眼睛不近视,无须戴眼镜。眼睫毛长长的也好看,假的根本想都无须想。总之爱美方面,一切都保持在自己能操控的范围内。欲望从没有大到超出自己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一旦到达那个限度,欲望也就到这里止步了,并不再往前越过半步。所以欲望也没有出卖过她。
性格方面,她自信她属于温柔的那种类型。那种温柔也在成长的路途中,一点点打造好了尺度。不长也不短,正好合适。既知道体贴人,又不粘连人。既不强势,也不缺乏主见。既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升官发财的野心。傍大款、大官的想法从来都不曾发过芽。生活自理能力更是没说的,样样都会。总之,把自己放在一个秤杆上等量,自己对自己也还算满意。普普通通,平平凡凡,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绰绰有余。
至于色狼也从来都没有碰见过。对她表现出好感的小伙子,或者男人,可以排成一个长长的队伍。但一般情况下,荞麦不会轻易对人打开情感的大门。对于怎样识人,她的内心里也有一把尺子摆在那儿。只要一见面,那把尺子的刻度就会告诉她对方的诚实程度。一般达不到那个刻度的,她就首先隐身而退了,没给人以可乘之机。
至于爱情,曾经也有过异常丰富的幻想。而且那种丰富有着她数也数不清的层次,一如亿万年的堆积层。并在过往的岁月里浇灌过她的心灵,让她觉得前方的一切都是那样美好。但认识牛娃子之前,真正算得上恋爱的也惟有两次。一次是在学校读大专的时候,与一个叫毛四开的同学有过一年多的爱情经历。毛四开来自于农村,长得也算标志。但那个愣头青留在她记忆里的,也只能算个哥儿们,或是姐儿们之类。爱情的温度并不高,不过是两个男女青年为了排解寂寞的一种相互吸引而已。尽管她把初吻给了他,尽管他曾不止一次地要求出去租房,或是去宾馆开房。但荞麦始终没有让他突破那道防线。即便内心的激情高过世上最高峰的时候,她也只让他摸过她一次。并且也只让他点到为止。此外就让他彻底止步了。一走出校门,面对日常生活那张枯燥乏味的脸,他们的那点细嫩的感情就在时光里蒸发了。如今想起来,出现在记忆天空里的也只有几朵淡淡的白云。
另一次就是在东莞那家电子厂认识了那个湖南小伙子。那小伙子叫周叶青。人倒长得并不怎么样,不过也没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基本上算拿得出手、对得起观众的那种类型。最初她也没对他产生过哪怕是一点好感之类的情感。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人家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又在电子厂从事着管理方面的工作。她不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妹。他们属于不同的层级。就如同墙内与墙外的风景,他们隔着一层厚厚的墙壁。他的鲜艳属于墙外的风景,与她毫无关系。所以她和他的恋情,是周叶青在她的内心里点燃的一把火。最初,那把火由他的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开始擦出火星。他见到她的时候,总是自顾自地来电,一如孔雀的开屏,一见到美丽的女人就自动地展开美丽。荞麦在他的电光中,也一点点察觉了他对她的好感。但那时火星的力量还有些微小,并没在荞麦那里产生哪怕一点点细小的热量。直到后来,他请厂里要好的姐妹把那层纸捅破,她才知道他来真的了。也就那样,荞麦内心的那把火就点燃了。因为随着一点点走进他的内心,她发现走进了一个风光秀美的避风港。周叶青聪明,又有幽默感,而且也知道讨她欢心。所以她便把她保护最完好的初夜交给了周叶青。可没想到,周叶青却用喜新厌旧,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内心。那里的伤痛也直到和牛娃子相识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地愈合。
不过总体说来,在爱情的路上漂泊五六年,谈了三场恋爱,也同样算是前行在单纯的路上,一切都算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并没有见识险恶,学会复杂。直到嫁给牛娃子,进入丁家,才算真正地进入这个现实世界的中心,开始与人性中最恶的那一面迎面相遇。
可是,出路又在哪儿呢?
倒了洗澡水,荞麦躺到床上,被黑暗轻轻地包围。她再次启动思维的按钮,开始寻找出路。
这种寻找她也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但每一次她不过一如一只闯进人群中的绵羊,只能左冲右突,就是找不到出路。因为与公公和婆婆闹僵,被他们严严实实地看管起来之后,她曾数次找过牛娃子,也曾找过母亲,希望在他们那里寻找到答案。可是他们却给不出任何方案。
牛娃子只是在电话里和稀泥。“至于吗?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们是为你好。”
“牛娃子。”每次一听他那无关痛痒的腔调,荞麦内心的气就一如蒸气,呼呼冒出。“你再要这样,我不理你了。”
牛娃子就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如公羊发情。
“牛娃子,你再要这样,我就和你离婚。”
“至于吗?荞麦。”
“我在家里受不了你父母的压迫。要不我也到东莞来。”
“你来干什么呀?我给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漂泊不定。”
“我没说一定要来找你。”
“你敢。你别想一个人出去混。我不会同意。”
“反正我也没怀上。”
“没怀上也得等等。你说为一颗种子我大老远跑回来也不划算。”牛娃子乐了。“反正养孩子迟几天无所谓。到时我会一打一个准。”
“不和你说了。”
每一次,也总是荞麦率先挂断电话。
而回娘家找母亲。母亲在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脸上竟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有什么不好?说明他们在乎你。”
“妈,不是你想的这么回事。”
“你行得正,坐得稳,时间一长,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
所以母亲的态度也是让荞麦急不死。
脑海里也曾经出现过快刀斩乱麻的想法,干脆与牛娃子离婚算了,彻底逃离这个地方。可是荞麦还是下了不这个决心。因为到目前为止,牛娃子还算对得起她。他们之间依旧有一根感情的线索相连。她并不想一下子拧断。所以那样的想法也只是一丝淡淡的影子,经不起任何风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这样下去哪里会是头呢?
至于出去打工,那也是一条行不通的路线。打工当然不是不可,她随时都可以出发。问题是打工也只是暂时地逃离公公和婆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们的包围圈依旧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心里堵上的石头也会顽强地存在于那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