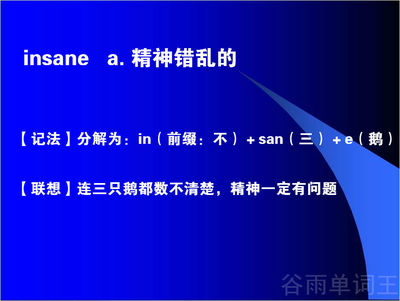安贾德·库扎巴迪(AnjadQusaibaty),现年28岁,叙利亚人,出生于大马士革。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和MBA学位,第二硕士在读。诗人。曾以阿拉伯语出版短篇故事集《硅》。因在叙利亚内战中撰写批驳阿萨德政权的檄文,被当局通缉,被迫流亡海外。现居荷兰鹿特丹。
以下故事为当事人口述,录音整理。
我的故事其实只是千千万万我的同胞们的一个缩影。我认为我足够幸运,才能够坐在这里,手里捧着咖啡,告诉你这些我的过往,以及我为什么来到这生活。你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大潮里人是多么的渺小与无助,甚至不能够独善其身。
这个故事开始在突尼斯,西方人叫它“阿拉伯之春”。
那是2010年12月的一天,一名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在街头用他的小推车贩卖果蔬时被一名女城管收走了物品。期间产生了肢体冲突,据说是被扇了巴掌。可能是因为没有某个层次上的“关系”,亦或是没有足够的金钱赎回商品,他向市政厅的申述被驳回。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不能承受这样的屈辱,所以他将自己的身上浇满汽油,在突尼斯一座小城的广场上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半岛电视台报道了这个事件。在那之后,人们被这个事情激怒了,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情绪逐渐由具体的事物转移到对当前政府,特别是政府领袖的不满上来。仅仅一个月时间,被认为是近东两个最为稳固的独裁者之一的本·阿里被赶下台,逃亡去了法国。人们说他的妻子从突尼斯中央银行带走了大量的财产,主要是黄金。突尼斯政府垮台后,这场被西方媒体冠以“茉莉花”之名的革命迅速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约旦、巴林,等等。一些独裁者非常聪明地在革命刚爆发的阶段出台了一些措施,譬如阿尔及利亚的独裁者将人们的食物配给削减了一半,所以人民敢怒不敢言,革命的火焰以非暴力的方式被迅速扑灭。在沙特阿拉伯,大量的现金被分发到户,政府还承诺大量修建免费住宅,人民得以保持沉默。所以在沙特,事情不是那么的棘手,因为经济较好,而且国家有大量的石油贮备,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较高。
这场革命的高潮发生在埃及。首都开罗有一个著名的“解放广场”,在那里,上百万的人聚集在广场上,昼夜不停地进行着抗议示威。大量的警察试图维持秩序,但是人实在是太多了,不管他们做什么,阻止这次示威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另一位被认为是近东最稳固的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也被迫下台,下台之前他委任了一位特别助理管理过渡时期政府,直到下次大选。
当时的叙利亚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风暴临近。因为在社交网络上早就有专门的主页宣传这次革命(SyriaRevolution),呼吁推翻阿萨德政府。所以他们有一个国家安全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全国范围内布置大量的秘密警察进行监听工作。如果你看过那部著名的东德电影《窃听风暴(DasLeben derAnder)》,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比那个还要更加的真实和严重。在叙利亚,最开始是德拉市的一间学校的学生团体,在墙上书写独裁者下台的言论,被秘密警察知晓。当天夜里秘密警察抓捕了其中的7人,并进行了刑讯逼供。人们闻讯赶来,包括一些重要人物,请求当局释放学生。当然,请愿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秘密警察将学生押往大马士革审讯后,撬掉了他们所有的指甲,然后让他们回了家。这个事情引起了人们非常强烈的抗议。所以在叙利亚,抗议是在首都周边城市开始的,逐渐蔓延到首都各区。当然,当局使用暴力的手段镇压人们的抗议活动。当庞大的人群向首都中心广场聚集时,阿萨德(叙利亚独裁者)下令警察使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阻挡人群,和人群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其实在我们国家,抗议是最开始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人们也并非想要将自己的诉求绑上武力的外衣。很多人最开始时还手捧鲜花,参与游行。但是当政府使用暴力镇压抗议的时候,就有人使用武力开始了反击。流血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在此期间,政府禁止所有除官方媒体以外的媒体或社交通道报道这次抗议活动。阿萨德政府一直强调,参与抗议的人群很多都不是叙利亚人,这是一次有组织和有预谋的颠覆政权的行动。实质上,真正从外界进入叙利亚参与内战的那一部分人,两年以后才出现。心虚的政府捏造了很多虚假的事实用以误导民心。
逐渐对局势失去掌控的政府开始采用更加极端的方式对待民众。军方开始使用实弹进行示威镇压,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军人都愿意面对着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他们中的一部分脱离政府方面,加入了一支成分复杂的反对武装力量,这就是后来的叙利亚“自由军”。再后来,正如你在新闻里看到的,我的祖国,叙利亚,开始了内战。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我出生于一个上层家庭,虽然我们居住在首都大马士革,起初我的感觉是战争离我还是很远的。
当内战刚开始的时候,那是2011年的3月,我保持着沉默。但从我懂事开始,就反对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的独裁,我对他们统治国家的方式感到厌恶,包括他们对待不顺从民众的方式,对待有异议者的方式,就是统统把他们关进大牢,标榜为叛徒,被折磨至死。
当然我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能够看到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于提振国家的努力,包括在外交上试图和法国,包括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等等。他有很多的支持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英国取得了博士学位,人们觉得他比他的父亲老阿萨德(叙利亚上任总统,2000年去世,自1970年代开始在叙利亚执政)要更为优秀。
老阿萨德的另一个儿子则把持着暴力机关,确保政权的稳定性。这是一个典型的独裁者家族。任何“不听话”的人在他们眼里看来,就是叛徒,会被处以极刑。
内战最开始的时候几乎都是叙利亚人之间的战斗,正如我刚才讲的,两年以后(2013年),一群极端伊斯兰教徒进入叙利亚,加入了战斗,并试图进一步恶化局势。他们从一小撮人迅速壮大了为成了一支行为非常极端的军队,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的极端思想,甚至是出版刊物,吸引全世界的宗教极端人士加入他们。他们在占领区实施非常残酷的伊斯兰教法,折磨民众,斩首各国记者。他们现在拥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部分土地,人们叫他们ISIS(伊斯兰国)。
但当内战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我是高兴的,心理面想总算是有人揭竿而起了,我在前两个月保持沉默的原因是我想要观察一下局势,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止不住心中熊熊的怒火,开始写东西。那时候我什么都写,诗歌、文章,但不是很多,大概10来篇的样子,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发布出去。如果我被抓住,这些文章足够让他们把我判刑至死。有人只写了一篇,就被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一名医学院学生,只写了一点点文章,就被秘密警察在街头带走了。期间受到了军政府的虐待,所幸家族里有成员在军队,将人捞了回来,否则他很有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虐待。所以,总之当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的家庭非常担心我,他们试图做所有的事情让我在脸书(Facebook)上删掉我发布的文章。但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写作者”要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既写文章,又到街头抗议;还有一种就是我这样的,我只写文章,风险会小一点。有些人发布文章会使用假名,但是我不会,我直接地使用我的真名。有些人会使用隐喻(Metaphors)来讽刺时政,我则是就事论事,非常直接,用我自己的真名。
我的家人吓坏了,那段时间只要有人来敲门,大家都会变得异常的紧张。当然,我被带走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问了我一些问题,譬如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给与我警告,就放我回家了。很多我的朋友都被带走过,但是他们都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们被关在牢里,一个又一个月。
我的前女友,也被带走过。但那个时候我已不在国内,所以我们的交流仅仅限于通话和视屏,当我从她的家人处得知她被抓进去之后,心急如焚,想尽一切办法要救她出来,可是鞭长莫及。所以最后我还是可耻地妥协了,动用了我最不想动用的关系——在阿萨德政府担任部长的某位亲戚。
她被救出来了。
对于这件事情,我既感到悲伤也感到庆幸,如果没有这位亲戚对我的保护,可能当时的我也不会这么快被放回家,甚至会被虐待,更救不出我的女友。同时,我又为他为流氓政府工作而感到非常的遗憾。
当她被救出来的时候,据说身体非常糟糕。皮肤蜡黄、松弛,情绪接近失控,双眼无神,并且患有进食紊乱,无法进食。但是她对于她在狱中所遭受的事情只字未提,我也从不敢向她问起。
时间线拉回我还在国内的时候一点点,那个时候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压抑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被带走。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对我发出警告,还有来自朋友苦口婆心的劝诫。但是想要表达的欲望又无法让我做出停止写作的妥协。所以,我的家人开始策划让我逃离。
最终让我决定离开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2011年底,我在叙利亚完成了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依照政府的法律规定,育有两个男孩以上的家庭,在他们成年后必须全部为国服役一年半的时间,这是强制性的兵役。但是在战争时期,这就变成了一道强制性的动员令,不断地补充着政府军在战场上的人员损失。我不愿意加入政府军,也不愿意将我的枪口对准那些手无寸铁反抗的民众,更不愿意杀人。所以,逃离就变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时间来到了2012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告诉我的家人,我不想一次又一次地把你们置于危险之中,我也不想举枪去杀人,我也不想保持着缄默,所以,我决定离开这里,离开叙利亚,前往埃及。当我踏出叙利亚边境的那一刻,我知道很长时间内,我都回不去了,我将和我的家人相隔在两个世界,如果我在阿萨德政权依然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情况下贸然再次回国,在机场我就会被抓住,送进监狱,罪名在除了反动罪之外,还会被加上一条:逃服兵役。这可是重罪。而且,在被判刑之后,可能我还会被送回战场,被刻意安置在最前线,成为一名“光荣的”炮灰。
我有很多朋友在战争爆发前就在军中服役,直到现在。在大量的伤亡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超期服役,顶在前线。他们不被允许离开军队半步,哪怕是回家探亲,都不可以。
我从2012年起开始了逃亡。我最开始来到了埃及,寄宿在祖父家。我的祖父在埃及已经20年了,并且了有一些产业。我在那里申请到了一份在迪拜的工作,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打算前往阿联酋。但是突然却被告知签证申请未获得通过。就在那一小段时间内,我发现叙利亚的护照几乎一夜之间在所有的国家都失效了。一个接一个国家拒绝来自叙利亚的签证申请,就像一盏又一盏关上的灯。甚至是在科威特——我们有一半的家庭成员住在科威特,我的叔叔甚至还邀请过我过去为他工作,他在当地创办了一家企业。但是现在都不行了。唯一还承认叙利亚护照的国家,全世界范围内,只剩下了三个:埃及、黎巴嫩和土耳其。
当我发现自己在埃及之外的国家找到一份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之后,我开始在埃及境内寻找工作。但是埃及在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中同样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经济一蹶不振,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我又失败了。此刻的我已经接近破产,身无分文,靠家人的接济勉强生活。这时候我的侄子告诉我,他在黎巴嫩的一家创业公司工作,与老板有一些交情,他答应提供给我一份工作。于是我动身去了黎巴嫩。在等待了4个月之久后,这家创业公司遇到了问题,因此无法雇用我。这个时候我的黎巴嫩签证已经开始过期了,我不得不去大使馆申请续签。令我非常意外,甚至连黎巴嫩都拒绝了我的续签申请。
黎巴嫩物价非常之高,和欧洲主流国家相似,但是基本收入却只有这些国家的一半。如此高的生活成本使我连黑在黎巴嫩的机会都没有,垂头丧气的我又回到了埃及。期间我又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来回地奔波,试图寻找到一份工作,但是都没有成功。背井离乡、来回的奔波、无助、绝望,这些情绪和遭遇伴随我度过了2012年。
2013年,我放弃了在这些国家找到工作的想法,开始申请荷兰的研究生。其实我并没有选择荷兰,而是荷兰选择了我。他们提供了一份专门针对叙利亚学生的援助计划,只要叙利亚学生前往荷兰就读研究生,就能够享受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补贴。其实我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从学历上来讲,我并不需要另外一个硕士。但是这是我唯一能够留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的方法。可以说,我参加现在的研究生课程的唯一也是最终目的,就是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留在荷兰。2013年的7月我向荷兰寄出了申请材料。在等待期间,我又去了黎巴嫩。因为当时埃及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让我无法继续呆在那里。这次在黎巴嫩期间,我收到了全额奖学金的批复和入学通知书。
拿到这些东西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长久的压抑和无止境的迁徙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此刻在精神上我已经要好受多了,至少暂时是这样。我在黎巴嫩的一家DVD店找到了一份店员的工作,打发入学前的时间,顺便赚取一些生活补贴。那是2013年的9月到2014年的1月,我还要在入学拿到奖学金和生活补贴之前在黎巴嫩活下来。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00美金,我住在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只能够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还有一部电视机。房租是每月375美金,这只留给了我每月225美金的生活开支,通常一周不到就会被花光,所以最终我还是靠着亲友的接济活了过来。
凭借录取通知书我拿到了签证。2014年2月,我正式来到了荷兰,一个再也不用我东躲西藏的地方。我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尝试着重建我的生活。但当我在夜晚躺在床上时,经常会有噩梦袭来,我远在叙利亚的弟弟被抓走充军,我的父母被杀,而我却根本不能回去救他们。甚至连葬礼,都无法参加。
很多时候,我都是哭着醒来,房间的黑暗助长了无助的蔓延,我逐渐发现,这些事情,我不敢去想,也不能想。但是我的生活还要向前,我必须要在这里站稳脚跟。我的律师,从下个月开始,会帮助我逐步申请政治避难。帮助我取得荷兰的居留许可。只有这样,我才能救出我的家人。
尽管我们家属于中上阶级,但是在战火连绵的叙利亚,每个人的生存都会变得异常艰难。我很担心他们,可是,我又无能为力。我只愿所有的担心都化作乌有,愿我的家人在我救他们出来之前能够平安生活。
祝我好运吧。

策划/编译:雷司令原文刊载于微信公众号《世界青年》
世界青年请使用微信扫码关注我们或在微信搜索框中输入“世界青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