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试映会不到2个月时间,范立欣带着《归途列车》再次重归故里,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片举行正式的首映会。
在首映会的前夜,范立欣来到汉街文华书城,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演讲,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消息的影迷们蜂拥而至,看片的人一直排到了走廊深处,一些没有座位的人干脆就坐在地板看完了影片。三月的武汉依然笼罩着冬日的阴霾,但影迷的热情让范导大呼“武汉的朋友们太给力了”。
黑色外套,黑白条纹的T恤衫,简单的牛仔裤,再普通不过的行头;生于70年代的武汉,来自书香门第,五官白净清秀。从范立欣的谈吐中,旁人总是能从一种谦和的亲切感里,感受到来自他的独特气场。
回家的绿皮火车
影片的海报上有一列向前行使的绿皮火车,窗口露出一位大眼睛女孩远眺的侧影,眼神幽怨而不满,稚嫩而迷茫,这个女孩就是张琴,张昌华和陈秀琴的大女儿。
张昌华夫妇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从广州回家,需要先坐火车,然后转乘汽车,之后转坐船,最后再坐汽车才能达到,这里是景色迷人的小乡村,有翠绿的稻田,烟雾笼罩的江面,美丽却让人觉得没有希望,因为十分贫困。1990年,夫妇俩为了生存,扔下8个月大的女儿,到广州打工,成为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在镜头里,父亲张昌华大多沉默不语,眼神流露的情绪展现了他矛盾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母亲陈素琴的话语稍多,恰当的充当了旁白的角色。
这是一家典型的农民工家庭,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在寻寻觅觅的一个月碰壁中,范立欣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拍摄对象。摄制组跟随这个家庭拍摄了3年时间,1095个日夜,同吃同住,由陌生到熟悉,由抗拒到对摄影机的视而不见,在不断的磨合中,范立欣将这种关系调和到了最佳状态。
范立欣称张昌华为“张哥”,在三年的拍摄时间里,从2007年到2009年,他见证了这个家庭的裂变。由于缺少父母的照顾,初中毕业后的张琴叛逆不羁,和父母关系紧张而敏感,16岁的她跟着外婆干些农活,装满玉米的背篓把她衬得过于矮小,她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田里全部的玉米运回家。张琴跪在最爱的外公坟前,哭诉着对现实生活和父母关系的不满。这一年,张琴决定辍学,南下打工。走前一天的夜幕时分,张琴对弟弟说:“如果我走了,以后给外公烧纸这些事就得你去做,我也不可能经常回来,我也不想经常回来,怎么说呢,这里始终都是一个伤心的地方。”说完便沉默不语,久久的望着远方。范立欣说:“张琴曾跟我说,她想追求自由,对她而言,自由就是快乐。”张洋则是张昌华的小儿子,正在读高中,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外婆。
在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群像:拥挤不堪的广州站,黑压压的一片蠕动的人头看不到边际,人们拿着、背着、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焦急的翘首以盼,广播的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警察组成的人墙能在瞬间内被挤崩溃掉。当闸门打开放行,人流如潮水般涌入,冲散了上一刻还在身边的亲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春运,每年都要上演一次。
2008年是张琴第一次参与春运,也是她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深陷在春运拥挤的人流里,张琴觉得新鲜而好笑。恰逢全国遭遇雪灾,火车停运,60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焦急的人流几度导致场面的失控,未知的复车时间表让归家的人们陷入深深的不安和恐惧,不停有人高喊着“不要挤,不要挤”,却于事无补。张昌华一家在火车站等了4天4夜,在经过层层突围之后,他们终于坐上了归家的绿皮火车。陈素琴叹息着对张琴说道:“不好赶车只觉得很可悲,不好笑了,哪一个人觉得很好笑的,没有一个觉得很好笑的,只觉得很可悲,很遗憾不能回家过春节。”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有个女孩因为虚脱,被急救人员抬出了人群,嘴里虚弱的喊着“帮忙救我妹妹!”,接着妹妹也被搀扶着出来,两个女孩一边跺着脚一边坐在板凳上抱头痛哭;面对警察的阻拦,一位农民工父亲彻底崩溃了,他的两个孩子被困在外围:“我们等了几天了,饭也没的吃……我要进去,我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办……”,他在激动的绝望中对着警察陈述,尽管没有人回答他。
影片的每个镜头都很稳,即使是在人流如织的广州站也如此。范立欣说:“这都要归功于摄影师孙少光,他对构图和光线十分讲究,在人多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拿稳。有时我会劝他,不稳也没关系,但他还是苛求既要确保真实性,图片和画面也要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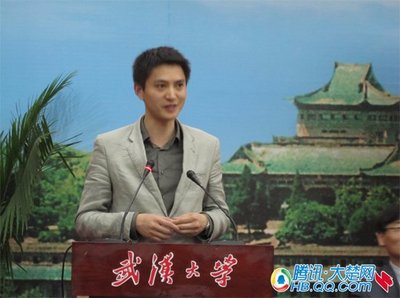
农民工的归途
在每个城市的火车站,总会有这样的标语:****祝您旅途顺利。但现实总是残酷的,那些为城市建设打拼了半辈子的农民工们,连最基本的诉求:一列能够将他们安全送达到家,春节与家人团聚的绿皮火车,都显得难于登天。范立欣说:“每年我在广州站看到成千上万为‘振兴中华’付出了努力与牺牲的农民工,如蝼蚁般滞拥在这块大号牌下时都觉得特别讽刺,他们为国家付出得太多,我们给他们的回报太少。”
整部片中,张琴的际遇和命运让人心痛又不忍,直到现在和张昌华夫妇的关系依旧不好。她是留守儿童,在一个没有父母关爱的环境中长大,正值青春期,性格叛逆,无论是面对家人还是外来者,她的眉头从未舒展开来。
2008年春节回家之后,父女的矛盾到达顶点。因为张琴上学的问题,父女俩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而张琴脱口而出的“老子”一词,彻底惹火了张昌华,两人大打出手,这位话不多的瘦弱男人在这场交战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几次将张琴掀翻在地。范立欣和摄制组对这一突发事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作为一个记录者,以职业道德而言,不应该干涉拍摄对象和事态的发展,但站在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应施以援手。最后,范立欣还是忍不住冲进房间,扯开了扭打在一起的父女。面对眼前的这一幕,范立欣是心痛的,这一幕发生的时候,他和这一家人共同生活了2年。
第二次南下,在滚滚向前的火车上,张琴面对镜头说到:“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我去深圳嘛,也没什么目标,开始是玩,然后再工作吧,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她青涩稚嫩的脸上,看到了对于未来的迷茫。范立欣说:“张琴的问题反映出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巨大的伤痛,这样的伤痛几乎是不可愈合的。”之后,张琴选择在一家娱乐场所打工,她拎着两打啤酒,瘦小的身影穿梭在嘈杂的音乐声和五光十色的炫目灯光之中,她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一样的路。
在范立欣看来,张昌华所带代表的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赚钱养家,背负起家庭的责任,拥有强烈的自尊,不轻易接受帮助,隐忍自爱;而他们的子女,农二代们更渴望飞出贫穷的桎梏,在城市开垦一席立足之地,融入城市的生活。
女儿张琴的叛逆让夫妇俩伤透了脑筋,他们把希望放在儿子张洋身上。为此,万般无奈之下,陈素琴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回家照顾儿子。范立欣说,张扬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明年就能参加高考。
范立欣在记录一个时代,用微小的个体,映射出了所有人的影子。农民工父母一辈子的诉求,仅仅是赚钱养家,供子女读书,希望他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世界,不再重复自身的悲剧,这样的爱太沉重了,以至于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懂得,就已经偏离了轨道。
3年的拍摄中,农民工的艰苦生活和对未来的茫然无奈是对范立欣冲击最大的部分,“下一部纪录片我会关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和父辈不同,他们成长在信息化的时代,对权利和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他们更希望融入城市,我非常感兴趣探求他们未来的路会在哪?”
纪录片的春天
导演范立欣是武汉人,住在万松园一带,长大后虽然回武汉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回来都会感觉变化特别大。当然,他会先到三镇民生甜食馆解解馋,点上糊米酒、豆皮、热干面和生煎包,摆成一排,然后统统吃光;再到武汉关坐一坐轮渡,最后带着浑身的武汉味回家。
首映会在万松园西园商业街的银兴乐天影城举行,截止开场半小时后,总共卖出43张电影票。
43张电影票不多,但对于《归途列车》这样的纪录片而言,却不少。《归途列车》总共花费了100万美元的制作费,投资商来自世界各地,唯独没有中国,在这点上,范立欣直言不讳,觉得“很悲哀”。影片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城市都进行了公映,并取得了45万美金的票房,获奖无数。
去年7月,《归途列车》在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放映,每场的上座率能达到80%,这让范立欣大感意外。范立欣认为:“市场的偏好其实就是消费者的偏好,在中国,纪录电影市场小,那说明观众不喜欢看纪录片。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好看的纪录片,也可能是因为大众太浮躁,对纪录片没胃口。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所以需要各方的努力。”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范立欣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影片,来关注社会底层的这么一群人。目前,中国的纪录电影走向市场化还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体系。“观众基数要足够;影片宣传要精确针对小众观众;艺术院线如果还不能存在,至少应该有艺术影厅联盟,否则市场不够大,无法支持一部影片全国发行的最低成本,也就无法持续;还要注重开发电影衍生品。”
对于武汉本土纪录片人张以庆的作品,范立欣有赞赏也有遗憾:“张老师的静观式创作我很喜欢,如果当年有更多国际交流和制片的机会,能让这样的中国故事更多走向世界观众和市场就更好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