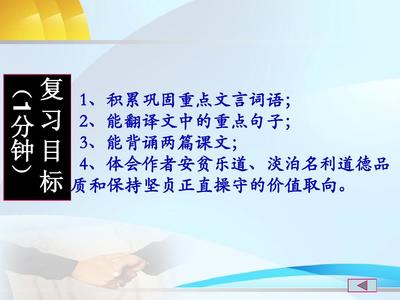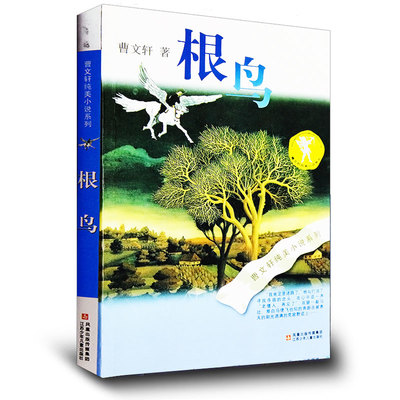自梳 (作者:柏邦妮)
一梳福,二梳寿,三梳平安,四梳坚心,五梳金兰姐妹情深。
是哪地的风俗呢?好象是广东,穿黑衣的自梳女,聚集成一派,统统是处女。她们不愿委身男人,防身是剪刀,出门缝裤腰,谁来抢亲了,一群肃杀的女人,捧着尖刀,抵住喉咙……那架势,如同困兽。她们是豁出命去的。茫茫红尘中,女人的命是不值得什么,最大的,不过是豁出去。意欢,便是如此,却在她舍命的时刻,有人相救。不是面如冠玉男儿郎,却是老爷的八姨太,堂子里最红的妓女玉环。她将钱扔在地上。这么轻贱。可是,另一个女子,在此刻,就将一生的目光,都倾注在她身上。谁来疼女人?只有女人她是个女子,我也是个女子。自梳,多么高傲。梳发自是自梳自,却表明不是装扮给男人。因此,堂子的女人破身,叫做梳拢。这样的一头青丝,如何梳,一生的命都定了。玉环是多么精怪的女人,七个姨太都斗不过她,她们骂她爱给男人睡,她说:“是男人爱跟我谁,赶都赶不走。”一个耳光闪过来,身影晃动,她替她挡住。小小的自梳女,意欢。老爷将玉环作为礼物换去一桩生意,玉环被关了几天,意欢就在门口等了几天。如瀑的雨,面色灰白的玉环被放出来,车窗扫过,门外躺着的意欢,她尖叫起来:“放我下车.放我下车……”玉环仍是高傲的,她对老爷不屑,是他,仍将赎还的她,置在窑子里。她劈手夺过姨太的项链,没有她,就没生意,这些,算得什么呢?灯火下,意欢战抖着替她涂药,她的背上全是伤口。手一抖,重了些,她疼得一抖。疼啊。意欢再也忍不住,用处女柔软的嘴唇,轻轻碰触伤口,泪滴下来,咸的,该是更加疼了。玉环不觉得。意欢爱上一个男人。 应该的。临走前,玉环亲手替她缝的领口,回来时,破了。玉环逼问她,她阅历风情如此多,可是她愚蠢地问她,直到她满面春风,告诉她,她爱上一个男人,请她祝福。绝望,她卑微:“那么我呢?”那么,我呢?世界如此大,你要将我安置在哪里?世界如此大,除了你的心,你还能将我安置在哪里?又不过是一场负心。意欢在澡盆里,将铁钩伸进去,她无声张开嘴,不能,不能喊叫,血水,源源不断。将一席草席裹了她,自梳女将意欢抬到玉环门前。玉环震惊,奔去看,心疼——那些,我承担过的苦楚,我千万次企求不会降临你的苦楚,竟然,你并没有逃脱。意欢醒来,想自杀,玉环夺过刀。气闷地坐在长凳上,手抓住刀刃,破了,不觉得疼。意欢悄悄走近,拿布来裹好,安静将满头秀发的头颅,靠在她的身上,玉环握住她的手。缠绵,并蒂莲。两张清丽的面孔,只有承欢,没有哀怨和恐惧。不疑惑。不厌弃。白色棉布蚊帐,竹席,枕头上委蛇的浓发,不必梳起。乱世,一张船票,撕做两半,我们谁也不走。没有男人能拆散我们。香港,半个世纪后。兰有个意欢姑婆,爱说话,泼辣,狡猾,难打发得紧。却在兰失去男友寻死觅活的时刻,果断喝住她,目光,慈悲如观音她执意要去广州找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船等不到,船淹了。她哭起来:意欢,意欢……她是玉环。她找了多年意欢,直到人们喊她做意欢。她抚养意欢的弟弟,接济意欢的家庭。火车站,人都散尽了,冲撞中,玉环手里的酸瓜洒了一地那是意欢最爱吃的呵。最后,颠颠扶出一坐轮椅,上面是颗灰白的头颅
玉环,紧张地拢拢头发,低下身去,全心全意,伸出手去,将手放进她手掌的,乃一双十八岁的玉手,盈盈站起身来的,是十八岁的清秀纯美,满目信赖和痴慕的意欢,
那边,是美艳,青春正盛的玉环。
紧紧,拥抱在一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