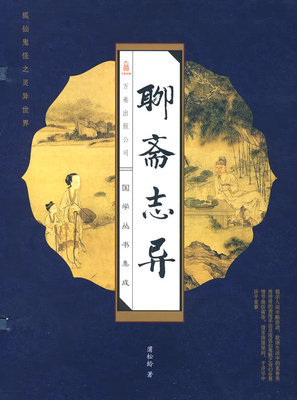嫦娥
太原有个宗子美,跟着父亲远游外地,从师求学,住在扬州。父亲和红桥下的林老太太从前有过交往。一天,父子二人路过红桥,遇上了姓林的老太太老太太一再邀请,把父子二人请到家里.煮茶待客,坐在一起唠嗑,有个少女站在旁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父亲一次又地赞美她。林老太太看着宗子关说:“你儿子性格温柔,容貌清秀,像个女孩子,是个福相,若不嫌弃我的女儿,就给你做媳妇,怎么样?”父亲满脸是笑,催促儿子离开席位,叫他参拜老太太,说;“这可是一言千金!”在这之前,姓林的老太太一个人过日子,女郎忽然自己来到老太太的家,告诉老太太,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老太太询问少女的名字,少女名叫嫦娥。老太太可怜她,就把她留在家里。实际上是等侍机会要把她当做可以高价出售的奇货。当时宗子美十四岁。一眼瞥见了嫦娥,他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就在背后告诉了母亲。父亲听到后说;“那是以前和贪婪的老婆子开个玩笑罢了。她不知要把女儿卖多少黄金,这哪里可以轻易说妥的?”
过了一年,父母相继去世了。宗子美心里总忘不了嫦娥,就在将要脱掉孝服的时候,托人把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了林老太太。老太太起初不承认。他很气愤地说:“我生来不轻易给人弯腰施礼,为什么老太太把我的弯腰看得不值一钱呢?她若违背从前的婚约,必需给我还礼!”老太太听见这话才说:“从前和他父亲开玩笑的时候,也许说过婚约,但却没有说定,就完全忘掉了。现在既然如此,我难道要把女儿留在家里嫁给天王吗?按照往常的嫁妆,实指望换取千金的聘礼,现在甘愿要他五百金,可以吧?”他自料难以办到,也就放弃了。
恰巧有个寡妇租房子住在他的西邻,寡妇家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名叫颠当。他偶然看见了颠当,文雅秀丽,不次于嫦娥。他很爱慕,时常以赠送东西做因由,一步一步地向颠当靠近;久而久之,逐渐熟识了,时常以眉目传情,想要说说知心话,又没有机会。一天晚上,颠当爬过墙头向他借火。他很高兴地拉住颠当,于是就像夫妻式恩爱了。。要和颠当定下嫁娶的婚约,颠当借口哥哥做买卖没有回来,从此以后,两个人寻找机会,偷偷地互相往来,形迹很秘密。
一天.他偶然路过红桥,恰好看见嫦娥站在门里,赶紧迈开大步,想要赶过去。嫦娥望见了他,向她招招招手,宗子美就停住了脚步;嫦娥又向他招招手,他就进了屋子。嫦娥责备他违背了婚哟,讲了违约的原因。嫦娥进了屋里,拿出一锭黄金送给他。他不接受,辞谢说:“我自料和你绝情了,就和别人订了婚约。接受你的黄金,和你结成夫妻,是对别人的负心;接受你你的黄金,不和你结成夫妻,是对你的负心,我实在不肯负心。”嫦娥想了很久,说;“你所定下的婚约,我早就知道了。你们的婚事肯定结不成;即使结成了,我不怨你负心也就是了。你快走吧,老太太快要回来了o”
宗子美在仓猝之间,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接过黄金就回去了。隔了一夜,告诉了颠当。颠当很赞成鏛娥的一番话,劝他只能专心于嫦娥。他沉默不语;颠当向他表态,愿做小老婆,他才高兴了,打发媒人把黄金送给林老太太做聘全,老太太无话推辞,就把嫦娥嫁给了宗子美。
进门以后,他把颠当的意思全部告诉了嫦娥。嫦娥微笑着,表面上怂恿他,叫他娶颠当为妾。他很高兴,想娶赶紧告诉颠当,但是颠当的足迹很久也不蹯进他的门坎了,嫦娥知道颠当是为自己的缘故,所以她就暂时回了娘家,故意给颠当一个机会。告别的时候,嘱咐宗子关偷取颠当的佩囊,过了一会儿,颠当果然来了,和她商量以前的婚约。颠当说不要着忙。及至解开她的衣襟亲昵谈笑的时候,见她肋下有个紫色荷包,就要伸手摘下来。颠当立刻变了脸色,,爬起来说;“你和别人一心一意,和我三心二意!负心的郎君!从此永别了。”他低三下四地挽留解释,颠当不听,径自走了。
一天,他路过颠当门前,进去看看,已经另有一个姓吴的客人,租房子住在里边,颠当母子已经搬走很久了,从此就形消影灭,没有地方可以打听她们的下落。
宗子美自从娶了嫦娥,家境突然富裕起来,楼阁连着楼阁,长廊连着厅台,连绵占了几条街。嫦娥性格恢谐,善于开玩笑。她碰巧看见一幅美人图,宗子美说:“我自己认为,你这样的容貌是举世无双,但是没有见过赵飞燕和杨贵妃是个什么样子。”嫦娥笑着说:“要想见到她们,这也没有什么难的。”就拿着画卷,仔细看了一遍,便进了卧室,对着镜子化妆,仿效赵飞燕的舞风,又学杨贵妃的醉态。长短肥瘦,随时变更;风情神态,对着画卷一看,很逼真。她正在粉演的时候,有一个丫鬟,从外面进了屋子,再也不能认识她了,就很惊讶地询问同伴儿:同伴告诉她以后,再向美人一看,恍然大悟。这才笑了。宗子美高兴地说:“我得到一个美人。千古的美人,都在我闺门中的床上了!”
一天晚上,正在沉睡的时候,有好几个人撬开房门进了屋子,火光照射在墙上。嫦娥急忙爬起来,说:“强盗进来了!”宗子美刚一醒过来,就要呼喊。有个人把刀子按在他的脖子上,他吓得不敢喘气。另外一个人,把嫦娥枪过来,背到背上,一哄而散。他这才呼喊,家人全都跑来了,屋里的奇珍异宝,一点也没有丢失。宗子美很悲痛,又惊又怕。没有办法可想,告到官府,官府派人追捕,毫无消息。时光过了三四年,他心情郁闷,百无聊赖,所以就假装赶考。进了京城。在京城住了半年,打卦算命,明察暗访,无计可施。偶然路过姚巷,碰上一个女子。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畏畏缩缩的,好像一个乞丐。他停下脚步一看,原来是颠当。很惊讶地说;“你怎么这样憔悴?”颠当回答说:“离别以后,搬到南方,老母去世了,被坏人抢来卖给满人,受尽了打骂凌辱,换尽了冻饿,实在不忍告诉你。”他问道;"“可以赎身吗?”“难哪。要耗费很多金钱,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说:“实话告诉你这几年堪称家道小康,可惜客居在外,盘缠有限,就是卖光行李,售出坐马,也在所不辞。如果赎身的价钱要得过多,我立即回家为你操办。”颠当约他明天出西城,相会于丛柳之下,并且嘱咐他,叫他自己去,不让别人跟去。”他说:“可以。”
第二天,他很早就前往相会的地点,看见颠当已经先到了,穿着鲜艳的裤褂,绝不是昨天的形状。便惊讶地问她,她笑着说:“昨天是试试你的心,幸而你还没有忘了旧情。请到我的家里去吧,我一定要报答你。”往北走了几步,就到了她家,便拿出酒菜,互相饮酒谈天。宗子美约她一起回家。她说:“我被很多俗事拖累着,不能跟你回去。嫦娥的消息,我已经听到很多次了,宗子美赶紧询问嫦娥在什么地方,她说:“嫦娥行踪缥缈。我也不能深知。西山有一住位老尼姑,瞎了一只眼,你去问她,就会知道的。”于是就在她家住了一宿。天亮以后,给他指出一条通往西山的道路。宗子美到了西山,有一座古寺,周围的垣墙全部坍倒了;竹林子里有半间茅草屋,有一个老尼姑,穿着千缝百纳的僧袍,坐在屋里。她看见客人来了,不理睬,不能以礼相迎。宗子美向她行个揖手礼,老尼姑才抬头问他做什么。他把姓名告诉了老尼姑,就提出了要求。老尼姑说:“我是一个八十多岁的瞎老婆子,与世隔绝,什么地方能够知道佳人的消息呢?”他很固执地向她请求。她才说:“我实在不知道。我有两三个亲戚,明天晚上都来看望我,女孩子们也许认识娥娥,也未可知。你明天晚上可以再来看看。”宗子芙听完就出了茅屋。
第二天再到那里,老尼姑已经外出,草房的破门锁得紧紧的。他等了很久,漏壶的声音已经催动更鼓,明月高悬,走来走去,无计可想,远远看见两三个少女,从外面走进来,嫦娥也在里面。他高兴极了,突然跳出来,赶紧拉住她的袖子。嫦娥说:“真是一个莽撞的郎君!吓死我了!可恨颠当多嘴多舌,竞教情欲又来缠人。”宗子美拽她坐下,手拉手地顷诉衷情,把自己的艰难困苦从头到尾告诉了嫦娥,不觉一阵心酸。嫦娥说:“实话告诉你:我真是被贬的月里嫦娥,出没在人间,因为被贬的期限已经满了,就假托被强盗劫去,是要断绝你的想望罢了。老尼姑也是王母娘娘守卫府门的人,我刚一遭到谴责的时候,因为受到她的收养和周济,所以时常前去看望她。你如果放了我,我就把颠当领来代替我。”宗子美不听,总是低着脑袋落泪。嫦娥望着远处说“我的姐妹们来了。”宗子美刚向四处看望,嫦娥已经无影无踪了。他放声痛哭,不想活在世上。所以就解下带子,悬梁自尽了。
恍恍惚惚的,觉得魂魄已经离开了躯壳,迷迷茫茫,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徘徊了一会儿,看见嫦娥来了,一把抓住他,把他提起来,两只脚离开地皮;拎进了佛寺,从树上轩,解下他的尸首,把魂魄往尸首上一推挤,呼喊着说:“痴廊,痴郎!嫦娥在此。”他忽然像从梦中醒过来了。镇定一会儿,嫦娥就怨恨地说:“颠当这个贱丫头!坑害了我,又杀害了郎君,我不能饶恕她!”下山租了一台轿子,回到家里。宗子美回到家就叫家人准备行装,又返身出了西城,去感谢颠当;到那一看,屋舍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惊愕了半天,只好长吁短叹地回来了。心里暗自庆幸,以为嫦娥不知道。进了家门,嫦娥迎出来,笑着问他:“你见到颠当了吗?”他徒然一惊,无可以回答。嫦娥说:“你背着嫦娥,怎能见到颠当呢?请你坐下等着,她会自己来的。”
等了不一会儿,颠当果然来了,慌慌张张迪的跪在床下。嫦娥叠指弹着她的脑袋说;“你害人不浅哪?”颠当给她叩头,只求饶她不死。嫦娥说:“把人推进火坑里,你想脱身于天外吗?广寒宫的十一姑不久就要下嫁,需要绣制一百幅枕头,一百双绣鞋,应该跟我一起去,我们一同给她作出来。”颠当很恭敬地宥求:“我只请求分工制作,按时给送去。”嫦娥不答应,时宗子美说;“你若给她说说情,我就放她回去。”颠当眼睁睁地看着宗子芙美,宗子美笑眯眯地不说话。颠当狠狠地瞪他一眼。颠当请求回去告诉家人,嫦娥点头应允,她就走了:。宗子美打听她的生平,才知道她是西山的一只狐狸精。就买了轿子等着。
第二天,颠当果然来了,就一同回了老家。但是婧娥重新回来以后,经常谨小庄重自爱,不轻易开玩笑。宗子美硬要叫她过亲昵的夫妻生活,她就暗中叫颠当代替她颠当很聪明,喜亍诌媚。嫦娥乐于一个人独宿,常常推辞,不和丈夫一起睡觉,一天晚上已经鼓打三更了,还听见颠当的卧房里,有哧哧不绝的笑声。就打发一个丫鬟偷偷地去听声。丫鬟回来了不把情况告诉她,只请夫人亲自去看看。她扒窗往里一看,只见颠当穿着华丽的衣服,学做嫦娥的形状,宗子美把她抱在怀里,呼她的为嫦娥。嫦娥微笑着退下去了。过了不一会儿,颠当心口突然痛起来,急忙披上衣服,拉着宗子美,到了嫦娥的卧室,进门就跪在地下。嫦娥说;“我难道是个用咒语制人的巫医吗?你是想要自己捧着心口,东施效颦罢了。”颠当给她磕头,说她知罪了。嫦娥说:“你的病好了。”她就站起来,笑出了声音,走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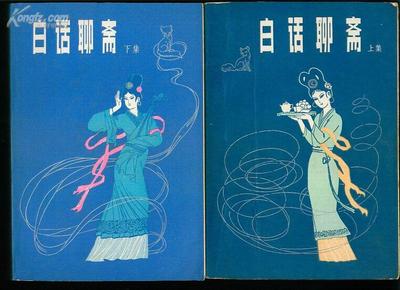
颠当私下对宗子美说:“我能叫娘子学观音。”宗子美不相信,所以就开玩笑似的打了赌。
嫦娥每次盘腿打坐的时候,总是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颠当悄悄地把柳枝插在玉瓶里,放在嫦娥面前的矮桌上;自己就披着头发,两手合十,侍立在身旁,樱唇半启,玉齿微露,眼睛一眨不眨的站着,宗子美一看就笑了。嫦娥睁开眼睛,问他笑什什么,颠当说:“我学龙女侍候观音。”嫦娥笑着骂她,惩罚她,叫她学习童子拜观音。颠当束起头发,就四面朝拜。趴在地上翻来覆去旋转,卖弄技巧,变幻各种姿态,左盘右曲,侧身侧拜脚上的袜子能够摩擦她的耳朵。。嫦娥笑容满面,坐着踢她一脚。颠当仰脑袋,用嘴叼着嫦娥的一只脚,并用牙齿轻轻地碰撞着。嫦娥正在嘻笑之间忽然觉得有一楼媚情,从脚趾往上升腾,一直达到心房,使她神志放荡,产生了淫欲,几乎不能自主,于是急忙收起神志,呵斥说;“狐奴该死!不选择人就进行迷惑吗?”颠当害怕了,松了口,跪在地下。嫦娥更加严厉地责各她,大家不知为什么要责备她。嫦娥对宗子美说;“颠当的狐性不改,刚才几乎被她愚弄了。如果不是个跟基很深的人,堕落下去有什么难的!”
从此以后,见到颠当的时候,常常是严厉地防御她。颠当又羞又怕,告诉宗子美说:“我对于娘子的一肢一体,没有不爱的。爱到了极点,不知不觉就谄媚了她。说我对她有二心,不但不敢,也不忍心。”宗子美就把颠当的心意告诉了嫦娥。嫦娥待她仍和当初一样,但是因为无节制地轻狂游戏嫦娥屡次告诫宗子美,,宗子美不听,因而大大小小的仆妇丫鬟,也争做轻狂的戏耍。
一天,两个人挟着一个丫鬟,学作贵妃醉酒。挟着的两个人以目传情,心领神会,诳骗那个丫鬟,叫她骨架松懈,装作醉态的时候,两个人突然一撒手;丫鬟猛然跌到台阶底下,噗的一声,好像倒了一面墙。大家正在吵吵嚷嚷的,有人到她跟前一摸,已经是马嵬坡前的杨贵妃,死了。大家害怕了,急忙跑去禀告主人。嫦娥惊讶地说:“惹祸了!我的话怎么样!”前去检查,已经不能救活了,派人去告诉她的父亲。其父某甲,一向没有德行,一路号叫着跑进来。把尸体背进大厅,百般叫骂,宗子美关上房门,心里惴惴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嫦娥亲自出来责备某甲说;“主人虐待使女,直到死亡,也没有偿命的法律;而且,偶然之间,突然死了,怎知她不能复活呢?”某甲吵吵嚷嚷地说:“四肢已经冰冷,哪有复活的道理!”嫦娥说:“你不要吵吵,纵然不能复活,自有官在。”说完就进了大厅,抚摩丫鬟的尸体,丫鬟已经苏醒了。她伸手一摸,随手就站起来。嫦娥抹回身子,怒气冲冲地说:“幸好丫鬟没有死,你个贼奴才,怎么敢无礼理取闹!应该用草绳子把他捆起来,送进官府治罪!”某甲无话可说,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哀求免罪。嫦娥说:“你既然知罪了,暂时免于追究,也不处罚。但是无赖小人,反复无常,留下你的女儿,终究是个祸胎,应该马上把她领回去。原先若干两银子的卖身价钱,你应该急速筹办,马上送来c”说完就派人把他押出去,叫他请来两三位村老,写了赎身文书,并在文书的尾前,让其甲亲自问她:“你没事吗?”丫鬟回答:“我没事。”于是就交给某甲,叫他领回去了。
办完这件事情,就把许多丫鬟都叫来,数落她们,责备她们,挨个儿都打了一遍。又招呼颠当,严厉禁止她的玩耍。对宗子美说:“现在才知道,做为主人的一颦一笑,也不能轻狂。玩笑从我开始的,流弊就不能制止了。凡是悲哀的,都是属阴的;欢乐的,都是属阳的;乐极生悲,这是循环不已的定数。那个丫鬟的灾祸,是鬼神逐渐前来报信的。再若执迷不悟,倾家荡产的灾难就要临头了。”宗子美恭恭敬敬地听着。颠当流着眼泪,请求从苦海中把她拉出来,嫦娥就掐着她的耳朵;掐过一刻才松了于,顷刻之间,颠当怅然若失,忽然好像从梦中醒过来,跪在地上自己承认错误,高兴得快要舞起来了。从此以后,闺房里清清静静,无人敢于喧哗了。
那个丫鬟回到家里,没病突然死了。某甲因为赎全没法偿还,就哀求村老替他说情,哀求可怜他,饶恕他,嫦娥答应了。又因为有服役的情义,施舍一口棺材,把他打发走了。
宗子美时常忧虑没有儿子。嫦娥的肚子里,忽然听见了男孩子的哭叫声,就用刀破开左肋取出来,果然是个男孩子;过了不久,又有了身孕,又破开右肋,取出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像他的父亲,女孩子很像她的母亲,长大以后,都和世家大族结了亲。
异史氏说:“乐极生悲,至理名言哪!但是家里有一位仙人,幸好能够极我之乐,消除我的灾害,使我长生不老,使我不能死亡,这样一个安乐乡,可以老死在里边。可是仙人有什么疑虑呢?天道循环的气数,固然是理之当然;但在世上潦倒一生,而达不到乐境的人,又怎能解释呢?从前的宋朝,有人求仙而不得的,常说‘做一日仙人,死不遗憾。’我再也不能说笑他们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