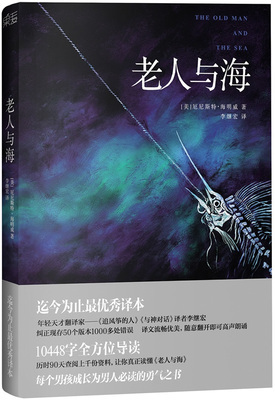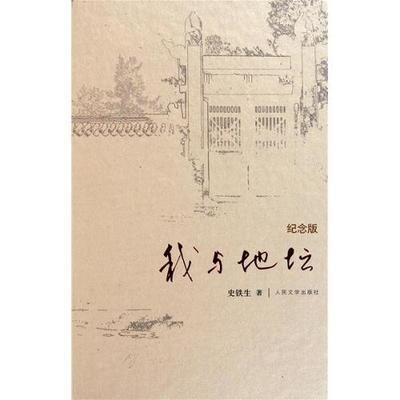大约在2009年底,我和几个做图书编辑的老朋友,密谋成立了一个既紧密又松散的组织,名曰“水汪汪小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某种奇妙的巧合,这几个会员都是双鱼、巨蟹、天蝎等水相星座。由这种团队构成也可以反推一下,是不是水相星座更易于从事出版行业?
所谓紧密,是指大家结成一个守望相助的小班子,彼此分享信息,互通有无,相互切磋,而大家共同的手段和目的,就是鼓捣几本自己最想做的书出来。所谓松散,是因为各自没有什么同事关系和利益冲突,每个人对自己要做的书,负最大程度的责,这本书出版过程中所有的环节,都由这个人说了算。一个人浸淫这个行业久矣,但说实话,当家做主的时候并不多,而我们这个小团体,就是要结结实实地推行一种“编辑中心制”。
这一年来,几个人分头确定了自己的项目,便各自投入战斗。大家同时相约,要把工作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与他人共享,以求共同进步。有的人还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自己的编辑日志。我理解,这有点儿像DVD光盘里附带的幕后花絮,制作特辑,“Makingof”什么的。
我做的书中,有一本是《童年与故乡》,这本书相较其他同仁的出版计划,显得较为容易(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他们那么严重的拖延症),所以11月份就出版了,是水汪汪小组中最先推出的一本。按照起初的设想,把自己编辑这本书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想法汇报如下。
2009年9月份,《读库》推出了新一批Notebook《线条的舞蹈》、《张光宇》等八种。我收到老读者宋焱的一封电子邮件,言及“看到这次线条舞蹈的主题,向你推荐我最喜欢的漫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我见到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的十六开本,黄纸封面。古氏的漫画有特别淳朴诙谐的意蕴,尤其加上吴朗西的译文和丰子恺的书写,可谓三绝。我觉得特别适合你的NB选用。那本书我初次见到买了一本后,中午回去看过,马上返回书店把所有库存的十几本买回来,分送友人。后来又见到2001年再版的本子,封面设计和印制都没有上次的好,但还是把店里进的大概二十本都买回来”。
宋焱在信中说:“说了半天,没准你也有那个书。再拿出来看看吧,我觉着特别耐看。我还想买这个书送人可是买不到了,下次你出笔记本,就用那个温暖的黄色封面,想想都美极了。”惭愧的是,我没有这本书,曾经在书店里翻看过三联书店版的《童年与故乡》,但印象不深。
201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去三联书店汪家明老师的办公室串门,他送我一本书,正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版的《童年与故乡》——这本书是他当年在该出版社供职时做的,那时他还署名“汪稼明”。翻看这一版,我才知道“三绝”——古尔布兰生的绘图、吴朗西的译文、丰子恺的书写——结合在一起的妙处,而我此前所见的三联书店版,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居然将丰子恺的书写体内文改为印刷体排版。我擅自揣度,大概因为丰子恺先生的手书是繁体中文,编辑担心出版会有麻烦,读者会有阅读障碍,所以才有此变动吧。
山东画报这一版初版于1998年,早已绝版,我便动念,应该重版此书。但山东画报这一版内文用纸较为薄透,不能用来扫描。汪家明老师说,他这一版中的图画、文字,是以五十年代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制版的。遗憾的是,原书在制版过程中被工厂丢失。
与水汪汪小组说起此事,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的王曦老师自告奋勇,说看看能否从国图借出品相较好的五十年代版本。但最终未遂。我又想起向每次邮件署名都有“甘肃省图书馆”字样的宋焱同学求助。电话打通,才发现原来宋焱是位女士。
甘肃省图书馆也没有,但宋焱同学动用业内资源,最终从辽宁省图书馆借出了一本馆藏的文化生活版《童年与故乡》,五十年前的书,近乎全新。
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江苏美术出版社也曾经出过一版,名曰《故乡的回忆》,但不是吴朗西先生的译本。
文化生活版拿到手,才发现山东画报版的封面字体,不知道什么缘故,居然有些横向压缩,导致丰子恺先生的手书变得瘦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再版,原始信息都会有所损失,有所改变,几乎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这很让人遗憾。那么,我们根据文化生活版转制,会不会离原版更远呢?我决定,寻找德文原版,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并尽量按照最原始状态来重版这本书。
再次向《读库》老读者求助。“老读者”是我自己起的一个名谓,意指那些《读库》的多年订户,甚至从创刊伊始就不离不弃。我们之间有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是默默地交钱订书、等着收书,而有的则在书之外还要探讨人生,长久以往,许多人的底细,都被我知道了大概。我把邮件发给了远在德国的吴枚同学。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1934年出版的德文版《童年与故乡》。这本书大概来自旧书市场,封二还粘有一张原主人的藏书票:
看到原版,才知道中文版从开本到版心,均做了调整。德文版比中文版的规格大了那么一号。对于一本书来说,有时候三五毫米的差距,给人的观感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德文版的版式要疏朗粗放,中文版则紧凑密致:
按照“无限接近原版”的原则,我确定了这样的编辑方针:依照德文原版样式,采纳中文版中丰子恺先生的手写体正文,及德文版中古氏的插图素材,重新拼版制作,并恢复为德文版的开本规格。
经对这些泛黄的页面的修复、整理、拼接,最终出来的内文版心是这个样子:
内容方面的修复之外,则是图书物理状态的还原了。中文版的三个版本,应该说是每况愈下,三联版的编辑理念便不足道,前两版与原版的差距,主要是受时代条件所限。平心而论,那时候中国出版界与世界的差距,主要是硬件方面的,导致七十多年前的德文版,我们过了二十年、六十年再做出来的,仍大有不如。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超有钱,国内印厂拥有了几乎世界上最顶尖的设备,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出不逊于七十年前德文版的书呢?
首先,德文原版是精装。精装书的最大难度,在于能让内页平整地摊开,封面不弓不翘,平展熨帖。经过这几年来与印厂的合作,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而原版的用纸,却令我大伤脑筋。
拿到德文版后,我之所以产生“一定要按原版来做”的冲动,主要原因就是内文纸张给人的那种温润、爽利又厚实的手感。为此,我寻访了许多家纸商,并请中国造纸研究所来鉴定这是一种什么纸,最终的结论是,当年的造纸工艺,现在已经没有了。好在经过百般挑选,最后总算找到一种基本接近原版的特种纸——这家纸厂采用的就是德国技术。等我战战兢兢拿到成品书,触摸到那种古朴醇厚的质感,看到线条印在上面宛如手写的错觉,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从封面来看,新版比原版似乎大了一些,这主要是现在精装书的装订工艺所致,图书封面的纸版要比纸芯多出三毫米,而原版的纸版是与内文同大的。新版有所改进的是,我们将原版的钉装改为锁线,这样时间长了,不致有锈迹。
由于我国对出版物的一些硬性规定,所以封面没能采用原版的设计方案,这算是一点小小的遗憾,为此我将原版的封面用图印在了封底上。
原书到这一页就结束了,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幅画面。
但考虑到大家对繁体中文的荒疏,特别是这本书很大一部分的目标读者是青少年,所以又将吴朗西先生的译文整理为简体中文,以印刷体附后。由此导致新版比德文原版厚了将近五分之一。这是一件让人不得不生发感慨的事情:长此以后,我们为繁体中文需要额外付出的,将不止五分之一。
吴朗西先生的“译者后记”与丰子恺先生的“写者后记”也附在后面。
并不夸张地说,《童年与故乡》是我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具备“一本书本来该有的样子”的书。
如此热切地鼓捣这本书,并非只是出于对一本书物理状态的迷恋。《童年与故乡》真正好看的,是它的内容。
“奥纳夫·古尔布兰生(OlafGulbransson),1873年生于挪威,二十岁后赴德国慕尼黑从事漫画杂志编辑工作,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童年与故乡》出版于1934年,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记录。四十篇散文,两百幅漫画,非常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的童年,家庭,学校,军队,初恋等天真烂漫的生活履历,同时旁触到北欧的大自然和它的动物,山林以及纯朴粗野的农民生活。图画文字都有独特的风格。
“译者吴朗西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和翻译家。由于德文原版为手写、手绘,为了使中文译本‘更加生色’,吴朗西先生便也遵从德文版体例,请好友丰子恺亲自书写配图文字。
“丰子恺先生也认为:‘古尔布兰生的画,充分具有写实的根底,而又加以夸张的表现,所以能把人物和景物的姿态活跃地表出。他的文字近于散文诗,也很生动。他把童年在故乡所为,所见,所闻的精彩的片段,用绘画和文字协力地表现出了。有的地方文字和绘画交互错综,分不出谁是宾主。这种艺术表现的方式,我觉得很特殊,很有趣味。’”
以上几段文字,是我整理出来的关于这本书的简介。古尔布兰生、吴朗西、丰子恺,这样梦幻组合的创作团队,提起来就足够诱人,童年、故乡,更是图书市场非常讨喜的“概念股”。但这本书并非只是有个怀旧又讨巧的书名而已。编辑过程中,我屡屡惊喜于书中插图精妙的表现力,更惊讶于作者的文字表达,给我带来的新鲜阅读体验。
先说绘画。古尔布兰生确属大师级别,线条之生动,构图之幽远,让我经常感觉像在看一部电影的分镜头。事实上这本书创作于上世纪初,那时的电影工业应该还没有这么丰富的镜头语言。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伟大的画家,其实是启发了电影导演?
再说文字。一提童年、故乡,多是柔和、舒缓、亲昵、怀恋的完美主义温情基调,但古尔布兰生并没有这样写。他的文风硬朗,粗砺,荒蛮,沉厚,一反那种甜腻腻、软绵绵的写作定势。看他描写的主人公及其父老乡亲、男男女女,我总想起两个字眼:混、嘎。他写出人与人的冲突,也正视人性中的弱点,甚至直面伤痛与死亡,但骨子里却有一股既冷又热的趣致。我们的文字,也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吗?
在这个拿男孩当女孩养的脆弱娇嫩的时代,在这个背离家乡再渴望寻找心灵原乡的矫情时代,古尔布兰生吹奏的关于童年与故乡的箫管之声,便显得尤为悠长。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有几点感触,与大家汇报。
校样交到出版社,复审编辑问,为什么没有页码?我回答,没有必要有页码,也没有必要有目录。这本书在后记之前的所有内文中,我希望看不到一个印刷体的字(当然出版社的社标不得不加上)。事实上,图书出版之后,并没有读者质问这一点。打破一些小小的常规,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要想做一本“能拿得出手”的书,除了编校质量、设计品位、印制水准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努力做到版权上没有瑕疵。我查了一下,古尔布兰生于1958年去世,所以少了联系外文版权这一道。但应该尽力找到吴朗西、丰子恺两位先生的后人,得到他们的授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汪家明老师与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女士相熟已久,很快就联系上了。如何找到吴朗西的后人?当时毫无线索。有好几位同行劝我,可以不必理会,或者在版权中心挂个号、寄存一笔稿费即可。但我尝试在网上搜一下“吴朗西之子”、“吴朗西之女”,马上就有了他的儿女的名字,然后找张小强、李辉老师帮忙,很快联系到在日本的吴念圣先生,得到授权。原来吴朗西先生过世时,他们几兄弟就商定,父亲的稿费收益都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等书出来,再与吴念圣先生通邮件,得到他们兄弟三人的地址,吴念祖先生在上海,而长兄吴念鲁,就在北京。分别打电话给他们,原来历年来的出版情况,他们都知道。真是“人在做,天在看”。即使他们不追杀上门,但如果没有经过这几关,如何能够心无挂碍地到处秀这本书,像一个丰收的农民一样享受收获的喜悦?
图书出版之后,我登陆豆瓣网,试图上传相关材料。这才发现,豆瓣的图书条目中,不像影视剧那样,没有图片展示栏。难道不需要吗?任何一本出版物,都应该是内容与形态的完美统一,文字排出来的空间感、纸张、封面、印刷、装订所依附的物理属性,越来越重要,读者也越来越看重。以后再有新书出来,编辑除了写宣传文案外,还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找摄影师拍关于这本书的性感写真。
《童年与故乡》一经推出,反响惊人,读库网和淘宝店的销售创历史新高,发行商也直说他们的货要少了。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当宋焱同学向我力荐这本书时,当汪家明老师赠送我这本书时,当吴枚同学在德国上下而求索,得手后反而感谢我让她买到了一本好书时,一位出版界老前辈的话言犹在耳:一本好书,一定会让人产生与人分享的冲动。
身为编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分享变成现实,荣幸莫名。
读库网购买连接:http://www.duku.cn/pages/Store.aspx
淘宝网购买连接:http://shop35372084/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