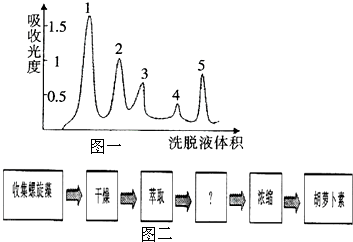“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徐 贲
据报道,“唱红歌”要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方式加以推广,因为“唱红歌”创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提倡者预言,“红歌”能够“提振社会‘精气神’”,定能有效地起到群众教育的作用。
在预言红歌群众教育功效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唱红歌”是怎样一种教育手段?它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是道德教育,还是公民教育?或者只是一种单纯的党化教育?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唱红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党员或党员干部,应该不是一种单纯的党化教育。“红歌”既然是为了“群众自我教育”,是让广大的普通民众唱的,那么,想来“唱红歌”的目的是要对普通国民进行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作用。

当今中国确实非常需要有以普通国民为对象的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社会生活许多领域中发生的道德危机、伦理失范、公民素质下降,面对这样的状况,人们热切的期待能找到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靠“唱歌”,哪怕唱的是“红歌”,能让期待者心想事成吗?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真正的价值观念,是经过选择的结果,个人若无选择的途径,事实上选择的的行为不可能发生,而真正的价值也就无法发展。因此,个人价值的建立,要由多种可能的选项中选择才有意义。而且,价值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感情冲动下,或未经思考,若贸然选择,不能主导真正的价值。个人唯有对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所思考,比较利弊得失,做出理智的决定,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才可作为公共生活的指南。
唱歌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唱歌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听觉的印象上。“红歌”里确实有某种道德信息,但是,歌的音乐彻底改变了道德信息的接受方式。人们听歌,首先的反应是歌好不好听,不是歌词在理不在理。道德教育是一种说理的教育,一种关于在理和不在理的判断教育。“歌”把理性的“说理”和“判断”变成了一种直觉“好听”和情绪化的“喜欢”,这就取消了它自己的道德教育作用。说理和判断让民众能通过分析和讨论,达成共识并形成可以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这与“好听”和“喜欢”是不同的,我觉得好听,喜欢的,你可以觉得不好听,不喜欢。我们不能把道德教育从一个理性的逻辑判断变成一个情绪性的爱好判断。
比起道德教育来,唱歌更没法起到公民教育的作用。公民教育应该让人们了解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了解宪法和他们社会秩序和正义观的关系,了解民主法治的特征和运作。除非你把宪法谱曲,把公民权利和责任编成歌来唱,歌是起不到公民教育的作用的。美国初中英文教科书有一篇长达60行的《权利法案饶舌歌》,唱的是公民拥有的神圣权利。即使这样的歌,它的公民教育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这是因为,公民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强迫灌输,也不是对动物的条件反射训练,它需要让国民通过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清楚地了解与公民行为世界有关的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政府?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等等。
好的音乐并不需要歌词,而离不开歌词则未必是好的音乐。红歌传递的是政治信息,与音乐的好坏没有关系。红歌传递政治信息,这和广告音乐传递商品信息是同一类用途。广告音乐和政治音乐都是为某种与音乐无关的目的“配”上去的音乐,前者是为了让人接受某个“商品”,后者则是为了让人接受某种“正确思想”。“文革”中,作曲家李劫夫为许多毛主席语录都谱了曲,传递的就是这种政治信息。歌里唱的全是革命的大道理,亿万人民唱得也非常有“精气神”,但却并没有就此在中国实现什么有持久影响的道德或公民教育。如果真的想要进行具有持久功效的道德和公民教育,那就需要在“唱歌”之外想想办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