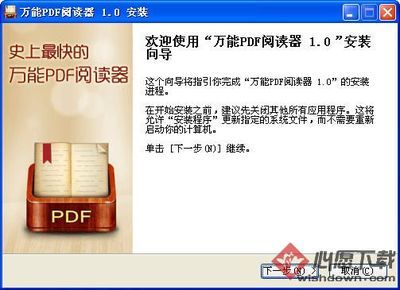一
不知道用怎样的语句描述近一周的状态,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状态。对一切都没兴趣,对任何人都没兴致。无喜无悲,表情平静,我的脸总也呈现出沉静如水的样子。
这种状态是我从未有过的样子,一直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遭总也有很强烈的感觉,一点点儿小事都能让我起波澜,而现在,此时,什么事情都唤不起我的热情,甚至有种“生无可恋”的感觉。但对死也没感觉,所以就这么活着。
就是平静,我真的内心平静。那天Y姑娘说:“你活的太明白了。”我恍然大悟,是的,总也是活的太明白,总也是太懂事,总也是太容易了解他人的心思,所以没意思。突然就想起三毛的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肯定不是因为我想不开,而是因为想的太开。
你理解这句话吗?并不是说因为想不开所以忧郁,而是因为想得太开,所以内心平静,只因为一切都明白,所以无所谓。所以没有感觉。
说实话,如此这般的我,甚至让我不自觉怀念自己难过纠结的时候。至少还有感觉,而现在是真的意兴阑珊,对于任何事都没兴趣,对任何人都没感觉。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荒岛上,看不到周围纷乱的人们,听不到他们说话,感觉不到他们。
我终于成为一个没有痛感的人。
二
想起了沈从文先生的爱情。他说过的一句话曾顽固地让我痴迷,他写给张兆和——他顽固地爱着的学生——最后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幸福地携手终生。
他的话是: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他对她的爱炽烈而绵长,他一封封情书写给她,以文人特有的方式表达爱意。而女学生张兆和却始终保持沉默,只是把老师的情书一一作了编号。
直到全校起了风言风语,说是沈从文因为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这个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去找校长胡适。
她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对校长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文人胡校长以文人的方式评价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先生不死心,又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看到张兆和的态度如此,胡适不便再插手了。
于是胡适写信劝慰沈从文:“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但爱情一旦开始,注定无法结束。他的情书仍一封封不停写,如潮水一般涌出。他写这样的诗,名为《我喜欢你》: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战,身就沁汗
并不当到别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喊你的名字
他写这样的文字: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炽热的爱情。1932年7月,沈从文去看望在苏州家中过暑假的张兆和。他带去的礼物是一套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据说,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
沈从文在苏州停留了一周,他每天一早就来到张家,直到深夜才离开,在这期间,张兆和慢慢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长达三年的情书追求终于有了回报。
但这次拜访,生性腼腆的沈从文并未提亲。但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张兆和的二姐允和写了封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二姐妹询问父亲的意见,张兆和的父亲思想开明,他答:儿女婚事,自己自理。
于是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
后来周有光(张允和的丈夫)回忆说:“张允和呢就复他一个电报,就是允,允呢就是张允和的允,这一个字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表示是允许了,另外一个作用呢,允是她的名字,回复电报人的名字。所以实际上呢,就叫半个字的电报,姓名不算呢,只有半个字,半个字的电报也是很古怪的。”
半个字的电报发出去了,张兆和却仍忐忑不安,她担心老实人看不懂,于是就追发了另一封电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 沈从文与张兆和举行了婚礼。
从此,他们在一起将近六十年。她叫他沈二哥,他叫她三三。
1937年1月7日,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上写信给妻子: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她也写出这样的话:
乍醒时,天才蒙蒙亮,猛然想着你,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不放心路上不平靖,就只担心这个,因为你说的,那条道路不好走。
正是靠这些家书,沈从文创作出《湘行散记》,他写给他的三三一个人看。如果没有那么深爱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大概不会诞生晶莹透亮的文字,诞生这本书。
“三三,一切生存皆为了爱,必有所爱才能生存下去。”
“又有了橹歌,同滩水相应和,声音雍容典雅之至。我歇歇,看看水,再来告你。我担心墨水不够我今天应用,故我的信也好像得吝啬一些了。”
“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听,船那么“呀呀”地响着,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的“呀呀”地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
“一切声音皆像冷一般地凝固了,只有船底的声音,轻轻地轻轻地流过去。这声音使你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而是想象。这时真静,这时心是透明的,想一切皆深入无间。我在温习你的一切。我称量我的幸运,且计算它,但这无法使我弄清一点点。为了这幸福的自觉,我叹息了。倘若你这时见到我,我就会明白我如何温柔!”
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沈从文和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离开北平。张兆和和儿子留在了北平,他们靠家书联系。
张兆和担心着:
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
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这些家书,后来成了那本《从文家书》。
三
今天,我再次想到沈从文先生,于是重读他的情书,再一次被感动。或许感动是可以不停地回味的吧,即使在这样一个阴沉的夏日,即使在我意兴阑珊时,久违的感动仍会涌上心间,让格子间里的我内心澎湃,想要拉着谁,一种想要分享的冲动再次翻腾起来。
于是在昏天黑地的工作中拔出那一点点儿时间,写下这些文字。
而想起沈先生,就想起美丽的湘西,美丽的翠翠,也好似觉得那道澄澈、纯净的湘水,哗,一下子流过来,将好似得了瘟疫的我,将虚脱的我,一下子冲得站了起来……
或许,我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强大;或许,我曾经口出狂言的坚强从未造访;或许我的消极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但我分明也感到一些力量,那被日复一日的生活一点点消磨的日渐坍塌的内心信念也有了轻微的回转,这些从书中汲取的营养,或者能够让我维持时日,继续相信信念,并为之努力。
祝我好运吧,期待女超人早日回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