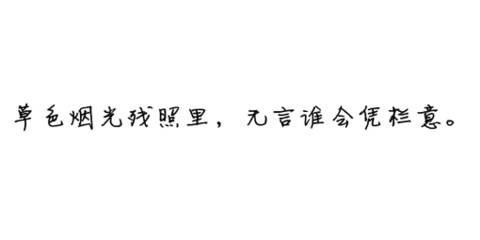对西方翻译理论家Lawrence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
马会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100089)
提要:本文在阐明美国翻译理论家Venuti所主张的异化翻译理论的实质的基础上,以实例说明了该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没有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目的和接受者的需求。其次,异化翻译能否改变英美国家的翻译状况值得怀疑。第三,“流畅”的归化翻译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是强势国家的主流翻译方法。本文最后指出了异化翻译的理论基础及其可能的负面影响。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real nature of Lawrence Venuti’s theory of foreignizationstrategy,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limitations mainly from threeaspects: (1) Venuti’s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ignores the purpose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receptors of the targetlanguage;(2)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can change the translation situations of Anglo-America publishingindustry; and (3)Fluent domesticating strategy is dominant intranslation practices regardless of the power differentials betweenthe two countries concerned.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explore thetheoretical basis of Venuti’s theory and its possible negative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rategy,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1.引言
中国翻译界在2002至2003年曾一度对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探讨非常感兴趣。据估计,这一时期只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这方面的论文就有十一篇(曹明伦2004)。其中不少主张异化翻译的论文显然是受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异化翻译运动(foreignizationmovement)的影响。 这场运动以法国的AntoineBerman,美国的Lawrence Venuti和 Philip E.Lewis为代表,他们反对归化翻译,主张异化翻译(Robinson1997)。其中,美国的Lawrence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影响最大。在JeremyMunday介绍的西方翻译研究各家流派的专著Introducing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Applications(2001)中,其中有关Venuti的翻译理论就占了一章的篇幅。笔者近来在深入研究其理论的基础上,发现Venuti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理论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在剖析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实质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翻译实践详细探讨了其理论的不足之处。
2.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
Venuti的异化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和The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Difference(1998)中。在这两本著作中,他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翻译,认为翻译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影响翻译过程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并进一步将翻译方法与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他从英美出版界出版的翻译作品的数量只占出版作品的总数的2.5%——3%得出(英美)强势国家和(非英语国家)弱势国家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平等交流,而是存在着一种文化霸权。通过对英美翻译历史的研究,他得出英美文化中译者和译作实际上处于“隐形”状态,并进一步指出翻译的‘隐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译者本人倾向于‘流畅’的翻译,努力使译本语言地道,‘可读性’强,从而使读者产生译文‘透明’的幻觉;(2)译入语文化中的不同读者层解读翻译文本的方式。译文读起来流畅,使人们觉得这不是翻译,而是‘原文’时,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认为这样的翻译作品(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小说还是其他类型的题材)才是可以接受的(1995:1)。
Venuti认为造成译者隐形的原因是由于归化翻译是英美翻译界的主流翻译方法所致(1995:20)。归化翻译使“外国文本的种族中心让位于[英美]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anethnocentric reduction of the foreign text to target-languageculturevalues),而透明、流畅、译者风格‘‘隐形’’则使译文几乎没有‘异味’(1995:20)。Venuti认为这种翻译类似于施莱艾尔马赫所反对的翻译方法:“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995:19-21)。与施莱艾尔马赫有所不同的是,Venuti的归化翻译还包括译入语文化对文本的选择,即有意挑选那些能够采用归化翻译方法的外国文本,以便于将之同化到译入语主流文化当中去(1997:241)。
鉴于归化翻译是英美翻译作品的主流翻译方法,而译者在这些翻译作品中都是“隐形人”,Venuti主张“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号召译者采取抵抗翻译策略(resistanttranslation),以显示自己在翻译中的存在。异化翻译与施莱艾尔马赫所赞成的“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的翻译方法极为相似。但Venuti的异化翻译的内涵更为宽泛:不仅包括译者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而且还包括译者选择要翻译的内容。即译者在“选择要翻译的外国文本和翻译策略时,选择使用那些被译入语主流文化价值观所排除在外的外国文本和翻译策略”(1997:242)。用Venuti的话来说,异化翻译是“对[译入语文化]价值观施加种族离心的压力,以[在翻译作品]中体现外国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1995:20)。他认为,异化翻译能够“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的暴力”(torestrain the ethnocentric violence oftranslation),抑制英语国家‘暴力’的归化翻译文化价值观(1995:20)。因而异化翻译又被称作是‘抵抗翻译’(resistanttranslation),即译者通过采用不流畅的翻译手法,突出翻译作品中外国文本的外来身份并保护原文本不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自己不再是翻译的隐形人(1995:305-6)。在1998年所著的TheScandals ofTranslation中,Venuti又将异化翻译称为“少数化”翻译(minoritizingtranslation),认为这种翻译能够创造出一种富有变化的、“含有异质成分的话语”(11)。
以上就是Venuti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的主要观点。下面,我们以Venuti自己翻译的意大利作家Tarchetti的作品举例说明他的‘异化’/‘抵抗’/‘少数化’翻译的实质。首先,他认为他所选择的作品就是一种少数化翻译策略:Tarchetti是十九世纪一位名气不大的意大利作家。他使用标准的托斯卡纳(Tuscan)方言来实验性地创作哥特式小说,以此来挑战当时的道德观和政治价值观。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对当时意大利文学规范的一种挑战。其次,从语言的角度来说,Venuti有意使自己的翻译语言包含一些异质成分,例如使用现代美国俚语来体现译者的存在,使读者认识到他们是在读翻译的文学作品。Venuti还从中节选了一段翻译,指出他所认为的最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包括对原文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亦步亦趋、仿造词语以及使用古代的短语等(1998:16-17)。另外,他还同时使用英语古语和现代英语口语,使用英国拼写法,来使读者认识到他的翻译是‘含有异质成分的话语’(Munday2001:147)。可以说,Venuti对自己译作的分析很好地阐明了他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的实质:(1)选择翻译那些被译入语主流文化排除在外的外国作品;(2)采用多种异化手段来翻译(这些手段能够使读者觉得这是翻译而不是原作)。Venuti似乎认为,通过他对外国文本的选择和异化翻译方法的使用就能够挑战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以达到文化平等交流的目的.
3.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中存在的问题
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使人们在讨论翻译方法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考虑到译者的翻译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政治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考虑到翻译方法与主流话语中意识形态的动态关系,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有利于我们从翻译历史的角度来较为客观地考察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地位。然而,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如下:
3.1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没有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目的和接受者的需求
按照Venuti的分析,由于英美文化翻译界中存在着大量的归化翻译,许多欧美翻译理论家提倡‘流畅’的归化翻译(如在国际上影响颇大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理论),绝大多数翻译家也在采用归化翻译,这样势必导致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在译入到强势国家中去时产生一种文化霸权,因而他呼吁译者来进行“抵抗”翻译,不“流畅”的翻译,以抵抗这种文化霸权。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当今西方翻译界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会响应Venuti的号召转而采用异化翻译吗?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两个实例。
当今西方著名的翻译家EdithGrossman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翻译以One Hundred Yearsof Solitude闻名英语世界的哥伦比亚作家GarciaMarquez的作品。在与英国翻译学者JeremyMunday的通信中她谈到自己翻译GarciaMarquez的翻译目标是“如果GarciaMarquez会用英文写作,他肯定也会这样写”(‘towrite as Garcia Marquez would have done had he been writing inEnglish’)(Munday2001:193)。笔者在爱丁堡大学听汉英翻译实践课时,翻译学者TyldesleyEsther(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和里兹大学翻译系,最近刚出版了她的英语译作AGood Woman ofChina)在课堂上对她的学生强调再三的却是“不要受翻译界什么异化翻译理论的影响,好的翻译应该自然、地道,能为英语读者所接受”。在几乎每堂课上,她都不厌其烦地举出学生作业中大量的chinglish,反对他们使用一些抽象的英语现代作品中很少用的古词,反对他们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混在一起使用,反对他们拘泥于原文的直译,因为她认为这些不和谐成分的存在会使英语读者觉得刺耳,妨碍读者的阅读兴趣;强调英语读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欣赏和娱乐,有他们的审美期待。有趣的是,在Esther看来,一部作品中的‘异质成分’实在是太多了,译者根本就不用有意去创造。如在翻译贾平凹的《闲人》时,其中有一段谈到闲人同他的女朋友“就会同骑一辆车子招摇过市,姑娘分腿骑在后座上,腿长而圆象两个大白萝卜”。她说一般英语读者读到这里就会感到困惑,因为把腿比做“turnip”在英语里不是说腿好看,而是说特别难看(英国的turnip粗短,颜色为紫红色)。还有在把一个人的眼珠比作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没有表情”也使她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在英国,水仙花是养在盆里种在土里的,而不是养在水里、有黑石子做衬的缸里的。她对学生说,直译的adaffodil vat/vase会使英语读者困惑不解。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来看,无论是吃翻译这份饭的名译家,还是从事翻译实践教学的翻译教师,Venuti的抵抗翻译方法至今好象少有译者效法。事实是,当代西方译家(不是翻译理论家)在谈翻译时,还是倾向于使用传统的“准确”和“流畅”的翻译标准,倾向于听起来“顺耳”的翻译语言(Munday2001:152-153)。
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在Venuti提出译者隐形的原因以前,少有译者认识到翻译的不平等,现在既然知道了,为什么响应异化翻译的译者如此寥寥呢?难道他们甘愿做隐形人,不愿反对翻译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其实,反对文化霸权还有更好、更有效的法子,即作者拒绝自己的作品翻译到英语国家当中去,如爱尔兰诗人BiddyJenkinson(Hermans1999:40)]1。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是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娱人;二是翻译的性质要求遵循一定的写作规则。文学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娱乐普通读者,使读者能够欣赏到异国的风俗、思想(当然,文学翻译史上也有个别的翻译例外)2。而翻译就其性质而言跟写作相同,必须遵循一定的写作规则,即英国文论家HerbertSpencer所说的“效果原则”:作者用词造句尽可能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保证行文能够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使读者费最少的力却能获得最多的信息(1959:19)。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流畅”的归化翻译在英语翻译史上一直受出版商和读者欢迎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古今中外真正受欢迎的优秀翻译家在翻译中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都是“流畅”的“隐形”翻译3。例如,十七世纪的英国翻译家Dryden在翻译Virgil的诗歌时说,如果Virgil出生在这个时期的英国,会讲英语的话,他也会这样说(“makespeak such English as he would himself have spoken, if he had beenborn in England, and in this presentage”)。我国优秀的翻译家傅雷说:“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又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罗新璋1984:989;558-59)。在我国颇有影响的钱钟书的‘化境说’,也要求译文语言既无“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要“读起来不象译本”。可以说,Venuti无视文学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性质是他的异化理论在西方应者(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寥寥的主要原因.
3.2异化翻译能否改变英美国家的翻译状况值得怀疑。
A Pym在其书评“Venuti’s Visibility”(1996)中,对Venuti的异化翻译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如果译者拒绝流畅翻译,英美的翻译状况就会改变吗?我们还可以接着问,译者是改变英美翻译霸权现状的决定因素吗?Pym一针见血地指出,Venuti号召译者“反抗流畅翻译”,但实际上却是除了他本人作为一个翻译理论家进行实验性的翻译实践外,英美翻译界少有译者响应(如3.1所示)4。即使有译者响应,Pym也怀疑他们的翻译作品能否被出版社接受出版。
英国翻译学者Munday提供的一个翻译案例恰好证明了Pym观点的正确性。Munday曾翻译过一部拉美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篇阿根廷作家HectorLibertella所写的小说“Nineve”。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故意使用含糊的语言和语言游戏来描写主人公(一个考古学家)对古代碑铭的理解,以揭示人类试图通过阅读古老的象形文字来破解古代文本的主题。作者在叙述故事时有时故意使前缀词re与它的构成词分开来写(如repartimos, repone),以形象地再现主人公费力解读碑铭上的象形文字的神态。为了体现作者这一用心,Munday在翻译时,有意识地采用了异化翻译方法,将这段西班牙文翻译为下面的英文:
Extending his gaze over these lines, Sir Henry re read them athous and times, as far as his dis tracted eyes allowed him, and bydin of pure re petition petition he eventually ex hausted the linesand ex hausted one letter more every time he re read them. And rered them.
在上面的这段文字中,尽管作者并没有使用前缀词re与它的构成词分开来写这种创新技巧,但在翻译时,译者有意采用了前缀词re与它的构成词分开的做法,试图再现主人公在反复阅读碑铭上的象形文字时的困惑。另外,译者还创造性地使用rered这一手法(故意将re read拼错)来试图形象地再现主人公在费力阅读的过程中不小心漏读了一个字母的情景,以使译文读者在读到此处时感到惊讶。然而Munday按照异化翻译方法所翻译的这篇小说,却遭到了出版社的拒绝,因为出版社认为译文读者难以理解他所尝试的翻译实验(2001:177—178)5。
这正如Venuti本人早已经意识到,并且所指出的,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地位极其低下,要翻译哪些外国作品(无论它们是符合主流文学规范还是不符合主流文化规范),委托哪个译者翻译,支付多少稿酬,甚至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都是由出版商来决定的(Venuti1992:1-3;1998:31-66)。其实,不用说译者,有时连作者选择译者的权利都没有。例如,德国作家ThomasMann的作品都由拥有其作品专卖权的美国出版商AlfredKnopf 委托美国翻译家Helen Lowe-Porter翻译。在翻译 TheMagicMountain(1924)时,作者对Helen是否能胜任这本书的翻译表示怀疑,希望出版社能找别的译者来翻译,但是出版社最终还是决定由Helen来翻译,虽然作者和译者的翻译主张极为不同(Hermans 1999:1-2)。
而且,出版商和他们的编辑无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都喜欢“流畅”的归化翻译。多数编辑在工作中最为关注的是翻译应该在译入语中“读起来不错”(readwell)(Munday2001:154)。身处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的译者,虽然可以选择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只能是自己的译作被拒绝出版。这样一来,又有多少译者勇于(不计经济利益)进行“抵抗翻译”呢?(美国翻译理论家DouglasRobinson好象说过,职业翻译家是不敢像有稳定工资收入的大学教授那样想怎么译就怎么译,而不考虑翻译发起人/委托人的要求的)。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理论家的号召归号召,英美翻译界的状况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将来也是不大会改变的。当然,从翻译数量上来说,随着英美出版书籍的增长,翻译作品的数量也会相应地增长,但这很难说是异化翻译理论的功劳。
3.3“流畅”/归化翻译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是强势国家的主流翻译方法。
“流畅”/归化的翻译不仅在英美强势国家是主流翻译手法,在其他弱势国家也是占主流的方法。Pym指出,尽管Venuti在倡导他的异化翻译观时,关注的对象是英美国家的翻译作品中存在的霸权倾向,但是‘流畅’/归化的翻译手法在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作品里也普遍存在,如巴西、西班牙和法国的翻译作品都是如此(1996:170)。意大利名作家UmbertoEco在其新作 Mouse or Rat? Translation asNegotiation(2003)中指出,无论是他翻译别人的作品还是各国的翻译家在翻译他的作品时,他对翻译的要求都是“好的翻译必须能够取得原作所追求的效果”[agood translation must generate the same effect aimed at by theoriginal (56)]。例如,在他的小说“Foucault’sPendulum”中,主人公经常使用文学典故来描写他们的所见所思,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文学典故,他告诉各国翻译他的作品的译者,他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按字面意义译出这个典故,而是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文学典故来替代,因为他更为关注的是译本所产生的效果能否和他自己的作品所产生的效果一致(66-71)。在Eco对翻译的要求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的影子6。
实际上,就连Venuti所攻击的奈达的归化翻译理论,其目标也不仅仅是将希伯来语、希腊语《圣经》归化到英语国家中去,还包括将《圣经》翻译到许多弱势国家的语言中去。奈达的专著Theoryand Practice ofTranslation(1969)实际上是一部指导世界各地的《圣经》译者的教程。由于他的翻译理论成功地指导了《现代英文译本·圣经》(Today’sEnglishVersion)的翻译,从而使《圣经》协会及其译者相信奈达理论在《圣经》翻译中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多的《圣经》译本才开始采用奈达的翻译原则。例如,《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翻译就是在其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在该译本《圣经》的翻译启动之前,奈达在台湾和香港主持了《圣经》中文翻译的讨论班(Strandenaes1987:123)。1971年,香港圣经协会和台湾圣经协会联合制定了《现代中文译本》的译者所必须遵循的“1971年翻译原则”(Principles1971),这个原则与《现代英文译本》所采用的翻译原则几乎完全相同(Strandenaes1987:131)。这样说来,Venuti指责奈达的归化翻译理论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7。因为按照Venuti的说法,弱势国家若采用奈达的归化翻译,那么奈达的理论实际上则成了反文化霸权的理论。这正如Tymoczko所指出的,Venuti提倡的翻译策略只适用于占优势的强势文化,对于受压迫的弱势文化并不适用(马会娟2001)。然而,Venuti本人却声称,他的异化翻译理论并不限于哪个国家和哪种语言,而是具有理论的普遍意义(2001见其与马嘉的通信)8。
如果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说,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翻译主流方法更是归化翻译,如我国翻译家孙致礼所指出的:以英语翻译界为例,近一百年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些翻译大家,从晚清时期的严复、林纾,到三四十年代的朱生豪、吕叔湘、张谷若,到建国后的杨必等人,个个都是‘归化派’的代表;这些人物当中,除严复、林纾之外,其他人的译作至今还在广为流传,并受译评界的赞赏。而在“异化派”的代表译家中,鲁迅虽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但其译作因为过于拘泥于原作,故而不像其创作那样广受欢迎;董秋斯的译作虽然力求忠实,但有时过于拘谨,缺乏文采,因而其感染力也大打折扣;卞之琳等译家虽然成功的用诗体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但影响似乎还及不上朱生豪的散文译本。(1999:31-32)
可以说,无论是Venuti所批评的奈达的翻译理论,还是弱势国家的翻译实践都说明了Venuti将翻译方法与文化霸权联系起来的做法过于勉强,难以自圆其说。正如Pym所指出的,在当前翻译界,不管原语和译语之间的权利关系如何,归化翻译仍将是各国翻译家所采用的主流翻译方法。Eco对各国翻译他的作品的译者的要求(既包括弱势国家也包括强势国家),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翻译趋势与意识形态并无多大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Venuti本人也已经认识到他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存在着问题,如异化翻译这一概念是主观的、相对的(1995:29)。在他的著作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1999)的意大利译本前言中,Venuti还指出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不是两元对立的,而只是“具有启发性的概念,旨在引起人们的思考和研究”。他解释说,“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这两个概念根据具体情况是可以变化的,它们只有在作品被翻译并产生影响的具体文化情景下才能够被定义”。这样看来,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极为模糊了
四、结论:异化翻译的理论基础及可能的负面影响
由于Venuti过分关注政治对翻译方法的影响,其所提倡的异化翻译理论忽视了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没有考虑到接受者的需求。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读者无论是读本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消遣娱乐。如果像Venuti那样为了证明其异化翻译理论而进行的实验性翻译,不仅是评论界对其译作褒贬不一;而且,到底有多少读者会耐着性子把这样一部读来费力(不流畅、不透明)的翻译作品读完而不是中途抛掷一边也值得玩味。当然,这样说也许过于绝对,DouglasRobinson所说的文化精英分子也许会对“异化翻译”作品欣赏有加。因为这些人读翻译作品不是为了去接近外国作品(因为他们本人都懂外语),而是想换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译作[据说,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翻译家Dryden和当时的许多译者所翻译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是给那些能够阅读拉丁语或希腊语古典作品的读者去阅读的,因为他们感到好奇,想了解译者在翻译中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优雅和灵活。(Hermans1999:40)]。可以说,异化翻译的对象主要是一小撮世界主义知识分子(cosmopolitanintelligentsia),而异化翻译所存在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文化精英主义”(culturalelitism)。文化精英分子瞧不起普通大众,嘲笑他们要求容易理解、读来省事的翻译。Venuti在强调利用翻译方法来反抗文化霸权的过程中,无疑把自己摆到了文化精英的位置。这也就难怪他所提倡的翻译方法既得不到他所要拯救的译者的响应,又受到一些西方翻译理论家质疑的主要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Venuti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可能给我国翻译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给那些翻译水平不高的人从理论上找到借口(毕竟出版商有时出于节省成本的目的或缺乏对翻译的认识,而应用一些只有外语能力而不具备翻译能力的人去做翻译),打着名正言顺的异化翻译的旗帜去制作大量的“不流畅的”劣质翻译。实际上,在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就有论者认为赛珍珠译《水浒》中,将所有的骂人的话“放屁”都译为“Passyourwind”是作者有意采用的“保留原文特色的”异化翻译手法,而不顾这样的翻译是错误的、歪曲的翻译的事实9。如果不顾语境的直译算是异化翻译的话,是不是“嫁祸与人”译为“marrymisfortunes to others”,“意趣横生”译为“interestsflowhorizontally”都是反抗文化霸权、追求文化交流平等的好翻译,值得未来的译者效法呢?
注释
1.BiddyJenkinson拒绝将其诗歌翻译成英语,因为她反对那些以为任何作品都可以翻译成英语而没有损失的出版商和译者(Hermans1999:40)。
2.例如,英国十七、十八世纪有些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读者读翻译作品只是为了想了解译者在翻译中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优雅和灵活程度(Hermans1999:40)。
3.这也是译者甘愿做隐形人的主要原因。另外,Venuti本人所说的在翻译那些被译入语主流文化所排斥在外的外国文本时,可以采用流畅翻译,道理似乎也在此(Venuti1995:310))
4尽管Venuti认为Pound采用了异化翻译,但Pound选择的翻译方法并不是针对英美的文化霸权,而是为了实现他的革新创作的目的。Hermans这样解释道:Pound通过介绍或寻找诗歌创作的新颖方式试图打破爱德华时代的诗歌创作的风气。他选择某些文本来翻译,使用一种特别的、令人惊讶的翻译风格,来作为撬开当时流行规范的撬竿,其最终目的是用自己喜欢的诗歌模式取而代之(Hermans1999:33)。
5.从本文中所引的Venuti的异化翻译的翻译实践来看,他所采用异化的手段并不都来自原作,还可以源于译语。从这一角度来说,Munday的翻译确实属于异化翻译,目标都是让读者感到吃惊,使他们认识到这是翻译。
6.在Eco关于“好的翻译”的注释里,就有参考奈达的Towardsa Science of Translation有关等效翻译的论述。
7.张南峰在“Value Judgments in Chinese TheoreticalTranslation Studies: As Reflected in the Reception of Nida’sPrinciple of EquivalentEffect”(1999)一文中指出批评奈达的翻译理论为文化霸权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奈达的翻译理论除了指导《圣经》英译外,还指导《圣经》译者将其翻译到非洲等小语种中去。
8.Venuti在与马嘉的通信中声称(请参见马嘉《当代中西异化论的差异性》的附录),他所提出的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具有普遍性,并不限于英语国家:Youwill notice that I have not referred to specific languages orcultures. I do not regard any of these ideas as applying solely toEnglish or English-speaking cultures. On the contrary, no cultureseems to me immune--or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the interrogationthat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can bring to it through certainlinguistic and cultural moves, whether that culture is globallydominant or marginal, whether the language in question is major orminor.
9.见马红军《为塞珍珠的“误译”正名》(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三期)。
参考书目:
Eco,Umberto. 2003 Mouse or Rat? Translation as Negotiation,London: Eeidenfeld&Nicolson.
Hermans, T.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Manchester: StJerome.
Munday,Jeremy.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and Ap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Nida, Eugene A. 1964 Towards a Science ofTranslating. Leiden: E.J. Brill.
Nida, Eugene A. & Charles R.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E.J.Brill
Pym, A. 1996 ‘Venuti’s Visibility’ (Review of 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Target 8.1:165-77.
Robinson, Douglas. 1997, What Is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Interventions.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pencer, Herbert. 1959, The Philosophy of Style. New York:Pageant Press, Inc.
Strandenaes, Thor.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D].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7.
Venuti, Lawrence,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2.
---.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5.
---.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M. Baker (ed.) The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Routledge 305-15.
---. L’invisibilita del Traduttore: una Storia dellatraduzione, translated by M. Guglielmi, Roma: Armando Editore.
曹明伦《异化翻译讨论中的几个异常之处》,2004。见网址http://tscn.tongtu.net
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
马嘉《当代中西异化论的差异性》,2002。见网址http://tscn.tongtu.net
马会娟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况-兼谈MariaTymoczko的翻译观》载《中国翻译》,2001。
孙致礼《翻译的异化与归化》载`99全国暑假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讲义,1999。
http://seis.bfsu.edu.cn/cont2.asp?n=378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