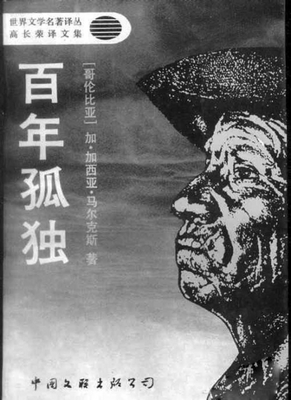《八千里路云和雾》,从近日一场举办于上海的,从演奏者到现场听众都并不那么完美的医师交响音乐会谈起,可谓思绪纵横古今,帷幄千里的一篇雄文。文章以音乐会为轴线,穿插着听者不断跳跃而递进的思想变奏,主题由此更加复杂而深刻,同样有交响乐的结构特色。亦可命之曰“熊文”——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我向来尊重,喜爱的五颜六色的熊先生。
诚如空空般若兄之论此文:我看到了一篇美好的“音乐会”!那么如果能有更多朋友加入进来,这场交响乐,岂非可以通过多种乐器的加入,多部乐章的迭加,经由磨合,排演,达致和谐与多元统一的,更为美妙的境界吗?故此,在欢喜赞叹之余,不禁也起了奏鸣,应和之意。于是,便随着熊先生的主调,有了下面的复音协奏。
熊文的精彩,拜读过的朋友当能体会,限于原文篇幅之大,所论之宏远,也不便由我在此复述。不过,我们若将熊兄文中列数的,诸多关涉音乐会听众文明素质;汇率,通胀,银行呆帐;土地财政,政府债券危机;金圆券往事与当下滞涨困境;金融体制及房市骑虎难下,以致决策高层左右为难;民间高利贷及老板走佬,国内中小企业之现实困境;中上阶层吸吮民脂民膏,纵欲淫逸,华西村之剥削与集权本质,传统文化之中庸,国共之争......种种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归结起来,或许可以如很多有识之士之论中国模式的本质那样,皆因其低人权“优势”。由此所导致的“中国社会目前处于城乡失衡、东西失衡、贫富失衡、朝野失衡、经济失衡、外交压力的六重危机之下”,由此所呈现的畸形当代中国,也就无法避免。
既然难以为继的“中国模式”的根子在“低人权优势”,而“低人权优势”的根子又在此制度,那么我们当然要从制度谈起。面对无孔不入,却又无迹可寻的制度,个人的力量自然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即便连熊兄也在文末坦然而无奈的承认,“凡此种种问题,作为小民无力左右,但小民们聚在一起,难免对中央智囊团有所不恭。”——是啊,眼见得如此前现代之,长期停滞之国民心理,民众素质,加之变态维稳,新式洗脑(手段为控制网络微博,内容为鼓吹明君崇拜,在对当局的改革寄托下,分为:一,言行不一,只讲单向度“宽容”,“非暴力”,从不践行“不合作”的体制内改良派,二,价值观模糊混乱,既不愿右更不敢左,勉强拿党国不分的国家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做遮羞布,鼓吹愚忠愚孝的当权的维持现状派;三,新老毛左派。进一步来说,新左派诉诸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诉诸十七年路线或新民主主义,或回到马克思原典,毛左派诉诸文革模式),想要“聚在一起”,何其难也!所以熊文最后,也只好不出所料,聊尽其责的回到新文化运动的旧辙上。并且有如此一番感叹:“复杂的人类根本问题还是低俗与贪婪,要解决的终极还是只能靠文化启蒙”。
诚然,这个药方是不错的,是政治正确的,但我们都无法否认:它实在太空幻,太遥远。想要在目前文化体制改革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制度环境下,实现民众的文化启蒙,简直比当年新文化运动要艰难千百倍。而且经过多年红色洗脑,我们也不可能奢望等待大多数民众觉醒之后,才来谈制度转型问题。要求沉重现实下一点切实的,可以把捉的希望,依然只有靠先觉者和先行者的坐言起行。通过“聚在一起”,达成基本共识,形成组织上的凝聚力,并藉由信息时代的多点传播,放大效应,造成思想和社会风潮,最终点燃自由之火,遍传所有存在着不公不义的专制之恶的角落。
事实上,从近期的利比亚,也门到叙利亚,到远一点的东欧苏联,都是这样由点及面,聚少成多,逐步的,分阶段的开展起来,终于成就民主伟业的。现实当然不容乐观,但并非我们就此放弃的借口。只要回首1500年源自欧洲的全球化,现代化历程,历来的制度转型,社会变迁,便会发现,从来都是少数人带动大多数不知所措,无所作为的国民,然后吸引更多人加入民主事业,迫使那些不愿走,不敢走,不能走的人动起来,直到最后从量变到质变,来到那个在长期积蓄力量之后因某个偶然性因素而触发的临界点,最终走向根本制度的丕变的。
所以对现实我们当然要如熊兄那般,清醒认知,尖锐批判,但又不仅如此,更不可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遥远的,难以落到实处的“文化启蒙”之上,留待将来而想要无病无痛,无伤无损,在社会全体都达成共识之后,才来毕其功于一役。越是面对严峻现实,越是需要我们站起来,站出来,越是需要我们保持乐观态度,坚持到底,否则大家都被历史,文化和现实压死,又何谈任何希望?
我曾一再强调,如今问题已非单纯的主义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之争。试想,当局都是体制内精英所组成,获取比大众更充分,及时和完备的信息与思想资源,难道我们能设想他们比盲愚大众更不懂得现代普世价值,不懂得专制之害,不懂得自己在玩危险的击鼓传花游戏,不懂得民主对国家民众的好处吗?问题正在于此制度钳制和利益所在,使得那些当权者面临逆向淘汰机制,无意更无法对自己动刀,如此,我们就更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从外部对此僵化的制度进行彻底批判和组织撬动,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望于“文化启蒙”这个远景上,如果依然在秦晖先生所批评的,“器物,制度和文化”的三级思维框架下思考问题,一次次陷入“文化决定论”的陷阱里,以至于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核心的,关键的制度链条,以至于主动的放弃了自我拯救,自我组织的意愿,那么我只怕此类民间的,散乱的,茫无目的的启蒙,势必将遭遇专制当局集中所有资源所进行的反启蒙,遭遇合法暴力的任意打击迫害,而少数的启蒙者,将在孤立无援和普遍的误解与嘲笑,沉默中,就此消失于黑暗的监狱里。
显然,我们需要如熊兄这样,清醒而尖锐的审视当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现实的批判者。无疑,这篇文章透露出来的思辨深度,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些见木不见林的,有意无意为当局背书,一厢情愿乞求当局施恩放权的体制内改良派。但仅仅认识到问题还不够,我们必须从具体问题透视更深层的制度根源,因为文化是虚的,是需要长期的,缓慢的改造的,而制度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可以切实改变的。仅仅因为现实的黑暗而诉诸“文化启蒙”,以至于忽略制度层面的思考,恐怕过于理想,也无法落到实处。何以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启蒙很快被专制党所挤压,被革命,战争的主旋律所凌驾?不正是那些文化启蒙者永远停留于口头笔下的启蒙,而从未形成真正现代的社会民主力量吗?
当然,以上只是就熊兄文末将中国的出路归结为“文化启蒙”这个观点的一点补充,并不意味着否认启蒙的巨大功效。我的意思只是提醒作者和朋友们:启蒙是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绝非全部。在坚持思想启蒙的同时,我们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工作可以做,应当做,必须做。
这也可以说明我对体制内改良派的一贯态度:这些体制内朋友出于学术研究或良知促使,打破多年来党内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沉默顺从局面,勇于面对大众,对形而上的民主观念作普及,启蒙之功,对局部现实的某些揭露和批判,实在不应忽略,应当给予高度评价;但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却是不切实际的,是掺了思想的毒药的。我们既不能因后者而否定前者,也不能因前者而对后者全盘接受。
既然谈到了改良派朋友,这里不妨再对之作一点社会身份和思想背景上的考察。前文已经初略涉及国内改良派的社会基础——即百分之一的特权党及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被剥削者以外,那百分之几所谓“中产阶层”,这里就改良派本身也来审视一番。由于共产体制对知识分子的多年持续整肃,严密控制(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运动:反右;对当下有直接影响的政治操作: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全面清查监控),所以今天体制内知识精英,从一开始便背负了沉重的身份局限,组织关系,另一方面又因当权者的收买拉拢,与此体制早已利益攸关——相反,若是敢于违逆上意,很快就将遭遇职业,事业与经济危机,甚至招来司法迫害,牵连亲友,种种无妄之灾。比如长平先生,非但被南方系扫地出门,甚至连赴港工作也成泡影,天下之大,竟然无一人立身之所。我党为了杀一儆百,非得置之死地不可。
在组织控制,个人名利的多重羁绊之下,在威逼与利诱的正反合力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体制内知识精英思想背景上,更为复杂深刻的问题。可以说,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受传统士人思想,精英治国论的潜移默化,故而对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发展出来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都情有独钟。这种深层的传统思想烙印,使得很多现当代知识分子仅仅把民主自由当做缓解层出不穷的国内矛盾,推动国家富强的方便工具,权宜之计。其中体现出工具主义,实用理性的浓厚色彩,而非将之视为最核心的价值理性。所谓“取法乎上,得其中也”,如果对自由民主本身便是我们存在的出发点和目的,这一点也无法体认,仅仅满足于不说假话,或是做一点补苴罅漏,聊胜于无的工作,甚至最高理想也不过是做到“王者师”,又如何期待体制内能有真正的民主斗士,挺身而出?
由于来自极权社会对知识精英,和知识精英价值观本身的,内外部的诸多制约,决定其自我定位和价值取向上的混乱,导致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内部对立与巨大张力。由于多年权力操弄,任意折腾,使得像吉拉斯,王若望这样毅然决然,走出死海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始终百不一见,寥若晨星,反而促使体制内知识分子出于现实考虑,出于自保本能,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由主义摆在党国主义之后,将集体主义凌驾于个人主义之上,竭力维护其真正信靠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结果被以党代国,以党制国,以党灭国的当权者利用。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甚至沦为权力核心的一部分,党阀与学阀,党棍与学棍沆瀣一气,从青年到中老年,从投机到投身,自理想主义的高度一点点蜕变滑落,为政统之合法性,及其与道统的合一出谋划策,宣传鼓吹。
对多数体制内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从始至终都把自己摆在谏臣的卑微地位上,奉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有少数人见缝插针,无惊无险的宣传以个体独立自由为起点的现代价值理念。自己都谈不到独立自主,却鼓吹公民自由,结果自然无法做到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人,自我期许完全落空。在此无法调和的身份与思想矛盾下,既得利益者与知识分子的角色错乱中无所适从,甚至人格分裂,由此导致批判的范围,力度徒有其表,言论的自我审查,思想视野的自我设限也自然是题中之义。终于沦为叶公好龙之辈,惹人嘲笑与叹息。
将岔开的话题拉回,让我们回到《八千里路云和雾》来。无疑,一方面,熊兄已经比改良派走得更远,已经完全对当权者否定,不再抱有任何体制内改良的希望,无论是思考深度和批判锋芒,在此文都有精彩展现。大概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都自叹弗如。但在结论部分,却和改良派并无多少不同,过于寄望于所谓的“文化启蒙”,或是“国民自省”。在八千里路的跋涉起点,在云里雾里中,临歧徘徊,以至迷失了方向。
我们中国人,向来既喜欢无原则的中庸调和,在同而不和之下,在无法可施之下,又往往爱走极端。其实制度层面的努力空间,大有可为,精英政治固然不可缺少,草根组织也需要认真扎根。可惜很多朋友如辛亥革命之后民初的知识分子一般,尚未于此真正尝试,有效开拓,或是稍微遇到阻碍,便轻易否定了制度建设或社会自救的重要性,跳跃到最后亦是最无可奈何的“文化启蒙”,或民族性,国民性层面。这背后透露出一种深切的无力感,我也感同身受,但为了走出制度依赖,打破恶性循环,依然要指出其中的某些认识上的局限,提示路径选择的另一种思路。
笼而统之的认定存在决定意识(制度决定文化),或是意识决定存在(文化决定制度),都不免偏颇。然而人是活的,能动的,人之为人,便在其自我建构之主体意识,并将此主体性主动投射于个人生活与社会之中。即便是宗教信仰,也是通过对至善至美至真之人格神的崇拜,汲取精神力量,藉以建立起信众自身的圆满精神世界。由此看来,今日无数个体的选择,决定了日后吾国吾人之整体命运。故无碍于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撷取其中关键,以为链式聚变之机。对此间轻重缓急之取舍,在《怎样打破制度死结?》一文里有更详细的讨论。并于文末引用了《“三个链条”捆死了中国》这篇文章。我们不妨将其中如何解开“三个链条”的相关论述,摘录如下:
“这种皇权至上的传统文化,巩固和维系了专制制度。而统治者又用绝对的权力,保持这种文化的独尊地位。这两个“链条”的相互捆绑,就勒出了劣质的中国人。於是,劣质文化塑造了皇民,皇民维护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保护劣质文化的垄断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由此形成中国几千年的专制、落后和封闭。
“怎样打破这个链条?有人提出必须先造“新人”,中国才会有真正民主;否则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没有民主意识的人,都不会成功。因而中国改革派知识份子十多年前就提出“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更早时,梁启超则提出“新民说”。这位曾到美国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启蒙者,看到中国人在旧金山仍是一团散沙,勾心斗角,根本不参政问政,因而更加确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国才能建立民主。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可能是受梁的影响,也要塑造“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后都失败了,因为专制制度不改变,不仅无法塑出新人,即使像毛那样造出“新人”,也是《动物农庄》式的整齐划一,反而更糟糕。
“在中国知识份子中,更有人大声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文化基因不改变,根本不会有现代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胡适一生强调西化,都是认知到改变中国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无论是鲁迅时代,还是胡适活着时的台湾,以至当今的中国,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西方文化的进入,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一种会唤醒人的权利意识,最终结束他们统治的文化。因而中国几次文化启蒙运动,最后都失败或无疾而终,都和当权者的抵制或压制有关。
“由此看来,在制度、文化和人的三个链条中,首先应该把制度的改变作为优先目标。因为只有结束专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竞争的环境下,以优胜劣败的正向淘汰,扬弃专制文化,改变传统价值取向。而且和改变一种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改变制度较快,其他两项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渐进演变。
“当然制度的改变只是第一步,更关键、更长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变,只有这种改变,才可能产生具有公民意识的新人(不是顺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维持和完善一种民主的制度......要想改变这三个链条的捆绑,首先需要有智慧看到这种链条的落后和禁锢,然后有勇气参加打破这种链条的行动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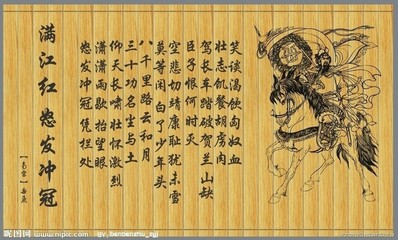
旧文俱在,道理亦经反复申说,说多了未免无趣,还是就此打住。
(全文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