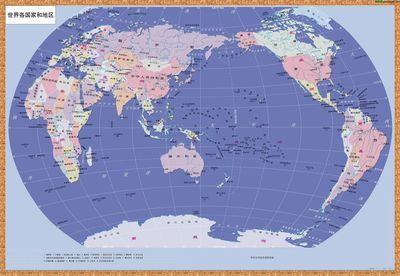回想起22年前,我们在统战部座谈,讨论多党合作制度,当时我有一个发言,认为多党合作没有什么前途,只有多党竞争才有前途。我举的例子是:共产党在野时是最有活力的时候,但是一旦获得政权以后,其活力逐渐丧失,是因为不再有竞争。
学潮期间,统战部邀请参加调停,我都积极参与;戒严前夕,我曾给陶斯亮打过一个电话,问能不能有老同志出来说话,救救这个党?——她的回答令我很无奈:“老同志们的想法都和你相反”,事件的结局会是怎么样,我也就明白了。到戒严那天就更明白了,老人和年轻人,是同一种体制教育的产物,具有非此即彼、成王败寇的思维。我们中国人几千年都吃这个亏,不懂得妥协,不懂得共存,只懂得“彼可取而代之”,只懂得“均贫富”。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上的仇富、民粹主义等等,还是这个心态。我很感慨的是,这22年 的时间,把改革耽误了,我们已经从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现在还要面对这些问题。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中华民族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形铁路上行驶,我们绕了一百年圈子,仍在追求宪政,最后还追尾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可悲不可悲?我觉得很可悲!中国能不能有宪政,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是要多参照一些失败的先例,中国历史上改革没有成功的,改革家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封闭的循环之中。
清末的改革,戊戌变法由国事变成家务事,变成母子之争。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党派的利益与全民的公共利益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界限?我觉得要改革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徐景安刚才谈到他的方案,主张我们考虑清楚哪些是执政党不能接受的,哪些是它的底线。底线其实就是永远执政,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
大清的宪政改革是失败的,国民党46年搞行宪国大的时候,也想改革,但是没有时间了,最后被共产党带领农民把他们赶走了。国民党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老蒋时代搞土地改革,小蒋时代又搞政治体制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蒋经国是个拥有资源的强人,这种人在历史上不是很容易碰到的,我们这个体制已经不太容易生出这样的强人了。蒋经国他也有这个见识,他经历过斯大林时代那一套,国民党的特务政治也搞过,最终认识到“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句话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舍得”,就没有后来国民党通过选战,政权失而复得。一个政党的活力在于竞争,从竞争中胜出的才是强者。
这六十多年就是从无竞争状态中走过来,现在的“顶层设计”不包括竞争机制。或许有党内的竞争,但是不可能有党与党之间的竞争,只能通过内生的党内民主等方式实现一些竞争,这样的竞争是否足以使共产党重新获得活力,我是很怀疑的。当今已是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号令不出中南海,地方不对中央负责,部门不对全局负责,党员不对党的执政地位负责。这样的体制不改革,一味重金维稳,最终只会压垮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除了今天在座的各位在党的同志,已经很少有人为执政党的未来着想。不少党员都在谋私利,党垮台与否与己无关,捞够了钱,孩子家人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船。有的没准还在琢磨,手里的昧心账不好交代,一旦变天了,这烂账就抹了……。
我感觉现在中国不危险,共产党真的很危险。我是一个不在党的人,只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观察目前共产党的处境。从情感上来讲,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力政权突然崩溃后,变成一个失控的暴力世界,经济民生遭遇重大灾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场景。
不久前与法学界朋友聚会,合影照片被人贴到微博上去了,于是有网友问:你们这些人在干吗呢?我的回答是一则寓言:“危楼上,江湖郎中数人夜酌,聊起一桩疑难杂症。体量虚胖,五脏溃烂,病入膏肓,中枢麻木。病家讳疾忌医,医家徒唤奈何。”个人点评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注:此文刊于《炎黄春秋》2012年1月号)
章立凡在深圳大学的讲演(摘要)

章立凡在深圳大学讲演现场
同学们好!我今天下午才过来,在这之前我曾经跟主办方有一些沟通,我说我是很愿意和同学们一起交流的。而且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觉得我好像年轻了好多。我们这个话题怎么说起来的呢?我做点交代,本来商量的时候,凤凰网他们说您是研究近代史的,是不是给同学们讲讲北洋军阀史,讲讲他们不太了解的。后来我想,是不是可以聊聊我们大家都共同经历了的“历史”。
已经凝聚的历史,你们上网可能就能查到。有一些历史,是不知不觉地从我们的经历中逐渐地凝固下来,变成历史的,这其中就有互联网。我可以这样说,我算是一个资深的网民,我的网龄大概有15年,我是1997年开始上网。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我大体是经历了。我以前常这么讲: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你昨天经历的事情,它就逐渐在凝固,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归到历史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可能都会走进历史,包括我自己;也许哪天我就跟你们大家都告别了,这个没有办法,是自然规律。
我先说说我自己当年是怎么学习的,大家都说现在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但是学习的方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和互联网出现以后有非常大的区别,对我这种同时有两种经历的人来讲,几乎是有颠覆性的。1979年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记笔记。
我们那时的写作就是爬格子,在400字的稿纸上写,我写作都是一稿、二稿、三稿、四稿,我都要重新写一遍,这种写作方式,现在大家不会采用,除了一些老先生还这么写。到1997年,这一年我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我开始上网了。我上网的时候还是很原始,是用电话拨号上网。那时稍微早出现的东西就是手机,在9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一开始是像半块砖那么大的手机,然后逐渐缩小,接下来才有上网。
我那个时候上网,说实在的,那个网络是一片蛮荒,或是完全是江湖。你在上面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任何的规矩,也没有防火墙、金盾工程,这些都没有。坦白地讲,我也看了很多以往非常禁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黄色网站之类的,也确实看了。
这个没有办法,那时我也只有四十多岁,还不算老。但是有很多的思考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忽然发现人可以通过网络走出国界,互联网这个东西是一个两头在外的东西,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什么护照,什么这一套出国的签证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了,只要大体上你会一些外语,你又会汉语拼音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本事够,你能搜到你想要的东西。我刚刚上网的时候,除了雅虎以外,还没有像Google这样的东西。那时搜索还不是很方便。后来金盾工程出来了以后,有网络长城了,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有些网站我访问不了了。刚开始采取的办法就是用代理服务器,那时候我们现在常用的几种翻墙软件还没有出现,主要的办法就是去找境外的代理服务器,通过它就翻过墙,可以看到你想看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心态,就像儿童一样,你越不让我看的东西我越想看,其实我对不让我看的东西,本来不是很有兴趣。只不过因为是大人不让看,所以我反而要偷着看,就是这么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怎么来的?我后来自己也做了一些反省,好像人都是这样的,包括看A片也是这样的,都是大人不让做的事情,一定要偷偷的试一试,包括吃禁果也是一样。
这个事情我后来又有一个思考,我为什么总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人家管着?谁有资格来管我?我开始反思,管我的体制是不是也需要适应、需要与时俱进,不能总停留在平面传播的时代?我发现互联网这套管理体制,实际上是跟文革前包括文革后一段时期,没有出现互联网的时期相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平面媒体上获取资讯。管理只要卡住了源头就行了,只要变不成铅字你就传播不了,那个时候的管理是比较简单的。
自从出现了互联网以后,它是有颠覆性的。我在想,这种颠覆到底有什么特征?简单的来说,我在刚刚进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抄卡片,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一些史料上来。我们主要的功课就是抄卡片。抄卡片这种治学的方式,用史学界位前辈范文澜先生的话讲,“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那个时候由于资讯的匮乏,你获取资讯的周折比较多。我们很难得有一本好书,你一定要把它读透。而且要写读书笔记,要做卡片。所以那个时候的做学问不像现在,现在是你有非常广泛的资讯来源,你上网一搜,主题词下给你提供各种各样海量的资讯;那时只能凭有限的一些书刊、资料,你把它汇拢过来筛选,最后得出你想要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写成论文或书。那个时候做学问,由于来源少,手段落后,我们治学的认真程度是比较高的,有一本好书就要把它读透。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方式逐渐的消失了。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某一个人很投入的去读一本书,认真的做读书笔记,做卡片,把它真正消化掉。现在好像不是这种治学方式了。在90年代末,我和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对话,谈今后会是怎么样,今后社会、学界会是怎么样。
我提出一些观点:一是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我预测在未来十年以后,写论文、著作的方式会有改变。因为大家只要上网,把各种各样的文章拷贝下来再重新组合一下就变成一篇论文甚至是一本书。我说那个时候浮躁的学风一定会出现。二是将来不会再有名人手稿或是名人书信尺牍之类的东西。因为以后大家都用电子邮件交流了,你想搜集名人的手迹,这一类的东西不太容易了。再过若干年我们俩又聊起这件事,他也确实承认,我说的这两点好象都变成现实了。至少我知道像在北京的潘家园,如果你想买一份名人书信,价钱上去了,这类东西已经变成藏品,而且越来越少了。
治学模式的改变,还有一种是思维模式也在改变。人变得很浮躁,我自己体会就变得就比较浮躁。为什么呢?我以前写文章如同我刚才描述的治学方式,我都很难坚持了。为什么呢?互联网太方便了,我不用去买书,也不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我坐在家里,搜索、拷贝一些文章就可以组合成新的文章,这个时候自己好像面临一种思想上的危机,到底我这么做还有意义吗,这还算是做学问吗?我常常会问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上一代人教给我的,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他教给我的这些东西让我逐渐摆脱了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种逆向的思维,凡是老师教的,书本、教科书上讲的,或是领导说的,总之权威的资讯,允许不允许质疑?我的父亲跟我讲是可以质疑的,报纸说的也好,领导说的也好,你一定要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之所以在后来还能继续产生思想,还能够写东西,就是得益于这一点。就是对于海量的资讯,面对海量资讯的互联网时代,我还能够有自己筛选的标准,有自己对于资讯的分析和判断的标准,主要是来源于相对独立的、甚至是逆向的思考。
刚才讲的,是自己思维和治学模式的一种变化。如果你想能做得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话,这点经验也许是我敝帚自珍,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我们中国是瓷器之国,鉴定瓷器有“民窑”有“官窑”。民窑怎么就变成官窑了呢?是烧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窑变”,原来上的釉彩变了色。窑变在瓷器学里是很珍贵的,突然这个东西就有价值了。我现在也在反思,我们常常说要抵制网络谣言,但是也有些谣言其实说的是事实,只不过是暂时没有被官方证实的事实。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以往权力对于资讯的垄断在这一刻被打破了,而且这种打破是很令人恼怒的。过去在只有平面媒体的时候,报纸、宣传可以随便说,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亩产万斤都可以相信,因为你一遍一遍强化这个东西。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特别容易相信纸上印成文字的东西,中国人对于文字有一种崇拜,日本人好像也有这种毛病。你看以往中国人对有字的烂纸应该怎么处理?过去正规的做法,一定要把这些烂纸收集起来,只要是有字的。收集起来要拿到庙里焚化,有字的纸是要敬重、爱惜的东西,这中间就包含了一种迷信,就是对于印在纸上 的谎言有迷信。一旦这种垄断被打破以后,我觉得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没法维持了。
还有,解构一个偶像的话,速度也非常之快。我经历过文革,我们那个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毛主席从建党到延安整风,树立了他绝对的权威,这中间大概经历了21年才达到成功。毛主席的威信在文革中应该说是达到了绝对的权威,全国人民疯狂的拥护他。后来忽然有一天,大家觉得毛主席说的是不能全信的。
这个事从哪儿开始呢?从林彪事件开始,因为他树立了这么一个副统帅,也把副统帅继承人的地位写进了《党章》,后来在1971年“9.13事件”,一下子副统帅自我爆炸了,也把统帅的威信爆破掉了,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
再看重庆这座城市就不太一样了,从今年2月6号发生这件事到3月15号,这个城市的第一把手被解除职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变化就这么快,虽然他也用将近五年的时间经营这个城市,也经营他自己的形象,经营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但是这套东西的解体,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也发展非常迅速。
同样是副手出逃这样一件事,你想解构毛主席威信的话,这个过程就比较漫长,到现在也不能算是解构了。解构一个小毛泽东的威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的威力。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比如说苏联的解体。后来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的时候,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总结了一下,“三个垄断”导致他们政党的解体。他说,一是意识形态的垄断,一言堂;二是权力垄断,搞政治暴力;三是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位领导人,后来被铁托拿下了,这个人叫吉拉斯,他在50年代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新阶级》。他 在那个时候就提出来,斯大林式的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靠什么控制呢?一是权力,二是所有权,三是思想。这两个人的总结虽然中间相隔了几十年,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不过一个人早一些,一个人晚一些。
我觉得权力的垄断、思想的垄断和资源的垄断,这三个东西是配套的,如果其中一种垄断被打破的话,另外的两种垄断维持也不会太久。所以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有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是网络。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个判断是会实现的。
我们再来谈一谈信息时代的中国人,如何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每天产生的海量的信息?有很多是垃圾,我们如何筛选,如何判断,如何变成独立思考的人?
我想我们需要把宣传和新闻、资讯做一个区别。有些人因为掌握的资讯太少,这样就比较容易被洗脑,也有很多人他没被权力洗脑,也可能被民间的宗教团体或是迷信团体洗脑,这和传销是差不多的。
我们还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们如何能不被人家忽悠,不会被一些海量不靠谱的资讯忽悠?我在做这场演讲之前,曾经在网上征求意见,问说大家希望聊点什么?有一个网友说,是不是可以聊一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讨论一下。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现在清华大学还有块碑,是纪念王国维的,说到一句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永不磨灭的。
我们不要忘记,陈寅恪先生写这篇碑文的时候还是民国年代,到了1949年以后,陈先生的说法还是有变化的。虽然他强调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他也声明,他不跟体制作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宣统三年在西方就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他认为不应该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说我要请个人,带个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就不是我的学生。
我在想,陈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不愿意介入到政治里,所以他不想和体制作对。但是他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当时中国科学院请他到中古历史研究所当所长,他说要允许中古所不学习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他居然说想请毛泽东、刘少奇开一张证明作为挡箭牌。我们只知道有句话叫“法律不是挡箭牌“,现在翻开历史来看,可以做挡箭牌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毛主席、刘少奇开的证明,也是可以作为挡箭牌的。
陈先生这种思想,我认为对于多数不愿意介入政治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底线。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讲,我并不赞成年轻人都去参与政治。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去关心政治,而不关心我们的经济,不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健康的社会不会有太多的人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搞得不好,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
也有人在网上说,章先生可不可以讨论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本来是不想讨论的,我觉得在校园里面,学校是学校,政府是政府,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教育,学校也不要跟政府发生过多的关系,相互之间应该是有自己的范畴。现在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确实是很难处理的。
还是重复陈先生的底线,如果你是来学习的,你是要做学问也好,或者是要学到知识将来去拓展你的人生也好,不一定要走一条和现行体制完全格格不入的对抗道路。我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多数人来讲可能是不适合的。但是不等于你对社会的现实没有你自己的见解,而且我认为,你愿意表达的时候你还是有权表达的。
所以,该属于你的权利你应该坚持,但是你不一定拿它作为你的职业,我往往觉得,职业化的政治人物有的时候是不太可信的。这点我也承认,是受上一代人的影响,他认为政治运动应该是有职业人的运动。比如说你是服务于商界,或是服务于学界,你去关心某些政治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政客。
我个人也是这么一种态度,我自己是一个学人,会去关心很多的社会问题,而且对于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有批评,但是我并不需要、并不愿意一定要发生某种正面的碰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制非常强大,这种碰撞的结果对我来讲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不等于我不说话。
当然有很多人也不赞成我这种态度,甚至觉得我做得很不够。我发现,所谓的左派经常指责说我是右派,为什么我是右派呢?因为你爸就是右派,所以你一定是右派。还有一部分右派也指责我,说你不够右,为什么你不够右?因为你对他们有批评,但是你没有站出来公开的对抗,所以你不够右,我们比你要彻底。
我自己始终认为,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我的立场是独立思考的学者。这个立场并不需要采取某种很极端的方式,来去实现一些主张,而是用一种理性的态度进行表达。我也确实认为,现有的表达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最近我也在反省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反省,就是对于我自己所经历的这几十年的反省,主要是从文革的角度来反省的。文革这么一场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一直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温总理这次在人大结束的时候回答记者的提问,也特别提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还会不会发生?就这一点,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分析文革的基因有五个,一是政治体制的垄断,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垄断”,不容政治异己,不容分享利益,也不容异质思维。
二是民粹主义的基因,民粹主义这种东西是很有伤害性的,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价值观。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一个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是反智反精英的,但是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需要反对什么的时候,就采取一种发动民众的方式,来反对特定的对象。
胡绳曾经指出毛泽东建政以后就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在革命成功以前就已经在中共内部存在,所以老百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发动群众斗富人、斗知识分子、斗干部,最后没得斗了,就挑动群众斗群众。你看毛泽东讲8亿人口不斗行吗?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斗”。在重庆模式上,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
还有第三点,国民性有一种暴力的基因,这种暴力的基本特征就是蔑视人权。你看历史上以“均贫富“为号召的,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利用这种口号,这种以暴易暴的周期性的动乱,在中国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这个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是长期的生活于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中国人,人格常常是处于分裂状态。
一种是太平顺民,就是从圣、从众、从权,听圣人的,听大家的,是听权力的。还有集体无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到暴力事件大家冷血围观,这是一方面。人格分裂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乱世暴民,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只讲立场不讲是非,依附权势,一旦出现动乱的时候,迅速的由顺民变身为趁火打劫的暴民,这是文革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蒙昧主义和个人崇拜,蒙昧主义从哪儿来的?从教育来的。美国有一个例子,一个中学老师曾经做过一个法西斯实验,他用希特勒的办法,用纳粹的办法来训练他班上的学生。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成功了,他成功掌控了所有人的思想,而且在他的学生中间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种东西在美国,算是人格相对独立的民族中间也能够出现,也能够实现,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就更容易。有句话叫“魅力型领袖“,魅力型领袖大家都会崇拜,因为他有个人魅力。这种个人崇拜往往是产生于后发型的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你看魅力型领袖,像卡扎菲也好,萨达姆也好,这一类的人在他们的国家特别容易得逞,而且特别容易在当权的时候受到大众的拥护。
在中国也是这样,40年代有一种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再加上50年代开始的苏联式的教育生产线,这种生产线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而是为培养臣民设计的。基本特征就是排斥独立思考,把人作为一个大机器上的标准件来进行生产。这是50年代以来教育最大的弊端。这种弊端也是产生文革的基因。
第五是封闭社会下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平等。1949年之后是把社会变成二元结构,就是农业户口、城市户口,直接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所以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是受到抑制,一直是受到压抑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享有特权。这种情况下,原来建国承诺的“共同富裕”就成为泡影。这种民间积蓄愤怒的情绪被利用,被伟大领袖利用起来作为打倒他政治对手的工具,这是文革形成的第五个基因。
现在我觉得,要再出现文革不那么容易,为什么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了互联网,在网络上你想宣传一个东西,你想宣传某种主张,马上会有很多人来跟你争论。你想制造一种舆论,有很多人会冲出来表达不同的意见。互联网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平等,章立凡这人有一点号召力,他说的话有很多人信,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也有很多人专门来挑你的毛病,来找你的差错。其实反对我的那部分人,在互联网上和我是平等的,章立凡是一个ID,反对你的人也是ID,他 也有同等的发言权。
这种情况下,资讯的垄断和权威的树立,都不像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么容易了。刚才我们讲了某一个偶像的解构,还有现在网民们经常在说的,某一个青年作家的偶像解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对他是有批评的,但并没有认为他不应该存在,我认为他也是有权存在的。只不过他这个偶像也确实是通过互联网被解构了。当然,解构后面的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不太容易出现像“伟大领袖”那样的人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讯不再被垄断了,而且资讯的传播走向已经改变了,从自上而下的传播,变成了自下而上向四周立体的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很容易把资讯的垄断打破。
在前一段我也曾经跟袁伟时是先生有过讨论,也是就韩寒讲的这几个问题,自由、革命、民主这些问题。后来我提了三个命题:
1、改良是革命的解构,革命是改革的清盘。
2、自由是民主的终极追求,民主是自由的游戏规则。
3、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
我们这个讨论最后有点共识,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信息传播的模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启蒙的手段变得更加便捷。举例来讲,革命前的英国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包括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他们都没有见证过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我认为韩寒“素质论“的提法是站不住了,认为中国人素质不行,不配享受民主,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肯定高于刚才历史上这些国家的人民。
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享受民主,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时代变了,潮流变了,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教育官员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最后我想小结一下,这个小结是一个抄袭,因为我在来之前,正好在看凤凰台,吕宁思先生有一段小小的插播,我就专门到网上找了这段插播,把它录入并打印出来了,给大家念一下。
十种有益的思维方式:
1、逆向思维,帮你突破教条。
2、批判思维,帮你突破桎梏。
3、联想思维,帮你突破尝试。
4、换位思维,帮你突破主观。
5、系统思维,帮你突破片面。
6、开放思维,帮你突破僵化。
7、形象思维,帮你突破枯燥
8、逻辑思维,帮你突破表象。
9、前瞻思维,帮你突破短浅。
10、简单思维,帮你突破烦琐。
我觉得他讲的这十点,概括的来讲就是一个独立思考,只不过他把独立思考分解成十个不同的层面来说。至于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说了一个“碎片化”?我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自由讨论。
自从有了微博以后,自从变成了微博控以后,我觉得我很吃亏,为什么很吃亏呢?就是我的思想碎片化了,原来我有很多想法,是可以写成一篇篇文章,可以码成1500字到3000字的文章,还可以收点稿费。但是我批发改零售了,就在网上和网友交流的时候,在140字以内把我的思想给零售出去了。这个零售我还一分钱没赚到,只不过分享了一种愉快。
我分享到了跟大家交流的快乐,严格来讲,网上聊的可能出一本、两本、三本书的,最后就没出。我自己反省,是思维碎片化的结果。这个结果,我有后悔的地方,也有不后悔的地方。后悔的地方无非是自己的蝇头小利丢了,不后悔的地方,是我分享到快乐了,而且这个快乐是很多网民和我一起分享的,我觉得值。
今天也是这样,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半天,可能你们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我讲的过程也希望是快乐分享的过程。你们觉得快乐或不快乐的,都可以把砖头扔过来,我就说到这儿。
(注:本文摘自凤凰博报《名博校园行》14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