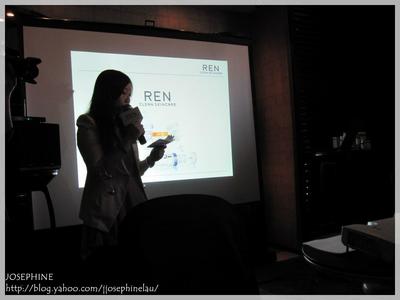康德的意志概念的两个方面:实践理性和自由抉择
2015年09月25日 16:37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53期作者:江璐打印纠错分享推荐
Two Sides of Kant's Concept of Will:Practical Reason and FreeWill
作者简介:江璐,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广东 广州510600
内容提要:意志之实在性的奠基、自由之因果性的根据,是理解康德意志概念的关键。分析康德文本中关于“意志”和“自由抉择”的解释和阐述,并以此来梳理意志概念的不同意义层次及其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勾勒出康德实践哲学中人的理性行动的结构。在人的行动中,目的性和因果性结构是其主要方面。康德目的性模式和传统的关于行动的目的论模式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康德的实践理性自身即为其行动的目的,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那样以一个外在对象为目的。
关键词:康德/自由抉择/意志自由/目的论/因果性
一、康德对“意志”(Wille)和“自由抉择(Willkür)的定义和区分
现代哲学的“意志”概念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以及后来经院哲学对意志、抉择、理性和自由意志这些概念的讨论之上。现代“自由意志”概念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1)承认有这么一个可以在完全具有意识的时候选择错误行动的能力;2)承认有意识地做出错误选择的能力是一种绝对的能力,不可再追溯到另一原因,这是判定做出错误行动的人完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基础。[1]在讨论意志自由时,要把它与行动自由加以区分。前者指没有外在的阻挡而能执行自己想做的行为,而意志自由指的却是没有内在逼迫,重点在于“自愿”。同样,自由抉择涉及的是后者,只有在思考到我们是如何做决定的时候,才会呈现出“意志自由”与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把意志看做一种绝对的抉择能力的时候,有哲学家认为具体的意愿是没有任何前提从无中生成的,但这不符合一般日常看法,也缺乏让人信服的解释。由此感性和理性就成为具体意志出发点的候选者。感性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具有必然因果性,如以感性为出发点,意愿会处在自然法规的规定之下成为必定的,也就毫无自由可言。理性作为自由意愿的发起者的看法或许更加合理:意愿起始于理性思考,即理性对理由的权衡以及对感性冲动的克制。有了理性对意愿的预先规定,我们也就对我们的意愿以及随之而发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既然有对不同理由的权衡和对冲动的抑制,我们的意愿也就有了多种可能性。然而具有多种选择并不是指两种同等程度的选择,而是指在更好和较差的可能性之间的选择。只有在不同可能性之间的选择才可能是由理性所引导的,因为在更好和较差的可能性中做选择需要理性的权衡和判断。这种由理性规定意志之自由抉择的模式并不与感性世界中所有发生均为自然规律之因果性所决定这一事实冲突,因为自然规律的因果链不能回答“出于何理由”的问题。负责给抉择提供理由的是实践理性。在决定行动的整体结构中,内在的部分是无法通过外在物质世界的因果法则所描绘的。①可见“自由意志”概念包含不同的、相互间具有特定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意义层面。康德的“意志”概念包含了传统的“自发性”“自愿”“自由选择”和“理性”这些意义。“自律”则是他新添加的。“Wille”一词康德在特定上下文中分别表达其多层含义中的某一特定意义层面,他也试图讨论这些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本文则要对此展开分析,并指出,刚才提到的理性到底是起到因果作用还是只是为行动提供根据的这个问题,在康德那里其实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自由意志具有真实的因果性,但同时也有提供根据的功能。另外要考虑自由抉择在因果关系层面上面临的哲学问题:如内在的意志决定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明“为何(出于何种理由)”的根据,然而却无法确定它在客观因果链中的地位,那么要问:意志抉择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有具体的决定作用?如果理性所引导的意志抉择其实并没有任何实在作用的话,那该如何理解意志自由呢?这样的自由是否只是一种假象呢?对此,可在以下两个领域分析康德的文本:1)内在的理性考虑,以此确定某一特殊行动中的特定意愿;2)所确定下来的意愿与其在外在世界中行动之实施间的关系。首先要分析的是狭义上“意志”与“自由抉择”的区分和关联。
1.康德对“意志”的定义和描述
(1)“意志无非就是实践理性。……意志是一种能力,仅仅选择理性不依赖于偏好而做人做实践上必然的亦即为善的东西。”[2](2)“意志被设想为依据某些法则的表象来规定自己去行动的能力。”[3](3)意志被解释为一个具有理性的生物对它针对自己的行动的因果性的意识,或被直接定义为“有生命的存在者就其理性而言的一种因果性”[4]。(4)意志被描绘为一种欲求能力,也就是世界中某些自然原因中的一种,或那种按照概念起作用的原因;并且所有被设想为通过意志而有可能的(或必然的)一切,也就被称做实践上是可能的(或必要的):为的是把它和一种不是由概念所规定的(而是像在无生命的物质中由力学所规定的、或是在动物界由本能所规定的那样)原因所引起的效果之物理性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加以区分。[5](5)意志还被解释为知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关系:在理论认知中知性与对象有一种关系,然而知性与欲求能力之间也具有一种关系,即意志。如在纯粹知性(理性)通过对律法的单纯表象而变得具有实践性的时候,那么这个意志也就是纯粹意志。[6]
2.康德对“自由抉择”的定义和描述
(1)如规定欲求能力行动的基础是在欲求能力本身中,而不是在(它所追求)的对象中,这样的一个欲求能力是按概念来行事的,此时,它也就叫做一种按照心愿可做或不做的能力。如果它是与其行动之能力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就叫做自由抉择(Willkür);如果它没有与其相连的话,那么这个行动本身则叫做愿望。欲求能力的内在规定的基础,也就是说心愿,如在主体的理性中,那它就叫做意志(Wille)。意志也就是欲求能力,但不是同时从它与行动的关系方面来看(比如抉择),而是从规定决断来决定行动的这方面来看,并且它在自己之前没有其他的规定基础了,而是因为它能够规定自由抉择,就是实践理性本身。
(2)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指的是抉择能力(Willkür)不受感性动力的强迫。因为决断在生理意义上受影响(即通过感性的动因而受影响)的时候,它是感性的;当它在生理意义上能被决定的时候,它是动物性。人的抉择能力虽然是一种感性的决断,然而却并不是动物性的,因为感性并不让人之抉择能力的行动变成必定,而是人有一种能够不受感性动力的强迫而从自身出发来规定(自身行动)的能力。
(3)就理性可以规定欲求能力而言,在意志下面可以包含有抉择,也可以包含单纯的愿望;能够由纯粹理性来规定的抉择,叫做自由的抉择。而那只能由倾向(感性动力,刺激)来规定的,是动物性的抉择。人的抉择是这样的:它虽然受到感性的影响,但没有被感性所确定,这样,从自身来看并不是纯粹的然而还是能由纯粹的意志来规定的。抉择自由也就是指其自身的规定不受到感性动力的制约;这是抉择自由的消极概念。其积极概念是:纯粹理性对自身而言为实践性的能力。这却只有在让每一个行动的准则都符合能够成为普遍律法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因为当纯粹理性在不考虑抉择的对象,而被应用在抉择上的时候,理性也就可以作为(制定)原则的能力(这里指的是实践原则,所以也就是制定律法的能力),由于纯粹理性没有律法的质料,而只是具有那种可以使得抉择之准则成为普遍律法,甚至成为抉择之规定的根基之最高律法的能力的形式。②
我们在这把“Wille”固定称做“意志”,而“Willkür”称做“自由抉择”。维拉舍克区分了康德对“意志”和“实践理性”的两种着重点不同的用法:“意志”一方面指的是人具有理性的欲求能力,也就与“受理性引导的抉择”同义;另一方面指的是人之欲求能力的一个特殊方面,即理性的主动规定,在这层意义上“意志”与作为欲求能力的“抉择”有区分,后者是被动受理性规定的机制;“实践理性”一方面指的是受理性引导的自由抉择,即一种可以理性行动的能力,在另一方面指的是引导和规定行动的理性本身。“意志”、“自由抉择”和“实践理性”在这里均指同一能力,它们之间的区分仅为功能性。[7]直到《道德形而上学》康德才对“Wille”和“Willkür”进行明确区分。他强调了前者是内在决定程序中的一个要素,后者则是在规定实际行动时候的一个要素。可以说“Willkür”是连接实践理性和外界物理世界的桥梁。在这里要注意两点:1)与理论理性不同,实践理性不是一种综合的应用,因为它的应用没有感性因素参与,这一点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做出了阐述。[8]2)实践理性虽是一种纯理性的应用,却与外在的世界具有因果关联,而理论理性是不建立任何因果关联的。
对理性的实践运用不可以是类似认知那样的综合,而必须处在纯粹理性概念的层面上。那自以为具有独裁地位的运用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中以幸福为最高目的的伦理学,他把人的感受(幸福)作为理性的最后目标和标尺,把自爱的原则作为自由抉择的最高规定根基。后者的最高规定根基,在康德看来,却应当是纯粹实践理性,即意志。把感性对象作为自由抉择之最高根据的做法是超越性的,因为它把感性质料用来规定和它在性质上相异的理性能力,后果是把意愿的质料与律法联系在一起(因为伦理学是提供实践准则的学问),质料却是欲望的对象,以此来规定自由抉择,就出现了他律:自由抉择在这种情况下受制于自然规律,而意志则不是自己给自己制定律法,所施加的仅仅是要求理性遵循生理规则的条例。意志必须是以自身作为自我规定的根据,不处在自然的规定下,前一情况是内在的、自律的,而后者是超越的、他律的。
与意志不同,自由抉择在康德那里是感性的。然而具有理性的人的抉择和动物的决定不同,不是通过感性条件而被必要地规定,而是自由的、可通过理性而出自意志的行动。Wille不受制于他者,是自我规定的源头,而Willkür受制于意志,也受制于感性。意志和“自由”、“自律”、“自发性”等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意志是制定最高准则的能力,而自由抉择则是按准则做出选择的能力。意志是自律性的,而抉择是他律性的,因为前者并不受到任何理性之外的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受感性条件的影响和规定。③
至于对意志作为一种关系的描述,这里的“意志”其实指的是“意志的规定”。对意志作为一种欲求能力的规定有两种:质料性的意志规定和形式性的意志规定。质料性的意志规定为意志的后天驱动力,而形式性的意志规定则是意志的先天原则。然而质料性的原则并不是指身体性的、感性的原则,而是指意志所欲求的对象这一原则,比如,他把意志的质料阐释为“意志的对象”[9]。形式性的原则是无内容的,仅体现了理性立法的形式,即“准则之普遍性的实践律法”。在这里也就是要把与知性世界相联系的理性设想为可能具有效应的,也就是说对意志起规定作用的。只有形式性的意志规定才是自由的。纯粹知性(即纯粹理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形式,这个形式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因为它在先天的道德律法中就如同一个事实一样被给予了。“意志”这个概念中已包含了“因果性”这个概念,而在“纯粹意志”这个概念中则已包含了“藉着自由的因果性”的概念,即一种与自然因果性相区分的因果性。由于因果性也就是理性实践性的体现,而理性的实践性是在单纯表象到一个律法时出现的,则这个律法即是引起这种因果性的根基,同时它通过对欲求能力的规定而引发了这种因果性。这样,道德律也就是意志的核心。在意志直接受到道德律规定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则为道德的。
二、实践理性在规定意志时的目的性模式
用来解释行动的哲学模式基本上有两个:目的论模式和因果论模式。康德关于意志的论述中同时包含了目的和因果两个概念。康德认为意志是按照某些律法而来规定自己付诸行动的能力。意志自我规定的客观基础就是目的,而主观的自我规定基础则为驱动力。目的是一种对象,按上面的阐述即为质料。然而上面已提到意志对欲求能力的规定是一种形式性的规定。如此,规定欲求能力的道德律在对行动的规定中具有三重不同的功能:1)为行动的形式性规定基础;2)为行动的质料规定基础,然而却不是作为主观的感受,比如快感等,来规定行动的,而是作为欲求的对象,即在善恶的概念之下来规定行动的;3)作为主观的驱动力。在2)中所说的也就是道德律在目的论模式中给予行动一个目的的功能。3)则是在因果模式中起了一个动力因的作用。这个道德情感是以理性生物的感性为前提的,因为它是实践理性对感性之作用的效果。然而由于它只是在因果模式中拥有动因的地位,行动善恶的判断并不是通过道德情感获得的。道德情感并不是那种与快感联系在一起的情感,道德情感的作用在于使得客观道德律法成为单个行动主体在行动中所依据的准则。2)与3)分别对应了行动的目的性和因果性模式。
霍恩指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认为我们实践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一个“本身为善的意志”,这个意志是至善。[10]至善的意志取代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幸福”成为了人行动的最终目标,然而此时传统的目的论式结构并未被取消。[11]但由于作为理性的意志是欲求能力的形式规定,那么至善的意志是如何可以成为欲求能力的对象呢?这里要考虑到的是康德对“以自身为目的的目的”的解释:具有理性者都以目的本身的形式存在,而定言命令,即道德律的基础也就是理性本性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着。理性本性与其它本性的区别在于它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不是一个行动的效应或结果,也从不是手段,它是一个自立存在的目的,其实也就是所有可能目的的主体本身,这样的主体同时是可能的绝对善的意志的主体,不可能受制于任何一个对象。按上面的第2)项和所提到的在康德那里意志的客观规定基础,实践理性通过道德律给予了作为欲求能力的意志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也必须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理性本体。而仅仅只是包含了以目的为其结果的行动之可能性的基础的,则为手段。每个理性的本体都以目的自身的形式存在着,而不是仅作为手段意志随意使用,这样的本体在其针对自身和其他理性本体的所有行动中,都必须同时被看做目的。理性本体被称做“位格”,因为其本性就已经把它标示为目的自身,而不仅仅是手段,这样也就限制了一切任意性。④这样的目的不是用来实现另一个目的那种对我们来说具有主观性价值的目的,而是客观目的。这些本体自身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而且不可以被另外一个作为另一目的之手段的目的所取代。理性本性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是最高实践原则的基础。这样,实践理性也就把自身作为目的。
在康德看来善良意志不是因为它所引发的结果为善,也不因为它的目的或它能够达到所设定的目标为善,而仅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意志是绝对善的,不是恶的,也就是说,意志的准则在变成普遍律法时,从不可能自相矛盾。意志的最高原则是:有些准则的普遍性是你也可以当做是律法的普遍性而所愿意的,你每时每刻都该按照这样的准则来行动。唯独在这个条件下,意志才永不会自我矛盾,这样的一个命令式是定言式的。因为作为针对可能行动的普遍律法,意志的有效性是和按普遍规律所联系在一起的物体存有达成类比的,而这种普遍规律是自然之形式的一面。这样的定言命令式可以这样来表达:你要按照那样的准则来行动,也就是那些同时能把自己当做是普遍自然法则之对象的那些准则。这也就是绝对善的意志的公式。这种表达体现了一种目的论的结构:至善的意志作为最高目的是以具有普遍性的规则而行动的意志;意志的目的就是它自身。
康德把实践理性的概念定义为:对作为自由之可能的效果的对象的表象。实践认知的对象和实践认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意志有可能实现的行动和意志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实践理性的对象,即某个可能的行动,当做是规定我们欲求能力的根据的话,我们也就必须考虑到实现此行动的客观条件,以此来判断这个目的是否是实践理性的对象。然而如果把仅仅是形式的律法拿来作为规定行动的根据的时候,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不是行动本身的客观可行性,而是行动的道德意义,即,在有可能实现某一件事的情况下,要先考虑该不该去做它。在这里所规定的不是行为实现的可能性,而是行为的道德可能性。在此情况下,作为意志之规定根据不是行动的对象,而是意志的道德律。在此康德批评了传统的目的论式伦理学:实践理性的对象其实只有两种:善或恶的。善的对象是欲求能力所要追求的,而恶的对象是欲求能力所要逃避的。然而如果把对象,而不是形式作为意志决定的规定的话,那么,由于与善的对象所联系在一起的是快感,而我们无法先天知道什么东西会带来快感,只能后天获得这样的经验,这样也就在规定意志的时候受制于外在条件。所以,善必须是直接从实践律法推导出来,才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善恶概念表达的是与理性律法所规定的意志之间的关系,意志从不受其对象的规定,它自己决定它所要追求的目标。意志是理性的规则变成一个行动之动力因的能力。
善恶指的也就只是行动本身,而不涉及个人感受。如一个行动是绝对善或恶的,那它就只涉及行动的类型、意志的准则和行动的个人,而不涉及物。我们称之为善的,也就必须在每一个理性的人的判断中成为欲求能力的对象,而恶则正好相反。实践律法作为理性原则是直接规定意志的,符合律法的行为则是本身为善的,制定符合实践律法的意志是绝对善的。康德明确地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善”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不该像古人那样先定义善,然后把它拿来做意志的规定基础,而应该是意志先规定自己,然后才将“善”作为对象提供给在形式上已经先天规定了的意志。“善”“恶”这两个概念是先天意志规定的结果,它们也就以纯粹的实践原则和纯粹理性的因果性为前提,并且与纯粹知性概念不同,不是后来被应用到对象上,而是以有一个对象为前提。这里康德并不是说有一个外在的善或恶的概念来衡量我们的行动或选择,而是说我们的选择自身就带有善或恶的概念,有了选择才会有善恶,而符合道德律的选择,就是善的。选择是不是要让我们的行动符合道德律,这是我们在行动中所要做的第一步。善恶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同一范畴,也就是因果性这个范畴的样式。实践理性的规定也可以按纯粹理性的范畴表将杂多总领在同一先天意识下,但它总领的不是现象世界的杂多,而是欲求的杂多。作为“善”概念前提的,即自由之范畴的对象,其实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被给予了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道德律。然而这样的运用必须与范畴的理论运用加以区分:与理论运用中的范畴不同,实践运用中的范畴自己会创造出自己的对象,而它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也就是意志的存心⑤,给予了实践认知以实在性。由于意志可以引发出一种内在的直观,也就是存心,那么它也就是主动地自己给予了自己一个对象和内容,而不是像在理性的理论性运用中消极地等待,在外在世界中它被给予直观。先天的实践概念被应用在实践理性自己所引发出来的对象上,也就带来了实践认知。
我们先天就有一个最高的道德律,这是规定我们意愿的原则。这是个形式。而意志的对象则是由“善”和“恶”的概念所规定的。然而道德的善是一种超感性的对象,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的道德行动如何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实现?自由的律法(即道德律),或是说无条件的善的概念,没有具体应用中所相应的直观或图示,有的仅仅是知性,然而由于是纯知性的,所以可以在纯形式上用知性的理念,即知性的律法,来规定感性世界中的行动,这种理念康德称之为“范型”。
康德所描述的行动体现的仍是一种目的性结构。由于至善在康德那里是和受理性规定的意志同一的,那么也就并不存在外在的目标。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具体行动时就不需要目标了,人行动的结构仍然是目的性的,但我们必须先通过道德律(定言命令),由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给作为意志的欲求能力规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经验性的,而是先天规定的。那么在康德定义下作为能够选择理性在不受制于偏好的情况下而认识到为善的目的的意志,所选择的目的也就符合理性律法。这样,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最先要决定的是我们是否要按道德律来行动。这确定了我们行动的最高目的,在意志做出这样的决定而通过自己所包含的道德律来规定欲求能力的对象时,这个欲求的对象,即善的行为,也就可以用来规定我们实际行动所要依照的准则。这样看来,康德把亚氏的行动目的论模式颠倒过来了:亚氏所前设的至善在康德看来是在道德律之后的,而且受道德律所规定。在实践理性对作为欲求能力的意志做了规定之后,意志即会把道德律作为其欲求对象,这是在所有具体行动之先的实践步骤,然后就出现了指导我们在具体行动时候所要参考的定言命令的各种公式(道德律和定言命令还有一定的区分,道德律在康德那里是“纯粹实践理性自律的律法,即自由”,它是所有准则的形式条件。自由抉择在这里,也就面对具体实践情况,使得它的准则符合道德律)这就是康德实践哲学中关于行动的目的性模式之基本结构。
三、意志在行动之中的因果作用
自由抉择是与行动相连的,由此人的行动也就不可避免地也是内在的,同时有因果性结构。行动的因果性与自然因果性不同,是一种出于自由的因果性。《纯粹理性批判》的同一处康德还提到了自由的另外一个特性:自发性。自由的先验理念和实践理智中的自由均具有自发性,也就是说,是一个因果链的绝对起因,这个起因自身不受另外一个异者的推动。因为自然中是没有这么一个绝对起因的,而理性却要求有一个因果链的绝对整体,出于这个需要,理性也就给自己创立了这么一个理念。康德认知论中的先验理念并不具有认知功能,而只能规范性应用。而实践理智中的自由则是实在的。这一点康德试图通过他著名的对物自体和现象之间的区分来阐明。自然规律所描述的是现象间的联系,这样自然中的因果关系是处在时间之中并有时间上的先后,所有现象都必须遵从自然定律,那么所有的现象的因果链都是必定的,而没有偶性的发生,自由也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有了上述的区分,不同于自然法则的另一种因果性才有可能。就康德说来,
如果诸现象只被看做它们实际所是的东西,即不是被看做自在之物,而是只看做依据经验性法则而关联着的诸表象,那么这些现象本身就必须还拥有本身并非现象的根据。但一个这样的理知的原因就其原因性来说是不被现象所规定的,虽然它的结果能显现出来并因而能被别的现象所规定。所以这个理知的原因就其原因性来说是不被现象所规定的,虽然它的结果能显现出来并因而能被别的现象所规定。所以这个理知的原因连同其原因性存在于序列之外;反之它的结果却是在经验性诸条件的序列之中被发现的。所以这个结果就其理知的原因而言可以被看做自由的,但同时就诸现象而言可以被看做按照自然必然而来自现象的后果;这样一种区分,如果以普遍的和完全抽象的方式阐述出来,必然会显得极其玄妙和晦涩,但它在应用时就将得到澄清。[12]
现象可以有两个不同种类的起因:它在现象的序列中是由另外的现象通过自然法规而必然引发的结果,然而这样的现象也有一个理知的起因。这样康德在理知世界和现象世界间建立了一个连接,它通过被称为“实践自由”的因果性得到了表达。此因果性并非一种神秘的、跨越两个性质上全然不同的世界的连接。由于康德哲学中的现象是通过先验主体而得到构建的,现象本身也就具有主观性,所以认为有一个本身不是现象的物体是现象的起因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尴尬借口,而是康德哲学内在逻辑的必然推理。这个因果性的特点在于其原因是理知的、非感性的,而其效果则是感性的现象。通过这种因果性引发效果的过程是行动,行动主体不是时空内的个人,而是一个先验的对象。也就是说正在打字的我,具有血肉之躯的我,是现象世界的对象,我的任何举动都受制于自然法则的制约,比如生物学上的规律,然而作为一个先验的我,我对自己的行动拥有自主权,并且是一个自发的、不受其他条件制约的第一起因。这样的一个自我却没有办法直接被认知到,而是被设想为一个理知的根基,这样的一种设想不改变经验中的任何规则和联系,因为它只涉及纯粹知性中的思考。
人是会通过统觉,或在非感性印象的行动和内在的规定中认识到自身的。人具有某些特别的能力,即知性和理性,在涉及这些能力的方面,人是一个理知对象。理性具有因果性的这一特性在命令式上得到了体现。应然所表达的必定与自然规律的必然是有区分的。知性所认知的是事实,而非所谓的“本应如此”。实践意义上的“应然”表达出来的是个可能的行动,而后者的根基只是个概念,自然中行动的根源却必须是现象。现象世界中的自然条件虽然可以是人想要某一东西的动机,然而却不能对我们的自由抉择起到规定的作用,也没有办法引发出应然,这些自然条件只能引发一种任何时刻都是受制的意愿,而对于这样的一个意愿理性则颁布了标尺和目的。目的有可能是感性的对象,比如舒服的东西,或是理性的对象,也就是至善。理性在这里并没有受到经验条件的制约,也不顺应感性事物的规律,而是以完全的自发性自己创建出一个单独的理念秩序。在理性看来,经验条件必须顺应这个理念秩序,并且理性按这个秩序也宣称某些行动为(道德)必要的,尽管这样的行动还未发生或者有可能并不发生。这样,理性也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经验性的一面,其前提是,理性能够对出于现象世界中的行动具有因果性的作用,否则,作为起因的理性与现象的行动之间就没有任何质性的共同之处,那么它们之间会有因果联系的说法也就不可信了。人的自由抉择是具有经验特性的,也就是说,它是人所有行动的经验原因。而理性却是所有自由行动的先验性制约。这些行动是人的现象。作为自由抉择的制约条件,理性也就成为了人行动的非现象性起因,这个起因是不再受外条件制约的。那么理性也就是因果链条中第一个、绝对的部分。这样传统意志概念的另外一个要素,即自发性,在康德这里也得到了描述。
理性与现象性的行动是如何以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未做出更清楚的阐释,这构成了康德诠释的一个难点。在那里康德试图用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只有在我们认为他有道德上责任的时候才可以责备他,如果他的行为都是由感性条件所确定了的,那么通过理性就会树立一种应然,做了错事的人没有满足此应然,是要受到责备的。理性可以通过自身来规定应然而无需考虑任何感性条件。理性也不是与感性条件一起来确定目标或应然的,而是独立于任何一个感性条件自主规定应然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自律。而人的自由在于不管他的经历和处境如何,他仍可以决定不做错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到,他在这里阐释的自由(作为因果性的自由)是一个先验的理念,并且这里也并没有证明这个自由的可能性。在此能够证明的仅仅是自然并不与自由的因果性达成矛盾。
这一点在康德后来的伦理学著作中却有所改变,特别是自由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同自然中的因果关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一样,人自由抉择的因果性是遵循道德律法的,因为因果性的概念就已经包含了规律的概念。自由的意志也就是一个处在道德律法下的意志。而相对《纯粹理性批判》中把自由仅仅当做先验理念,其实在性甚至可能性都无法证明的做法,康德则提出了如果没有证明自由理念中道德律法的实在性,那我们也无法证明它的有效性和遵循它的必要性。然而在此康德仍未提供任何证明,不过他在《实践理性批判》写道:
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而一切其他的、作为一些单纯理念在思辨理性中始终没有支撑的概念(上帝和不朽的概念),现在就与这个概念相联结,同它一起并通过它而得到了持存即客观实在性,就是说,它们的可能性由于自由是现实的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个理念通过道德律而启示出来了。[13]
这个实在性是如何得来的呢?康德解释道,是实践理性为自己赋予了因果性这一范畴的对象,即自由的对象的一种实在性,也就是通过一个事实来确定只能被设想的对象的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针对理论认知否认了自由之实在性,然而,在关于实践认知的理论中,他却认为自由是有客观实在性的。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作为自由的主体时是思想体(Noumenon)⑥,而在考虑到他在自然中么责备他也就毫无意义了。而如果具有了理性,那的目的和作用的时候,则是他经验自我意识中的现象。这也对应了康德对自然抉择做出的经验和理性的双重性的说明。但其实这里也就蕴含了自由理念如何能够具有实在性的道理:前一节的分析指出意志是纯粹理性、不具有感性一面的,而自由抉择则具有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并能被意志所规定。那么意志在自由抉择上的作用就是具有实在性的,因为自由抉择在规定自己的行动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在自然中(也就是现象世界)中所要实现的目的的,在这方面,自由抉择的行为作为现象界中的发生就是内感官的外在表现,那么意志作为纯粹理性则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说,有着因果作用。所以康德写道,理性至少在其实践性的使用中可以取得对意志的规定,并且在涉及(内在的)意愿行动时,总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14]另外康德更重要的一段话是:然而欲求的主观基础是动力,而意愿的客观基础则是动因。[15]这里,动机是用来解释行动的根据,而动力则是因果关系中的原因。那么,在康德这一描述中有着目的模式的维度,即在一个行动中,会有一个意愿的内心活动,而这个意愿的客观基础是用来解释这个行动的,这也就是这个行动的目的,而目的并不是引发人实施这个特定行动的因果性动因,而是人主观的欲求。但康德在后来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又说,作为客观规定基础的道德律法同时也是主观的驱动力。[16]道德律作为理性的概念是如何在我们的内心中起到作用的呢?康德提到了一个消极的和一个积极的方面:在消极方面,道德律法限制了我们的偏好和的倾向,这也就以先天的方式引发出一种类似痛苦的情感。纯粹实践理性克服了自大,并使得我们的自爱成为一种理性的自爱,也就是说去除了我们偏好中与道德律法不相符的成分。道德律积极的方面在于理性的因果性即自由的因果性,因为在抑制自大的同时,道德律法成为了敬重的对象,这也就是一种积极的情感的基础,这种情感不是感性引发的,而是可以先天认知到的。这样,康德也就解释了自由之因果性的问题,因为道德律法作为纯理念也可以引起主观的情感。纵观上下文,情感应该就是上面提到的“存心”。情感或存心都处在现象世界中却非由外界或内在的现象而引起,而是以先验的方式由道德律,或更确切地说,由“对道德律的意识”或先前已经提到了的“某些律法的表象”所引起,也就不受制于现象,亦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康德称此情感为“道德情感”。这却不是道德情感主义所说的那种情感:道德律的首席权否定了我们的自爱,后者是感性的,由于自爱受到抑制,而从负面产生了上述的痛苦。这个痛苦是对理性的道德律的敬重,结合感性和理性这两方面,我们可以说有一种道德情感。
我们没有单纯理性的先天理论认知,却有先天的实践认知,后者是明证确定的,是道德律,并如同纯粹理性的一个事实。这样一来,道德律法的客观实在性就不是通过演绎,而是通过经验后天得到了证实。道德律是表达自由之因果性的律法,是关于超感性的本性之可能性的律法。它对思辨的理论理性无法规定的因果性作了规定,并给予它客观实在性。在第一批判中已经阐明了先验自由这个理念是没有矛盾的。纯粹理性在理论认识时是无法认知到作为人行动理性起因的意志的,因为理论知识要求要有一个直观,而对那些理知对象,我们是没有直观的。只有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我们才会体验到意志的实际存在。我们无法体验到作为理知对象的意志,却在经验意识中能体验到它作为原因所引发的作为内在现象的效果。既然没有对意志的直接直观,也就无法获得对此的理论知识,然而通过其作为现象的效果我们可以知道意志的存在。如同康德表明的那样,对自由这个概念的实际应用具体表现在存心和准则上。由于能阐明“因果”这个范畴在实践运用中的客观实在,康德以此类推,认为其他的范畴也同样可以在实践运用中获得客观实在。
综上所述,理性的行动基本上具有这么一个结构和受规定的次序:首先,一切理性行动的最高原则是道德律。实践理性判断中道德律直接规定了意志;而意志针对行动的自由在于能够有一种不同于自然因果律的因果性,也就是可以对作为现象实践中的人(感性的人)加以抑制,使得人能够在他感性的偏好和理性道德律之间选择以道德律作为行动的首要原则,出于这种限制,人的感性也就会有不悦之感,或按康德的话来说,是一种“挫损”⑦。但正是因为有了遏制才会有道德律相对于感性的提升,即实践上的优先性,从这方面来看,就有对道德律敬畏的情感,它由于是直接触及道德律的,所以也就是推动实践理性用道德律来规定理性的驱动力。这样便可清楚地解释康德对意志和自由抉择的区分在这样的行动框架中有着何等功能了。意志所涉及的是上述的前一部分,也就是在一个理性的行动中,首先是意志把道德律拿来作为行动的最高原则,这个做法随后规定了自由抉择,后者各有感性和理性的一面,在意志的因果作用下,自由抉择可选择遵循理性律法,随之制定符合道德律的准则,这与普遍性的道德律不同,不是完全形式的,而是具有具体内容、可指导针对某一特定情况的行动的。这样看来,康德所说的自由的因果性,指的并不是先验主体的实践理性与外部现象世界之间的因果联系,而是人在做具体行动决策的时候内在的因果联系。这个因果性模式可以解释人行动中动机的问题,却并不自诩能够解释人在外在物理世界中作为第一原因的因果性。外在物理世界中的现象是完全服从自然因果规律的。这也就不需要用意志的自由来加以解释,然而在完成某个特定的行动之后,理性的人可以通过他内在的决定和动机,来给他的行为提供根据,这是解释的根据,却非自然因果链中的某个起因。
①关于上面的叙述参见ErnstTugendhat,Anthropologie stattMetaphysik,Müchen,C.H.Beck,2007,pp.57-84.
②(1)-(3)都没有按常规引用邓晓芒或李秋零的译文,而是我自己的翻译。因为邓晓芒在这里把“Willkür”错误地翻译成了“任意”(相应出处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4页),而张荣和李秋零则把同一个词译成了“任性”(相应出处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2页)而这里指的其实是“自由抉择”。张荣和胡万年已经非常详细讨论过这个词的翻译,并指出译为“抉择”的正确性,参见张荣:《“决断”还是“任意”[抑或其它]?——从中世纪的liberumarbitrium看康德Willkür概念的汉译》,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以及胡万年:《康德文本中Willkür概念的诠释及启示》,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③参见Nicholas Bunnin &Jiyuan,Yu编,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Philosophy中的词条“will(Kant)”。见:Blackwell Reference Online.02 December2013。
④与《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本(参见本文参考文献[6])第74页提到的情况不同,这个词在此是以通常语义来使用的,而非康德实践哲学中的特定用法。
⑤原文“Gesinnung”。“存心”是台湾译法,邓晓芒在其翻译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译做“意向”。
⑥大多数时候被译做“本体”,然而这种译法不准确,因为这个词是希腊文“noúmenon”,即“所想的东西”的意思,而中文哲学界中已经有了“本体”这个词,是“subtance”的翻译,比如吴寿彭在其翻译的《形而上学》译文中就用“本体”一词来翻译希腊文的“ousia”[英文:substance]这个概念。而且哲学上有“本体论”这个学科。所以用“本体”来翻译“noumenon”不仅意思有误,而且容易造成误解。
⑦这个词邓晓芒在其翻译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成“谦卑”。康德要说的并不是感性自主地谦卑礼让理性,而是指理性的强势遏制了感性,所以感性对此会有反抗,这个词在日常用语里也有类似用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