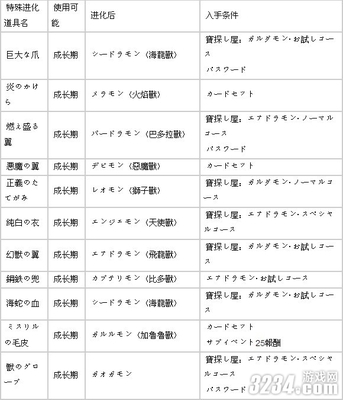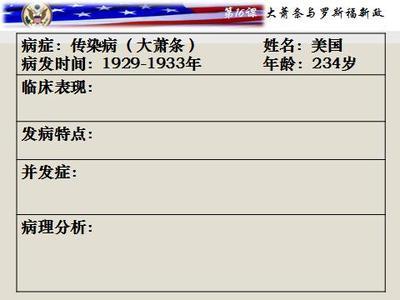穿越时空的物品向你述说:《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潘城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英]尼尔·美格雷戈 著 余燕 译
新星出版社
2014年1月
这部世界简史是大英博物馆从800万件馆藏中精选出100件,展现200万年的人类史。大英博物馆馆长亲自撰写,大英博物馆、BBC联手打造,历时4年,动员100多名馆员,400余位专家参与,BBC播出,创下1100万人口同时收听的记录。《纽约时报》评论为:全世界只有大英博物馆才能办到的世界史撰写计划,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巨献。
来自过去的讯息
在本书中,我们将穿越时空,去见证过去两百万年中,人类是如何塑造世界,同时又不断被世界塑造的。本书试图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解读文物跨越时空所传递的信息——来讲述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些信息有关民族与地区,环境与接触,历史中的不同时刻以及我们对其做出反思的当下。它们有的确凿可靠,有的仅出自推测,还有更多有待探寻。与我们可能会见到的其他证据不同,它们所表现的是整个社会群体及其复杂的演变过程,而非一些独立事件,它们所讲述的是制造它们的时代的故事,也是它们经历重塑与迁徙的时代的故事,有时,它们还能获得超越制造者原本意图的含义。人类制造的这些物品,缜密地构成了历史的原材料,在成百上千年的历程中,它们的经历还常常很有趣,而这些正是《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想要呈现给读者的。本书囊括了各种类型的物品,它们都曾被精心设计完成,有的得到无数赞誉,被小心珍藏,也有的在损坏后便遭丢弃。从煮物罐到黄金帆船,从石器时代的工具到信用卡,一切都来自大英博物馆的收藏。
这些文物所展现的历史也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本书很少涉及众所周知的事件、战役或日期,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军队摧毁巴格达,欧洲文艺复兴,拿破仑战争,美军轰炸广岛,等等。这些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并非本书的重点,但它们会通过一件件的物品被表现或反映出来。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政治事件决定了人们对萨顿胡遗址的发掘与解读。罗塞塔石碑(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是英国与拿破仑治下的法国进行艰苦斗争的记录。美国独立战争在书中通过一张美洲土著所绘制的鹿皮地图这一独特视角展开。整体来说,选择的这些文物往往讲述了多个故事,而非单一事件。
必不可少的诗意
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达到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已发展出一系列帮助我们阐释的重要手段。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也是大英博物馆的创立者们所熟悉的方式,在他们眼中,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人在做同样的工作。中国的乾隆皇帝是与英王乔治三世几乎同时期的统治者,他在十八世纪中期同样致力于网络收藏、分类整理、探索历史、编纂词典与百科全书,并记录自己的发现,从表面上看,他无异于一位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学者。他的藏品中有一枚被称作“壁”的玉环,非常类似发现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的中国商朝殉葬品中的玉璧。它们的用途至今仍无人知晓,但可确定的是,它们是贵族用品,做工精美。乾隆帝十分欣赏玉璧独特的美感,进而开始揣测它曾经的用途。他所采取的方式既表现出研究式的严谨,又充满想象力:他知道它年代久远,于是对比了一切他所知的类似物品,但仍陷入了迷茫。因此,他依照自己一贯的作风,作诗来纪念为研究此物做出的努力,并作出了或许会让现代人十分震惊的举动:将诗文刻在了诗中所赞美的文物上。在诗中他得出结论:这块美丽的玉璧是个碗托,因此又为它配了一个碗。
尽管乾隆帝对玉璧用途的推测是错误的,但我承认,我很欣赏他所采取的方法。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地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造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地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物品的传记
这本书更贴切的名字也许是“通过经历了不同世界的物品来讲述历史”,因为这些物品的一大特点便是,自面世以来,它们就不断地变化或被改变,最终承载了制作之初完全无法想象的意义。
在我们选择的物品中,有数量惊人的一部分都携有后期事件留下的印记。有时是在漫长的时光中遭受的破坏,如瓦斯特克女神破损的头饰,也可能是不小心的挖掘和强制移动带来的损伤,但更常见的是后期有意识的干预,或是为了改变它的含义,或是为了表现新主人的自豪与愉快。这样的物品不仅记录了制造它的那个世界,也记录了之后改变它的那些世界。譬如日本陶罐,它表现了日本早期在陶艺上取得的成就,也表明炖煮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它内壁的镀金则反映出后期美学主义的日本已经认识到本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重温并赞颂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物品本身成为对自己的注解。此外,非洲豁鼓尤其能表现物品所经历的命运波折。它最初为小牛造型,很可能是为一个居住在刚果北部的统治者而造。随后,它在喀土穆被改造成一件伊斯兰物品。之后又撑了基钦纳伯爵的战利品,被刻上维多利亚女王皇冠的图案被送至温莎——这是对帝国征服故事的一件木制记录。我不认为有任何文字能将这一段段非洲及欧洲的历史融合起来,或是表现得如此直接有力。这是只有物品才能讲述的历史。
本书还有两件物品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面对社会奔溃、组织坍塌时的不同面貌。从正面看,复活节岛的巨石像何瓦·何卡纳奈阿以坚定的自信呈现了祖先的威力:只要后人善加供奉,他们便能保佑复活节岛的平安。但在他背后却雕刻着这一信仰的失败:随着复活节岛的生态系统被破坏,对岛民生活至关重要的鸟类进行迁徙,焦急的人们用新的信仰代替了祖先崇拜。该社群绵延数世纪的宗教史在这尊巨石像上得到了清晰体现。俄国革命瓷盘则与之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了人类选择和政治博弈的结果。用帝国时期的瓷盘来承载布尔什维克的图画本身带有一种欺骗性的讽刺意味,但很快,冷静的商业智慧便战胜了它。制作者准确地揣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收藏家愿意花大价钱收藏一个同时带有革命者的镰刀斧头和沙皇时期帝国徽章的瓷盘。瓷盘表现了苏联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绵延七十年的复杂的历史妥协的第一步。
穿越时空的物品
纵观一定历史时期之内的整个地球,并非人们通常讲述或教授历史的方式。我猜很少有人在上学期间会被问到一〇六六年日本或东非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但如果我们选取某一特定的时间点来观察整个世界,结果通常出人意表并发人深省。比如在公元三百年前后,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以一种令人疑惑的同步性,共同采用了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具象手法,开始以人类的形象来表现神祗。这是一种惊人的巧合。为什么?难道它们三者都受到了希腊雕刻悠久传统的影响?还是因为它们都源自富庶并正在扩张的帝国,因此有大量财力可被投入这种新的图像语言?是否产生了一种地区间共享的新观念,认为人类与神密不可分?我们无法得出定论,但只有这样观察整个世界,才能如此尖锐地提出应被置于讨论核心的历史问题。
所有的博物馆都希望——或相信——对文物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世界有更加真实的了解。这也正是大英博物馆的监管宗旨。来福士勋爵大力宣扬这个观点,他把藏品送进大英博物馆,部分目的即在于说服欧洲人,爪哇拥有可与地中海灿烂文明相媲美的文化。来自婆罗浮屠的佛头和皮影比玛在这方面便极具说服力。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在凝视它们时对来福士的观点感到全心赞同的人。这两件物品将我们带回爪哇历史的不同时期,表现出文化的持久性与活力,并展现了人类活动的两大不同领域——对启蒙的孤独追求以及大众娱乐的狂欢。通过它们,我们得以窥探、欣赏并赞美这一伟大文明。
也许,最能表现本书乃至大英博物馆本身抱负的物品,想象并理解我们无法亲身体验、只能通过他人的描述和经历来了解的世界的绝佳范例,便是丢勒的《犀牛》画像,他所描述的是自己从未见过的野兽。一五一五年,他听说一头从印度古吉拉特邦而来的犀牛被送给了葡萄牙国王,便从当时传遍欧洲的关于犀牛的文字描述中尝试勾勒这头惊人巨兽的模样。这与我们审视自己所收集的材料、构建起关于远古世界的想象的过程是一样的。
丢勒所描绘的犀牛,有着令人难忘的庞大体量与布满鳞片的褶皱皮肤。这是伟大艺术家的杰作,看上去如此真实而具有冲击力,不禁让人担心它会从画里逃脱。当然,它对犀牛的表现有误。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痛苦还是宽慰的错误呢?我不知道哪个词更准确。但到最后,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丢勒的《犀牛》见证了我们对尚未了解的世界无止境的好奇心,也体现了人类探索与了解未知世界的渴求。
书评:吾与尔偕藏
人与器物的关系,我以为没有谁比王小波剖析得更为深切了——“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和技能,在方法和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
读厚厚的三部头《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却有轻松愉悦之感,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人类的历史不是以时间或观念来划分,而是通过器物连接。一百件器物从大英博物馆浩如烟海的收藏中被挑选出来,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通过书页、图片与文字的细细展示,一方面它们成了始终“保持缄默”的伟大历史面前的“呈堂证供”,另一方面它们仿佛也成了我们读者手掌中亲切可触的把玩之物。
这一百件物品带我走过了一部时间简史,同时也让我对身边所有的物品产生敬畏之心,人所创造的如此珍贵。在我的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中,贯穿着一把曼生壶,这把壶跟随着杭氏家族六代人的命运起伏沉降,百年沧桑之后,几离几归,终于回到杭家人手中。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宠辱皆为过眼烟云。就这样,那忠诚的器物,成了人们生命的寄托,最亲密的接触。由此追想,一百件历史的证物背后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又如果这部“世界简史”选取完全不同的一百件物品,可能会道出全然不同的人类故事,历史也可能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且有无限种可能。
由于我们个体所处空间的局限性,世界历史对我们来说通常是被切割的块面。你对本国历史如数家珍时未必就了解印第安人的生活,或者非洲大草原上的情况。书中展示的物品其实是世界历史的一些“别针”与“纽扣”,通过它们,我们所见的不再是不同文明的截面抑或它们被一一分离状态下的历史。文明间存在着可观的接触,它们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此外这些物品的力量,“让我们即刻与生活在遥远时空中的人相连接,让所有人都能在共同的故事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读者,我们与这些器物之间有了一座通达的桥梁,它正是以人类的万丈雄心搭建而成的。因此,“人类一家”并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口号。不管这个家庭通常表现得多么功能不良,整个人类总是拥有共同的需求与关注,恐惧与希望。自祖先走出非洲,去往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不管是石头、纸、黄金、羽毛还是硅,人类必定还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塑造或反映自身世界的物品,它们将帮助后人定义今日的我们。
这部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与我在撰稿央视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中所认识到的非常接近,“世界历史并非一部文明史,它应当是有同有异、始终互动的世界多种文明的演变史”。
最后,关于人类与器物,我还是想起了那把曼生壶上的壶铭,曰:“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藏。”

2014年3月15日
此文发表于《浙江日报》阅读会专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