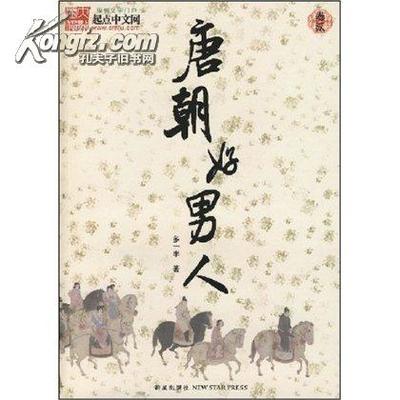纪念程乃珊:小说《金融家》评点
程乃珊是我印象中较为深刻的一位上海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像上海女性映衬下的上海男人总在人们习惯的语境中前面挂着一个“小”一样,上海作家也呈现出某种“阴盛阳盛”态势,即使是男性作家也带着一股弱弱的纤细的气息,如陈村。程乃珊一度时期与王安忆相伯仲,她们带有上海女作家的共性特征,都是从少儿文学起步,而后在成人文学方面占据了上海文学的领军角色。只是后来程乃珊移居到香港一段时间,从而拉开了与王安忆的差距,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程乃珊对上海的本土文化要比王安忆更为熟稔一些,因为王安忆是南下干部的子女,其实生活在一个普通话圈子里,并没有程乃珊接受过地道的上海方言的熏陶,这使得王安忆的文学中上海的纯正风味要稍逊一筹。
近日,因为程乃珊的去世,使我再次对程乃珊关注起来,这不能不提到程乃珊那部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金融家》。
一、《金融家》中的中行行史素材
本来这部小说要写成三部曲的,第一部发表在1990年左右,但是奇怪的是,程乃珊本来有较为宽裕的时间,完成这可以填补中国金融文学空白的长篇系列小说,但由于受到一种出于她的小说定位的原因,她终于没有打造成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完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曾经在文章中写道:“拙作小说《金融家》即取材于祖父及中行此时段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直接标注出“中国银行”,而是虚构了一个中华银行,在小说里,中华银行也不是一个官股占有大多数的官办银行,而是一个风雨飘摇中苦苦挣扎的民办银行。小说里的金融家祝景臣是华行的总经理,按照程乃珊的说法,基本对应于她的外祖父程慕灏,但实际情况下的程慕灏只是中行的一个副经理,而程乃珊在结构小说时,将主人公祝景臣的职权作了简化与拔高,让他担任了中华银行的总经理,从而可以直接介入到银行的决策之中。
因此,《金融家》里,我们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丰富的中行行史资料。一般情况下,字正腔圆的行史,用的是公文笔法,采取的是提纲挈领的论述,少见鲜活的形象,虽然甲乙丙丁交待的十分明白,但是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却难以见到一个全景式的画面与细致入微的细节,因此,行史不管用了多长的文字,它只是像瞎子摸到的大象一样,只能注重一个片断,一个环节,而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而文艺作品就不同了,在作者确定下的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可以洞察到各个社会层面、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内在网络线索,营造出一个全景式的时代三D图景。这就是文艺作品的特殊映射与反映功能,所以,马克思曾经说过巴尔扎克的小说比经济家更透彻地反映社会现象,一部《红楼梦》几乎浓缩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代表性的符号,让人可以研读一生。
正因为这个原因,程乃珊《金融家》既然是以中行历史为背景,那么,在整个小说中,就可以看到许多在正规行史中忽略的众多细节。
比如中行行训“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於钱,外圆内方”,在小说里这一行训出自于华行的创办人已故前任华行总裁魏久熙,那么,这个人物对应于中行的那一个创办人?程乃珊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程乃珊却以她的清晰的记忆力,告诉我们这一个看似简单却意蕴深远的中行行训,在一般的行史书上却少见记载。
小说中的中华银行,其特征与中行相当吻合,比如“那枚印着外圆内方钱币的中华银行行徽”,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图案。至于华行的旧址,小说写道:“这里原是一个意大利商会俱乐部”,而真正的中行旧址则是德国商会,作者在德、意之间进行了移换,颇能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小说里的华行别墅,则完全对应于著名的“中行别业”,作者还对别墅进行了艺术性的描写,都可以弥补行史概略的不足。
程乃珊在小说中也对中行行员进行了大致的区分,小说写道:“华行的行员向来分两大阵营,一是留洋或商科银行系毕业的,另一派则是钱业学徒出身,俗称‘三考’出身。”在小说里,我们看到,由于管理者善于运筹,唯才是举,因此,“至少新老两派表面上各尽所长,相安无事。”这些描写,基本把行史中加以忽略的中行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了比较形象的表达,可以让我们感知到中国银行特有的谐和文化,对员工中正能量的营造起到了良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程乃珊秉承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作家的坚守原则,她在小说里,也不失时机地揭示出华行在旧时代无法避免沾染上的阴暗面:“岂知堂堂中华,也是一个强者肉食的战场;总经理吃经理,经理吃副理,副理吃协理,一级吃一级,吃得我们行员气也透不过。”这里反映出作者的一种历史的审判眼光以及超越情感之外的理智观感,这种不受情感左右的直揭现实的思考力度,使程乃珊的小说经得起历史与真实的考验,也让它描摹的画面,更能切近生活的真实。
实际上回过头来看看,对中行历史进行艺术化再现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程乃珊这个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的女性作家,却提供给了我们丰富的细节与生动的感情感触,在我们面前复原了一幅生动而凹凸有致的中行现实场景,为此,让我们感谢程乃珊。
二、《金融家》的曲折性不及中行史的百分之一
在程乃珊的《金融家》中,辨识中行历史的蛛丝马迹,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而实际上,程乃珊并没有正面描写金融界的经济纠葛与暗战,也许真正地描写经济领域的交锋只会给文本增添几分寡然无趣。所以,程乃珊选择了从侧面的角度,通过一个金融家的儿女们的情感主线来展现金融业的重大事件。这一选择,与《红楼梦》的策略是相同的,小小的大观园里,微观着大千世界的风云激荡。当然,程乃珊采取这一叙事策略,与她事实上对金融知识的匮缺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文中的情节编造来看,程乃珊一涉及到儿女情长,便能妙笔生花,洋洋洒洒,而在事关银行的生存与命运的章回,便多是概略性的介绍,而缺乏人物的剑拔弩张的心理活动,从总体来看,这部小说还不如现在的职场小说那样能够写出微妙的纵横捭阖的起伏流程,它的标题实际上换成《金融家的儿女们》来得更为切题。
《金融家》是以中行的历史为原型的,但实际上程乃珊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中行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要容纳到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去,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因此,程乃珊采取了删繁就简的策略,将小说的时间段,截取在抗战的八年之间,而更为关键的是,小说里的华行的身份,设定为一个民营银行,从而回避了中行起起伏伏、眼花缭乱的历史走向。因此,《金融家》里对中行历史的采用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而仅仅是这么一点中行史实的接纳,便使《金融家》近乎是填补了中国金融文学的一个空白,更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学里金融体裁面临着怎么样的一种缺失状态。这个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金融业更多的是一种智力上的暗战,很难通过外在化的形象予以表现出来,特别是金融的那种近乎“无影掌”的拳脚特征,也很难诉诸于形象的描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金融界对自己文化传播与张扬上的劲力不足。俗话说,贫穷出诗人,金融业的较为优裕的生活,也很难推动着创作者愿意绞尽脑汁去开拓一块金融文学的新天空。
可以说,真正的中行史就是一部鸿篇巨制,一部铺展开来,足以让托翁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相形失色的经典名著。《金融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它仅仅管中窥豹中行的一角,便让我们看到了中行历程中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亮点。
因此,在《金融家》中撷取主要的情节元素,推敲一下它们与中行历史的因果关系,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小说里,最初描写了一起挤兑风波。这一情节,也许更适合一个财力有限的民营银行,对应中行历史,我们看到在行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倒是中行的抵抗“停兑令”中对中行信誉的奠定与激发,因此,程乃珊对应对挤兑风波的这一情节的设置,只能说是对“停兑令”造成的挤提风波的影射,而程乃珊对挤提的原因的解释,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她在小说中写道,之所以发生了挤兑,是一名有着特殊背景的员工,擅自对外出卖有价证券浮动行情谋取私利,以致让人授华行行风不正的话柄。这一点,未免夸大了一些内部的营私行为对信誉所造成的影响,银行的复杂的连环性的风波产生规律,在程乃珊的笔下,被简化成如此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显然反映出程乃珊对银行业务流程的欠缺。当然,在小说里,这并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真实的一个情节,但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对银行业并不了解的一般读者,并不会深究其是否合理性。
在小说里,与中行史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抗战事期,由于国民党与汪伪政权之间的特工大战,对中行员工造成的血腥伤害。抗战时的特工大战,是当前抗战神剧的一个重要部分,电影《色戒》可称着代表。中行员工的卷入完成是无辜的,小说里写到,日本人为报复重庆的暗杀,绑架了华行12名行员,后辗转找人,联络到吴四宝,才放了行员,但却将其中的老曹给打死在家门口。这一段情节,程乃珊综合了绑架江苏农行十二人及枪杀中行两人的情节,进行了重新的加工,使情节更简单凝炼。
而在抗战结束后,小说主人公被指认为汉奸的情节,在中行行史中也有翔实的资料印证。如在《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第八章第六节“对吴震修表示理解的函件”中,记载了吴震修在沦陷后的上海出任伪中行管理处一把手而导致的汉奸指责。
在小说里另外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地下党对民族金融业的支持。在行史中,我们也知道,中行的地下党早于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展了活动,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地下党在帮助银行家如何说动下岗的员工方面提供了支援,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政府将华行列入伪汪政权资产时,是地下党组织了静坐示威。小说里设定了一个名中行员工的儿子范仰之,是他时刻以地下党员的身份,给予金融家提供着生存的方向与导向,而中国银行家也深刻地感到了共产党给予他们的政治上的支持,所以小说里的中国银行家在最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银行业的期望,这正由百年中行的历史得到了富有说服力的验证。
《金融家》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它的丰富性与曲折性与中行的宏大的历史相比,显得太为局促与简单,令人觉得就像是一本放在高教教材下面的小学课本,但它在金融文学中的地位不容忽略。所以,小说也启示我们,相比于中行历史的丰富多彩,金融文学大有可为,也必有可为。
三、程乃珊为什么没有写完《金融家》三部曲
程乃珊的《金融家》以其鲜见的对中行史的形象描绘,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了一席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作者本来是要将《金融家》打造成三部曲的,目前的《金融家》仅仅是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但是,从第一部小说诞生于八十年代末之后,一直未看到这部长篇巨制的后续作品问世,而事实上,程乃珊直到她离世,几乎有近乎二十多年的时间可以供她完成她的作品,但是,直到程乃珊病重之际,她仍然未对后两部作品写出只字片语。然而,程乃珊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忘记她心中的对这三部曲的宏伟规划,可以说,程乃珊的遗憾不仅属于那些关心金融文学的普通读者,也属于她个人的。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陈思和也在回忆文章中对程乃珊没有打造成三部曲的完璧流露出了遗憾。个人对陈思和并没有好感。因为我最近购了一批旧书,有一次翻阅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帮派文艺的代表性刊物《朝霞》合订本的时候,看到陈思和一篇愤怒控诉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檄文,大吃一惊,用鲁迅对“流氓”的定义,很适合此人。陈思和在他的那本被许多高校作为教材的文学史中,竟然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把《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说成是妓女的代名词的“风尘女子”,而在对浩然的评述上,更与剑桥中国历史的公正客观的评述大相径庭。因此,对此公的识力,我是尤表怀疑的。
但陈思和称赞程乃珊最重要的作品是《金融家》,则并没有言过其实。那么,这部程最重要的作品,而且在重病之际,仍然使她耿耿难眠的长篇巨制为什么没有写完,也就不得不让人去多想一下。
实际上,看看小说的文本,不能不说,程乃珊自己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无法完成任务的绝境之中。也许探讨一下程乃珊的困窘并非没有意义,因为这不是程乃珊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个行业文学总体的困境所在。
《金融家》这样的小说的最大的难度是在那里?
我想,小说里已经鲜明地展示了这一点。据一篇回忆程乃珊的文章介绍,程乃珊有一次在谈到汉奸的时候,说了一句:汉奸不汉奸是无所谓的(大意)。
程乃珊为什么有这种观念的模糊?《金融家》里已经作出了明晰的透露了。小说中的华行总经理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人虚与委蛇,百般周旋,在抗战胜利后,被当成是汉奸。这一段经历,实际上与程乃珊的个人情感有关。真正情境下的事实是,程乃珊的祖父在抗战时期,的确有一段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苦心经营中行的艰难经历,而事实上,那一段时期沦陷区的经历,事关到民族的大是大非理念,容不得任何形式的讨论与模糊。陈凯歌导演的影片《梅兰芳》的立意,最终是放在了梅兰芳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蓄须明志、坚不合作这一高昂的基调上,在电影里,梅兰芳几乎被拔高成江姐式的民族英雄,与《风声》之类的抗日剧有得一比。可见,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是不可能给予任何含糊以空间。张爱玲出于隐讳的情感因素,而在《色戒》中写了一段超越是非正义的个情感存在,可以让我们看出,文学作品的背后的作者情感因素,往往在制约与左右着小说的立意与走向。
因此,程乃珊在写作《金融家》的时候,固然由于她来自于上一代人耳提面命的便利,得以得来全不费功夫地获得更多的历史的细节,但是,她的一脉相传的情感线索,使她无法超然地站在血缘之外,进行客观的、公正的、甚至必须是背叛一个家庭与传统的立场去抒写她对社会与人物的认识,这才是程乃珊无法让她的小说充溢着更符合历史立场的主题意旨的原因。而一个文艺作品,如果没有一个符合历史进程、符合人性基线的主体框架铁骨铮铮地插入到文本中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是无法支撑起来的。
我们在文学史上,可以看到众多这样的事例。托尔斯泰在创作的时候,立场尽管站在农场主的角度,但是,他的思想上,却批判性地指向他所属于的那个阶级;巴尔扎克的思想观念不能说有多么进步,但是一旦在文学作品中进行着社会描摹的时候,便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他偏爱着的那个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卑鄙。而与这些经典的人文名著相比,我们便会看到程乃珊的《金融家》缺少什么。
在小说里,程乃珊对于小说里的主人公进行了过于偏爱式、袒护式的描写。我们看到,小说里写到在上海沦陷之后,华行经理因为投资房地产,却发了一笔国难财,收益颇丰,但是,程乃珊却把这一切,归之于地下党的决策指导的结果,在小说里,地下党劝说华行祝经理,劝诱他利用汪伪的资金,去投资房地产,因为这些固定资产,将来还是要归之于人民的。如此说来,在日寇铁蹄下的为虎作伥的经营行为,都可以在最终目的上有利于国家。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再看小说里投入了巨大笔墨加以再现的金融家的家庭秘史,这些情节的设置,完全是移用了程乃珊的家族历史,而在这里,更可以看出程乃珊虚晃一枪,对于那个由金钱支撑起的贵族之家,进行了虚情假意的遮掩。小说在这里的批判锋芒,与《雷雨》、《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就连张爱玲的早期揭露旧家庭罪恶的小说也是相距甚远。
比如,金融家祝景臣的大哥,年轻时流散在外,后来意外地找到了,大哥留下来的孩子,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但是,祝老太太凭借着家财万贯,为这个痴呆儿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孩,新婚之日,这个女孩不堪丈夫的不谙人事,而上吊自杀。这一行为,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屡屡提及的,经常用以揭示金钱掌控下的镀金时代对人性与生命的扼杀,而在程乃珊的小说里,这一切却被温情脉脉的贵族之家的遮羞布给掩盖了百丑,作者连一点怜香惜玉的激情都懒得在小说中进行表达,只是描写罪魁祸首祝景臣心里涌上一点遗憾,随即又自我安慰,认为那个冤死的新娘毕竟是自己愿意的。我们再来看看巴金的《家》中,当鸣凤投河自杀的时候,作者是如何进行了情感的渲染?
再看金融家祝景臣的弟弟景文,原来在乡间有一个妻子,在小说的描写中,景文对这乡下妻子自然是没有感情的,但是每一次回乡的时候,总是禁不住妻子年轻的身体的诱惑,发生肉体关系,生下了几个小孩,后来这个景文,来到上海滩上,又找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妻子,一妻一妾,这样奇特的人性关系,在作者笔下,也作了淡而化之的描写,作者无意也无暇去写出“新人笑、旧人哭”的人性的悲欢。而张艺谋为什么能用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震撼世界电影节的评委们,就是因为电影里充溢着的一种对人性的呼吁与张扬。当然,张艺谋最近被曝有多名子女的秘辛,实际上,张艺谋已经走向了青年时代他的反面,成为他当年在电影里加以批判的那个“老爷”的拥趸者与效法者了。
而小说主人公景臣丰富多彩的爱情经历,在程乃珊的笔下,也作了某种程度上的美化,我们可以看到,景臣本来与自己的妻舅的妻子有着暧昧的关系,后来又徘徊在是否迎娶前任董事长的遗孀的纠结中,直到找到了一个小他许多的交际花作为妻子,这一切复杂的情史,作者都置于一种理所当然的漠然状态中加以描绘,未能写出这种关系给予一个家庭带来的伦理上的冲击,对孩子精神上的毁灭性的打击。
上面三个主要人物的情史,在程乃珊对家族史的回顾中,都可以一一对应地与程的祖父辈的家人划上完全的等号。程乃珊显然在揭示出大家庭的光怪陆离而又在那个时代见怪不怪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没有找到她应该保持的立场,她如实地写出了这个家庭的光明与阴暗的一面,但是她的情感却没有赋予这种历史事实以一种超脱于时代的力量,小说里的旧家庭,在“雷雨”、“家”等作品中,本身就是一个毁灭旧时代的力量,但在程乃珊的笔下,她显然没有作出这种穿透历史的深刻的批判,虽然她为显者讳的动机,削弱着小说的锋芒,但实际上也让她走上了一条难以续接的断桥,她难以为她的这些人物找到继续与时代并行的温暖与光明的力量,她无法在一个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人性的角度与场合里继续展开她的家庭的叙事,所以,小说只能戛然而止于抗战胜利这一个节点。
回过头再来看看小说本身,我们不能不说程乃珊对小说的定位上的失误。小说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程乃珊的小说里始终没有放弃一种阶级性的观念,生拉硬扯地将金融家的家史,拉扯到当时的一些由地下党主导的革命斗争中,小说中的地下党范仰之总是适时而神秘地出现在祝家的周围,并且与祝家小姐发生了一段恋情,但是,程乃珊不得不遵循史实的发展,因为事实上程家并没有一个地下党介入到家族的族谱之中,所以,范仰之的那一段爱情故事只得无疾而终,对祝家小姐的形象塑造也显得毫无意义,这不能不看出,程乃珊在照顾到社会客观环境的大背景之后,不得不削减了小说中的人物与真实性相匹配的定位,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创作主体性的萎缩。
可以看出,《金融家》的定调,限制了程乃珊可以更自由地抒写人性的冲突的可能,使得小说的延展性受到了阻碍。因此,程乃珊已经无法再让她笔下的人物,在接下来的作品中继续展开他们的情感的冲突,程乃珊就被无奈地卡在了金融家在抗战阶段的这一段短暂的区间与时段之中,从中我们感受到的文学创造的困窘,其实并不应该由程乃珊一个人来承担,而实际上反映了金融文学自身规律所带来的重重障碍。程乃珊作出了努力,但她无法突破文学规律对她的制约,也许我们从程乃珊的创作局限中,可以更好地看到金融历史文学的一些瓶颈所在以及可能的突破性出路所在。程乃珊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文学创作的经验,从这一点上来说,程乃珊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