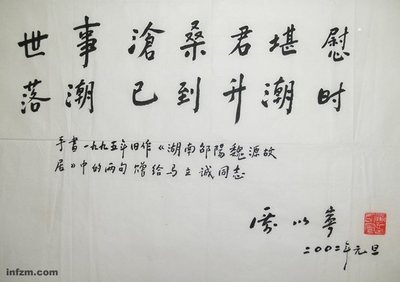5月13日下午打羽毛球时,听马扬老师说胡新和老师去世。5月17日参加了胡老师的追思会。科技哲学界的老中青三代人均表达着对胡老师的怀念。
和胡老师的交往,应该始于2004年。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举办期间,在承担宣传工作之前,我和胡老师曾搭档,担当“门童”,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台阶上,迎接各界来宾。间隙,坐在台阶上,胡老师笑眯眯地讲述他80年代初怎么考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怎么和中科院研究生院擦肩而过而后回归玉泉路。
而后,在学校从事宣传工作期间,我们举办过数次征文活动,诸如“教育创新之我见”、“与改革开放同成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胡老师作为人文学院副院长,是当然的评委之一。每次活动的评审任务,他都欣然答应,并按期高质量完成;特别是与纪念改革开放相关的那次征文活动,还专门举办了评审会,胡老师把他看过的每一篇文章,都仔细地罗列了优点、缺点及其建议的奖项,认真劲让人赞赏。
2009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刚看过一个画展,骑车带着父亲回家。手机响了,是胡老师打来的,“兄弟我当选为全国科学哲学学会会长,准备发一个消息”,我为胡老师感到高兴,也为他愿意将这一喜讯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而高兴,随后我们及时在学校网站发布了这条信息。当年,这条消息还作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十大新闻的候选条目,在年末被大家反复阅读。
在准备博士入学考试的日子里,我深感科技哲学之难。曾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的老师聊天,他们认为科技哲学,是一门伪学问,没有体系、没有方法、也没有价值,这只能说是隔行如隔山吧。科学作为人类远古以来推进社会变革、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动力,它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方面,当然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在学习科技哲学进退两难的时候,我曾特意请教过胡老师,打完电话,相约在他办公室相见,十分钟后,他骑着自行车如约而至。不足半个小时,他把《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本书的脉络,和科技哲学的主要流派和观点讲得非常清楚。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我在中国知网搜索了科技哲学的相关文献,特别是中国科技哲学界的重要活动。从80年代以来,胡老师大致参与了每次全国性的活动,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组织者。2009年,他当选为该协会的领导应该是当之无愧吧。
再后来是2011年冬天。博士生专业课是讲座式。那天上午,我从北五环到学校,已经迟到半小时了,正是胡老师的课,“迟到了,不给成绩啊”,幽默的提醒、善意的微笑。落座后,胡老师将科技哲学与唯物辩证法等的不同,阐述得格外清晰,课堂上,还有讨论,只是12点的午饭时间已经到了。这次课,是我在课堂上第一次以学生身份听胡老师讲授;这次课,也是我听过的很多课程中,层次和逻辑分外分明的一节。
2012年夏天人文学院举办的一次论坛之后,和胡老师一起吃饭,他问起我的博士论文题目,“科学家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这个题目不好做啊!”胡老师说。在11月的开题报告上,他就这个题目的可行性提出了很多建议。“不好做”是胡老师对我的告诫,也是警示。“不好做”不是“不能做”,题目有难度,但并不是没有意义、没有可行性。如今,正因为这个题目不好做,所以需要我特别静下心来,阅读、思考,反复调整方案,争取不辜负老师们的希望。我将带着胡老师那个题目“不好做”的告诫,重读那些文献。
在胡老师逝世后,旅美科技政策专家王作跃老师在第一时间写了悼念文章。前一段时间我也看王作跃老师写的《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这本书。王作跃是80年代出国、如今在旅美的科技政策专家中颇有建树的一位,他在2009年曾应邀到研究生院演讲,我也听了他的报告。在此我想说的,是同辈学人,在不用的环境下发展路径和学术成就的差异。在国内,胡老师是库恩研究的权威,《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学界公认的最好的中译本,他本人也成为这个领域的一面旗帜。科技哲学是外来的种子,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需要向胡老师这一辈学者的译介、付出和耕耘。王作跃老师80年代到美之时,科技哲学已经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他们只能在这课大树上选择某一枝条作为自己毕生耕耘和栖息的土壤,《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便是这种长期努力的结果。
做人难,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有分量的人更难。在追思会上,多位与会老师提到胡老师的为人和为学,“他将儒家的儒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风骨,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诸多的发言中,我听到的一句,概括得全面准确。追思会上情真意切的发言,和大家不能自已的泪水,不仅是对胡老师为人、为学的纪念,也是肯定。胡老师,安息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