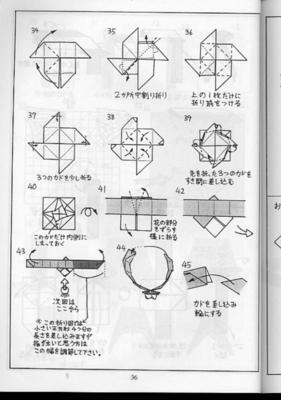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件小事,但它却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恨它:我可以整整一个月不沾烟酒,然后又开始重新抽上一口或喝上一杯。我是个瘾君子,在和我的毒瘾较量,而且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我天生就会上瘾,而且对任何东西上瘾。日子好的时候,上瘾的是台球;日子不好的时候,上瘾的是毒品,我最大的问题是大麻。人们总是说你不会成为瘾君子,说大麻不是毒品,而我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1998年,我又开始抽烟喝酒,正在走向灾难。我已身心疲惫。我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我是位成功的斯诺克台球手,世界排名又回到了第三,但我有一种罪恶感。我那对任何事情都上瘾的天性在驱使我去达到完美,而由于我从来没有能做到完美,我便时刻有一种失败感。我的生活模式在过去六七年中一直是这样:为完美而努力,为无法做到完美而感到绝望。奇怪的是这种痛苦又让我感到舒服。也就是说,每当我感到痛苦时,我又非常高兴。我已经习惯这种模式,而且我总是找借口不让人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不让人说我,也不让人骂我。当我觉得的自己没有权力感到抑郁时,那才是真正最痛苦的时候。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约翰 希金斯的家乡苏格兰举行的“恩巴希”大师赛中战胜他。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想在决赛中乱打一气,因为我知道每次“恩巴希”赛之后总会有一个盛大的宴会,主办方邀请的客人们会拿着节目单过来,请参加决赛的选手签名。我想,如果我输了,我就能赢得人们的同情,然后我就可以说“我累了”,而且我会不可思议地为此感到高兴。我脑子里当时想的就是这些。我在折磨我自己,在问自己:你为什么想扔掉三万英镑,然后找借口让自己痛苦?这说不通。
决赛的大部分时间我打得都不错,但打到6:6时,我突然来了精神,进入了最佳状态,而约翰则完全傻了。四周都是他的家乡父老,而他们在期待着他获胜,因为他三个月前刚刚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我估计他当时可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就像我在温布利那场比赛一样:你非常想在自己家门口获胜,结果心理压力变得很大。
我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失望或痛苦,可我却仍然感到失望和痛苦,而且我还得在人前装出一副幸福高兴的样子。我一直认为自己必须实现人们对我的期望或希望。决赛结束后,出席“恩巴希”大师赛宴会的那些人都在说,“罗尼,你刚刚获得冠军,现在一定欣喜若狂吧?”可我内心却感到很痛苦。我真正想做的是对他们说,“谢谢大家,我现在要回房间去了。”可我觉得自己不能那么做,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欢庆,应该和大家一起热闹。我在想,我还得说几句话,说说这场比赛多么出色,主办方有多么了不起,伊安 道尔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经纪人,他对我来说是多么坚强的后盾,感谢苏格兰人,我很高兴能在他们面前打球,而且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明年再次回到这里。但我真正急不可待地想做的是赶紧离开那里,赶紧回到我的房间,对道尔发一通脾气。他能够处理好我,他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知道我只是在人前装样子,因为他整整一星期都和我住在一起,知道获得冠军并不能让我好受一些。
我站起身来致辞。约翰 希金斯刚刚说完,而且他非常自信地称大家为“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客人们”,因此我便想,该死,我该说什么?他说这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并且为我赢得冠军而高兴,然后他说了几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刚刚输了球,可他很开心;我刚刚赢了球,心里却异常痛苦。我站起身来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当时有三百个人坐在那里,都是赞助商“恩巴希”烟草公司请来的贵客,而我都不敢直视他们。我记得我当时说,“非常感谢大家”,但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说了那句话,然后我简单地补充道,“呃,就这些。”我听到大家哄堂大笑,我可以肯定他们是在笑话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他们可能根本不是在笑话我,可我当时就是这么疑神疑鬼。
在赢得苏格兰大师赛不到一个月后,我去爱尔兰参加一些表演赛。我让戴尔和我一起去。我不在乎自己时候会在戴尔面前感到痛苦——他能帮我减轻痛苦。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绿色英里》的话,那么戴尔就是影片中那位能将别人所有痛苦吸走的黑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确切地说,是他陪伴我经历了那么多。我知道,如果没有他,我今天可能不会还活跃在台球桌旁。戴尔唯一沉溺的是生活,他给人带来欢乐。无论什么事情,他总能看到好笑的一面。我和他在一起总是乐不可支。他就像一剂药。
在爱尔兰的第一天晚上,“砰”,棒极了,我打出了单杆一百四十七分,博得了满堂喝彩,大家都疯狂了起来。我在九局球中又打出了三个单杆过百。我每次打表演赛时总能打出一百多分和最高分,因为在表演赛中我既不能表现我的战术球技术,也不能表演我的绝技。如果我再不打出单杆过百,那些下赌注的人就会想:我看罗尼 奥沙利文比赛时,他连五十分都打不出来,而且一句话也不说。妙极了!正是这种压力在迫使我尽情展示自己,否则观众该看什么呢?对于“龙虾”丹尼斯 泰勒,你可能一整夜都无法看到他一杆打出五十分,但你能看到他打出一些非常漂亮的花式球,博得大家的笑声。所以,那天晚上我的球感非常好,我自己感觉也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幸福。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了莉莉 波尔德洛斯夜总会,在那里喝酒,抽大麻,后面还跟了几个爱尔兰朋友,他们个个喜笑颜开。戴尔凌晨三点左右离开,而我仍然意犹未尽。我们又从那里去了里森街,并在那里一直待到早晨七点钟。我毫无睡意,异常兴奋,也不想回旅馆,于是我的那些朋友说我们可以去一家开门比较早的酒吧。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他们解释说有些酒吧早晨七点钟开门。“太好了,”我说,“可以用吉尼斯啤酒来当早饭。”我们一大老早行走在市中心,而周围都是匆忙赶着去上班的人。我穿着一件大衣,里面什么也没有船,因为我朋友吐了自己一身,我只好把我的衬衣给他。我们看上去一定像四个刚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我想,人们会怎样看我们?不过我当时已经醉了,根本不在乎。我们坐在酒吧里和吉尼斯啤酒,一直喝到中午。当天下午我还有一场表演赛,当然等我赶到球场时,我一个球也打不进。
我们就这样整整过了五天五夜。最后一个晚上,我双手抱着头坐在那里。戴尔问我怎么啦。我知道他还没有意识到我多么难受。我感到自己像是死了一样。我无法动弹。我说我无法坚持下去,还说我们应该把下赌注的那些人的钱还给他们。我们去了表演赛的现场,打完了比赛,然后我第二天就飞回了家。回到家后,我一头倒在沙发上,无法动弹,过去一周中所做的一切让我精疲力竭。现在离英国锦标赛开赛还有九天,所以我还有九天的时间来恢复自己。让我疲惫不堪的不仅仅是酒,我心情沮丧,而且体力不支。
我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体能锻炼,因为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我没有任何求胜欲望,甚至都不想练球。我在感情上没有准备好参加任何比赛,甚至做任何事。而且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在让他们失望。我毕竟是卫冕冠军。我向自己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我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是,就在我跨越这道栏杆之前,我还得面对更糟糕的事。我要不要告诉父亲我已经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是否应该等到比赛前一天再告诉他?摆在我面前的是台球届最重要的赛事之一,而我心理上已经完全垮了。我想,身陷囹圄的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无节制地饮酒作乐。可如果我因为这一点退出比赛,那一定会让他伤心透了。他绝对不会同情我。我知道他会说我一无是处,说我虚度光阴,说我给家庭带来了耻辱。我知道他会这样骂我,所以我只能祈求上帝不要让他把我骂的狗血喷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退出比赛,不向他做任何解释,因为他对此事的反应比我担心的还要可怕。我最后脱口说道:“爸爸,我上星期在爱尔兰搞得筋疲力尽,根本无法参加英国锦标赛。我精神上全垮了,我精疲力竭,甚至都无法捡起球杆。爸爸,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越来越绝望,但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情况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说,“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做,我认为你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我知道,爸爸,”我说,“我错了。我现在一团糟,但我绝不会再犯了。我像上帝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了。”我说我一定改过,但我心里明白那只是说说而已。
从那天起,他每天都打来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
“哦,还可以吧。我每天练一会儿球,然后休息,”我说。
但是,他每天和我通电话时,似乎总有新的什么事情让他对我生气。他认为导致我目前这种局面的不仅仅是我在爱尔兰的那个星期,而是我在过去六个月中所做的一切。他有一天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他说。“我和你母亲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你和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在尽心尽力,而你却没有尽一份力。我们再也受不了了。你母亲要你搬出去,我们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想你再来看我。我这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他就这样说呀说,越来越气急败坏。
尽管他这样苦口婆心地说我,我还是告诉他我肯定不会参加英国晋标赛。
“好吧,”他说,“收拾好你的东西,自己一个人去过吧。我祝你这辈子一切顺利,福星高照,但你不再是我们的合伙人了。”
我所挣到的一切,我父母所挣到的一切,我们一直共享。我们一起出钱买房子,而当我挥霍过度时,母亲用她自己的钱帮我度过了难关。大家挣到的钱大家一起花,父亲进去之后,家里买房子或者其他开销几乎全是我出的钱。
“你有那么多的抵押贷款在身上,却无法参加一项该死的锦标赛。”他在电话那头对我嚷道。
我知道其他犯人和狱警都能听到,而且那些狱警们可能还会沾沾自喜,心中想:他挺不住了,终于挺不住了。也许唯一能让父亲挺不住的就是这样的事——家庭的破裂。
我已心力交瘁。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一切,所以只能面对现实,不再去见他。我也很生气,生他的气,生母亲的气。我一直都在竭尽全力。不错,我是干了傻事,可我当时情绪低落,我的自尊降到了最低点,我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疲惫不堪。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也没有告诉过他们我对自己的感觉。他们只是认为我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饮酒作乐,偶尔抽一点大麻,并且认为我只要能控制住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我的情况非常糟糕,大麻几乎成了我的灵丹妙药,正变得比台球还要重要。我渴望体验那种瞬间就能产生的化学般的亢奋,以致我根本不去考虑后果。我知道这样做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但我这样做绝对不是因为我想让父母生气。他们总是说这世界上比我差的人多的是,他们当然言之有理。但是,尽管我知道自己想要买什么都能买得起,这却并没有能让我感觉好一点。他们无法明白这一点。人们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的感觉会有多么糟糕,也不理解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会有那么糟糕的感觉,除非他们自己亲身体验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没有用的帮助就是试图用逻辑的观点来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状态,因为抑郁症与逻辑没有任何联系。
母亲自然无法理解。她对我说,“你看看我所经过的一切,可我处理得很好。”
我说,“是啊,你做得非常出色,我为你感到骄傲,但那是你,而父亲进去并不是我唯一的问题。我每天早晨起来时都感到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每次去参加比赛时都无法面对大家。这非常不正常,该死的台球。我只是想每天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这样才能消除我的痛苦。”
我父母现在回忆往事时,能够理解一点:我需要经历所有那一切才能自己找到答案。如果我当时听了他们的话,我可能会在比赛过程中一败涂地。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我变成那样,但他们以为那就是让我感到痛苦的事。在这起事件之前,父亲总是说,“听着,如果是台球让你感到抑郁,那么你就接管家里的生意。我和你母亲一直经营得很好,我们认为现在可以交给你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走那条路。世间的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总会有自己的原因,如果我那么做的话,也许我就会放弃一切,结果同样感到非常糟糕。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幸运的是,我刚在离家不远处买了一栋小别墅。在与父亲吵架之前,我已经感到很孤独,但是我现在感到的是一种新的绝望。母亲不要我了,父亲也不要我了。我唯一的亲人只剩下了戴尔,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和家里闹翻了,已经从家里搬了出来,而且我精疲力竭。他倒是没有骂我一顿,不过他确实想知道我如何看待我和他的关系。
“戴尔,就你和我,”我说,“我们一起奋斗。”可我感到孤独至极。
戴尔给伊安 道尔通了电话,因为伊安当时是我的经纪人。他告诉伊安,说我将不参加英国锦标赛,而且伊安得告诉大赛组委会,卫冕冠军已经退出了赛事。报界那一天忙坏了,大肆报道说我已江郎才尽,说我心情沮丧,而那些专门报道台球的记者则在分析我的心态。我有一天打开了《每日邮报》,看到上面登了满满两大版,作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位记者。他说我本质上是个好人。这位记者叫特克斯 亨尼西,我十五岁时,他曾和他妻子一起在布莱克本请我吃过饭。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在那个时候充满了自信,可以战胜任何对手,可是七年后的现在,我却内心非常苦恼。他说他这么多年来看着我发生了变化,从顶峰进入了低谷。我边看边想: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但我在与我的噩运抗争,试图闯过这一关。他在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像是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在看着别的台球手享受生活,看着他们在赛场上兴高采烈。我仍然还记得那种感觉,我非常嫉妒他们。我想,你们这些该死的幸运儿。我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异类分子,我现在异常痛苦。
还有一件事压在我的心头:每个人都在说我浪费天才,说我应该赢得更多的冠军。我边看着所有这些文章,边在心里反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用台球来折磨自己?为什么我还在打台球?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就不能让父亲坐在这里欣赏我的球技?我心中想,如果他能出来,我一定不会是这种状况。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抑郁与他没有关系,但有时候又非常清楚,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进了监狱。
我知道,当父母亲把我从家里赶出来时,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出去花天酒地,毁掉自己,或者证明父亲的话大错特错。我迫切想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让他给我打电话,哪怕是透过母亲把话传给我,“告诉他,干得漂亮。”我知道他会的,因为不管他说了什么,他是爱我的。
几星期后,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问出了什么事,我为什么不和她联系,为什么不住在家里?她说话的口气像平常一样,仿佛她已经忘记了所发生的一切。
“爸爸疯了,”我说,“我再也不想和他说话。就我而言,我已经不是家里的人了。”这毕竟是父亲对我说的原话。“这没什么,我可以接受。你就让我自己生活吧。”
“我可不愿意,”母亲说,“我要你回家来。”她哭了起来。
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恢复训练——每天出去跑步,每天练六小时球。我没有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而是在第一轮就输了。不过母亲让我回家倒是非常重要的事。
 爱华网
爱华网